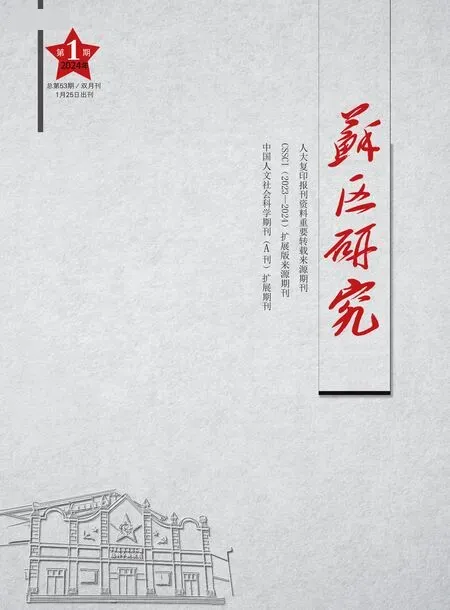统战工作与中共东江抗日武装的发展(1938—1940)
尹智博
1940年3月7日,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在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时提到:“(广东)其余游击区中真能作战者很少,还是以东江曾生部较强”,并主张将东江游击队“当作一个军士教导队的性质办,以便将来环境好转时再行扩大”。(189)《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3月7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7,内部发行,1987年版,第74、77页。可见张文彬此时已准备将以曾生、王作尧二部为核心的东江抗日武装(即东江纵队的前身)作为广东主力部队的种子来培养。然而,就在两天后发生了曾、王二部受国民党军围攻而被迫东移海陆丰的事件。该事件使已有相当实力的曾、王二部锐减至百余人,并促使中共事后对此前的统战工作进行反思。东江部队的主要领导梁广、曾生均认为,部队“受挫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上对国民党存有幻想”。(190)梁广:《关于东江纵队成长初期情况》,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案号:003483—17—4—22;曾生:《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页。张文彬也指出:“东江的组织工作较强,但统线策略差一点”。(191)《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3月7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7,第125页。事实上,广州沦陷前后,中共在广东的武装工作处于重建状态。曾、王二部能迅速崛起,离不开中共对统战策略的重视与运用。鉴于东江纵队在华南抗战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关统战工作与东江抗日武装发展的问题在近年来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并取得一定成果。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共在统战与敌后游击之间的徘徊以及背后所引发的国共斗争等方面(192)主要成果可参见杨新新:《在“统战”与“敌后游击”间徘徊:中共东江抗日武装的建立与发展(1938—1943)》,《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2期,第105—115页;尹智博、左双文:《国共离合与中共东江抗日武装的发展(1940—1943)》,《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4期,第69—83页;王英俊:《张文彬领导广东党组织对余汉谋部统战工作的历史考察》,《学术研究》2022年第6期,第136—145页;钟健:《从统战到自主:中共广东省委开展武装工作的历史考察(1938—1942)》,《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3期,第37—50页等。,对中共领导东江部队开展具体统战工作的考察仍显薄弱,而相关问题又恰是我们观察中共东江抗日武装独特发展路径的重要视角。因此,本文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以中共东江抗日武装初期发展中的统战工作为主体展开论述,重点探讨以下问题:作为远离中央、几乎白手起家的部队,东江抗日武装如何处理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余汉谋等国民党要员对中共的真实态度究竟如何?与国内环境相比,东江地区的国共关系有何特色?在结合抗战局势及广东客观环境的基础上,如何辩证看待此阶段中共的统战策略?
一、借重统战:中共广东省委对抗日武装工作的准备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中共开始有计划地布局对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召开洛川会议,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同时,还决定应尽快恢复、健全各地被破坏的党组织。(193)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综述、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其中,南方各游击区被中央视为“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194)《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1937年10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2页。,要求张文彬等华南干部应予十分重视,这为广东发展武装工作提供了方向性指导。
作为国际援华物资的输入要道与华南的经济中心,广东的战略地位无疑重要。但中共此时在粤的工作基础极为薄弱。受此前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和中共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全省有领导的党组织活动在1934年时即已基本停止。除孤悬海外的琼崖残留少数红军外,广东几乎没有成建制的武装力量。在1938年10月日军侵粤之前,中共发展武装工作的空间有限。基于现状的考虑,此时中共中央对华南的战略定位暂不在军事层面,而将推动与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南方党组织的着力点。(195)钟健:《从统战到自主:中共广东省委开展武装工作的历史考察(1938—1942)》,《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3期,第38页。这些因素导致武装工作成为中共在广东的各项工作中起步较晚、恢复较慢的部分。
1938年以来,随着厦门、南澳岛等沿海要地沦陷,华南抗战局势日紧,主持广东党组织工作的张文彬等人建军的心情日益迫切。2月,张文彬与廖承志研究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战工作时,决定要在华南地区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得到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的支持。(196)陈敦德:《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纪实》,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44—45页。4月,张文彬在宣布成立中共广东省委时,着重讨论了军事问题,号召党员军事化。(197)《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东江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广东省委在8月召开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专门提出要把武装工作提到第一位。(198)《中共广东省委四个月的工作总结报告——关于党的政治领导、组织发展及群运问题》(1938年8月),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内部发行,1987年版,第224页。武装工作的首要问题是确定建军路径及发展形式,鉴于中共在广东既无成建制的正规武装,又缺乏有经验的军事干部,张文彬决定另辟蹊径。他提出:当前在广东建军应以在统一战线下组织由中共领导的非公开的地方民众武装与游击队作为主要手段,同时也准备在将来发展由中共独立领导的武装,并以此作为未来扩大游击战争的中心。(199)《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的综合报告》(1938年),《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第336页。
张文彬作如此规划,一方面是因为他在赴粤前就以统战经验丰富著称,赴粤后他按中央指示以统战工作为切入点,迅速恢复与扩大了广东的党组织,这使他对统战工作的效力充满信心。另一方面,张文彬也充分考虑到广东的特殊环境。
第一,广东作为未被国民政府完全“中央化”的省份,派系复杂,且“中央与地方之摩擦常起”。在日军进犯的强大压力下,广东当局呈现出比较开明与进步的态度。余汉谋提出要“坚决守土”,谌小岑、李煦寰、钟天心等政要均公开倡导统一战线,支持开放民运。在张文彬看来,“广东工作有较顺利的客观环境”,并将工作总策略定为:“不急于在广东做出轰烈的事迹,而要在抗战的过程中埋头苦干,切实积聚力量,确切地建立强的群众实力”。在未来日军进攻华南或持久战到最后阶段时,要确保广东党组织能有力量积极保卫华南,支持持久战,并担负保障统一战线在国统区内巩固与坚持的责任。(200)《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的综合报告》(1938年),《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第300、312页。因此,第四战区政治部成立后,广东省委即派一批党员进入其中开展统战工作与政治宣传,以促进国共合作抗日。
第二,广东当局此时所倡导的民众抗日自卫运动有利于中共掌握民众武装。武装民众对抗战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国民政府在抗战纲领第九、第十条中,提出要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使之保卫祖国,同时要求各地指导援助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抗御外侮之效能。(201)叶健青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1册,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328页。中共中央也指示地方党组织应积极开展各种统战工作,“利用一切旧政权的武装组织形式,如民团、保安队、壮丁队、义勇军等,实行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并取得其中的指导地位”。(202)《中共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1937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19页。广东自抗战以来多次派军北上参战,本土防御兵力不足,故当局通令各县市要成立自卫团、壮丁队,施以军事训练来维持后方。(203)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民国广东大事记》,羊城晚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557页。广东又恰是民间散枪特别多的地区,武装民众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据张文彬估计,广东民间枪支“至少四十万,有的说有七十万以上到百万,不仅有步枪,而且有新式机关枪,迫击炮等”。因此,他要求各地以建立自卫团中的工作与组织为中心任务。(204)《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的综合报告》(1938年),《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第331—332页。1938年6月,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尹林平、组织部长李大林在广州召开军事工作会议,要求广州外围几县党组织要利用各种合法形式,率先组织并掌握民众抗日武装,加紧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准备。
在中共对武装工作的规划中,东江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作为中共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展过武装斗争的老区,该地革命基础良好。张文彬提出:“对将来游击战争的准备,一般着重沿海尤其是东江区。”(205)《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的综合报告》(1938年),《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第334页。另外,东江一带在历史上封建械斗频繁,民间藏枪丰富,人民骁勇善战,且此地接近港澳,容易购买武器,对中共发展武装工作很有利。广东省委曾拟定在日军入侵广东时,以东江的罗浮山、桂山为抗日根据地。广州沦陷前,东江一带的东莞等县开展武装工作也较出色。但广东省委并未预料到广州随后会快速沦陷,也没有估计到东江地区的武装斗争能快速发展起来。(206)《访问李殷丹同志记录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案号:001580—18—4—55。因此,中共对东江抗日武装工作的准备并不充分。
东莞作为当时广东共产党组织基础最好的两个县之一(另一个为中山县),自然是中共开展武装工作的重点。(207)王作尧:《东江纵队的诞生和成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东江纵队资料》,内部发行,1983年版,第48页。1937年9月,中共东莞中心支部成立后(次年4月改为中共东莞中心县委,负责领导东莞、宝安和增城部分地区的工作),即争取当地驻军第153师的支持,举办两期军事训练班,动员党员和进步青年200多人参加。受训青年结业后以153师军训教官的名义派到各地组织训练自卫团。另外,中共还派人打入国民党东莞县政府组织的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中,并以该委员会名义举办训练班来培训军事干部。次年7月,东莞成立常备壮丁队,中共通过争取国民党社训总队副总队长颜奇的支持,派人打入其中担任中队长、政训员等,掌握约两百人枪。(208)王作尧:《东纵一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除东莞外,东江其他地区的武装工作也有进展。1937年12月,中共广州市委派黄木芬等人到东莞、宝安边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通过争取宝安当地开明绅士曾鸿文等的支持,中共在观澜、龙华地区组织起抗日自卫队。1938年9月,中共在增城也利用抗日自卫团的名义组建两个大队,各有两百多人枪。惠阳的工作则得到香港党组织的大力支持。1937年底,港英当局取缔香港海员工会后,大批抗日意愿强烈的海员回到惠阳、宝安等地,成为组建抗日武装可以依靠的骨干力量。香港党组织以旅港的惠属海员、工人及爱国青年为主成立香港惠阳青年会回乡救亡工作团,以公开合法的名义在惠阳开展工作。1938年7月,该工作团通过驻淡水的何联芳旅举办“沿海青年暑期军事训练班”来培训干部,毕业后回乡组织自卫队。(209)《抗日时期惠阳党组织概况》,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编:《东江党史资料汇编》第1辑,内部发行,1983年版,第75页。
由此看出,中共在东江的武装工作自一开始即借重与国民党当局的统战关系,这正是贯彻广东省委相关指示的结果。广东省委在此阶段也对地方上的武装工作进行了积极的督促与指导。张文彬在开会时经常强调“党员军事化”,并要求党员好好学习《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每当地方领导前来汇报工作时,省委“都经常讲要他们抓武装,准备将来打游击战争,还经常询问下面的同志掌握了多少武装”。(210)《访问杨康华同志记录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案号:003106—16—4—61。从历史条件来看,广东省委借重统战来筹建武装的思路是符合实际的。一方面,统战有利于扩大党组织与武装群众。张文彬曾向广东的领导干部解释:“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是为了更有利于我们发展基本群众工作”。(211)《访问杨康华同志记录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案号:003106—16—4—61。尹林平也认为在广州沦陷前,省委在发展党组织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两方面“作出很大的成绩”。(212)《访问尹林平同志记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案号:001583—18—4—55。另一方面,统战掩护了中共发展武装。张文彬曾总结道:“我们的力量薄弱,他们(国民党当局)不足畏惧,而我们一开始便未有对立的团体、独立的运动,多以合法形式进行工作和尊重他们领导,避免摩擦”。(213)《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的综合报告》(1938年),《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第300页。李大林也认为:由于省委“没有公开号召群众抗日,且活动较隐蔽,故当时国民党只知道有我们存在,但不知我们活动的具体情况,对于我们开展工作是很有好处的”。(214)《访问李大林同志的记录整理》,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案号:004015—16—5—68。
受限于经验不足及客观斗争环境的变化,中共借重统战的战略也对武装工作的长期发展埋下一些隐患。首先,广东党内部因之难免产生一些“重统战工作,轻武装斗争”的思想倾向,武装工作也是广州沦陷前各项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尤其是沿海地区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异常不够(215)《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报告——关于党组织状况问题》(1938年8月),《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第235页。,此点曾引起不少干部的反思。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就认为:“当时广东省委对余汉谋太过于信任,对于坚持自己本身独立性的原则做得不够”“农运、工运方面的工作也做得不够”。(216)《访云广英记录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案号:001919—16—1—7。在其看来,“当时若多派些同志到农村去搞自己的武装,是可以大量搞起来的”。(217)《访问云广英同志记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案号:003594—16—5—65。据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干部连贯回忆,中共中央日后曾对广东省委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其将几百党员干部派往余汉谋部做政治工作,而派往珠江、东江的干部却很少,对东纵武装干部力量的建设不够重视。(218)《连贯同志谈关于张文彬、梁鸿钧同志的情况》,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案号:000269—17—1—10。结合广东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几位当事人的评价虽未必完全中肯,但映射出当时广东党内确实存在着重统战、轻武装的思想问题。
其次,尽管中共中央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2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但广东的不少干部对此领会不够。广东省委统战部长古大存即认为当时自己的思想还停留在内战时期的水平,存在着与国民党对抗的观念。(220)《古大存同志回忆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案号:000079—17—1—5。而延安援粤干部饶卫华则称:“我们从延安到衡阳时,叶剑英反复交代说广东有国民党左翼,应搞好统一战线,强调长期合作”。(221)《饶卫华同志谈广东党组织情况》,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案号:003193—16—4—62。在当时省委比较重视统战工作的背景下,一些基层干部很容易高估当局的合作诚意,自主意识不足,并放松阶级警觉性。
再次,除张文彬、尹林平外,广东省委的其他主要领导人均缺乏武装工作经验。军事干部不足导致武装工作的成效并不显著。中共原本在广州通过当局举办的劳工干部训练班掌握了数百工人的武装,有长短枪一百多条。但由于缺乏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意识,广州沦陷后该部并未布置到东江,而是随当局撤退到粤北,旋即被解散。尽管大部分队员后来转赴东江与珠江游击区参加游击队,但没有即时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对国民党的兵运工作方面,中共虽派人打入战地服务团,但多是搞文化宣传活动,很少去接近下级士兵。
另外,广东省委注重城市工作,对农村注意不够。所以取得成果有限。广东当局曾一度倡导的民众自卫运动因日军推迟进攻广州而“虎头蛇尾,终至搁置”(222)《广东的情况——关于政治、经济、救亡、党派活动等情况》(1938年),《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第268页。,影响了中共进一步扩大武装。就广东整个民众自卫团的数量来看,中共所掌握的部分非常有限。即使是在武装工作较出色的东莞,表面看有部分党员通过担任中队长、政训员等职领导部分队伍。实际上,由于“没有真正从下层去把握着基本的群众与部队,用党组织的力量去保证对部队的领导”(223)《粤东南特委工作报告》(1939年1月29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第351页。,使得部队仅在平日的检阅、巡行等运动中能动员来参加,“这些所谓掌握几乎完全等于没有掌握”。(224)《吴有恒关于粤东南特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特委的工作环境及对武装斗争等领导情况》(1941年1月13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1,内部发行,1987年版,第68页。
二、“白皮红心”:国共合作与中共东江抗日武装的成型
尹林平曾总结说:“东江游击队自诞生起,就注意团结国民党的一切抗战力量,取得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和种种社会关系,积蓄力量,发展进步势力”(225)尹林平:《东江纵队的统战工作》,中共惠阳县委党史办公室、东纵、边纵惠阳县老战士联谊会编:《东纵战斗在惠阳》,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这正是对中共东江抗日武装初期发展路径的经验总结。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强行登陆大亚湾,余汉谋部抵抗不力。10月21日,广州沦陷,珠江口至广州以及广九铁路两侧地区随后相继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军主力退守清远、新丰一线。由于组织撤退混乱,广九路沿线仍滞留有来不及撤退的国民党军一万余人。(226)主要有驻惠阳附近的第151师453旅(旅长温淑海),驻东莞、宝安附近的第153师457旅(旅长陈耀枢)及驻虎门要塞的一个守备团等部。中共方面也对时局的剧变估计不足。当时张文彬去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未归,代理省委书记的李大林不熟悉军事工作,“思想上缺乏警惕,没有两手准备”(227)《连贯同志谈关于张文彬、梁鸿钧同志的情况》,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案号:000269—17—1—10。,除匆忙布置撤退转移外,“没有对发动抗日武装斗争做更多布置”(228)《访问李大林的谈话记录——关于广东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情况》,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案号:000273—17—1—11。,导致省委与东江一带党组织的联系一度中断。
广州沦陷意味着广东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实施阶段。中共亟需对广东的武装工作方针进行调整,以适应斗争环境的变化。中共中央明令广东省委必须在广州及其他敌占区进行秘密工作,并在游击战术和政治工作上帮助友军开展游击战争;在东江、海陆丰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利用国民政府的命令到处组织自卫队,发展人民抗日武装。11月5日,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应当在没有充分发展或正在发展游击战争的华中、华南等地迅速地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并告诫地方党组织既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也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要采取独立自主的方针(22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第94页。,从而在中央层面确定了“发展华南”的相关方针。为支持广东武装工作的发展,中央选派梁鸿钧(时任延安警备区参谋长)、李振亚(时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教官)等一批军事经验丰富的干部到广东。周恩来也指示第四战区的中共特别支部(原为张发奎部第八集团军司令部战地服务队,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直属领导,此前不与地方党发生关系)与广东省委联系,以配合其工作。(230)胡提春:《关于抗战时期中共第四战区特别支部材料综合》,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案号:003486—17—4—22。
要想有效落实中共中央的相关方针,广东省委必须尽快将所掌握的武装力量进行整合并尽快建立抗日根据地。从广东的现实环境来看,借重统战仍是实现相关目标的重要手段。广州失守后,备受指责的余汉谋为建立部队的政治工作,要求中共“给一些有能力、没有红的干部帮他整顿部队,训练干部”(231)《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抗日战争发展、各政治派别关系、党的工作》(1940年4月23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7,第170页。,双方有进一步合作的现实需要。而新任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与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等为争取支持,也相继发表精诚团结、励精图治等进步言论。除第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王俊及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丘誉等少数亲蒋反共分子外,广东当局中的不少政要都呈现出“进步”与“开明”倾向。
广东省委认为战争的发展必然迫使当局进步,故决定“以支持余汉谋部队并推动其进步为中心”,运用广东各种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统战工作。(232)《广东民国史》下册,第843页。1939年1月1日,广东省委在召开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时,确定当前的任务是在广东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打击敌人,将广东建设成统一战线精诚团结的范例。同时要“在战争中积极培植自己力量”,并“把中心放在东区”,认为“这是支持长期抗战的重要根据地”。(233)《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抗日战争发展、各政治派别关系、党的工作》(1940年4月23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7,第164页。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张文彬在开会时特别强调要大力开展统战工作,而且在会后传达会议精神时也出现过于强调统战与合作的现象,导致一些基层干部不敢大胆发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武装,这为武装工作的开展造成一定消极影响。
作为广东最早沦陷且战略地位突出的地区,东江成为中共打开抗日游击战局面的重点地区。为加强对东江地区工作的直接领导,广东省委指示在香港成立东南特委,由梁广任书记。1938年10月13日,中共东莞中心县委以社训总队的名义成立完全由中共掌握的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全队共150人,以王作尧任队长,并从国民党县政府处领到40支枪。(234)《东纵一叶》,第24页。增城党组织也将掌握的武装改编为拥有一百多人枪的广东民众自卫团增城县第三区常备队,由阮海天指挥。王、阮二部虽规模不大,但敢于对日军主动出击,以伏击战等形式取得一些战果。
在东南特委看来,最先沦陷的惠阳才是东江各县中“地位最重要的”。廖承志处“有电台,与东江、坪山又接近,不搞抗日,那是天诛地灭”(235)《廖承志谈话记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案号:000147—17—1—6。,故决定派曾生率周伯鸣、谢鹤筹等一批有军队工作经验的干部从香港返回惠阳,成立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并尽快组建游击队。根据上级的相关方针,东南特委意图对滞留广九路沿线的国民党军展开统战工作,并通过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等团体向驻守惠阳、宝安附近的国民党军输送一批党员干部,要求他们“必须使这一万孤军保持作战精神,反抗敌人必然在很快期间内就会来的扫荡;并通过这些军队的关系,去建立群众性的游击队”。(236)《吴有恒关于粤东南特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特委的工作环境及对武装斗争等领导情况》(1941年1月13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1,第62页。
东南特委的要求应是考虑到发展武装的现实困难,惠阳当时并未像东莞等地一样掌握壮丁队等成规模的武装。尽管特委先后选派彭沃、翟信、陈石甫等原东江红军的骨干参加游击队,但此时组建部队依旧面临缺乏武器、经费及经验等诸多困难,加强国共合作无疑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此前,王作尧就曾率东莞的壮丁队联合当地驻军第153师一个营,在白沙打退日军进犯。当时驻惠阳附近的国民党军主要有第151师的温淑海旅及罗坤支队。其中罗坤支队作为地方武装,所部大都是靠坐地分肥的“胡子兵”,曾屡次被当局收编与遣散,是较理想的统战对象。惠宝工委一方面向两部派政治干部,意欲将其改造成大革命时期北伐军式的部队,另一方面又向温淑海部要来十多支步枪,向罗坤部要来五支步枪(237)李家富:《在东江纵队的回忆》,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案号:001505—18—4—52。,并通过动员党员和群众献枪,迅速组建起约三十人枪的曾生部。驻守坪山北岭的温旅麻玉标营对惠宝工委“很是友好”。该营通过惠宝工委发动群众支援粮食供给,并与曾部共同在北岭伏击日军。得益于对统战政策的有效运用及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曾部组建虽晚,发展却最快。当然,温淑海等对曾部表现出的“友好”主要是看重其背景所能带来的物质利益。比如,曾部“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番号就是温淑海要求“余闲乐社”在捐赠一百套棉衣的条件下才同意给予。东南特委派往驻宝安的第913团开展统战工作的人员也发现该部士兵“生活待遇很差,已有四个月没有发饷”,该部的营连长向工作团表示“如果有学赈会在经济上作靠山,在这里打几仗坚持下去是可以的”。(238)熊河清:《北撤风云》上,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案号:002038—16—2—19。中共能准确把握住国民党军的需求,体现出其统战策略已比较成熟。
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自身基础薄弱,在统战关系中处于弱势一方,曾、王等部此时对开展武装斗争的自主性与自信心出现先天性不足。1938年11月底,日军为巩固占领区,对广九路沿线的国民党军进行扫荡。国民党军迅即被击溃,并向香港撤退,最终大部在深圳、沙头角边境被英军缴械瓦解。彼时成立不久的曾、王等部由于“缺乏经验和坚持抗战之信心”(239)《广东工作经验教训研究》(1940年),《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7,第403页。,外加对国民党军的期望过高,也跟随其一路撤退。东莞的壮丁队除一部分在王作尧率领下转移到宝安章阁一带外,大部分在颜奇等率领下一直撤退到新界,并将大部分枪支丢弃。曾生部也跟着温旅一路撤退,几乎全部逃回香港,但没有伤亡。除武器埋藏在边界外,其他东西大部分丢弃。曾、王等部此次表现出的慌乱,不仅损害了平时在群众及国民党军队中建立起来的威信,而且使惠阳等地的工作一度陷入完全停顿与混乱。
相较于东莞、惠阳,中共在宝安的工作则较稳定。中共派人前往撤退到观澜山区的第913团与914团残部做政治思想工作,将其基本稳定下来。913团团长李纯不仅同意中共在该团设立临时性的政治部,还成立由黄木芬任队长的政治大队,并向其提供十多条枪。随后,中共又通过913团的关系,取得三个游击大队的番号,并在章阁村成立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第二大队,由黄木芬、蔡子培分任队长。后913团奉命调回河源整训,临行前给游击队留下一挺机枪和五六十支长短枪,使其扩展到约200人。
东南特委对东莞、惠阳党组织的逃跑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并要求其迅速返回内地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考虑到东江一带缺少有能力与威望的军事领袖,廖承志等人计划联系此时寓居香港的叶挺将曾、王等部集中起来,以此为基础在深圳以北地区活动。叶挺作为北伐名将,又是惠阳人,自是相当合适的人选,他也同意去东江开展工作。此议若成,必然能迅速打开广东敌后游击战争的局面。但中共的这一战略意图被国民党方面侦知。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情报认为:中共试图以香港为根据地而向华南及中国东南部开始活动,“在群众内培植相当势力,并与江南之新编第四军及华北第八路军形成三者鼎立之势。又秘密以叶挺为中心,纠合在琼崖、潮汕、东江方面之民众团体;依照叶剑英之例,不仅实施训练壮丁,且以此为机关,努力布置华南之游击区”。(240)《毛庆祥电蒋中正》(1939年3月2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80200—00519—053。因此,当余汉谋想委任叶挺为东江游击指挥时,受到蒋介石的极力反对。中共中央也认为叶挺在新四军发挥的作用更大,放在东江是大材小用,叶挺最终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叶挺虽未能留在东江,却为中共提出不少可行建议。比如,叶挺指出,在广州四周的惠阳、东莞、花县、南海、三水等地,日军由于兵力不足一时无力占领,国民党军又不敢到这些地区来组织抵抗,适合中共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他建议中共应该把各县已经建立的零散抗日武装联合起来,“统一组织,统一指挥,分散活动、逐步发展”。(241)熊河清:《北撤风云》上,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案号:002038—16—2—19。在听闻国民党军在香港边界溃散的情形后,叶挺建议曾生迅速前往沙头角收容仍滞留当地的千余溃兵。曾生按照指示,联系麻玉标收容到两连散兵,返回惠阳的途中又捡获不少国民党军丢弃的枪支,还买到两挺重机枪和不少轻机枪、步枪,部队装备得以充实。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正式成立,由曾生任队长。但麻玉标此时对在敌后打游击并无信心,将所部又带回到国民党一方。曾生后来对此倍感惋惜,认为如果能在国民党军溃退到沙头角时就宣布成立游击队,便能收容和掌握二三百或更多一些人枪,但“由于当时我们还很幼稚,没有这样的经验和胆略,错失了良机”。(242)《曾生回忆录》,第108页。
按照叶挺的建议,中共决定将东江的抗日武装进行联合与整编。鉴于惠阳作为东江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的中心,此前一直被认为是进行持久战和消耗战最有利之地区(243)《PT从东江巡视回来给长江局的报告》(1938年7月20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1,第9页。,东南特委决定仍以惠阳作为武装工作的中心,领导上也更偏重于曾部。为加强曾部实力,东南特委将撤退到香港的部分东莞壮丁队并入曾部。东莞县委将宝安的黄木芬部和王作尧部集中整编后,从中挑选一百二十人,重新组成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队长。曾、王部虽同属东南特委领导,但具体状况差别较大。曾部由于全部经费由香港工人和南洋华侨大力捐助,南洋华侨也派相当多的人回国参战或服务,发展较快。王部则因东莞华侨较少,难以接受大量捐款,经济困难,发展较慢。曾部骨干大都来自城市,生活条件比较好,新兵又占大多数,作战经验缺乏,故被称为“太子兵”。王部的大部分士兵则拥有一年半的入伍时间,作战经验较丰富,其艰苦精神与士气都较好。另外,王部在敌后,是灰色,国民党注意较少。曾部在前线,由于经常组织学习红军上政治课、做群众工作等,比较暴露,引起了当局的警惕。温淑海返回惠阳后,即要求曾部交回以前借的枪,并说奉令撤销以前委给的番号。至1939年初,曾、王部已发展到约三百余人,枪一百八十,重机一,轻机二,其中党员约130人(244)《粤东南特委工作报告》(1939年1月29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第360页。,成为当地颇具实力的部队,为争取当局的改编奠定基础。
1938年12月7日,兵力不足的日军为收缩战线,撤出淡水等地,国民党军此前已退到惠阳以东和东江以北,惠东宝一带暂时出现权力真空,这也为中共开辟根据地留出空间。曾生部开进淡水,并成立东江地区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国民党惠阳县长蓝逊因缺乏实力,对统战的态度较为开明。在承认既成事实并征得中共方面同意后,他将“第二区行政委员会”改为“第二区区署”,原来的工作人员不变。1939年春,国民党军重返惠阳成立第四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香翰屏为主任,并在惠阳、博罗一带成立第三游击纵队(司令骆凤翔),在东莞、宝安、增城一带成立第四游击纵队(司令王若周)。此时,东江敌后形成非常复杂的局面。土匪、地主武装、散兵游勇和国民党的游杂部队遍布各处,“一方面是大鱼吃小鱼,另一方面又各找靠山”。(245)周伯明:《五十年后的思考》,《论东江纵队》编辑组编:《论东江纵队》,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广东省委考虑到此时东江回旋余地狭小,敌伪顽势力比较强,要建立一个旗帜鲜明的党军或所谓进步军队是不可能的,故要求实行“争取当局发饷,使党成为绝对秘密”的策略。这种“白皮红心”的方针不仅显示出中共此时重视统战,极力避免刺激当局而引发冲突的心态,而且也有利于解决曾、王部所面临的人、钱、枪、活动地区(即有利地形)缺乏的困难。
根据上级要求,曾、王部决定以爱国青年和华侨、港澳同胞自发组织的民众抗日武装的面目来争取国民党军番号。曾、王二人的身份也起到很好的掩护作用。曾生毕业于中山大学,又当过海员,在华侨中有影响。王作尧在广州燕塘军校学过军事,父亲又是国民党的乡长,与当局打交道加了一重保护色。王作尧利用同乡同宗关系,与王若周取得联系,改编为该部直辖第二大队。东南特委随后将增城的阮海天部调到东莞,编为王作尧部一个中队。曾生部则改编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曾、王二部名义上受香翰屏指挥,实则由东南特委领导,并保持原来的党组织和编制,完全独立自主,但不公开来往。
广东省委此时也给予部队有力支持。张文彬亲自负责东南特委的工作,并将梁鸿钧、李振亚等人派到东江参加抗日武装的领导。后又派邬强到坪山与李振亚一起主持省委举办的游击训练班,为部队培训近百名游击骨干。另外,张文彬还要求第四战区中共特别支部尽可能抽调一批人利用战区长官部名义到各地配合地方党的工作。其中,张敬仁到东江先后出任第四、第三游击挺进纵队政训室副主任、主任,杨冶明任干事,为掩护东江游击队、查探情报等提供了有利条件。为进一步加强对曾、王部的统一领导,东南特委于1939年5月成立东江军事委员会,梁广任书记,梁鸿钧负责军事指挥,对外依旧保持秘密状态。
取得合法地位既有利于曾、王二部发动群众,获取华侨及港澳同胞的支援,也有利于中共进一步对香翰屏、王若周等人开展统战工作。东江此时一半是敌占区,一半是游击区,日军统治较之华北等地松懈得多,国民党的统治力量也很薄弱。骆凤翔、王若周二人是无兵司令,对曾、王二部都有所倚重。尤其王若周对王作尧部比较友好,不仅按时发放伙食,还补充一些子弹给王部。香翰屏则对华侨的影响较为重视,其上任之初即表示欢迎带有中共色彩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迁到惠阳工作。而曾部的华侨背景正有利于其派员打入香翰屏指挥所的内部去展开统战工作,并获取不少情报。尽管曾生、王作尧在日后回忆中称香翰屏为“诡计多端的反共老手”(246)《曾生回忆录》,第138页;《东纵一叶》,第97页。,实际上,香翰屏此时对中共的态度还比较友好,这一点在国共双方的资料中都有所体现。张文彬指出:“香翰屏是余的人,然而我们的方针是继续争取他,同时把个人的利害与抗战的利害说明。因为李汉魂想夺取他的游击队和他在青年中的势力,和他有矛盾,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矛盾,建立起统一战线工作”。(247)《张文彬关于对广东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工作的情况给南方局的报告》(1940年4月23日),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军事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页。李汉魂日后在向蒋介石控诉余汉谋部“剿共”不力时,专门指责香翰屏在曾生部发展初期对其包庇维护,致使曾部最终坐大。(248)原文为:“本省目前奸党之最猖獗者,为东江之曾生一股。曾生初以华侨回乡服务团为名,在东江活动,职廿八年就任之始,即拟将其扣办,渠竟被夤缘得充游击大队长,而东江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复力加维护,无法执行,迨奸谋显露,欲加制裁,经已不可收拾”。参见《李汉魂电蒋中正》(1945年4月18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1—050005—00001—003。另外,曾部也比较注意争取地方武装的支持。罗坤曾要求曾部将淡水让给其驻防。为顾全大局,曾部退出淡水撤往坪山。此举颇得罗坤的好感,罗坤返回淡水后,对中共控制的第二区区署的各项工作,既不反对,也不过问,有时还说些好话。坪山地域虽小,却是内地与香港物资出入的要道。曾部在此仅每月护送来往货物所收取的费用就有约二万余元。王部则将统战工作的重点置于王若周身上,对东莞的地方武装争取不多,还曾因奉命剿灭流窜当地的土匪队伍,引起其他几支被当局收编的土匪队伍的戒心。
除不断推动统战工作外,曾、王二部还通过积极抗战来争取有利的生存空间。1939年9月,日军再次在大亚湾登陆,攻占澳头、葵涌、沙鱼涌等要地,严重阻碍内地与香港、南洋的联系。香翰屏令所部收复失地,但罗坤等部为保存实力均不愿主动出击,唯有曾部以袭扰战术收复葵涌、沙鱼涌,受到第四战区和东江游击指挥所的传令嘉奖。另外,曾部还在石(龙)深(圳)公路的鸡心石伏击日军,毙伤日军30余人,成为游击队创建初期以弱势兵力逼近袭击日军日间战斗的典范。12月1日,王部通过封锁包围的战术收复宝安县城南头。此时广东的抗战前线出现一种普遍现象,即作战时“正规军在后,保安团在前,游击队在更前,争功正规军第一,保安团第二,游击队无功,有也只是挂名的大老爷”。(249)《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3月7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7,第74页。相较之下,曾、王部的抗战表现既赢得了华侨及民众的支持,也使香翰屏等人暂时对其有所倚重,延缓搞军事摩擦的进度。至1940年春,曾部发展到500余人,王部发展到180多人,在东江地区初步站稳脚跟。但此时国内日益高涨的反共逆流也在逐渐波及到东江,并对中共下一步的统战策略带来考验。
三、斗而不破:国共关系的逆转与中共对统战的维护
在曾、王二部崛起的同时,广东的国共关系却不断逆转。在广州、武汉沦陷后,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内的反共势力不断抬头。以国民党在1939年1月底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为标志,第一次反共高潮不断在全国蔓延。针对形势的转变,毛泽东指出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与投降主义,为此要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只有使自己的力量增强起来,才能够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5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第109页。
从广东的环境来看,此前由于日军的威胁,余汉谋等对联合中共有现实需求,且与国民党中央有矛盾,故反共态度并不积极,这也是中共推进统战工作较顺利的原因。作为广东的地方实力派,余汉谋对中共更多的是利用心态,他不可能容许有中共武装在辖区内任意发展。随着广东的抗战局势逐步稳定,中共对余汉谋的利用价值降低,加之受国民党内部反共势力的影响,广东的国共关系变得非常微妙。除余外的其他高层人物中,张发奎虽然表现更开明一些,但其实权甚小,掌握实权的李汉魂、丘誉等人都是反共派。来自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情报即显示:李汉魂“对于共党之活动严重警戒,不予稍缓之故,致共党在华南方面之军事活动甚不自由”。(251)《毛庆祥电蒋中正》(1939年3月2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80200—00519—053。广东省委此前为争取余汉谋和中间力量,发展武装比较慎重。(252)《广东工作报告摘录及谈话记录——关于广州、琼崖、东江等地工作概况》(1940年6月11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7,第279页。一旦余汉谋部挑起军事摩擦,势单力薄的曾、王二部势必面临被动局面。
不可忽视的是,曾、王二部此前的统战工作虽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曾、王部虽使用国民党军番号,但其处处以八路军为榜样,部队设置政治指导员,经常上政治课并宣传《论持久战》等理论,显得颇为瞩目。尤其曾部中有数十名前东江红军的战士,其副队长郑晋就是前红十一军的团参谋,又曾与叶挺有所联系,故一直被不少国民党官员视为“赤色部队”。其次,惠阳的罗坤部及东莞的袁华照部、刘发愚部作为当地的实际统治力量,由于所部大都由土匪构成,东江游击队的战士多少都有些“瞧不起他们”,不愿与其过多往来。即使派往这些部队中做统战工作的干部也大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并不擅长做“这些江湖气概的工作,老是拿刻苦做榜样,反对走私、收保护费、吃大烟、赌钱,实际上是书呆子的行动”。(253)《吴有恒关于粤东南特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特委的工作环境及对武装斗争等领导情况》(1941年1月13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1,第80—81页。再次,游击队还进行了苛刻而过急的土地改革。(254)陈瑞璋:《东江纵队——抗战前后的香港游击队》,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曾部自香港返回淡水期间,曾未经公审处决十一名汉奸,这些举措引发当地一些士绅对游击队产生怀疑与恐惧。另外,曾部的缉私队曾在沙鱼涌一次查获罗坤部走私的钨矿二百担,价值达二十余万元。曾生也先后拒绝香翰屏、罗坤等拉拢其参与合伙走私的建议,这难免引起罗坤等人的不满。东南特委组织部长吴有恒在工作报告中就认为:统战工作“在惠阳则太左,在中山、东莞则太右”,特委本身在统战工作上是“右倾的”,“如对逆流来时,我们认为分裂是必然的了,因此就放松对中间力量的争取工作,不去多方利用对方的矛盾”。(255)《吴有恒关于粤东南特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特委的工作环境及对武装斗争等领导情况》(1941年1月13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1,第119页。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此前曾指出:在长期合作的原则下,“只有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否则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256)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年11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的重要历史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714页。对于“白皮红心”的曾、王二部来说,能否把握坚持权利的限度,并且明确合作与混一的界限是个很大的问题。
反共逆流波及广东后,中共武装工作较突出的东江一带成为反共派重点防范的地区。原先对中共较友好的惠阳县长蓝逊被撤换,继任的刘秉纲曾任国民党军团长,是以“剿共”出名的顽固派,该事件实际上是反共派为挑起冲突作准备。刘秉纲上任后,即在东江行政专员池中宽的支持下,动员数百保安队、警察特务队等,企图威胁解散或改编曾生部。但由于地方势力的反对与群众的拥护,外加曾部实力较强,故其阴谋暂未得逞。在东莞,翟荣基取代王若周出任第四游击纵队司令。翟本人极反共,不仅停发王部的粮饷,还与香翰屏商讨,企图以“集训”为名将王部包围缴械。香翰屏将曾、王二部布置在前线抗日,以保障其在淡水、惠阳的安全,却又不提供粮饷、武器,还限制部队人数和活动范围。这些变化使曾生感到自1939年夏季开始,部队的处境逐渐困难起来。曾生在参加大队长会议时,就曾遭到香翰屏的直接质问:“你们到底是走共产党的路线,还是走我的路线?”曾生则巧妙回答:“我们走的是真正抗日的路线。”(257)曾生:《东江抗日星火》,《东江纵队资料》,第41—42页。
有感局势的逆变,中共方面开始做出应对措施。南方局发出紧急通知:“现在各地方党的组织应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上是地下党的形式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各地公开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在可能条件下仍须继续其原来的活动,但应时时提防阴谋家的暗害,他们应与秘密的组织分开。”(258)《南方局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1939年6月29日),徐塞声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第63页。广东省委也要求实行“组织上的退却,政治上的进攻”,即将群众运动从城市转到农村,从表面转到实际(设情报站、联络站),由暂时的工作转到长期的工作。东江党组织按上级要求,将地方和部队的党组织分开,把公开活动暴露的党员撤到部队,县委主要领导人以商人、教师等职业隐蔽活动,减少群众组织的公开活动,一般都是以灰色面目出现。
中共此前所做的统战工作及东江地区的特殊环境对抵制国民党顽固派的活动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刘秉纲强制解散惠阳县第二区区政府,并对工作人员进行迫害时,罗坤就出面对其警告:“他们(第二区政府)为家乡做了很多好事,人人都知道,你们不要欺人太甚。”(259)《东江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东江党史资料汇编》第1辑,第66页。另外,罗坤也很想将曾部收编,并对骆凤翔说:“你怕共产党,我不怕,你不编,我来编。”东江华侨救乡总会则宣称曾部是华侨的队伍,并派代表向香翰屏及骆凤翔交涉说:“你们不承认它,我们四十万东江华侨承认它,你们说没有饷,我们给他们捐款,他们里面有几个百万富翁的儿子呢,谁说他们是共产党的队伍。”(260)《吴有恒关于粤东南特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特委的工作环境及对武装斗争等领导情况》(1941年1月13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1,第65页。在此情况下,香翰屏等人只好采取“先礼后兵”的手段。他们一方面妄图诱惑曾生、王作尧参加国民党,封官许愿;另一方面又以“协助工作”为名,派人到曾、王二部担任指导员、副大队长等职务,企图控制部队并进行特务活动,但均未如愿。香翰屏于10月将独立第20旅调到东江南岸,准备武力解决曾部。曾生此时正将东江华侨救乡会主席黄伯才请来部队参观,黄是惠阳有名的资本家,国民党军一时之间不好轻举妄动。结果独立第20旅却先遭到日军的围攻,损失惨重,旅长喻英奇为此向香翰屏大发脾气。该事件凸显出东江地区国、共、日三方势力交错、相互制约的复杂格局。中共方面观察到:日军有意只占领广州至石龙一段以及莞太、宝太公路上的点线,对于从石龙到深圳一线及路西的东宝地区故意不予占领,而让国民党军队驻扎进出,实行反共,以达其“以华制华”的诡计。但日军作为侵略者,在国共冲突中伺机而动,成为香翰屏等人在筹划反共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曾生将此生动地形容为:“日军一紧张,他们(香翰屏等)就松;日军一松,他们就紧”。(261)《曾生回忆录》,第140页。从现实情况来看,尽管中共在此期间为维护统战大局而保持克制,努力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但这种局面到1939年底就难以再维持下去。
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策略。同时,陈诚亲自到广东作反共动员和部署。广东当局于年底下令限制东江华侨服务团的活动,香翰屏等人再次调兵遣将,国共双方的摩擦呈现升级之势。
广东省委注意到反共逆流日益严重,并于11月召开第五次执委会议,决定要加强琼崖、东江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发展敌后游击战争。针对东江的军事危机,广东省委要求东江方面要继续“加强统线工作,接受当局派来的个别政工人员,但严防其破坏行为”,“准备突变,如果当局以武力相加时坚决抵抗,该时尽力深入与坚持敌后侧行动”。(262)《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3月7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7,第78页。广东省委此时对局势的把握还是比较精准的,但对余汉谋等人的真实心态却有所误判。张文彬认为余汉谋“为人忠厚软弱,无人启发,无得力干部,对中央与李(汉魂)都很怕,对进步动摇”,李汉魂“则较为多才,阴险、投机,有陈(诚)后盾,顽固要命”。(263)《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书记处报告——关于广东战后危机、民运、武装组织情况》(1940年2月12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7,第24页。据余汉谋亲信的评价,余为人“貌似愚忠,内藏机诈,肆应各方,极其圆滑”(264)梁世骥:《淮海战役后蒋粤桂的矛盾及其最后在广东垮台》,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精编·上编》第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96页。,其以往表现确实对张文彬产生了一定的蒙蔽性。余汉谋在向蒋介石转发潮安警备司令华振中所查获的广东中共青运会议录告词中称:中共“上层任务为对中央政府及各党派交涉,根据国际路线指示下级”,“下层任务为通过国民党形式隐匿活动实力,参加政府机关、三民主义青年团及各级低层组织,使之渐渐变质”,“工作姿态表面不左,防御进攻,软硬兼施,争取公开合法以求发展”,并“企图增高中共政治地位,发扬马列主义,吸收青年学生、工农干部取得领导,建立其所谓统一战线”,并建议对此要“严密侦察防范”。(265)《余汉谋电蒋中正》(1939年5月1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300—00015—522;《华振中电蒋中正》(1939年5月1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300—00018—081。这证明余汉谋不仅对中共的统战策略相当了解,而且政治态度并无中共所估计的那般进步。广东省委看到余汉谋与国民党中央、李汉魂之间存在较多的利益冲突,但对余、李等人在反对中共、维护国民党统治方面的一致性估计不足,从而导致其在统战中强调合作的一面,对余汉谋等人的反共一面警惕性不够。
受此前开展统战工作较顺利的影响,东江的一些干部也对反共逆流缺乏警觉。比如,当东南特委将逆流到来的政治形势传达到东莞时,东莞组织部长袁佩鸿就认为:“我们东莞不会这样吧。”(266)《吴有恒关于粤东南特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特委的工作环境及对武装斗争等领导情况》(1941年1月13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1,第97页。张文彬日后指出:东江地区在省委已传达逆流事实、警惕全党准备应付的情况下,依旧比较麻木,工作没有实际的转变。(267)《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一年来抗战的发展和军事工作、广东逆流的发展和当局内部的冲突》(1940年3月7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7,第109页。这种思想上的麻痹为中共接下来的反摩擦斗争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残酷的斗争现实又推动着曾、王二部最终走向自主。
四、走向自主:东移海陆丰与武装斗争策略的转变
1940年春,针对国内反共摩擦日趋激烈的形势,中共不断调适自己的统战政策。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作报告时指出:为扩大与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只有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同顽固派斗争时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26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第176—177页。随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均应该发展。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只有“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269)毛泽东:《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1940年5月4日),《建党以来的重要历史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第302、304页。周恩来在召开南方局会议时也批驳了在敌后搞游击区会“影响统一战线”的谬论,并肯定了广东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和做法。(270)《东江纵队志》编委会编:《东江纵队志》,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同时,中央书记处指示广东省委:“对惠阳曾生部等游击队须加强领导,动员地方党及同情群众对他们给予各种精神上、物质上的援助,使他们尽可能扩大,同时严防汉奸顽固派的袭击和瓦解阴谋。”(271)中央书记处:《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1940年3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案号:001668—18—4—61。广东省委要求党组织在大力帮助与推动余汉谋部巩固和进步的同时,必须注意余的动摇性,争取香翰屏等游击区指挥者对我们的谅解。并要求部队在坚持统战与合法地位的同时,必须慎重应付局部事变,慎重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广东省委为此还专门派李大林到东江军委传达中央与南方局的相关指示。
但此时东江地区的国共冲突已发展到统战难以调节的地步。香翰屏等趁深圳、沙头角一带的日军暂调他处的时机准备以武力来解决曾、王二部。1940年2月,香翰屏命令曾部限期到惠阳“集训”,企图将其集中后包围缴械。东江军委据各方情报得知其目的,以前线敌情紧张为由坚持原地整训,挫败其阴谋。香翰屏随后调集第186师558团、保安第八团以及汕头、东江地区的地方武装共三千余人,准备围剿曾、王二部。据梁广回忆,香翰屏曾在香港探听到曾生部由小林(梁广在党内的称呼)领导,于是便造谣说曾部是台湾的日本总督小林一雄领导,是汉奸部队,为消灭曾部制造借口。实际上,曾部的真实状况早已被当局侦知,香翰屏之所以如此宣传,应该还是对破坏统战及曾部的华侨背景有顾忌。为麻痹曾部并表现其解决事端的“诚意”,香翰屏在集结军队的同时,还先后派民主人士杨朴如、丘琮到曾部接洽商谈。丘琮在谈判时看到国民党军逼近坪山,曾打电话质问指挥所参谋长杨幼敏,但杨置之不理,仍令各部继续推进,可见香翰屏等人此时动武的决心已定,双方已无和谈余地。
在国民党军进犯的威胁下,东江军委一时间陷入两难境地。东江军委虽在无论形势如何发展都要坚持抗日武装斗争的认识上达成一致,但对如何应付军事冲突却未能作出正确分析。东江军委未意识到所面临的冲突是全国性反共高潮的一部分,认为不过是地方性的局部问题。且不少人认为敌强我弱,如果硬拼必然吃大亏。目前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也不好闹摩擦,最好还是自己主动“避让”。至于退避的目的地,主张去海陆丰的意见占据上风。尽管海陆丰此时是国统区,但该派意见认为海陆丰是大革命时期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好,且傍山面海,回旋空间广阔,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另外,国民党既已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统一战线将难以维持,日益加剧的武装冲突势必引起第三次国内战争,到那时就没有前线和后方之分了。此前东江军委已派一批干部到惠阳、海丰交界的多祝、高潭活动,并初步打开局面。(272)《东江纵队志》,第124—125页。广东省委也曾指示:为准备应付突变,至不得已时,经过战斗是可以向紫金、海陆丰撤退,但“这必须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必须要经过必要的战斗”。(273)《张文彬关于广东抗战形势、统战工作及军事工作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0年4月23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7,第187页。2月底,在游击指挥所工作的地下党员张敬仁等给东江军委送来国民党军正加紧部署,准备围歼中共游击队的确切情报。东江军委在仓促之下决定按原计划东移海陆丰,但转移时却未按上级要求进行“必要的战斗”。从决策过程可以看出,东江军委此时对在东江敌后坚持独立的武装斗争依旧信心不足,尤其缺乏坚决的反顽斗争意识。
3月9日晚,曾部撤离坪山向东突围。与此同时,王部也在东莞突破保八团等部的包围,向惠阳东南转移并希望与曾部会合。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军的“剿共”军事却率先激化其内部矛盾。李汉魂的政府工作报告曾提到:在战时物价高涨的情况下,地方保安团队与正规军“未能一体待遇,生活无法维持,尤以国军并肩作战之团队,士气受其影响”。(274)广东省政府编译室:《战时粤政》(1945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华南抗战时期史料汇编·第1辑》第19册,广东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144页。香翰屏为保存实力,消灭异己,刻意以地方武装打头阵充当炮灰,而以正规军在后压阵,结果引发部分地方武装哗变。据梁广报告:“保安八团有一排人杀死排长哗变;博罗游击队有四十余人哗变,向罗浮山去了;刘秉纲部有一中队杀死中队长一、小队长二,哗变;追击我部之敌军中有一中队长姓卢,带有四十余人哗变,当在轿岭之役时已要和我队联络,被我队员拒绝,事后不知去向;惠阳东南稔山附近有土匪百余人,自动打出红旗,派有代表来港与曾部联系,表示愿编入我部或合作等;罗坤部在坪山事变后,有二百余人枪失踪不知去向(此乃罗坤本人说法,不一定可靠);保安第八团第五连与第六连冲突械斗,双方损失甚重,起因为何不详。以上七宗据各方消息确有其事,但事前和现在我们都还未有和他们联络,正在调查找寻中”。(275)《梁广关于坪山事件经过的报告》(1940年4月12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7,第135页。国民党方的资料也部分印证梁广的报告。余汉谋向蒋介石等人报告:曾、王二部“于灰辰叛变,均受异党煽动,刻窜向海陆丰方面。保八团之一排往宝安接收新兵中途格杀官长三员叛变,东江情势日趋严重,兹为巩固粤省防线及肃清叛部起见,拟请调驻衡州附近之一五九师开赴惠阳剿办叛部,肃清异党势力,并整顿游击队以巩固东江防务”。(276)《余汉谋电蒋中正、何应钦、徐永昌》(1940年3月1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300—00202—109。这些哗变的产生应该是地方武装对当局消灭异己的恐慌与不满所导致,而梁广提到的部分哗变士兵愿意与中共合作的现象也能映射出中共此前对地方武装开展的统战工作有一定效力。
李汉魂也向蒋介石通报了曾、王部“抗令”及保8团哗变等情形,并引述香翰屏的话称,该事件“足证异党分子有整个计划,其阴谋并不在小”,“共党包藏祸心,粤省情形复杂……除电请香主任及饬属切实防剿,并请准余副长官派兵一团迅即追剿以免滋蔓”。(277)《李汉魂电蒋中正》(1940年3月1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300—00205—246。对比余、李二人电报可以发现,二者在调兵的方式和数量存在较大差异。李汉魂希望请准余汉谋派兵一团追剿,余汉谋则要求将派驻省外的第159师调回广东。考虑到曾、王二部其时总共不过700余人,李汉魂的处置相对切实,余汉谋则有借机索回调驻外省的粤军之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余、李二人解决中共问题的态度与做法并不完全一致,而参与“剿共”的正规军与地方武装之间则相互猜忌,为曾、王二部最终打破“围剿”埋下伏笔。
东江地区的国共冲突与曾、王二部的命运引起中共中央的关注。由于东移事发突然,广东省委未能及时获知事变的最新情况。正在重庆汇报工作的张文彬依然主张在广东发展武装“准备长期在友党统治下积蓄,必须用当局的名义,不暴露面目”,要“多争取中间分子与进步分子来领导”。(278)《张文彬关于广东军事工作情况向南方局的报告》(1940年3月7日),《南方局党史资料·军事工作》,第108页。中共中央对此批评广东省委:“必须认识时局的严重性,纠正对广东环境特殊的乐观估计”,“望立即将东江发生之重大事变的真相,查明电告”。(279)《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时局逆转与党的应付措施给广东省委并南委的指示》(1940年4月1日),《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文献(1)》,第228—229页。张文彬随后在报告中对以往工作进行反思,提出:“在反逆流的压迫下,要斗争适当。不要怕统线破裂,有时一定要斗争才能巩固统一战线”,并指示东江部队要“坚持在惠东宝地区斗争,只有深入敌后,利用敌人与国民党的矛盾才能生存”。(280)《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抗日战争发展、各政治派别关系、党的工作》(1940年4月23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7,第181、186页。毛泽东听取张文彬的报告后指出:“(广东省委过去)没有大力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一个缺点,今后工作方针应把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作为中心,应将工作重心放在武装工作和战区工作。现在一切偏僻的地方都是国统区,我们不要上山,而要下水,深入敌后活动。对于时局估计,要准备最坏局面,要在最坏一点上来布置工作”。(28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第188页。周恩来也指示张文彬:今后的中心工作要放到武装斗争上,要到敌后去活动,否则不能发展。(282)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周恩来与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5月8日,在得知曾、王二部东移出现危机后,中央书记处指出曾、王二部“不向敌人进攻而向我后方行动的政策,在政治上是绝对错误的,军事上也必失败”,要求他们“仍应回到东宝惠地区,在日本与国民党之间,在政治上与优良条件下,大胆坚持抗日与打摩擦仗”。(283)中央书记处:《曾王两部应回防东宝惠并注意行动事项》(1940年5月8日),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案号:001668—18—4—61。广东省委接电后,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指示”,并要求曾、王部“无条件地执行中央意见,加强内部团结”。(284)《给中央并南方局报告》(1940年5月17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7,第259—260页。
但当时曾、王二部尚未与中共中央建立直接联系,中央的相关指示直到6月初才传达到东江军委,曾、王二部东移的遭遇恰好印证了中央的判断。由于事前未估计到当局会集中如此大的力量前来围剿,曾、王二部在仓促行动中失去联络,各自为战,并极力避免与国民党军直接冲突。曾部由于行军速度较慢,在途中先后被罗坤支队、第558团追上偷袭,损失较重。部队在高潭休整时又遭国民党军围攻,最后转移到海丰。王部抵达惠阳后,与曾部会师不果,也向海丰转移。曾、王二部在转移中并未放弃统战当局的想法,曾部在高潭休整时,仍决定“政治上继续向当局争取合法存在,对各友军取联络,说明事变的因果,争取同情,继续合作抗战”。(285)《梁广关于坪山事件经过的报告》(1940年4月12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7,第134页。但这种想法显然不合时宜,反而造成不少干部“政治麻痹,缺乏警惕性,对国民党存有幻想”。(286)《华南抗日纵队抗日战争战史(初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案号:003363—17—4—19。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国民党正规军,地方武装对曾、王二部的态度和缓不少。曾部在高潭时遭到汕头的地方武装李坤支队的进犯,曾部派代表与其谈判,要求给一个合法名义。李坤尽管表示情况变化,没有胆量给其名义,但并未为难曾部代表。曾部代表李燮邦在返回途中与第558团遭遇,却被其无理扣押。王部在转移中被第558团包围于海丰斜嶂山,第558团用政治欺骗的手段约其派代表谈判,在谈判时将大队政训员何与成等干部及战士40余人扣押,其中6位干部(包括李燮邦在内)后被押送惠阳,惨遭杀害。另外,广大中下层干部及战士初时并不知道东移的真实目的,情绪非常不好,不理解为什么国共会分裂,对打内战不知所以然,外加对沿途环境不熟悉,后勤保障难以为继,导致部队减员尤其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
4月中旬,梁广由高潭抵达香港,从各方面情报了解到整个事变的真相后,迅即给曾部发来较正确的指示。梁广告知东江问题并非局部冲突,而是整个逆流的一部分,并要求曾部对国民党军既不能放松统一战线的政治号召,更不要放松高度的阶级警觉,尤其应谨防“反动势力可能利用交涉为陷阱”。行军中“时刻不要松懈作战防御的姿势,部队力量不要过于分散,而应有相当的集中”,“不要幻想建立一永久根据地,而应在港澳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中作飘忽行动,以避免正面不利的冲突”。(287)《梁广给曾部的紧急通知》(1940年4月12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7,第140页。但曾、王二部抵达海陆丰后,仅余100多人,且弹药缺乏,给养不继,处境十分困难。依靠当地党组织与群众的掩护,部队最终分散隐蔽下来。
从国民党方面的资料来看,其此次情报调查工作比较有力,战略行动颇有章法,说明其蓄谋已久,曾、王二部的统战思路自东移开始就已成幻想。香翰屏在3月时就预判出曾部转移的方向是“经澳头向稔山溃窜”,“有会合海陆丰中共余孽进扰海陆丰或南山模样”,并“分饬罗坤部暨地方团队分途追剿”,“海陆丰县长率队截剿”,“四纵队一支队开赴坪山办理善后”。(288)《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关于“围剿”曾生部情况给军令部的快邮代电》(1940年3月),《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图片、表册、参考资料》,第134页。4月17日,李汉魂向蒋介石等人通报其“剿共”进展,称曾部在海丰高潭北之柑树下“被我团队围击”,“结果俘三十余(内大队副、中队长各一),缴轻机枪一,国枪二十。余残敌窜匿沟金坑附近,其一部百余冬日由禾多东窜支午”,王作尧部百余“在海丰大洞附近发现,经凌团一营驰剿”,并“限令各部加紧追剿,务于本月哿日前将其残部消灭”。(289)《李汉魂关于“围剿”曾生、王作尧两部情况致蒋介石等电》(1940年4月17日),《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图片、表册、参考资料》,第137页。5月中下旬,追击到海陆丰的国民党军频繁搜索侦查,却找不到目标,加之受到日军进犯粤北的压力,便收兵请功。李汉魂致电国民党中央,称曾、王二部“已全部肃清,其零星散窜之匪亦经由本府电令池专员转饬有关各县切实清剿并注意地方善后”。(290)《李汉魂关于围剿曾生、王作尧两部致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公函》(1940年5月27日),《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图片、表册、参考资料》,第141页。
曾、王二部在接到中央及省委指示后,决定返回惠东宝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东移的残酷考验推动着中共不得不由统战走向自主。广东省委意识到:“抗战到了第二阶段,准备反攻,没有我们的力量是不行的”,“今后我们应把发展武装放在工作日程的第一位,我们要独立自主的,大胆的去发展,不必顾国党的反对”。(291)《广东工作报告摘录及谈话记录——关于广州、琼崖、东江等地工作概况》(1940年6月11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7,第279—280页。为加强对曾、王二部的领导,广东省委决定撤销东江军委,将二部交由东江特委领导,并派尹林平任政委。同时指出:尽管广州附近的敌占区纵深很浅,但仍有许多小块地盘,人口稠密可资掩护,且水多,敌人机械化部队活动困难(292)《广东工作经验教训研究》(1940年),《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7,403页。,适合开辟抗日根据地。9月,东江特委在宝安的上下坪村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中央的文件指示,并对以往工作进行检讨,最终确定: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军的进犯坚持自卫原则。为摆脱与国民党的原有关系,中共把曾、王二部的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曾生任队长)和第五大队(王作尧任队长),尹林平兼任两个大队的政委,梁鸿钧负责军事指挥。会后,第三大队挺进东莞开辟大岭山区根据地,第五大队在宝安开辟以阳台山区为中心的根据地。
此后,由中共独立领导的曾、王二部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先后粉碎日伪顽军的多次进犯。到1941年8月底,部队从100余人发展到1500余人,逐渐在东江地区站稳脚跟。在此后的反顽斗争中,曾、王二部逐步抛弃对广东当局进行和谈的“幻想”,坚定了在敌后独立自主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心,并对如何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因此,1940年可视为中共东江抗日武装由统战走向自主的重要转折点。1943年12月2日,东江抗日武装正式更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公开打出中共领导的旗帜,继而成为中共华南抗日游击队的主力。
结语
自1938年广州沦陷前后到1940年,广东的中共党组织充分展现其灵活、有效的统战策略,在几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打造出东江抗日武装这一精干的部队,并成功打开华南敌后抗战的局面。与华北、华中地区可以依托八路军、新四军等来带动敌后抗日游击武装发展的模式不同,中共东江抗日武装不仅远离中央及主力部队,而且身处日伪顽的夹击下,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因此,统战对曾、王二部的早期发展非常重要。曾生回忆:“我们从建队开始,就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利用日军与顽军、日军与伪军、顽军正规军与杂牌军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工作,或使他们之间的矛盾扩大,或者使他们在进攻我们时互不配合,或者利用杂牌部队来掩护我们的部队”。(293)《曾生回忆录》,第429—430页。但另一方面,对统战的倚重又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共对坚持独立自主领导武装斗争缺乏自信,进而导致部队在反摩擦斗争初期受挫。期间虽有曲折与反复,但得益于中共党组织积极有效的纠错机制及上层的高瞻远瞩,部队最终走上了独立自主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道路。这一过程所伴随的正是部队的统战策略不断走向成熟。正如尹林平后来所总结:“东江纵队在紧要关头能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原因是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东纵能够胜利发展、完成党提出的任务的根本保证”。(294)林平:《鏖战华南敌后的东江纵队》,《东江纵队志》,第24页
反观国民党一方,余汉谋、香翰屏等对中共完全采取利用态度。一旦形势有变,便迅速撕下其“亲共”伪装,不顾抗战大局而对中共大打出手。在“围剿”曾、王二部的过程中,国民党军内部争权夺利、党同伐异的弊端暴露无遗。正规军与地方武装之间互不信任,甚至激发兵变。李汉魂对此深感忧虑,称:“东江及潮梅方面,情形复杂,事权不一,见利则争,遇责则诿,前途实大可虑”(295)朱振声编:《李汉魂将军日记·上集》第1册,香港联艺印刷出版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289页。,这与中共方面上下一心形成鲜明对比。另外,东江地区特殊的斗争环境(日、伪、顽三方势力犬牙交错,且日军统治力量不如华北、华中巩固)及地形条件(人口稠密、水网密布、不适合机械化部队作战)为中共游击队提供了生存空间。国民党顽固派所挑起的内战对民族利益有害无益,更难以得到东江地区开明人士及广大群众的支持,这也是其尽管占据实力优势,却无法消灭中共武装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