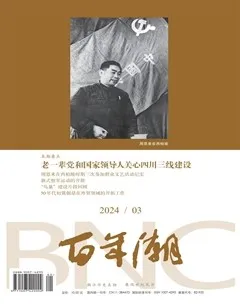在延安保小的日子
钱卓麟
本文作者1938年2月24日出生于延安。1945年在延安安塞保小读书,后随父母辗转南北,先后在东北育才、中南育才、北京二十九中、南开大学就读。1963年毕业后支边,分配到内蒙古通辽市哲盟教育局,1981年调入河北省承德市教育学院,1998年3月退休。
我小学在离延安百十里远的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部(简称保小)就读,学校坐落在安塞的白家坪。
上学那天是后勤部派人骑马送我去的。那时延安不但没有火车,连公交车甚至自行车都没有,骑马已经是最好的出行方式了。出延安向西北走去,不远处的山上有几排窑洞,那是边区最好的医院—中央医院。再往前走,有一片陕北少有的稻田,稻苗绿油油长势良好,据说这是从南方来的退伍老红军种植的。除此之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路上河多,走不远就要过次河。其实河并不多,只有一条延河,大概是道路蜿蜒曲折的缘故。
虽然是第一次骑马,倒也一点没害怕,虽然是第一次离家,到这么“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倒也没想家。只是等送我来的李叔叔帮我办完入校手续回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才感到有些不对劲了,忽然想家了,就蹲在学校大礼堂前的沟里哭了起来,正巧校长路过这里问我为什么哭。我不好意思说是想家,就灵机一动编了个理由:“我从家只带来了碗,没带筷子—叫我咋吃饭呀?”“这算啥事?”校长笑了,当然这难题难不住他,“我咋吃饭”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我很快就适应、融入到团结友爱的保小这个革命大家庭里,从此就再也没哭过。
学校所在的白家坪在一条山沟里,东边是教学区,有一排石窑作为各年级的教室,教室南边有一片平地是操场,各年级的体育课在这上,全校大会在这召开。晚饭后,同学都汇集到这里追逐打闹做游戏,那时不要说没有电灯,就是油灯、蜡烛也极少,可是暮色中、月光下的这片土地就成了我们的乐园,充满欢声笑语。沟的西边是宿舍区、医务室,大礼堂也在这边。
其实,进了学校大门就有一片更大的场地,也较平坦,但由于离教室和宿舍都较远,又太大,那时学生不算多,因而用不上,所以一直都空闲。这片空地的北边靠近山脚下有一排平房是厨房。大师傅做好饭后,用桶送到各班教室前,同学排队打好饭菜到教室里就餐。主食一般是小米饭,菜是一般的蔬菜,洋芋(土豆)、白菜、茴子白(洋白菜)之类,平常很难吃到肉。每当吃肉的时候,同学纷纷出来不断向厨房里张望,偶尔有大师傅出来,和同学开开玩笑。
同学住的都是石窑。早晨起床后,大家都沿着山沟往里走去,有条小溪,就在那里洗脸、刷牙。当时,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业落后,又受到国民党严密包围、封锁,物资极其匮乏,连牙膏都没有,刷牙只能用牙粉,价钱比牙膏便宜得多。
我对语文课(那时叫国文课)有些印象,其他课程就记不太清楚了。一年级上学期课文识字都比较简单,无非是“人、手、刀、口”之类,逐渐加难,比如“要吃李,没有李,要吃桃,桃有毛”“梨子树开白花,我们都是好小娃”“指甲长,指甲长,指甲里面藏肮脏”……那时用的都是繁体字,不过我学得倒挺有兴趣,不觉得太难。下学期难度进一步加大,思想性也加强了。我记得第一课的课文是:“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一夜就占领了沈阳城”,并且配有插图。老师认真讲解课文,使我们懂得了抗日的道理。
每周有一堂写字课,是我最喜欢上的。一年级的写字课不是用毛笔而是用铅笔写。每当老师拿着一个小小的长形布袋出现在课堂上,解开系着口袋嘴的线绳拿出一支支削好的铅笔发给同学时,我就兴奋不已,写起字来格外用心。下课时,老师把铅笔一支支收回,如待家珍般地放进小布袋留待下次用。边区的铅笔是一位爱国人士吴羹梅直运延安的,缓解了边区笔荒。

延安保小的學生在露天上课
1945年8月,毛主席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期间,会见了吴羹梅等几位工商界人士。毛主席一见吴羹梅就热情地说:“咱俩是老相识了!”吴羹梅很惊讶地说:“毛主席,咱俩是第一次见面。”毛主席从提包里拿出几支铅笔,笑着回答说:“咱们不是老相识吗?你创建的中国第一家标准铅笔厂生产的铅笔是我每天工作的好朋友。”吴羹梅这才恍然大悟。毛主席接着说:“谢谢吴先生两次共两卡车铅笔直接供应延安,按成本价使延安军民度过作战和学文化无铅笔的困难。”吴羹梅诚恳地说:“共产党的军队在抗击日军,这是我们炎黄子孙应尽的义务!”
铅笔那么珍贵并严格地控制在语文老师手里,珍藏在布袋里,除了写字课,平常是秘不示人的,更不要说使用了。其他课比如算术课做题,或者语文课学生字、写生字只能用石板、石笔。石板像块小黑板,平整光洁。石笔是用一种化石制成的,可在石板上划出道来,像粉笔能在黑板上留下痕迹一样。我们就是用石笔在石板上做算术题、写生字的,能省下大量的铅笔和纸张。不过,石笔得自己动手把较粗的化石磨成细条状才好用。即使如此,石笔有时也供不应求。

延安保小儿童图书馆管理员陈琳(右)在为学生借阅书刊
有一次磨完石笔后,我问旁边的一个同学:“你说,这化石是怎么来的?”这位同学回答道:“我听大人说,化石是由石头变的。把石头埋在地里,多少年以后就变成化石了。”我一听觉得挺神奇,并且是个简单易行的好办法,于是就建议:“那咱们就多找些石头埋起来,过几年就能变成好多化石,咱们就有的是石笔用了。”大家都同意,于是七手八脚找来不少石头,挖坑埋下,准备几年后收获化石。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一种童趣。
虽然当年陕北地瘠人贫,国民党又以重兵严密封锁,但党和政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尽最大可能对革命后代予以最大关心和爱护。吃饭不成问题,按季节发给服装,有病时有医生治疗,老师和保育人员又都很照顾我们。同学们都很团结友爱,亲如兄弟姐妹。
学校有个图书馆。我们一年级学生虽然识字不多,但也常到那里去借书,借的主要是有插图的儿童读物。从中读到的故事《吃枣枣》和儿歌《昨天晚上做了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吃枣枣》讲的是有个庸医自称专治牙病的“神医”,自吹自擂特别擅长治虫牙—能从长虫子的病牙中把虫子抓出来(后来发现是他身上藏着小小的虫子,给人治牙病时把藏在身上的虫子拿出来)。这样一来,牙病就能治好,病人的牙就不痛了。庸医就靠这套走村串乡骗吃骗喝骗钱财。有个儿童团长经过观察,识破了他骗人的把戏。嘴里含着一个枣枣装做很痛苦的样子去找这位“神医”。当“神医”从他牙里“抓”出一条不断蠕动的小虫并连蒙带吓唬群众的时候,儿童团长张开嘴使劲往地上吐出枣子,骗子的骗术被揭穿,灰溜溜地跑了。《昨天晚上做了梦》虽然篇幅不长,却最受同学们的欢迎。歌词是:“昨天晚上做了梦,梦见我在天上飞。飞呀飞,一飞飞到大前线,大前线鬼子多,我在天上喊口号,吓得鬼子蒙耳朵,我在天上撒泡尿,淹死鬼子几百多!”这首抗日童谣,短小精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活泼有趣、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充满抗日爱国激情,特别符合儿童心理,因而不胫而走,不管走到哪里,到处都是“飞呀飞”,好像同学们都做了一个共同的梦,都飞到了大前线。
老师还常领着班上的十几个同学走到延河上游,给我们讲故事。河岸大约有五六层楼高,河面很宽。老师给我们讲《洋铁桶的故事》,这大概是当时边区最为著名的一部小说,描写的是外号叫“洋铁桶”的抗日英雄的故事:“洋铁桶”和他的游击队战友,事先在母猪河高高的河岸上埋伏好,待一队日军在此涉水过河时,
“洋铁桶”一声令下,游击队居高临下猛烈开火,日军猝不及防,又陷于齐腰深的河水中,结果死的死伤的伤,很快被消灭。老师声情并茂、绘声绘色地讲着,充满激情,大大感染了我们,渐渐地把我们带进了故事中,使我们如同身临其境,仿佛眼前的这条河就是母猪河,我们都成了小小的游击队员,跟随勇敢无畏的“洋铁桶”居高临下,向河里的鬼子射出仇恨的子弹。
当年,我们都不知道老师讲的只是长篇小说《洋铁桶的故事》中的一段,更不会知道这部小说的作者是谁。直到后来,我才得知,这部小说的作者是柯蓝。《洋铁桶的故事》首先在延安出版,大獲成功,受到热烈欢迎,后被七个解放区用不同的七个版本印行。
后来,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给柯蓝写了封信,表达感激之情,着重写了当年老师给我们讲洋铁桶故事的经过。他不仅给我回了信,还将我写给他的那封信交给现代文学馆保存了。
我在保小学了一些歌,但记住的只有两首—说准确些就是一首零一句。“一首歌”的歌词是:“小小叶儿哗啦啦啦,儿童好像一朵花,生在民主解放区,唱歌跳舞笑哈哈,哗啦啦啦,唱歌跳舞笑哈哈。”“零一句”就是另一首歌中的一句—因为那是首讽刺希特勒法西斯的歌曲,对我来说歌词比较高深,我不太懂,因而歌词差不多都忘了,只记住其中一句歌词是:“他在世界上吃八碗!”多少年后,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才恍然大悟:那句歌词原来是“他在世界上逞霸王”—那是讽刺希特勒妄想称霸世界野心的,当年我不懂希特勒是谁,更不懂什么叫“逞霸王”,甚至连“世界”是什么也不太明白,再加上同学们都是满口地道、浓重的陕北话,以致让我误解了多年。待我理解时,只能哑然一笑。
我在保小只上了一年学,由于时间短、年龄小,不可能对母校有个全面、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留下的记忆只能是一鳞半爪、浮光掠影式的。即使如此,我的第一个启蒙学校还是给我留下不少美好、难忘的记忆,把我的人生一开始就引向正确的方向,扶我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影响了我一生。
(责任编辑 崔立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