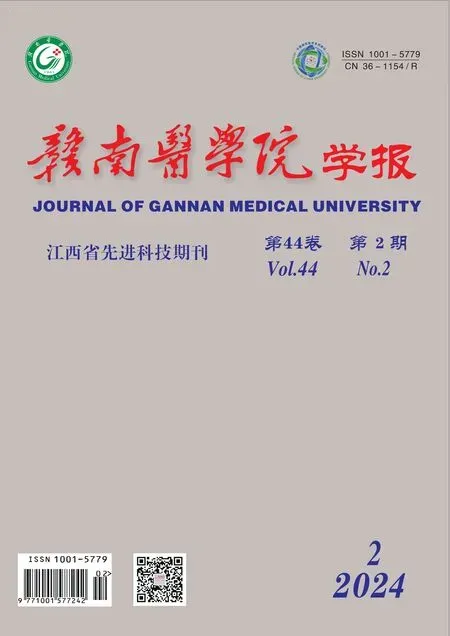炎症性肠病非侵入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胡 帅,谢 军
(1. 赣南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2. 赣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江西 赣州 341000)
众所周知,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炎性肠道疾病,主要分为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和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2 种类型[1]。目前,IBD 病因尚不明确,但广泛认为它是遗传易感个体中环境因素、微生物、感染及免疫反应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2-3]。在临床治疗方面,IBD 治疗目标是诱导和维持疾病的缓解,实现黏膜的愈合,进而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对IBD 患者治疗效果的准确评估对于制定和优化治疗策略至关重要。目前尚无单一“金标准”可评估IBD 患者的治疗效果;治疗效果的判断通常需要综合疾病活动指数、内镜以及病理学检查等多种指标[4]。近年来,无创检测的研究及开发为评估IBD患者的疾病状态和治疗效果提供了可重复量化的手段。探索新型的无创性生物标志物对于临床中评估治疗效果、减少药物不良反应、优化个性化治疗策略,以及早期识别IBD 疾病活动和缓解状态具有重要意义[5]。本文对IBD 无创性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血液生物标志物
1.1 富亮氨酸α-2 糖蛋白富亮氨酸α-2 糖蛋白(Leucine-rich alpha-2 glycoprotein,LRG)是一种富含亮氨酸重复结构域的微量蛋白,最初由HAUPT H等[6]于1977年在人类血清中识别。随后,TAKAHASHI N等[7]在1985 年对LRG 的结构进行了完善,发现其由1 个半乳糖胺基团、1 条多肽链和4 个葡萄糖胺寡糖组成。LRG 的来源及功能目前尚不明确,但TAKAHASHI N 等[7]研究表明,LRG 对中性粒细胞分化具有特异性,早期粒细胞分化的细胞因子,如TNF-α、IL-22、IL-1β 和IL-6 可刺激并诱导LRG 产生。进一步研究表明,在炎症反应中,LRG 扮演着重要角色。SHIRAI R 等[8]发现,IL-6与TNF-α在UC患者中可协同促进LRG 表达。LRG 还可以通过影响TGF-β 信号通路,参与炎症介质的表达,进而促进肠道炎症的发展。近期研究进展表明,在诸如系统性红斑狼疮、风湿性关节炎、炎症性肠病及恶性肿瘤等疾病中,LRG 水平呈现上升趋势。SHINZAKI S 等[9]进行的一项纳入129 例UC 患者的研究中,发现UC 患者血清LRG 浓度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且活动期UC 患者血清LRG 水平显著高于缓解期患者。SHIRAI R 等[8]研究发现,当UC患者接受生物制剂治疗后,若LRG水平降低超过30%,这些患者的疾病通常不会有明显的进展,这揭示LRG 作为一种潜在的监测生物标志物,可能具有替代内镜预测UC疾病活动和复发的诊断价值。
1.2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中性粒细胞(Neutrophils,NEU)是与肠道慢性炎症相关的免疫效应细胞,而淋巴细胞则是传统炎性标志物。中性粒细胞作为最先到达IBD 炎症位置的免疫介质,引起细胞炎症和组织损伤。研究表明,中性粒细胞在IBD 的病理生理中有2 种不同的功能:其一,黏膜损伤时初期中性粒细胞聚集,另一方面, NEU 产生的抗炎因子既能够维持肠道的内环境稳态,也能够保护肠道黏膜免受微生物损害[10]。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是机体炎症反应的有用标志物[11]。近年来有相关研究表明外周血NLR 与IBD疾病活动存在相关性。FU W 等[10]进行了一项荟萃分析,包括2 185 例IBD 患者和993 例健康人群对照。在这项研究中,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IBD 患者的血液NLR 显著增加,更重要的是,活动性IBD患者表现出比缓解期患者更高的NLR,这表明NLR可以作为预测IBD活性的有价值的生物标志物。
1.3 血清总胆红素传统上,血清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被认为是血红素(Hb)降解的最终产物,并且在高浓度下具有细胞毒性。研究证明这种铁卟啉的代谢物在生理浓度下具有抗氧化和抗炎作用[12]。在溃疡性结肠炎的动物模型中,血清非结合胆红素(通过腹腔内注射给药)对葡聚糖硫酸钠诱导的小鼠结肠炎具有保护作用,其机制是通过减少白细胞浸润和维护氧化还原稳态,这一研究结论为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13]。SCHIEFFER K M 等[14]进行了一项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发现UC患者的TBIL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同时LENÍČEK M 等[15]发现克罗恩病患者的TBIL 水平也较低,并确定这可能是由于炎症介导的氧化应激增加,而非遗传易感性。一种可能是肠道炎症和免疫反应的增加也可导致血清Hb 水平降低,从而导致具有严重疾病活动的IBD 患者的TBIL 水平降低。但也有学者指出部分UC患者血清Tbil水平偏高,因此仍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持。
1.4 中性粒细胞与白蛋白比值中性粒细胞与白蛋白(Albumin,ALB)比值(Neutrophil percentage-toalbumin ratio,NAR),这是一个新发现的指示全身炎症的指标,是结合血细胞计数和血清生化指标的信息参数的指标,已被用于炎症评估、血管疾病和癌症[16-17]。有充分的证据表明,IBD 患者的血清ALB水平较低,且低蛋白血症可能会降低生物制剂的治疗效果[18],虽然ALB也可能是IBD的敏感标志物,但ZHOU Z 等[19]的一项随机对照研究表明,与健康对照组对比,CD 患者的NAR 显著增加,且NAR 与CD活性和炎症负荷呈显著正相关。同时NAR 和单独使用NEU 或ALB 的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5、0.78 和0.79,说明NAR 比单独使用NEU 或ALB 的诊断效能更高,表明NAR 可能是克罗恩病诊断的有用生物标志物。
1.5 微核糖核酸微核糖核酸(miRNA)是一种单链非编码RNA,是17~25 个核苷酸小RNA 之一[20]。在各器官中都有广泛表达,它上调UC 的免疫应答,并参与UC 向结直肠肿瘤的进展[21]。据报道,miRNAs 可作为诊断和监测UC 的有效生物标志物;例如,miR-21和miR-29a在活动期UC患者中的表达显著高于IBD 患者和非IBD 患者,其特异性分别为92%和100%[22]。此外,循环 miR-375 在UC 患者中的表达高于CD和非IBD患者[23],证明其作为诊断标志物的可能性。此外,BATRA S K 等[24]指出miRNA对治疗反应也有预测的可能。
1.6 细胞因子肿瘤抑制素M 及其受体细胞因子肿瘤抑制素M(Oncostatin M, OSM)是一种生长调节剂,可抑制多种肿瘤细胞的生长。它调节细胞因子的产生,包括内皮细胞衍生的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和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25-26]。与健康对照组相比,IBD 患者在炎症肠道组织中表达更高水平的OSM 细胞因子及其受体(OSM receptor,OSMR),且OSM 水平与组织学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有报道,OSM 可以预测抗肿瘤坏死因子α 抗体的疗效,治疗前血浆OSM 水平低的患者在使用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后1 年的临床缓解率显著高于治疗前[27],而血浆OSM水平高的患者抗肿瘤坏死因子α抗体的失应答率更高。此外,在动物模型中,治疗耐受的OSM 缺失IBD 小鼠的炎症反应和结肠炎相比野生型更少。OSM 基因缺失或药理学阻断作用可显著减缓结肠炎的进程[28-30]。因此,OSM 有可能作为诊断和预测疗效的候选生物标志物。
1.7 抗整合素αvβ6 抗体整合素全称为细胞黏附分子的二聚体细胞表面蛋白,包括α 链和β 链,存在24 种链组合[31]。 αvβ6 蛋白是其中一种受体,它构成维持组织结构的细胞外基质网络,在上皮细胞中表达,并参与维持上皮屏障的功能[32]。抗整合素αvβ6 抗体被认为是一种抗上皮细胞黏附分子的自身抗体。抗整合素αvβ6抗体在UC患者中的阳性率极高,为92.0%,而健康人为5.2%。诊断UC的敏感性为92.0%,特异性为94.8%。此外, αvβ6 抗体滴度与Mayo评分呈正相关[33]。因此,它有望被作为监测IBD活动的标志物。
1.8 C 反应蛋白与白蛋白比值(CAR)C 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是一种与肺炎链球菌的C 多糖发生反应的急性期蛋白。它在肝脏中由IL-6刺激产生,在体内随着炎症而增加,通常用于炎症性疾病的评估[34]。目前有研究表明CRP水平与IBD患者之间存在相关性,在使用抗肿瘤坏死因子-α 抗体或维得珠单抗的几项随机对照试验中, CRP 水平降低与短中期预后较好相关[35-36]。然而,基线水平的CRP 值是否能预测治疗反应仍存在争议。血白蛋白浓度通常是反映机体的营养指标,低白蛋白水平说明营养不良。KHAN N等[37]指出,疾病诊断时低水平的白蛋白可以预测UC的临床病程。CHEN Y H等[34]在对275 例UC 和601 例CD 患者进行的随机对照研究中发现CAR 与IBD 免疫系统疾病活动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相关性。确定UC 中具备生物活性的CAR 比例的最合适临界状态为0.18,灵敏度高达67.8%,特异度为86.7%。LIU A 等[38]在IBD 生物活性基本指标研究内容中也证实,CAR 可用于鉴定大多数IBD患者免疫系统疾病的生物活性。CAR水平提高表明IBD 活动可能提高。评估UC 生物活性可能比CD 更具价值。因此从某种角度看来,这对于判断IBD的活动性和预后不可或缺。
2 粪便生物标志物
2.1 粪便钙卫蛋白钙卫蛋白是一种钙结合S100蛋白家族A8/A9复合物,在肠上皮细胞的细胞质、粒细胞和单核细胞中含量最高[39]。粪便钙卫蛋白(Fecal Calprotectin,FCP)是指检测粪便中钙卫蛋白的水平,在机体炎症时,炎症细胞可以渗透到肠黏膜使其受损,并释放出钙卫蛋白,最后与粪便相混合[40]。由于检测针对的是粪便成分,故不易受全身炎症的影响,因此FCP 在评估肠道炎症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2.2 粪便免疫化学检测粪便免疫化学检测(Fecal immunochemical test,FIT)是通过一种特异性的抗人血红蛋白抗体检测粪便中所含血红蛋白浓度的方法,目前被用来筛查结直肠癌。与传统的粪便潜血试验相比,FIT 具有灵敏度、特异性高的优势,因此在传统的愈创木脂法中,用于检测粪便中潜血的方法是基于对过氧化物酶活性的间接测量。由于许多食物含有能催化反应的非血红蛋白过氧化物酶成分,这种方法可能导致假阳性结果。虽然FIT 在结直肠癌的筛查中显示出较高的排阴效能,但其在识别癌前病变或早期的异型增生方面的能力相对较弱,如SHAUKAT A 等[41]发现,FIT 识别结直肠癌敏感性为74%,但其识别高级腺瘤病变时敏感性仅为24%。因此,在监测IBD 患者中的肿瘤风险方面,单依赖FIT 进行评估可能不足以发现肿瘤癌前病变,常需联合其他方法,如结肠镜检查等。鉴于FIT 可以直接反映肠道黏膜出血情况,而UC 主要表现为反复结直肠出血,故还被研究者用来评估IBD 患者黏膜炎症程度。在UC 患者中,肠道炎症首先表现出黏膜充血水肿,最后黏膜被破坏导致出血。在治疗后达到临床缓解期的患者中,阴性FIT(即没有检测到结直肠出血)的发生更为常见,这通常被视为黏膜愈合的良好指标。而且研究者发现FIT与FCP联合应用时,可以更好地预测IBD的疾病状态,进而及时进行临床决策。
3 体液生物标志物
3.1 前列腺素E-主要尿液代谢物在慢性炎症过程中,花生四烯酸经历一系列级联反应,其中由磷脂酶A2 催化作用,从细胞膜磷脂中释放出来。随后,在环氧合酶和前列腺素E2合成酶的参与下,花生四烯酸转化为前列腺素E2(Prostaglandin E2,PGE2)。PGE2 作为一种重要的化学介质,具有促进和抑制炎症的双重作用。已有研究证实,在黏膜炎症的情况下,IBD患者的PGE2水平会显著增加[42]。PGE2主要通过肝脏和肾脏代谢,然后从尿液中排出。其主要成分是前列腺素E-主要尿液代谢物(Prostaglandin E-major urinary metabolite,PGE-MUM)。研究发现,作为炎症标志物的PGE-MUM 在多种疾病中的水平有所不同。在UC 患者中,PGE-MUM 的水平呈现上升趋势[43]。进一步研究表明,高水平的PGE-MUM可能与某些慢性肠病有关,这些疾病可能由前列腺素E2 转运蛋白的遗传异常引起[44-45]。此外,PGE-MUM水平的上升不仅限于肠道疾病,间质性肺炎患者中PGE-MUM 水平升高也支持了这一标志物在不同炎症条件下的普遍相关性[44]。ARAI Y等[43]研究中,发现PGE-MUM 水平与Mayo 内镜评分(Mayo endoscopic score,MES)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这一发现对于评估疾病活性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当MES<1 时,PGE-MUM 对疾病活动的诊断效能高达0.98,高于CRP的0.96。这表明在轻微疾病活动的情况下,PGE-MUM 是一个更为敏感的指标。进一步分析,当MES=0 时,PGE-MUM 的AUC 值为0.90,而CRP的AUC值为0.77。这一结果再次证实了PGE-MUM 在诊断疾病活动方面,特别是在轻度活动时,相较于CRP 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敏感性。此外,PGE-MUM 还可以用于评估内镜下缓解、组织学缓解和完全内镜下黏膜愈合(Mucosal healing,MH)。即便在临床缓解的患者中,PGE-MUM 也显示出其在评估上的有效性[45]。PGE-MUM 的诊断能力,在内镜缓解、组织学缓解以及MH 方面,与FCP 和FIT 相媲美。然而PGE-MUM 值在UC 各表型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研究还指出,随着IBD 患者疾病严重程度的加剧,PGE-MUM 水平亦相应升高[46]。关于PGE-MUM 预测疾病复发方面,有研究表明,在缓解期的患者,如果在特定时间点检测出较高的PGE-MUM 水平,这些患者后续出现疾病复发的风险显著增加,这项发现强调了PGE-MUM 在监测疾病活动及预测未来疾病走向方面的潜在价值[47]。因此,它有望成为监测IBD 疾病活动的标志物,但仍需大型的前瞻性研究来佐证。
4 总结
综上所述,IBD 是一类病因未明、可反复发作、难治的慢性肠道炎症性疾病,其特征为临床表现多样,疾病进展多元化和治疗棘手。鉴别IBD 和非IBD 需要依靠多次结肠镜检查、病理学和影像学结果,患者依从性差,耗时及经济花费高。无创性生物标志物的检测对协助诊断和鉴别诊断、评估疾病进展、疾病类型、预测并发症和预后转归等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已有标志物当中,C 反应蛋白及血沉使用最为普遍,但其敏感性与特异性还不高,临床价值受到限制。其余新近发现标志物大多主要是对CD 临床行为进行诊断与预测,而应用于UC 研究的生物标志物很少。这些新型标志物在临床上是否实用,检测方法是否稳定及成本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验证与判定,以最终服务于临床。但对IBD 发病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寻找新标志物,使其能广泛应用于临床,仍然是未来继续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