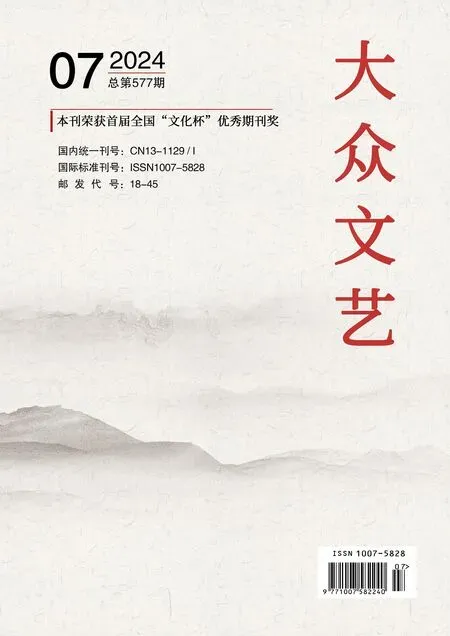论清末民初书法泛文化传统之变
牛苏杭
(郑州大学书法学院,河南郑州 450000)
艺术根植于文化而生新演变,因文化的生长、更新、衰亡而不断进行着自身内部规律的调整。民国时期内忧外患、时局动荡,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经济、科技、思想等文化共同充斥着20世纪的中国,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提出,以儒学为代表的古典文化被当时的社会思潮冲至角落。因此古典诗词、戏曲、国画、书法等根植于传统文化的艺术门类面临着生存空间的急剧变化,一些传统艺术形式如京剧、昆曲正在逐步走向流失,而同样身为古典文化之一的书法,却能够在泛文化传统的裂变中找到自身发展的方向。
一、书法“器用”之变
(一)现代书写工具的出现
现代书写工具包括钢笔、圆珠笔、铅笔、粉笔等具有较硬质地的物质材料,尤以钢笔为代表。钢笔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传入中国,随着国内报纸行业、图书出版商对钢笔的推销,以及国内生产商对国产钢笔的大力倡导,人们在日常生活领域中使用钢笔的频率逐渐超过毛笔,在一些正式场合如学校考试、政府决策、外交事务等领域,人们对钢笔的使用意识甚至超过了毛笔,“如果在现在这时候学习写字仍和从前一样,只用软笔不用硬笔,实是一个大大的错误。”[1]从普通民众到官方政府,钢笔凭借自身书写简易、流畅的巨大实用性获得了官方承认,并最终取代了毛笔的主导地位。
(二)传统书法实用性的衰退
传统书法自诞生之日就承担着记录汉字、传递信息的功能,实用性是其最主要、同时也是最先承担的任务。传统书法的实用性主要体现为以记言述事为主的传播功用和以承志载道为主的社会功用。
毛笔在古代社会作为最广泛的书写工具,承担了大部分实用目的性的书写任务,《释名·释书契第十九》云:“笔,述也,述事而书之也。”[2]在一些正式场合如政府颁布公告、律令或纪功述史,其文字内容多以整饬严谨的书法形式得以向历史呈现,如先秦时期的金石铭文、简帛盟书记录国家重大政治事件,秦汉至魏晋的墓志、摩崖等石刻文字记录国家制度沿革以及民族、地区间的历史事迹,唐宋至明清在科举制中对书法整齐、美观的要求也反映着传统书法实用性的因素。魏晋雕版印刷术出现以前,古代典籍的保存与传播依托的也是毛笔抄录的形式,并衍生出一批专职抄书的社会群体。普通民众的日常书写则以信札、尺牍的方式传情达意、遣兴抒怀。随着社会历史进程的不断加深,人们对于文字书写的速度与准确有了更高的要求,继而整个书体演进的过程呈现出“趋易避繁”的特征,“汉字由隶而真、行、草,日趋的省便和快速构成以实用为前提的书法史中字体演化的基本逻辑。”[3]
受儒家功利主义文艺观的长期影响,传统书法的实用性还体现为以承志载道为主的社会功用。古代士人将文章视为经国治道的“不朽之盛事”,书法作为文章的载体自然也成为士人立功树言的必行之途,是用以“明道”的手段。明大道即“厚人伦、美教化”,通过书写儒家相关典籍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影响书写者的思想观念,以达“化人”之目的;明小道则书其才志、显其名望,“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4]优秀的书法作品不仅能够反映书者的志学与人品,也可为其建功显名。善书可作为一项进入仕途的技能,与政治相结合为书者带来个人名誉与社会地位,据南朝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列举的书家名录可知,自秦代至魏晋,位高权重者多善书,且书法名重一时者多为后人所效法,“陈留蔡邕,后汉左中郎将。善篆、隶,采斯、喜之法,真定《宣父碑》文犹传於世,篆者师焉。”[5]而唐宋至明清的科举制,书法为士人立身行道、扬名显世的功用更是愈发彰显。钢笔等现代书写工具的出现改变了过去毛笔在书法实用领域的主导地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兼用钢笔与毛笔。鲁迅、朱自清等人都主张在教育普及过程中应当使用钢笔,以节省时间加快国民素质发展,毛笔则可在专业书画家群体中继续保留。文人书家为鼓励钢笔的使用进而对其作出书写规范,如邓散木与白蕉合著的《钢笔字范》汇集二人钢笔所作的楷、隶、行、草,以详尽的笔触和精谨的结构为时人学者示以明灯。书法的内涵因书写工具的拓展而得到了新的外延,钢笔字逐渐成为有别于毛笔字的现代书法形式。
钢笔的普及直接减少了知识分子的毛笔书写实践。在中小学课堂上,书法多以国文课为依托、以实用为目的向学生普及汉字而非审美教育,由钢笔书写的硬笔规范字便成为其主要传播形式,尤其在数理化、外语等课程中,为适应现代知识体系、提高学生学习效率,钢笔等现代书写工具甚至完全取代了毛笔的使用。毛笔使用范围的缩减改变了过去士人无不工书的局面,造成了传统书法与读书者之间的隔阂,进而影响知识分子对传统书法技艺纯熟度的把握,另一方面,钢笔与现代教育的结合使得传统书法为旧时期士人学子入仕显名的社会功用不再。新兴知识分子借鉴西方道德对传统道德进行“淬厉其本”“采补其无”的现代化转换之后,便不再将读书致仕作为唯一的理想抱负,而是投身于科学、文化等新兴知识行业,他们在向知识本身回归的过程中不断实现着自身的个体价值,书法在知识分子眼中更多的是“达其性情”的艺术表达而非“达其志向”的政治手段。
(三)传统书法审美性的进一步自觉
从书法史的整体进程来看,传统书法的审美性与实用性几乎是相伴相生的状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所侧重,总体而言,汉字的逐步可识化与书写工具的简便化推动书法实用性渐趋减弱而审美性不断加强。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将文字的生成类比为物象之本,进一步认为书法是文字的外化。因此,汉字的“依类象形”构成书法审美表现的基础。从原始刻符与图画文字到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汉字的可识性逐渐加强,与汉字异名实体的书法在完成了信息传达的实用任务之后便开始了审美意识的逐步觉醒,这在东汉末年出现的由隶书快写而产生的章草演变中尤为明显,崔瑗、杜度与张芝等人在闲暇之余以无意识的状态创造出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草书作品。在魏晋雕版印刷术出现以后,书法的实用与审美开始走向分离,并出现了注重书写艺术性的一流书家群,如西晋的卫、索、陆氏以及东晋的郗、庾、谢、王氏,传统书法的审美意识开始走向自觉化的阶段,而清末民初现代书写工具的出现则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
书写工具材质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传统书法的审美特性能够发生于毛笔挥运之下的线条形态转变之中。王羲之创作的《兰亭序》使用的是笔锋尖细的鼠须笔,通过赋予毛笔以开合、使转、疾走的连续运动,将天资与功夫的注入笔锋,使得笔下线条细则如游丝,壮则如磐石,唐代何延之评其:“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6]不论是古朴稚拙抑或是清雅流利的书风,都是不同方法之下笔锋使转的结果。继书写的实用性被钢笔所取代,传统书法便有了在审美意义上更加自觉化发展的可能。
审美是书法艺术的生命所在,历史上数次书法艺术发展的高峰都与其审美自觉意识的高涨相关,汉代崔瑗《草书势》从审美角度描述了草书“志在飞移”“将奔未驰”的动态美,赵壹《非草书》以“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7]的实用角度批评了当时以钻研草书为务的现象,这种在汉末发端于草书的书写审美意识在魏晋玄学兴盛之际,由王羲之变古质为今妍而走向全面自觉,至唐宋臻于完善,直到明清随着科举制度中书写要求的僵化而逐步受到裹挟,书家开始从篆隶古文字的形态中挖掘能够振发书法活力的审美要素。实用与审美的二重性一方面使传统书法得以绵延至今,另一方面二者的冲突也制约着书家创作时审美意蕴的抒发,如颜真卿的楷、行书写状态就截然不同,其楷书多为公文记事之用,须整饬流畅,米芾评其楷书:“颜真卿学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成之趣,大抵颜柳挑踢,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无遗矣。”[8]而颜真卿的行书多为日常信稿所写,人格学养与功夫资质全然流露其间,米芾评其《争座位帖》:“此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9]易辨易识的实用要求始终是制约书法艺术化表现的因素,因此,现代书写工具代替毛笔承担了这一实用性要求,人们面对传统书法不必将其局限于点画的一招一式,而更能将毛笔书写作为一种艺术化的恣意抒发。
二、书法“文本”之变
(一)白话代文言
文言与白话作为汉语的两种书面表达方式在南宋以后逐渐异其途辙,章太炎认为文白之别在于言辞修饰与否,“其所分者,非白话、文言之别,乃修饰与不修饰耳。”[10]文言重修饰的特性使其发展至晚清逐渐脱离民众日常,且自身的古汉语结构也使其无法容纳西方的新进概念。从清末民初维新派提出“言文合一”到五四运动知识分子的“文学改良”,白话文逐渐代替文言文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通用的书面语。
(二)文言与书法的一致性
传统书法艺术的构成离不开其“文本”内容与自身的表现形式,历代优秀书法作品无一例外都是“文笔双美”的典范,如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苏轼《黄州寒食帖》等,并且书者大都也是文学家。文学与书法内在的一致性来源于古典诗文的韵律感以及书法作品中笔墨、布白的节奏感,唐代张怀瓘在《文字论》中类比了文与书的关系:“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可谓得简易之道。”[11]文言文通过简省词类、协调声韵形成“数言”的形式,书法则以直观的笔墨线条和灵活的布白完成“一字”的表达,此为二者精简之共通;文言文以“数言”的形式凝练丰富的语意,形成严密简洁的“微言大义”式表达,而书法“一字”之间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意义与书家个人的情志,此为二者载道之共通。因此,形简意丰的共通性使得古典诗文与书法天然地契合,历代经典书法作品在极具艺术价值的同时,也具备文辞流美的阅读性,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
(三)白话与书法的冲突
“对书法作品文本的评价是书法评论标准建构的根本。书法作品文本包括形式与内容两大方面。”[12]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则破坏了书法作品文本的综合审美效应。首先,白话文将古汉语中大量的单音节词转化成了双音节词,并且以西方语言的词、句之法对文言文进行语义修饰与形式扩充,汉语的书面表达由过去的“铺陈直述”转向“严密繁复”,这就使得书法作品的书写内容变得烦琐冗长而缺乏节奏感。古典诗词歌赋以形音义一体化的汉字为基础单位,注重词句的对称、精练以及语篇的排布,由此形成古典文学特有的简洁、韵律之美,“文学语言尤其是中国的古典诗词对语音的高低、强弱、长短等方面的强调,可使人“诵之如行云流水,听之如金声玉振”,从而表达出起伏跌宕的情感。”[13]因此古代士人常以诗歌的吟咏兴会来抒发个人情感。书家进行创作时通过对书写内容的吟诵体悟将古典诗文的韵律转化为书写节奏的起伏变化,进而影响整体作品的流畅自然性。当书写内容变为“严密繁复”的白话文时,这种“文”与“书”相生相成的和谐之美无疑被破坏了。其次,白话文为求语言的通俗易懂,在对古汉语词义进行转换、更替时会发生词义范围的缩减或讹变,“且如‘勇士’‘贤人’,白话所无,如欲避免,须说‘好汉’‘好人’。‘好汉’‘好人’究与‘勇士’‘贤人’有别……以此知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14]因此白话文易使汉语表述粗浅,削弱文学内容的含蓄隽永之美,而书法在古代的皇家贵族、仕宦群体中是雅文化的象征,与文辞雅美的诗词曲赋相得益彰,如张怀瓘《书断》所云:“文章之为用,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乎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乎书。”[15]因此以语意粗浅、模糊的白话文为书写内容会影响书法作品格调的高低。
不论是白话文还是文言文,都属于汉语的书面形式,是书法创作的文字材料。从大量民国时期文人信札手迹中就可以看出,不管是日常书信、公文,还是带有文言因素的新体诗歌,书家将白话文的书面语和信札的形式相结合,依然能够创作出率真洒脱而颇具意蕴的书迹,与前代条幅、尺牍、中堂、楹联等形式相比,这种规格小巧而内容充实的信札书法更显时代新意,近可于掌中细细品鉴,远可于案头悬挂欣赏。因此白话文的书写内容依然存在与书法相结合的艺术空间,书法“文本”的古今之变一方面切断了书法与古典文学之间紧密关系,另一方面也使得传统书法能够以新的文字材料表现时代气息,这为现代书法创新提供了可能。
三、结语
现代书写工具的出现与汉语结构的古今之变为书法带来泛文化领域的改变,钢笔的普及使得书法的实用属性与审美属性进一步走向分离,一方面减少了传统书法中以实用为目的功能性呈现,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知识分子与传统书法的距离。白话文的普及使得书法创作的文字内容“去雅入俗”,进而影响书法作品的整体审美表现,但现代语言的灵活性与特定的书法形式相结合,又为现代书法的文本创新开辟了一定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