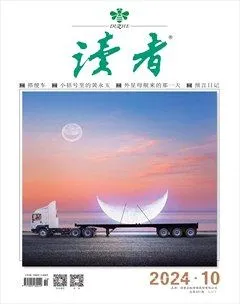出走的故事
申赋渔

小学毕业那一年暑假,我被父亲毒打了一顿,无法承受,便离家出走了。这次出走,对于家人和我,都是猛烈的震撼。
半夏河是一条人工河,当年为修河挖出的泥土就堆在村西南的河边上,沿着河,形成一座绵延几里的土山。
放了暑假之后,我和小伙伴们每天午饭之前,挖满一篮子猪草,就来这里玩“打仗”。
村里的大人们在小土山旁边的田地里干着农活,农活结束了,就喊自家孩子回家。
这一天父亲来喊我,我正大呼小叫玩得起劲,父亲喊了好几声,我完全没有听见,还在乱跑。忽然大家都停了下来,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我回过头,父亲已经到了我的身后,他扯着我的耳朵拉我回家。
走了好几步,我用力掰开他的手指,跑开去,找到我装猪草的竹篮子,飞一般往家跑去。
当父亲喊着正在疯玩的我,我完全没有听到的时候,有人挑拨着易怒的父亲说:“你看,儿子大了,管不了了吧?”在我挣脱父亲,一个人跑掉的时候,他们又哄笑起来,父亲觉得失了面子和做父亲的尊严。
我回到家的时候,父亲也回来了。他进了屋子,从里面拿出一根绳子,使劲地抽在我的身上,大声吼道:“叫你玩!叫你不听!叫你跑!”喊一声,抽一下。
我站直身子,不动,也不说话,任他鞭打。
不是我的哭喊声,我没有哭喊,而是父亲的咆哮声引来了邻居。有人抢下父亲手中的绳子,有人把他拉到了旁边。有人说:“你看这孩子多犟,跟你爸认个错不就好了?”我手里还拎着小竹篮子,沉默地站着。父亲被邻居拉走了,人群散去。
背上火烧火燎地痛。我用手摸了一下,一道一道的鞭痕已经肿了起来,我转身离开了家。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我只是想离开家。
我沿着半夏河朝东北方向走出申村,一直走到高庄的那座大桥上。大桥下停着许多船,我站在桥上不停地淌着眼泪——那个打我的人,是我的父亲——我不能对抗他,我能做的,只有逃跑。
我不能总在这桥上站着,我要走,走得远远的,走到谁也不能打我骂我管我的地方。我沿着河边的路一直往北走。天渐渐黑下来。虽然背上依然疼痛,心里的愤懑却渐渐消退了,我开始想我该去哪里。我十一岁,小学刚刚毕业,我没有吃的,也不知道晚上能睡在哪里。未来对我而言是黑色的,是可怕的,可是我宁可走进这个黑色当中去。我走了几十里路,没有回过一次头。
半夜了,我还在走,沿着河边。四周是旷野,最近处人家的灯光已经不见了,河上也看不到船。偶尔会听到风里传来奇怪的声音。脚被磨得很疼,我把鞋子拎在手里,光着脚走在路上,越走越慢,影子越拖越长。
下半夜的时候,身后骑来一辆自行车。车子越来越近,骑车的人用手电筒照着我,我回过头,是我的邻居铁头。
全村人都出动了,听到消息的亲戚们也出动了,人们去四面八方找我。有人说在高庄的桥上见过我。人们又从高庄的桥往各个方向去寻找。铁头沿着河,一路追了下来。
我不肯跟他回去。他说:“要不,送你到俞庄舅舅家吧,你哪天想回去了再回去,不想回去,就住着。”
整个暑假,我就和小舅舅住在搭在旷野的瓜棚里。这一大片西瓜地很少有人来。小舅舅给我找来一本破旧的《水浒传》,我就一遍又一遍地看。累了,就到田地里走走,或者卷起裤腿,站在旁边小河的浅水里,看小鱼游来游去。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根线牵着我了。
三十年之后,父亲常住南京,和我们住在一起。我有了女儿。女儿的小名叫“唱唱”,在南京仙林读小学,一周才回来一次。本该是我去接她的一个周末,因为有事,就请父亲去校车的停靠点接她。
他是坐公交车去的,下车之后,却怎么也找不到校车的停靠点。父亲借了别人的电话打给我,放下电话,我就火速赶过去。
天下着雨,我刚到接送点的对面,校车就到了。雨越下越大,家长们撑着伞,拥在路边等校车停稳。乱糟糟的人群当中,我看到了父亲。他没有打伞,也没有戴帽子,满头白发湿漉漉地贴在头上,踮着脚,紧张地盯着缓缓打开的车门。唱唱终于出现了,父亲挤过人群迎上去,满脸都是欣慰的笑容。他一手接过唱唱的背包,一手把拿在手里的帽子戴上,打开伞,罩在唱唱的头上。这时候,我也走到了他们旁边。
“爸,下这么大的雨,你怎么不打伞,帽子也不戴?”
“我怕唱唱看不到我。”
父亲用衣袖抹了抹脸上的雨,领着唱唱往前走。他左边的肩膀已经完全露在雨中,但他还在把伞向唱唱倾斜。
父亲是和母亲一起来接唱唱的。明明我告诉他的站名是对的,可是公交车停下来,却不是校车停车的地方。他让母亲守在原地不动,自己往回走,边走边问人。
等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找到了校车停车的地方,也终于接到了女儿。然后,我们又去接我母亲。可是到了母亲本该站立的地方,母亲又不在了。我心急如焚,父亲也急得手足无措。南京对母亲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而且,母亲不会说普通话,又不识字,丢了就真不知道她会到哪里去。
父亲气得直骂:“让她在这里一动不动,等我回来,她不听。随她去,丢了就丢了,丢了就丢了。”说着,声音已经颤抖起来。
唱唱不停地问:“奶奶呢?奶奶呢?”
我们又沿着路边往回走。雨不大,可是一直下着,父亲这时候还用伞把唱唱护得好好的,我和他的全身都已经湿透。走了一里多路,我看到前面十字路口有人站在那里踌躇着,看背影像母亲。我飞快地跑过去,到面前一看,果真是她。
母亲浑身上下湿透了,脸上也全是雨水。她担心父亲一个人找不到唱唱,也一路找过来,完全忘了自己会迷路。唱唱朝她跑过去,她连忙喊:“不要跑,下雨呢,待在伞底下。”
父亲和母亲把唱唱夹在中间,用伞罩着她一个人。
在一个屋檐底下等车的时候,看着他们又高高兴兴地向唱唱问这问那,我的心里变得暖和起来,仿佛女儿就是小时候的我。我就想,如果能把这个情景拍成照片,寄给三十年前的我,就好了。
我就不会那么孤单、那么伤心了。
(悉 知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半夏河》一书,刘程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