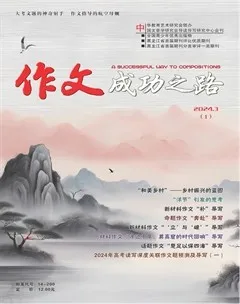她的黑绒裙
郭苏瑶
那是我第一次见她。
仿佛为她的回眸一笑而惊心动魄的不是沃伦斯基,因她身着黑绒裙、在人群中优雅从容而痴迷的不是吉娣,为她难掩的活力与热情而倾尽所有的不是那些伯爵与夫人——他们都不复存在——只剩我,贪婪地享受她所有的光辉给予我的震撼。
那是我第一次见她,却不得不承认,我已为托尔斯泰笔下最美丽的人物所折服。她在尚且年幼的我的心中,烙下了独一无二的印记。
但很快,我逃走了。
我已经记不清那是炎热的午后,还是微风拂面的傍晚,我躺在床上,准备将《安娜》的剩余情节看完。可很快,惶恐、震惊与恐惧在书页即将见底的那一刻包围了我——她选择在火车下结束自己的生命。直到火车来临的前一刻,她才惶恐地惊起“我在做什么”。可一切都已无法挽回。所有人为她的死而悲悯,沃伦斯基为她的死而撕心裂肺的结局已成命定。我静静地合起书,将它推到一旁,且自此很长一段时间都再没有翻开过它。
因为她美丽的身躯与灵魂在车轮下破碎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告诉我,我的心也同她一并破碎了。
那時的我尚且年幼,内心对一个美好形象的所有憧憬在一瞬被撕裂——这是莫大的冲击与多么残忍的惩罚!当时的我如同那些责问托尔斯泰“为何给安娜安排如此悲惨的结局”的读者一般,心中充满斥责与愤慨,更多的是悲伤与无奈。
过去了多久?半年,还是一年?当我在某个偶然间再度想起那个牵动着多少人心的灵魂,我就知道是她在催促我重新翻开那本书,重新拥抱一次,她那孤独而美丽的灵魂。
我深吸一口气,又读《安娜·卡列尼娜》。
于是莫斯科的凛冬又在我眼前降临,她再一次从列车上优雅自若地走下,再一次对擦肩而过的沃伦斯基勾唇轻笑……而我仅是站在她的身后,心中的炙热未退,只多了几分坦然与释怀。
我后知后觉——这不是作者刻意展现的艺术效果,而是一个切实的时代悲剧,一个在“封建”与“转变”的碰撞下诞生的时代悲剧。正是这样一个“一切都不同了,一切都颠倒过来了”的时代,安娜纯洁美丽、勇敢追求爱情的灵魂之火终于在新思想的冲击下被点燃。然而,她终究站在大环境的对立面,站在那个“尚在黑暗之中”的俄国社会的对立面,点点星火并未让她的人生绽放绚丽的火花,却最终让她引火自焚,以自我了结的悲歌收尾。她最后流下的泪水,我想,是在控诉这场“自挖自埋”的爱情,也是在控诉这个残忍、冷漠而满是罪恶的社会。
托尔斯泰曾说,她是可怜的、可爱的,也是可恨的。可我无法恨她,更无法不同情她,怜惜她,甚至是爱她——我也不得不赞叹作者惊人的写作手法,足以让一个人物,一个灵魂,在我心头不断徘徊,乃至永恒。我多想与她对视,用我的眼神告诉她,我有多爱她纯洁高尚的灵魂;可我又多怕与她对视,怕从她灰宝石般璀璨的瞳眸中,看见难平的哀怨与悲伤,致使我彻夜无眠,因其而悲。
安娜,我亲爱的安娜,我又拿起这本书,又见到你。看到你为“过剩的青春”而重新,不,是第一次找寻到“爱情”时,我是该为你喜悦还是为你担忧?为你喜悦,可“悲剧”的马脚一开始便有迹可循;为你担忧,可你从此多了多少幸福的笑容,而我又怎么忍心去“担忧”?我时常想,倘若沃伦斯基没有跟你上回圣彼得堡的列车,又或者你没有下定决心追随他、追随爱情而离开,结局是否会不一样?可你那白雪般无染的灵魂终究无法与这个时代契合——即使结局会有不同,你的灵魂终究也会因此熄灭,直至暗淡,最终再无光芒——迎来这般麻木不仁的你,是同样残忍的。
可惜她无法回答我,因为她看不见我,看不见未来的时代是怎样的一番光景,她只有只身在刀尖四伏的黑暗时代里赤脚而行。也许不知从何时起,她不再只是“小说角色”,她更是一个活人,一位穿着黑绒裙在舞池中央光彩熠熠的贵妇,一个忍受着“包办婚姻”而倾尽所有去疼爱儿子的母亲,一个即使诽语烧身也始终坚忍的女性。
安娜,我亲爱的安娜,我不会忘却你的苦难,但更愿记住你的黑绒裙——因为你身着黑绒裙第一次在我眼前出现时,我看到了你隐藏的活力和不甘逝去的热情,还有那令人怜爱的骄傲。从此,我愿带着你的记忆,在剩余的年华里一遍又一遍地再见你身着黑绒裙的模样,如同你美好的灵魂,在人间永不灭。
(指导教师 陈香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