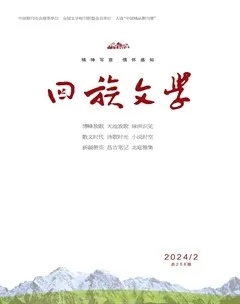你在布央想起了谁
刘月潮
绿。
无边的绿,耀眼的绿,干净的绿,丰腴的绿,素雅的绿,圣洁的绿,恰到好处的绿,浑然一体的绿,高低不一的绿,层层叠叠的绿,灵动的绿,流淌的绿,芬芳的绿,感恩的绿。绿就像大海里汹涌的波涛向我涌来,淹没着我,侵袭着我,俘获着我,也滋养着我。无尽的绿填满了我的身心,连一丝缝隙也没有留给我,我索性把自己完全交给布央这片大地,交给这片碧波荡漾的绿,直到我成为布央茶园的一抹绿色,一抹跳动的绿。
在三江布央,这些无穷无尽的绿仿佛在时时酝酿着什么,像聚在一起随时随地共谋着什么。一个个关于茶的传说与故事就在布央绿色的茶园里被时光渲染着铺展着,像一棵棵茶树在布央的大地上延绵不绝。
茶,在布央,远不止是一片树叶的故事。
茶树,在布央,同样不只是一场绿色汹涌的故事。
站在布央茶园的山顶上,眼前的每一棵茶树每一片叶子都在比拼着绿色,都在执着地绿着。我被无尽的绿色围堵着,我的身心被绿色浸润着,被绿色侵袭着。此时此刻,我早已不属于自己,只属于这无垠的绿色。
在布央,从冬到春,再从春到夏,从夏至秋,每一棵茶树都不分季节不分昼夜使劲积攒着绿色,都在倾其所有积攒着生命的力量,等待着某个时刻,一并爆发出来。每一棵茶树来到世间的职责仿佛就是给大地献上一片绿色。茶有春、夏、秋、冬四季茶,在布央,茶人只采三茶,冬季茶则留给茶园的生长。远道而来的我像是赴一场万年之约,奔赴一场绿色的盛宴,我对布央的认识是从山上一棵茶树开始的,也是从一抹绿色开始的。我被绿色抢夺了身心,只想在布央的茶园里安稳地做一棵茶树,呼吸着洁净的空气,吐纳着芬芳。
说起来我对茶树的习性并不陌生,我来自江南茶乡,熟知每一棵茶树的生长,熟识茶树每一片叶子生命的纹理,也熟悉它们生存的秩序。在那个饥饿的年代,老家人多地少,为了活命,从前生长茶树的地方都开垦成了田地,茶树被砍掉了,种上了五谷杂粮。茶树只零星残留在菜园地坝、高田后埂,数得清的茶树孤独地跟杂草灌木活在了一起,那些茶的一片片树叶和草木的颜色混杂在一起。
茶叶当不了饭,不仅填不饱肚子,还会像刀子一般搜刮着人,让人饥肠寡肚。一棵棵茶树不得不给人的温饱让路。
人不把茶树当回事,茶树稀稀拉拉地长在野草灌木中间,自生自灭,像一个找不着家的野孩子,攒足了劲儿野里野气地生长。茶树少了,茶乡也早已名不副实。
在我贮存已久的关于茶树的记忆里,每年一到清明、谷雨,茶乡人就会顺应时节,从野外那些零零落落的茶树身上,采摘着枝头上新簇簇的光阴。采茶,似乎早已变成茶乡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仪式,不过也有一些人家茶树砍光了,已无茶可采。父亲早年在房前屋后种上了茶树,茶树三四年就能产茶。我家不缺茶树,也不缺茶。一年茶树能产一二十斤茶。村里人都晓得父亲做得一手好茶,空闲时常上我家蹭茶喝。生活中一扇关于茶的门早已关上了,落满了尘土;另一扇门却霍地打开了,能耕种的田地多了起来。饥饿的时代早已过去,当年茶园改成的田地大多因缺水或路途远,后来统统被撂荒了。田地都没人下力气耕种,更别说会有人舍得汗珠子再去挖掉那些灌木杂草,恢复茶园了。
没了茶园后,村里多数人家也只采到几斤新鲜的茶叶,一片片初临人间未经世事的树叶,到了茶师的手里,经历一场场生命的涅槃,一片片树叶从此唤醒了深藏在体内的另一个自己,从生命的一种形态迈向另一种形态。
一季茶叶,往往也只得斤把干茶,平日都不舍得喝,藏在茶罐里,留着招待客人用。
在茶乡,茶一向被誉为闲茶,喝茶是农闲时用来一点点消遣时间的,而浸润在闲暇的时光里,一片片茶叶在茶汤里苏醒,一点点舒展身子。人同茶一般,从忙碌中忽然闲了下来,幸得茶汤相伴,人听从茶的召唤,挣脱岁月的负重,灵魂也跟着慢慢苏醒。此时,人和茶在流逝的时光中互相慰藉,互相唤醒对方,在各自的生命中浓缩、绽放,芬芳、淡雅。
众生皆苦,人来到这世间,像茶园的一片片树葉最终要遭受生命的种种磨砺。但变成茶的一片片树叶要经受的风霜雨雪自然不比人少。风吹过茶园,打开了每片树叶的天空,也打开了它们的梦想。它们在一个点燃着火焰的世界里行走闯荡,闯出了各自的一片天地。明前茶,一簇簇芽尖,从睁开眼来到世上,不过才一个月时间,采茶人就把它们从一棵棵茶树上揪走,安放在茶篓里。一簇簇新茶,在茶树上活着时从不低头,采摘后,它们的骨气和气节都浓缩在一朵朵茶花里。
一簇簇芽尖到了茶师手里,终结了一场短暂的生命旅程,进入了命运的另一场轮回。一簇簇芽尖在茶师手里开启了它们下一世的征途。那些芽尖经过杀青、揉捻、摊晾、烘干等,最终变成了茶叶。对每一片树叶来说,做茶的每一道工序就是一场命运转换的道场。
父亲是十里八乡有名的茶师,在刘家冲林场做过多年的制茶师傅,父亲做出来的茶像一粒粒米粒,一簇簇芽尖浓缩成了米粒般大小,经过烧开的山泉水的冲泡,一粒粒茶叶开始从沉睡中醒来,又回到一片树叶的模样。这片树叶却有了世上最醇厚甘爽芬芳的味道。人在茶的形色味里顿时迷失了自己。
父亲说,茶跟人一样,制茶人要懂得茶的性子,一棵棵茶树卑微地活在天地间,但一片片卑微的树叶里却藏着大地,洒落着阳光雨露,缭绕着云雾。制茶其实就是茶人每时每刻都在用自己的生命和时光去唤醒每一片茶的树叶,唤醒它们的灵魂,召唤出它们体内的阳光雨露,让它们重生,重新塑造另一种生命。
茶叶就是一片片茶的树叶在做茶人手上一回回死去后又接着重生。
少时,父亲在灶上做茶,我则在灶下煨火。做茶时父亲有自己的许多讲究,炒青烘干时有专门用来做茶的一口大铁锅,铁锅平日束之高阁,只在做茶时拿出来用,父亲说做茶的铁锅沾不得一星点油荤。父亲还会提前准备一大堆干燥的松毛。松毛一点就着,火的爆发力强,烧得旺,炒青时松毛火最合适,铁锅烧得红彤彤的,父亲撒下一把新鲜的茶叶,茶叶一沾烙红的铁锅就噼里啪啦地响着,父亲双手在铁锅里翻飞着,茶叶飞快地起落着,火候到了,再凭经验出锅,一片片树叶的身子在杀青后变得更加柔软,百折而不挠,茶叶青涩的气息也去除了。趁着叶子的热还没散去,要立马接着揉捻,茶叶被父亲揉成了一团,揉出了绿色的茶汁,揉捻要有手上功夫、技巧和力量。父亲把一团茶叶揉出了绿汁,又一点不伤茶叶。揉捻后摊晾,再烘干,一片片树叶早已不是原先的那一片片树叶了,在炒青、揉捻、烘干中改变了自己,一直到成了一片变形而又重塑自己的茶叶。
我见证了一粒粒茶叶在父亲手中诞生的全部过程,父亲做茶时身处高温的灶边,脸上淌着汗水,衣衫都湿透了,而即将成为茶的一片片树叶在烟与火中,在父亲汗水与揉捻中一回回重生。谁又能想到,一朵朵茶花,竟是从生活的辛劳中绽放出来的。
我从小爱茶,喝着父亲亲手做的茶长大。父亲做的绿茶滋养着我的身心,也滋润着我的灵魂。我就像大自然中的一只虫子离不了大地泥土和季节一样离不开茶。几年前父亲病故了,我再也喝不到父亲做的茶。老家的那些茶树还在,年年吐着芽尖,而父亲却从此归于尘土。喝不着父亲亲手做的茶,我对别的茶也忽然丧失了味觉。
当年茶乡人为了填饱肚子,把茶园辟成了田地,而布央人为了吃饱饭,过上富足的生活,在山上播下茶树的种子,栽起了茶秧子。从此茶树遍布了布央大大小小的山头,布央茶园的面积达到了三千九百亩。布央的人和布央的茶一直向美好的生活进发。
在布央,每一个生长的茶季,那千千万万的绿孕育着一片片新生树叶的涅槃重生。
我们这些外来的人流连在布央的每家茶摊前,一个个摊主一张张笑脸,宛若一朵朵盛放的茶花,热情地招呼着我们,我们随时随地在一家茶摊前歇下来,品尝他们沏的不同品种不同风味不同季节的茶。
喝着布央的茶,我忽然寻到了丢失已久的父亲做的茶的味道。那是一种久违的茶的味道。
在布央,茶不仅有清香、豆香、嫩香等各种香气,还有爱的味道。
在布央一家客栈挂的牌子上,我看到了一句令人心动不已的话:
你在布央想起了谁?
我在布央想起了做茶的父亲。是的,他跟布央的茶园一般,给我的灵魂植上了无边无际的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