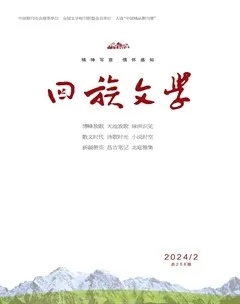墙
塞纳河
一
墙,无疑是世上最常见的风物之一。人眼一睁,首先面对的就是一面墙;而眼一闭,也往往少不了扶墙而行。
世上的墙种类之多,令人咋舌。依材质分,有砖石墙、土木墙、水泥墙、铁皮墙、玻璃墙、篱笆墙等;依结构功能分,有剪力墙和承重墙、空心墙和实心墙、外墙和内墙、单向墙和双向墙、景观墙和装饰墙等;依归属分,有私人的墙和公家的墙,也还有无主的墙;依颜色分,更是赤橙黄绿青蓝紫样样俱全。另有许多似墙非墙的衍生品,如隔离网(栏)、纪念碑、堑壕、照壁、界碑、墓碑等,那无非是墙的姻亲和子孙。
世上绝大多数普通的墙,没有显赫的身世和地位,因而也没有响亮的称谓,只能千篇一律拥有大致相同的名字:东墙、西墙、南墙、北墙。另有些墙,因为身世显赫卓尔不群,自然拥有响当当的名分。如为防范墨西哥人偷渡,美国人在国界线上修建的隔离墙,号称“全世界最特殊的墙”;巴黎蒙马特的“爱墙”,上书三百多句“我爱你”,涵盖了当时联合国一百九十多个会员国所有的语种,号称“全世界最浪漫的墙”;冷战时期的那座柏林墙,则号称“全世界最著名的墙”。
当然,也少不了中国古代宏伟壮观的军事防御工程——万里长城,被誉为“全世界最长的墙”;还有西藏布达拉宫的墙,因墙体泼了加白糖、蜂蜜和藏红花的牦牛奶,被誉为“全世界最甜蜜的墙”。诸如此类,异彩纷呈的墙文化,许多已成为人类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
可以想见,随着时代发展和技术进步,各具特色的墙也必将不断涌现,如3D打印墙、电磁墙等。
二
世上本没有墙,正如世上本没有路一样。墙无疑是人类文明的一大创造。
从百科释义看,“墙”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古字形由“啬”“爿”构成,意思是筑墙把谷物保存起来。其本意是房屋或园场周围的障壁,用来支撑房顶或隔开内外。如此看来,最初的墙,是用来防野兽防风霜防雨雪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发展成防人防盗防枪炮。
人们常常根据自己的喜好,赋予墙五花八门的含义,这从有关墙字的诸多成语中可见一斑。如铜墙铁壁、狗急跳墙、红杏出墙、祸起萧墙、扶墙摸壁、路柳墙花、朽木粪墙、墙风壁耳、逾墙窥隙、墙头马上等。
其实,附加如此名目繁多的意义,对墙而言多少是冤枉的。世上所有的墙,从根儿上说,都建于人心之中。墙,既是人心的投射,便可倒指人心。因为,墙本身是不偏不倚与世无争的,耽溺偏执和纷争的,乃是墙的主人们。君不见,宫廷和豪门大宅里,这道墙那道墙隔开的,是不同身份的人该走的路;君不见,沧海横流,欲望所到之处,虽有坚墙的阻隔,战争和掠夺照例不期而至。而战争和冲突,一方面摧毁了不少墙,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增加了更多的墙,以至让本已变幻莫测飘摇不定的世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动荡不安。
所幸,墙是一个忠实的哑巴,从不轻易把世间奥妙道出。也许,看风云变幻,观四季流转,它知道得太多,只好装聋作哑。殊不知,沉默的墙,难免打心底嘲笑那墙里墙外的喋喋不休乃至唇枪舌剑。
三
世间万物皆一体两面,墙也有阳面和阴面。
墙的光荣和欢乐,与它的悲哀和辛酸一样多。墙,既是威严实力和规则秩序的象征,也是恐惧怯懦甚至愚昧愚蠢的标记。墙,既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威胁。正如安了防护栏的楼房,虽可防盗,却不利于清扫和逃生。家里的墙多了,挡光线遮视野,给人压抑闭塞之感。更不消说,有墙就会有爬墙虎、攀墙藤、墙头草和隔墙耳。极而言之,墙倒还会砸死人。
人被墙所拱卫所护佑,也为墙所拘禁所困顿。墙的固执保守和狭隘闭塞,常常会挡住那些远足旅游、贸易往来和崇尚自由者的路。一个地方里里外外的墙多了,不仅给人高深莫测的疏离感,还难免成为阴森诡异的迷宫,令人屡屡撞墙后知难而退,避之唯恐不及。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墙虽有诸般好处,人名里带谐音“强”字者不计其数,却鲜有人将“墙”字入名,似乎隐含着人类对墙的某种禁忌和迷思,进而折射出墙的复杂性和多义性,犹如意象派的诗和画。
四
不论承认与否,于有形的物质的实墙之外,世上还有诸多无形的观念的虚墙,诸如制度的墙、文化的墙、心理的墙、网络防火墙等等。
无一例外,人人身上都有墙,正如人人身上都潜伏有细菌一样。有些墙有益无害,免疫力是墙,意志力是墙。倘若人体完全无墙,如何抵挡病菌感染和外界干扰,正常人与精神病患者又有何异?有些墙则有害无益,身病是墙,限制了人体器官的正常运行;心病即心墙,则遏制了心灵的自由发展。君不见,有人遇有大麻烦抑或受了大委屈,积郁成难以排解的心墙,进而觉得生活无望以至万念俱灭,不幸而选择了一头撞到南墙上,实现了实墙和虚墙的无缝对接。
无一例外,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墙。它贯穿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直至社会生活各领域,通常体现为法律、道德和习俗等。
同样,每个团体和组织也有自己的墙,主要砌在各自的章程或合约中,构成了彼此清晰的边界和标识。就连人际交往也不例外,财富、权力、地位、品相、性格、爱好、家庭、健康等,皆可成为横贯其中的墙,由此生成了各式各样规模不等相对独立的朋友圈。
五
显而易见,世上是不能没有墙的。
有些墙,源于人类的某种刚需强需,已然不可或缺。如城区高架桥上的隔音墙,美化生活健康向上的艺术墙、文化墙、屏幕墙、笑脸墙,抢险救灾中临时拉起的人体墙,具有一定历史研究和考古价值的文物墙,隔离病毒用的网络防火墙,等等。
退而言之,倘若有人犯了一般过错,需要面壁思过脱胎换骨,这时就需要墙;倘若有人犯了律法,以至罪不可赦,这时就需要高墙电网。
众所周知,凡事都有一个度,过犹不及,物极必反。墙虽不是越少越好,但肯定不是越多越好。开放和包容乃天地大道,作茧自缚,坐井观天,只能坐以待毙。少一堵有形的墙,视野就会更通透些;少一堵无形的墙,事理就会更通达些。世上原本已有那么多江河洋流、山峦沟壑的阻隔,为何非得再添堵墙不可。即使必须造墙,也不妨多采用透明墙,或者至少多安些窗户,尽可能地接纳些温暖阳光和新鲜空气。更何况,很多时候,一条帘子、一道屏风即可解决问题,何必苦心孤诣甚至劳民伤财一味造墙不可。
時移世易,凡事皆有定期。墙,无一例外挣扎在时间与时间、话语与话语、权柄与权柄的流变中。君不见,同样是墙,命运各不相同,个中缘由既有自然规律,也有社会法则。风吹雨淋会倒,人为因素会拆。有时拆得好,如阻挡文明进步的柏林墙;有时拆得就颇有争议,如某些古城墙。一面面墙不断竖起来又倒下去,正说明有些墙当时可能是刚需,现在则不一定是;有些墙,甚至一开始就未必是刚需,甚而说其开始之日便是终结之时。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墙的态度。倘若对文明起源与发展做深入研究,就不难发现,多元文化的相似性远大于其差异性,根源在于人性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往往直观地折射在肤色、服装、语言等显性方面,而这些恰似为同一首歌词谱上的不同曲调而已。其基本思想层面的差异,似乎不会大于前者的差异,关键在于求同存异合作共赢,说到底就是多拆墙少垒墙。
实墙也好,虚墙也罢,既源于人类的某种刚需强需,最好便止于这种刚需强需。有鉴于此,对于那些可有可无、晦暗不明的弱需不需之墙,不妨及时来个大清理、大拆除。正如电脑清理一样,该收藏的收藏,该升级的升级,该打补丁的打补丁,该格式化的格式化,该删除的删除,如此电脑才能运行得更顺畅更高效更快捷。
当然,但凡私人的墙,只要不违法不违规,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要不要建,怎么建,不妨充分尊重个人的合法权利。
墙,于风雨和阳光中,于白昼和黑夜里,于远古和当下,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人类,期待着人类。更重要的是,墙的命运,墙迟早会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