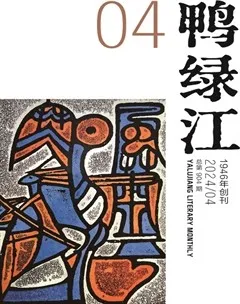方冰:歌唱二小放牛郎
陆天
“牛儿还在河边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莫非他贪玩耍丢了牛,放牛的孩子王二小……”悠扬的旋律一响起,大家纷纷跟唱。这样的场面见多了,我就问了许多次,问了许多人为什么跟唱。听到最多的答案是好听。再问词作者是谁,人們往往语焉不详。这一首《歌唱二小放牛郎》的词作者是我尊敬的长辈方冰。说起方冰,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了,可他的大女儿、著名演员方青卓却是家喻户晓。其实当年方冰在延安家喻户晓时,方青卓还没出生呢。这一首抗战时期流行于全国的《歌喝二小放牛郎》,被传唱了八十余年,至今依然广为流传。毫无疑问,这首歌已经融入中华儿女的血脉中,感动激励了我们民族几代人。
方冰出生于1914年,安徽淮南人,原名张世方,年轻时到延安参加革命,进陕北公学学习创作,取笔名为方冰。“方”是要求自己做人要方方正正;“冰”来源于“一片冰心在玉壶”,寓意心性高洁。许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方冰用安徽普通话吟诵的情景:“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缓慢的语速、庄重的神态,让人肃然起敬。
方冰在辽宁作协工作,是我父亲的老领导。辽宁作协办公地点在今张学良旧居,所以我小时候也住在那里。方冰喜欢孩子,尤其对我偏爱有加,每次远远一看见我就喊:“二嘎子过来扛木头。”我有姐姐,在家里排行老二 ,二嘎子就是方老当年给我取的外号。在他的故乡,二嘎子是对小男孩儿的爱称。我也喜欢这位没有架子、没有脾气的大人。小时候我把人分成小孩儿和大人两类,那时候我不知道方冰不仅仅是大人,还是一位大人物。“扛木头”是我们俩的专属游戏,他两条大长腿一叉稳稳站立,右胳膊向前一伸,小臂向上一收,摆好了架势。我就赶紧跳起来,用双手环抱,挂在他粗壮的大臂上打提溜。悠来荡去,累得不行时,游戏才在我俩的笑声中结束。笑声中经常还伴有糖果奖励。方冰有三个女儿,她们都没有这样的待遇。方冰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笑声爽朗、目光慈爱、带给我童年欢乐的长者。
方冰于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天到晋察冀边区打游击,同时担任宣传工作并开始写作。曾与田间等人发起街头诗运动,负责编辑《诗建设》。1945年创作了长篇叙事诗《柴堡》,反映抗日敌后根据地人民的艰苦斗争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大连市文化局长,1956年在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从事创作,后来担任副主席兼《鸭绿江》杂志主编,著有《战斗的乡村》《大海的心》等诗集,1997年因病去世。老人家去了天堂,他把《歌唱二小放牛郎》留在了人间,永远诉说着那段历史,永远为英雄的孩子歌唱。
抗战期间,中华大地涌现出了不少抗日小英雄,他们只有十二三岁,和平年代本应该上学,或者还在父母身边贪玩,可是日本侵华战争却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孩子们也被卷入战争,他们整天吃不饱,穿不暖,饿着肚子给部队和乡亲们送信、带路,做了许多工作,有的甚至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当年也有小英雄,为了打鬼子,不顾个人安危,把日本鬼子引入了我军的包围圈,被敌人识破后残忍杀害,这类故事在当时的晋察冀边区广为流传。
当时方冰和著名作曲家李劫夫一起在华北打游击,两人睡在一铺炕上,吃在一个锅里,一个作词,一个谱曲,配合得十分默契。身为记者的方冰敏锐地捕捉到这些信息,他想为孩子们写一首歌,让人们记住那些可爱的孩子,记住那些民族的小英雄。方冰和劫夫商量,两人一拍即合。可是方冰那时连一支笔也没有,不过这也难不倒方冰,他就地捡起一根草棍,在草棍一头绑上一个钢笔尖。没有钢笔水,就去医疗队要了一点红药水。草棍绑钢笔尖蘸着红药水,诗人满怀的激情化作了《歌唱二小放牛郎》。
因为形象栩栩如生,以至于我少年时代一直以为王二小真有其人,就问方冰,是不是真有一个王二小?方冰并不拿我当小孩儿看待,他认认真真回忆说:“在我的脑子中,确实有一个真名实姓叫王二小的小英雄,但是在我歌中所写的王二小是众多小英雄故事的再创作。我的王二小和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不一样,是我创作出来的典型艺术形象,是无数少年英雄的化身。我要歌唱的不仅仅是某一个人,而是广大少年英雄的抗日精神。”
我小时候就喜欢缠着大人问东问西,可惜那时候父母忙于运动,忙于工作,其他大人们也都疲惫不堪,没有人会认真回答一个孩子的问题。方冰不同,我的每一个问题都被他视为“答记者问”,认真详细回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来不敷衍了事。受到激励,我继续发问:“那么‘九月十六日那天早上,敌人向一片山沟扫荡是真的吗?为什么是九月十六日呢?”方冰身材高大,他蹲下来摸摸我的头,缓缓回答道:“不是真实的日期,九月十六日是我的生日。”很多小时候的记忆如今都荒芜了,唯有方冰这个九月十六日被我牢牢记住了。2023年9月16日,我在朋友聚会上唱了一遍《歌唱二小放牛郎》,可惜天人永隔,方冰已经听不到了。把自己生日设定为小英雄为国捐躯之日,这是怎样的情感投入!这是怎样的一腔孤勇!
方冰这首叙事诗形式的歌词非常具有画面感,语言朴实无华,娓娓道来,就像一位讲故事的老人在讲述一位小英雄从为东家放牛,到被鬼子抓走带路,最后把鬼子骗到八路军的埋伏圈,自己牺牲宝贵生命的全过程。著名作曲家李劫夫看了一遍歌词后非常激动,通宵达旦一气呵成,为这首诗谱了曲。歌曲拿到军区文工团去试唱,很快就唱响了根据地。从此,这首《歌唱二小放牛郎》宛如插上了翅膀,迅速唱遍晋察冀,唱响全中国。艺术家对孩子满腔的爱,对侵略者的愤恨,激励着大众的爱国精神,极大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名如其人,方冰为人方正不阿,他自己也承认“嘴敞”,就是心里藏不住话,有什么说什么,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对那些年过度政治斗争不满,就曾经公开讲道:“回想一下这些年,都干了什么了?自己人杀过来,杀过去,一个也没剩下。”方冰有点口吃,讲到“杀过来,杀过去”时往往情绪激动,口中拖着长音“杀,杀,杀过来……”手上还打着手势,从左边划拉到右边,又从右边划拉到左边,好像满怀的杀气快要溢出来似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别有用心的人添油加醋,举报了方冰。有一天,时任旅大市委书胡明召开会议,通知方冰也参加,当时方冰还在旅大文化局局长任上。旅大的很多人都知道,胡明是方冰的老战友、老首长,两人个人关系非常要好,谁也没想到的是,胡明在会上突然发怒,拍着桌子指责方冰胡言乱语,讲了不该讲的错话。不等方冰接话茬,余怒未消的胡明就代表旅大市委决定把方冰下派到熊岳印染厂负责宣传工作。这一决定着实让许多人震惊,他们觉得胡明不近人情,就为几句话处理这么重,等于把老战友一棍子打死,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说不过去。其实,大家都不知道,随后到来的“反右运动”对说错话人的处理力度远远不止于此。胡明是用这种方式把方冰保护了起来,不然方冰很可能被定为“右派分子”。“文革”后期,我母亲与胡明之女胡小红成为同事,方冰知道后,特意请我母亲转达对胡小红的问候。方冰内心一直对胡明充满了感激。
方冰有个爱好,就是收藏古玩。20世纪50年代末,他经常与著名书法家沈延毅先生交流,一起品鉴藏品。赏心悦目之后,两位大咖经常愉快地共同进餐。有一次沈老请他吃饭,方冰突然像有了考古新发现似的说:“沈老,你太奢侈了,你用這盘子是道光年间的。”沈老说:“不可能呀,这是新买的景德镇青花瓷,就是普通日用品,怎么可能是道光年间的呢?”方冰端起盘子,把盘里面的剩菜都倒进了自己面前饭碗中,然后边笑边说:“你看,这不是倒光是啥?”沈老这才恍然大悟。沈老一贯不苟言笑,一想到景德镇变身“道光”,禁不住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1965年,为了彰显工农兵作家的重要性,方冰积极落实“走出去请进来”的方针。“走出去”是指作家们到基层体验生活,“请进来”是指把基层作家请到作协大院里来。方冰决定把一位名叫霍满生的农民诗人请到作协大院来,与专业作家诗人们交流。方冰主抓诗歌创作,交流会自然由方冰主持。霍满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平时爱说顺口溜,很有生活,有一些还挺有趣。比如他写的一首:“扒着门缝往里瞧,我儿我孙吃火勺。我儿吃火勺不给我,我孙还照我儿学(方言,读音同“淆”)。”把一位农村老人对儿子不孝顺的无奈和愤怒表达得非常幽默,同时老人对美食的渴望也鲜活生动。霍满生还有一些歌颂人民公社的诗歌,其实并没有太高艺术价值。不过当时霍满生走进作协大院开诗会,确实像一股叮咚作响的山泉,给大院留下了不少欢乐的话题,以至于我从小就认为诗歌应该带给人欢乐,诗人也如是。方冰对霍满生也很感兴趣,经常带头朗诵霍满生乡土诗歌,笑声最为爽朗,富有感染力,现场也常常满是欢声笑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作协首当其冲。作协内部分成三派,开始对老干部老作家进行批判。幸运的是作协的领导和普通干部都比较温和,斗争的形式仅限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斗会等,没有人身伤害,也没有人员伤亡。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67年1月,院外的造反派来到作协,他们领头的是大东区一个工厂的工人,业余作者,爱好写诗,但多次投稿《鸭绿江》,编辑部也没有采用。此君对作协的专业作家及编辑非常痛恨,认为这些“文霸”把持《鸭绿江》才造成工农兵的作品不能发表。他们进到作协后强行把大灰楼的地下室作为造反派总部,经常花样翻新地整治这些专业作家。不过作协内部的造反派并不买这帮人的账,一时间,作协内部造反派和作协外部造反派冲突不断,双方经常因为一些观点发生矛盾,唇枪舌剑。有一天院外造反派小头目把老作家、老编辑召集到一起训话,小头目说:“你们这些人过去为什么压制工农兵作家?方冰你先交代。”方冰本来有点口吃,又见院外造反派头目来势汹汹,方冰口吻郑重,回答说:“我……我……我没有压制工农兵作家,《鸭绿江》有规定,每期都用十页版面发表工农兵作品。”小头目瞪了一眼方冰说:“你还敢抵赖?”说着就把厚厚的一沓手稿摔到方冰面前说:“你看看,这都是我的诗稿,全部被你们退回了,铁证如山,你还敢抵赖?”方冰就势把手稿拿过来,蹲在地上认认真真读了起来,就像平时坐在办公室里翻阅作者来稿一样。造反派本来想批判“文霸”,看到“文霸”认真审稿,希望发表的小火苗再次升腾起来。批斗会好像就地变成了诗歌创作交流会。全场鸦雀无声,在场被批斗的其他作协领导、“文霸”如韶华等人不知结局如何,只好忐忑等待。时间静静流逝,方冰翻阅半天,抬起头来说:“现在……看,还是……不能发表。”方冰一丝不苟的回答,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把在场的人们全都逗乐了。谁也没见过这么欢乐的批斗会。小头目又心虚又不甘,气急败坏地问:“为什么?”方冰答:“概念化,尽是口……口号。”方冰的回答当然换来又一场疾风暴雨般的批判,好在个小头目好歹也算是个文化人,并没有动粗,只是实施语言暴力而已,这才使作协的老干部老作家们免受皮肉之苦。
有一天,院外造反派小头目手下的女红卫兵在地下室里唱起了歌曲《美丽的哈瓦那》:“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新屋,门前开红花。”歌声悠扬动听,传出很远。这是一首赞美古巴的歌曲。当时古巴已经被定义为修正主义。作协内部的造反派在楼上听到地下室传来的歌声后,立即组织人力跑到地下室展开批判。作协造反派早就看着这几个外来的造反派不顺眼,这回抓住把柄,岂能放过他们。院外造反派小头目自知理亏,也不敢再恋战,怕引火烧身,遂决定撤退,于是这伙院外造反派就这样狼狈逃窜了。作协大院的管控权又回到了内部造反派的手中。
“文革”期间,方冰被下放到内蒙古农村。他方正耿直,嫉恶如仇,看到当地农民吸食鸦片,非常痛心。他曾经目睹农民毒瘾越来越大,烟瘾一上来,鸦片断供,只好把以前吸食剩下的鸦片膏注射进血管,结果当场死亡。用方冰的话说就是:脖子向前一伸,“艮搂”一声就死了,人命还不如一只小鸡崽,场面惨不忍睹。方冰经常出面制止村民吸食鸦片,他不知道,也不屑于知道,当地鸦片交易背后有着巨大的利益链条,方冰不但动了利益团体的奶酪,而且他的行为也惹恼了吸食鸦片的农民,丑恶的利益和可悲的愚昧搅和到一起,眼看要燃起一场大火烧毁方冰的“冰”。一伙农民聚集到一起想要灭了他。方冰和方孝孺是一样的“方”,不过关键时刻发现自己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方冰的理智占了上风,他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紧急避险,不得不跑回大连投奔女儿。结果到了大连以后,被警察当作盲流抓了起来。在一起被抓的三十多人中,只有方冰穿着呢子大衣。当过战士的他身姿挺拔,气质出众,小警察怀疑方冰的问题最大,就向旅大公安分局副局长汇报,说抓到的盲流里面有一个人不同寻常,请领导亲自审查。这位副局长见到方冰,愣了一下,赶紧快步向前握住方冰的手说:“老首长,你怎么也被抓到这里来了?”原来这位公安分局副局长曾经是方冰的警卫员。在旅大刚刚解放时,方冰随大部队进入旅大城市接管,带的就是这个警卫员。当年的警卫员如今已经成长为公安分局副局长,副局长当场释放自己的老首长。
“文革”结束后,方冰又回到作协,担任领导工作的同时仍然坚持创作,1978年后陆陆续续写了不少诗,1985年出版了诗集《大海的心》。正是在那段时间里,我也对诗歌创作有着浓厚的兴趣。关于什么才是优秀作品,我和方冰讨论过,他有自己的思考和看法。近几年来,《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被不断翻唱。岁月沧桑,社会发展波澜壮阔,似乎一切都变化了,但这首歌没变,它依然受到人们的喜欢,依然被广为传唱,方冰用自己的作品回答了什么是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