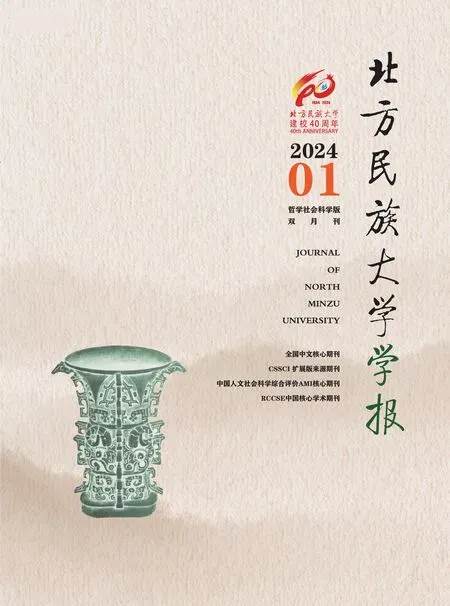中华民族是具有共同历史文化记忆的人们共同体
——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试用本)
沈桂萍
由国家民委组织编写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试用本)(以下简称《概论》)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论证了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共同历史文化记忆的人们共同体;在今天主要指具有共同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大陆各族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华侨”。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定义完成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人类学意义上民族实体的内涵、结构和属性等方面的学理建构,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理论贡献。
一、讲清楚了中华民族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实体,是对中华民族“建构论”和“各民族总称论”的学理超越
《概论》从理论、历史发展规律和当代实践等方面,讲清楚了中华民族是古往今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民族实体。
众所周知,我国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是梁启超,但百余年来,我国学界关于“中华民族是什么”的阐释主要侧重于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层面,形成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或“中华民族是多个”的较长时间的学术争鸣,而在这一学术争鸣中,中华民族的概念长期停留在“各民族总称”层面。1988 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1],虽然强调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但中华民族形成于何时,中华民族作为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内涵和特征是什么,并没有给予明确的阐释。相反,主导学界的“中华民族是各民族总称”话语叙事,凸显了中华民族是政治共同体、不是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属性,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华民族到底是政治共同体还是“具有共同历史文化记忆的人们共同体”,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除了“各民族总称论”,关于中华民族的阐释还有“建构论”的学术叙事。有些学者根据西方学者安德森关于民族是建构起来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2]来认识中华民族,认为不存在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换句话说,中华民族是晚清时期为了应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建构起来的,目的是为现代国家提供一个民族身份。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华民族作为现代国家民族身份,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命题,不是“具有共同历史文化记忆的人们共同体”,也就不具有文化人类学的学理属性。
虽然1988 年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论证了中华民族是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民族实体,特别是1991年费先生专门解释过中华民族不是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而是“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3],但其论述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没有完成中华民族是“具有共同历史文化记忆的人们共同体”的学术论证,以至于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这一具有建构性的学术叙事,在学界关于中华民族与各民族关系的讨论中一直有较大影响。
《概论》关于中华民族是“具有共同历史文化记忆的人们共同体”的定义,完成了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中华民族的历史叙事。《概论》指出,作为具有共同历史文化记忆的人们共同体,中华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孕育,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实体基本形成,魏晋南北朝历经400年的大动乱,不仅没有使古代中华民族的各个部分走向分殊,反而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的大融合,为隋唐以后中华民族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走向统一打下了基础,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本确立,处在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前夜。
晚清,各民族同胞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是将中华民族的传统国家变革为现代国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完成了中华民族从古代封建国家到现代人民国家的转型。在国家转型中,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逐步唤醒了各族人民统一的国家民族意识,因此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转型并没有造成中华民族大分裂,相反,各民族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如1911 年12 月1 日,一些蒙古王公在沙俄的指使下,在库伦成立了以哲布尊丹尼为大汗的所谓“大蒙古帝国”。针对这样的分裂行为,1913年初,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召开西蒙古王公会议,内蒙古22部34旗王公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并通电全国申明:“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当一体出力,维持民国”[4]264。
正是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推动了近现代以来中华各族儿女共同投身中国革命,对外致力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对内致力于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华各族儿女的中华民族意识觉醒不仅推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也推动中华民族迈上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所以,《概论》关于中华民族是“具有共同历史文化记忆的人们共同体”的定义,是对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的中华民族历史的科学阐释,也是对“各民族总称论”和“建构论”的学理超越。
二、完成了古往今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缔造伟大中华民族的历史叙事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话语叙事。一是“版图中国”的历史叙事。谭其骧先生在1991 年提出“版图中国论”[5],通过论证,确认了1840 年之前“版图中国”的法理性。依此学说,中国史就是1840年之前中国版图上中原政权、边疆政权共同发展的历史,吐蕃史、古高丽史、魏蜀吴三国史等都是“版图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版图中国论”完成了“主权中国”的历史叙事,但没有建构不同民族、不同政权共同建构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学理逻辑。二是56个个体民族史的历史叙事。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代代民族史学家关于各民族独特的历史渊源、传统生产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研究,产生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56个民族建立起独特的历史文化叙事。这些历史文化叙事为形成“四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提供了基本的史料线索,为建构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的中华民族历史叙事奠定了史料基础。三是古代民族关系史的历史叙事。传统古代民族关系史叙事从民族平等视角观察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但没有勾勒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逻辑。
与上述三个主要的中华民族历史话语叙事不同,《概论》以“四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指导,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维度,围绕“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展开历史叙述,揭示了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孕育形成、自在发展,到近代形成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多元一体”格局。这种历史话语叙事以版图中国史、少数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叙事为基础,是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的升华,是对上述各民族史学观的创新发展,为各民族同胞正确认识和把握个体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提供了学理依据。
这样的中华民族历史叙事有助于纠正两个历史叙事偏差:“王朝中国”叙事和“外化于中华民族”的话语叙事。
一是纠正了“王朝中国”叙事异化为“汉族中心论”的偏差。《概论》以“四个共同”为指导的叙事,强调先秦时期就孕育并影响历代王朝的“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以“大一统”制为制度载体,“汉化”与“胡化”双向互动为主要表现,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断发展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王朝中国”历史叙事最典型的表现是王朝史的编纂,以王朝为主线,以边疆地区为副线。以《史记》为例,《匈奴列传》仅占《史记》庞大的“本纪”“年表”“世家”“列传”的一小部分。诚然,这种叙事主线鲜明、逻辑清晰、便于写作,但落脚点是古代中国的王朝史,容易让人忽略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动态网络中的作用与价值。此外,“王朝中国”叙事容易使人产生中华民族史就是王朝史的错觉,误导读者产生中国历史等同于汉族历史、中华文化等同于汉族传统文化的错觉,对于这样的认识偏差,虽然很多人已经认识到其危害性,但仍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
二是纠正了“外化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叙事偏差。中华民族指的是古往今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及其先民,中华大地上的古代历史既是中国版图的历史,也是这块版图上各民族及其先民的历史。虽然西域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管理体系是在汉代,但早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中就有周穆王巡游西域与当地首领西王母交往的记载。西域古代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缔造的过程,西域古代各民族与中原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缔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过去有些个体民族历史文化叙事孤立地追溯某个古代部落、某个神话传说、某个历史人物的关联和传承,强调独立的族源、特定的生产生活和特定地区的关联等,强调独有历史记忆和标识,这就不自觉地忽略了“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1]的历史事实。
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中华民族历史的叙述,既不能窄化为“王朝中国”叙事,也不能停留在个体民族和民族关系史叙事,汉族中心主义叙事和“外化于中华民族”历史叙事都潜在地解构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体性,不利于全面客观准确把握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关系。
从《概论》“四个共同”的历史叙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同融合形成的统一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是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日益增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哪个民族建鼎称尊,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国家,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正统。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日益紧密地结成文化相通、血脉相融、命运相连的共同体。
三、讲清楚了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虽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客观地理条件,但决定这个地理范围活动的诸多古代文明集团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交往交流交融,最终汇聚成中华民族的是主导古代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思想在推动古代各族先民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共同的中华民族意识、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思想由来已久。西周时期实行分封制,但已经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疆域观念;战国时期,纷争不断,孟子提出了天下“定于一”的主张;秦汉以后,“大一统”格局逐步形成和发展;及至元、明、清三朝,实现了统治疆域辽阔、政治局面稳定、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的局面。
古代中华儿女传承的“大一统”思想不仅指导各族儿女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且“天下观”“大一统”“华夷一体”等国家认同与“和而不同”“包容差异”“有容乃大”等中华民族共有精神,为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实体打下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爱国主义根植于我们共同经历的奋斗岁月,正是由于中华各族同胞血脉深处的“大一统”思想,才确保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探讨救亡图存,以共同体为本位,强调家国天下,重视责任伦理。清末,专制国家走向民主共和,虽然以西方民族国家为表,但注入了传统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文化基因。晚清政府调整了多民族国家统一体中本民族认同与“大一统”认同之间的关系,为各民族走向统一的民族国家塑造了“中国观念”,逐步完成了传统中国由“天下”到“中华民族国家”的转变,确保了辛亥革命时期没有出现民族分裂,更没有陷入类似西方自1517 年宗教改革以来因语言、种族或宗教立国在欧洲大地上产生的300多年的各种战争。
综上,《概论》关于中华民族是“具有共同历史文化记忆的人们共同体”的叙事,鲜明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实体属性,不仅对长期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的内涵、结构和属性的学术争鸣给出了权威性定论,而且为新时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学理支撑,为全体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团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旗帜下砥砺前行、攻坚克难、万众一心向前进提供了思想引领,成为指导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