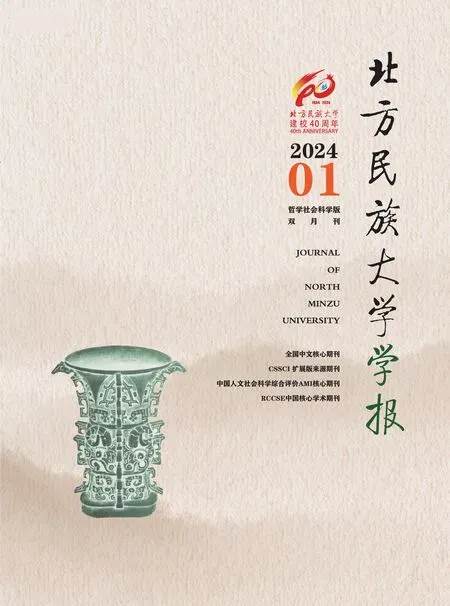巴迪欧本体论思想及其对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启示
符 俊,尉迟光斌
(汉江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十堰 442000)
哲学作为反思人类根本问题的学科,其中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哲学家们围绕本体论问题不时地、反复地展开讨论,从而使不同时代的思想者基于各自时代的知识累积而拓展出各个时代的思想空间,为各个时代的进步探寻一种新的可能。法国哲学家巴迪欧对本体论的探讨即是如此。20 世纪,在哲学家们纷纷高喊哲学已经终结之时,巴迪欧逆势而上,借助现代集合论数学科学最新成果,把对西方哲学本体论的探讨提升到真理本体的视域,通过批判“计数为一”的西方本体论哲学传统,以超越百科全书的“不可辨识之多”和主体介入的逻辑为事件的发生和真理的诞生贡献了新的本体论哲学智慧,为共产主义真理时代的来临提供了新的逻辑论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从人类历史的长河看,中国的进步堪称人类奇迹,成为人类实践和人类认知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党的二十大更是提出,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实践探索和十八大以来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大中国特色和九大本质要求。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话语并未像中国实践那样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成功的事业离不开真理的话语支撑,所以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是我国理论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巴迪欧的本体论思想可以为之提供一个重要视角。纵观人类历史,从巴迪欧真理本体论意义上看,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以中华民族为集体主体而进行的实践创新,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历史性变革事件,中国话语代表着人类知识体系总汇中的共产主义真理,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可借助一套巴迪欧真理主体意义上的忠实程序。
一、巴迪欧从对西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中创建数学本体论
在《存在与事件》“导论”中,巴迪欧指出,当今世界哲学的症候是,海德格尔被视为最后的哲学家,英美的数理逻辑保留了科学理性的思想范式,笛卡尔的后主体学说大行其道,形而上学的思辨体系广受挞伐;但从时代际遇看,我们正处在继古希腊和伽利略之后的第三个科学时代,这是马克思、弗洛伊德和拉康掀起的第二个大写主体时代,也是消解了真理与知识关联之后真理学说的新时代[1]10。有鉴于此,巴迪欧对本体论的探讨依然沿着这三个思想轨迹展开,即像海德格尔那样重新定位本体论,充分利用弗雷格—康托尔数学革命开启的方向,坚持运用现代主体学说,在纯数学的形式中设定本体论,把主体融入本体,将事件引向真理,绘制新时代的思想参照系。
沿着重建本体论科学的思维轨迹,巴迪欧首先检审了西方传统存在论。古希腊哲学从探讨世界本原开始,或归之为水,或归之为气,或归之为火,古希腊人把世界万物归为一种最初存在的运思方式,构成了西方传统本体论的创始形态。在巴迪欧看来,这种运思方式就是在寻找“一”,这种以“一”整合世界的思维方式本质上就是“计数为一”的运算。自柏拉图迄今的西方哲学皆是如此。柏拉图的理念就相当于计数运算的“一”,近代的本质主义也是“一”的逻辑布展。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说:“如果不是‘一个’,那就什么都不是。”[2]574此处的“一个”就是柏拉图理念概念的逻辑符码,相当于计数运算的“一”。近代本质主义建基于柏拉图理论,也是“一”的逻辑运算。这种把存在之所为的存在归为“一”的范式建构了西方哲学的“巴门尼德式”布局。
在巴迪欧看来,正是柏拉图的“巴门尼德式”布局注定了西方传统本体论的“病灶”。按照存在之所为的存在只是本体存在的逻辑,如果存在的本体是“一”,那么,与之相对的“多”就是非存在,但思维的悖论是,若“多”不存在,何以有“一”,进而,若“多”先于“一”存在,“一”如何作为本体存在。巴迪欧说:“没有一,只有计数为一。”[1]34巴迪欧认为,本体的“一”只是一个数字,作为本体之“一”只是在进行“一”的运算,“一”并不存在,“多”才存在。巴迪欧所运思的“多”绝非“一”之下或相对于“一”的“多”,因为这样的本体并没有逃离“一”的逆运算,本体之“多”是在被“一”计数为诸多之前就已存在的“多”,是未被纳入“一”运算的“纯多”。“如果存在本体论,本体论必然成为多之为多的科学。”[1]40
为了进一步阐释本体之“多”,巴迪欧引入了“连贯多元”和“不连贯多元”的概念。若“多”接受“计数为一”运算,则这个“多”是“几个一”之“多”,这样的“多”是“连贯多元”。若“多”只是呈现而作为“一”的前项,此“多”则是“不连贯多元”。“在呈现中,不是一的东西必然是多。”[1]35相对于“计数为一”,“诸多”运算连贯起来,而“诸多”之“多”因未被运算,是不连贯的。巴迪欧认为,从“计数为一”的机制说,先有未运算的不连贯之多,后有经过运算的连贯之多;从计数的逆运算看,正是由于“不连贯多元”的不可还原的性质让计数得以发生,产生了“连贯多元”。巴迪欧从对运算逻辑机制的反思中建构了自己的新本体论,“本体论就是这种不连贯多元的独一无二的理论”[1]40。
巴迪欧试图极力摆脱的是西方哲学那种“计数为一”的算法机制,因为巴迪欧认为“计数为一”之“一”代表了人类所有的知识体系。“计算为一”就是指用人类已经产生的某一个概念或观念对世界的整体把握。对于人类知识体系而言,“连贯多元”就是“可辨识之多”,而“不连贯多元”就是无法被人类知识体系认知的“不可辨识之多”。巴迪欧在《存在与事件》“导论”中已表明其对本体论的讨论是沿着三个路线进行的,其中之一是沿着海德格尔返回古希腊对存在本体重新定位的路线,但是在巴迪欧看来,海德格尔通过诗的非确定性语言来颠覆一切确定性而构建起来的“诗性本体论”否定了对本体论规律的把握,本体论应该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它具有最严格的规律。巴迪欧意在建构一种既有严格规律,又脱离“一”之运算逻辑的本体论。若真如此,那么就有一个难题摆在巴迪欧面前:人类都是以话语来言说的,所有理论的构建都离不开概念,那么新的本体论究竟用什么样的话语才能摆脱已有概念或语言的算法呢?“哲学必须思考的东西是不可思考的,亦即哲学在无法通行的死局中穿行。”[3]8
巴迪欧解开这个死局的办法是通过数学集合论中的公理体系实现的。数学中的公理问题是古希腊逻辑学创始人亚里士多德最先讨论的,他把公理定义为从直接观察得来的不证自明的道理。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列出了五个公理,比如“整体大于部分”等。到19世纪后半叶,随着对有理数和实数等问题的讨论,数学的公理化运动日益兴盛。“就像数学家希尔伯特说的那样,几何中的那些点、线、面以及其他元素,可以用桌子、椅子、啤酒杯以及别的什么东西来代替。”[4]174在巴迪欧看来,数学不展现具体对象,但并非空洞的游戏,自成秩序的数学公理是不需要人为制定规则的,数学中的自由变量使用拉丁字母“α”“β”等可以避免“一”形式的命名或下定义的缺陷,而且本体上的不连贯性经过现代集合公理体系转变为本体论上的连贯性。“本体论,多的特殊的不连贯性的公理体系,通过将所有的不连贯性变成连贯性,以及将所有的连贯性变成不连贯性,而把握了多本身。”[1]43在某种程度上,巴迪欧通过数学创造了一种以原初不连贯而自明性连贯的本体论辩证法。
巴迪欧对本体论的逻辑论证是在公理体系集合论下展开的,其中关键的一步是把逻辑上的“不可辨识之多”等同于公理体系集合论中的空集。根据空集公理,空集存在于一切集合中,是一切集合的子集。幂集公理规定任何集合都有子集,子集又有子集的子集,子集的子集又有子集的子集的子集,以至于无限。同样,根据正则公理(奠基公理),所有非空集合α 中至少有一个这样的元素β,它与α本身的交集为空集,无论序数集合还是幂集集合,如果不断回溯,它们最终都会回溯到一个奠基的点上,而这个点就是空集。在回答雅克·德里达质疑“多”的存在是否有一个终点的问题时,巴迪欧说:“是的,存在一个终点。但是这个终点并非一个原初对象,或者一个原子般的要素,它并不是大写的一的形式。这个终点必然是一个多元。这个多元是并非多元的多元,一个作为虚无的某物,一个空,一个空的多元,或者说,一个空集。”[5]82通过集合论与“不可辨识之多”的缝合,巴迪欧创建了数学本体论。
二、巴迪欧从数学本体论转向事件哲学
作为欧陆哲学的发展者,巴迪欧把“纯多”与“空”缝合的思想与黑格尔的本体论思想有着明显的联系。黑格尔是把“有”作为存在论的开端,但是在黑格尔那里,作为存在本体的“有”是“纯有”,这种“纯有”就是无。黑格尔说:“这种纯有是纯粹的抽象,因此是绝对的否定。这种否定,直接地说来,也就是无。”[6]192“只有就‘有’作为纯粹无规定性来说,‘有’才是无——一个不可言说之物。”[6]193黑格尔本体论关于“无规定性”“纯有之无”,与巴迪欧的存在本体之“纯多”“不可辨识之多”“空”等思想如出一辙,但是巴迪欧认为,黑格尔从“有”的角度来把握存在,本质还是一种“计数为一”,“在根本上,黑格尔特有的本体论上的困境集中在他坚持认为存在着太一,或者更为准确地说,他认为呈现生成了结构,即纯多自身中就保留着记述为一的结构”[1]200。
总体而言,巴迪欧重建的本体论是要打破西方传统本体论那种本体“计数为一”的逻辑,但巴迪欧本体论的旨趣并不全在于此,他关注的是这种本体论如何跃迁到现实中,实现从数学本体论向事件哲学的转变。为此,巴迪欧在集合论逻辑下提出了一对概念:“情势”与“情势状态”。在集合论,“属于”(用符号“∈”表示)标识元素与集合的关系,表示某一个事物是某一集合的元素,“包含于”(用符号“⊂”表示)标识集合与集合的关系,表示某一集合的所有元素包含在另一集合中。巴迪欧把集合的这种因“属于”关系而形成的结构称为“情势”或“原初结构”,把这种因“包含于”关系而形成的结构称为“情势状态”或“元结构”。“情势”的原初结构与“情势状态”的元结构之间既联系又不联系。如果一个“多”既“属于”某个集合,又“包含于”其子集集合,表明这个“多”在“情势”和“情势状态”中被两次计数,在“情势”或“原初结构”中的第一次记数称为“展现”,在“情势状态”或“元结构”中的第二次计数称为“再现”。但真实的历史是“展现”“再现”并非同步,在一定的“情势状态”中会形成三个基本项,即“一般项”(既被展现又被再现)、“赘余项”(只被再现而不被展现)、“独有项”(被展现而不被再现)。巴迪欧又把展现和再现形成的情势论区分为“自然情势”“中性情势”和“历史情势”,其中,“自然情势”中所有项都是“一般项”,表现为一种稳定的自然状态;“中性情势”不涉及生活和历史问题,是一种浑浑噩噩的懵懂状态;“历史情势”是一种不稳定的、非自然的状态,相对于既被展现又被再现的“一般项”,“历史情势”中存在着被展现却不被再现的“独有项”。
巴迪欧说:“对于实存之存在,属于和包含于有着无法化约的断裂。”[1]108借助集合论“包含于”相对于“属于”的绝对溢出,巴迪欧把实存本体与“情势”和“情势状态”联系起来,把历史情势中实际存在而不被再现的“独有项”视为“不可辨识之多”。巴迪欧模仿数学中“位”和“点”的概念创造了一个新概念——“事件位”,使历史情势成为巴迪欧“事件”出场的重要概念。他说:“我将会把这种完全异常的多称之为事件位,即一个多,它没有元素展现在情势之中。”[1]217这个“位”之多是属于原初情势的元素,而非情势状态的元素,“位”之多自身被展现,但“位”之下的元素未能被展现。巴迪欧把这种“位”的情况比作一个法国家庭:如果其中一个家庭成员是黑户,该家庭虽登记注册,但其个人未登记入户,只能非法单独行动,那么这个家庭被展现又被再现,但家庭中的这个成员却未被展现,这个成员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却是未被计数为“一”的“多”,一个非在的存在。根据巴迪欧的本体论逻辑,“位”里的这个“多”就处于“空”的边缘,处于“位”的家庭中的这个成员“多”有可能发生一个事件,让人们发现未被注册的这个人的存在,真实存在的本体就在“空”之“位”上凸显出来。
巴迪欧认为,“位”只是提供了事件发生的前提,要让事件发生还离不开主体的介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巴迪欧依然使用的是公理集合论中的逻辑证明。选择公理提出可以从诸多集合选择一个“多”,组成一个新“多”的集合。当集合有限时,选择没有问题,但是当集合无限时,由于选择意味着无限运算,选择函数此时是漂浮不定的,这意味着由选择函数而组成的“多”并不确定,需要某种介入。巴迪欧说:“在本体论之内,选择公理将介入的断言加以公式化。”[1]283“选择公理本身就是介入行为的特有呈现形式的本体论陈述。”[1]287选择公理表明了主体介入的逻辑必然。借助保罗·科恩的数学力迫法,巴迪欧明确了使不可辨识之“多”得以凸显的主体作用。“主体力迫地生产了包含于情势之中的不可辨识之物,它不可能摧毁情势。主体所能做的就是生产出之前无法决定的如实陈述。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我们的主体的定义:支撑一个忠实的力迫,它用不可决定的决定阐明了不可辨识之物。”[1]514
事件位提供了事件发生的可能,主体介入让可能事件成为现实事件,从而把真实的本体存在凸显出来,而这个由事件凸显出来的本体经过从有限到无限的类性延展,就演变成了真理。巴迪欧“将事件【介入】与忠实程序【关联的运算符】之间关联的过程本身称之为主体”[1]297,“忠实主体谋划的身体的当下时刻就是一个真理的新时代”[5]123。巴迪欧强调,主体介入事件的逻辑旨归在真理,他把真理分为科学、政治、艺术、爱,其中爱的真理主体是个体,艺术和科学的真理主体是混合主体,而政治的真理主体是集体主体。从事件生发到真理需要一套忠实的主体程序。忠实程序主要有三个步骤:一是对事件的命名;二是进行调研,把关联与事件、非关联与事件逐项汇聚;三是进行类性延展,把有限之物延展至无限,使真理得以诞生。巴迪欧从数学本体论转向事件哲学是从抽象的哲学逻辑转向现实的真理逻辑,尽管他在论证时使用的依然是数学集合论的方法。
三、巴迪欧重建本体论哲学的评价与反思
整体来看,巴迪欧在处理本体论问题上的突出特点就是将数学进行到底,他的整个讨论都立足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一”与“多”的问题域。不同于海德格尔批评西方哲学把存在者指认为存在的思想,巴迪欧认为西方传统哲学把本体存在归结为本质存在,实际上是计数“一”的运算,真正的本体存在是计数前的不可辨识之“纯多”,此“多”因其未被纳入“一”之辨识,实为“空”,此“空”并非经验对象上的真空,而只是未纳入“一”之运算的“乌有之空”,这就是集合论中的空集,而空集是所有集合的基础,这意味着世界上所有存在都基于这个本体之多。接着,巴迪欧从集合论“属于”和“包含于”的辩证关系中论证溢出是逻辑的必然,进而,巴迪欧从选择公理和埃斯特定理指出溢出的数量确定需要主体的介入,科恩的力迫法明确展现了这一逻辑。整体上,巴迪欧的数学本体论逻辑是明晰的:真正的存在本体是未纳入“一”之运算的“多”,在数学逻辑上,此“多”就是集合论中的空集,但公理体系集合论发展的成果证明此“多”无法自动建构,自动建构是康托尔—哥德尔明晰数学的逻辑,此“多”之出现需要主体介入,而主体介入的此“多”在历史情势中实际上就是一个事件,经过主体的一系列忠实程序,经过有限向无限的类性扩展洗礼,这个“不可辨识之多”本体最终演变为一个新的真理。我们该如何评价巴迪欧以数学重建本体论的哲学努力呢?
首先,在解构主义盛行的年代,本体论遭遇集体挞伐,巴迪欧却逆势而上,试图借助现代数学重建具有最严格规律的本体论,这至少体现了巴迪欧作为一个哲人的担当。本体论被称为“第一哲学”,可以说是哲学皇冠上的明珠,每一位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都试图去触碰这颗明珠,以探寻人类最高智慧。俞宣孟在《本体论研究》第三版“前言”中说:“读西方哲学而不及本体论,就好像是进庙宇而不见菩萨。”[7]2本体论作为西方哲学的概念,从西方第一个哲人泰勒斯提出水是世界的本原以来,一直是西方哲人从事哲学研究的主导范式,但是我国哲学界对本体论的认识并不一致,尤其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本体论这一问题,至今没有定论。有的学者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物质本体论,有的学者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本体论,还有学者主张劳动本体论,高清海和俞宣孟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本体论。如果像蒯因在《论何物存在》中把本体论作为促使一些理论组织成为一个体系的最根本的概念结构,那么这确实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域,但是若从世界本原问题所关注的存在与思维之关系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维的产物,肯定有其思维产生的本体存在,所以无论从世界本原的角度看,还是从相对地先于思维产生的逻辑考量,存在必然有其本体存在。然而,巴迪欧本体论紧紧抓住西方传统哲学中已有概念“一”之运算的死穴,试图完全依赖非常规语言的数学符号,把本体存在逻辑地定位于所有语言概念之前的状态,这至少从认识论层面提供了重新打开本体论问题的一把钥匙。
其次,对于巴迪欧是否彻底解决了本体论问题,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立场上说,他既解决了又没有解决,因为其思想的深刻中免不了潜存着某些偏狭。比如,巴迪欧选用现代数学的公理体系集合论探讨本体论问题,意在使本体论讨论缩离语言而规避人为的规定,这可以说是独辟蹊径,而巴迪欧把存在本体与隶属于认识论范畴的真理关联起来,指向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谈到的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但是他却把二者混为一谈,把隶属于认识论的真理等同于客观存在本体,反映出其思想受到现象学运动的影响,试图逃逸本质主义,最终却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
再次,巴迪欧从数学本体论转向事件哲学,最后落在真理问题上,但是他在《存在与事件》“导论”及其后的《哲学宣言》《第二哲学宣言》中,都把真理局限于爱、艺术、科学、政治四个领域,既不讨论四者之间的关系,也不说明何以只有四类真理的原因,这表现出其某种理论武断。在真理的类性扩展程序中,巴迪欧特别反对“百科全书决定因子”对“不可辨识之多”的宰制,但其最后把真理分为爱、艺术、科学和政治,一定程度上表明其重建的本体还是未能逃出常见知识分类的辨别和运算。巴迪欧试图把存在本体定位于人类知识体系之外的运思,与欧陆哲学家借助宇宙大爆炸理论探讨世界“奇点”问题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另外,从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角度看,巴迪欧讨论真理时特别强调的类性扩展在唯物辩证法下并不复杂,矛盾的特殊性中蕴含着普遍性,个性中有共性,任何真理的认知都是从特殊到普遍的辩证发展过程。
实践无止境,认识不停息,每一代人的认识都是背负着时代之壳前行的认识。不管怎样,巴迪欧把存在本体借助事件和主体的显现诠释为一个新真理诞生的思想,可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自近代以来,西方率先出现的工业革命借助资本主义的资本增值运动让西方势力扩张全球,西方化变成了世界化,在游走于国际舞台上的西方人的潜意识中,西方知识体系就是世界知识的全部,世界各地的非西方实践皆被标识为“愚昧”和“非文明”,由这些实践形成的知识体系一直不被认可和接纳。当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但是一些势力借助西方话语霸权,不断解构着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为此,我们需要从理论层面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巴迪欧从本体论层面开启的真理话语建构是可以借鉴的资源。
四、巴迪欧本体论哲学思想对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启示
理论话语是基于实践成就并引领实践行动的逻辑表达、价值阐述。从巴迪欧本体论的角度看,新的概念诞生于新的存在本体事件的发生,中国话语体系展现的是中国特色的实践成就和中华民族的价值表达,代表着社会主义真理在东方国家的诞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和话语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8]156。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三大问题,“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9]。因此,无论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立场,还是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角,构建中国话语体系都是中国理论工作必须完成的任务。巴迪欧重建本体论从存在本体推演到事件、真理的逻辑进路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首先,巴迪欧对西方传统本体论“一”的反对,与我国冲破西方话语体系、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西方传统本体论是把“一”作为存在本体,未被纳入“一”之下就是非存在,巴迪欧认为此“一”并非存在本体,此“一”只是人为的运算规定。巴迪欧的这一本体论思想实际上揭示了国际舞台上西方话语的本质及其打压发展中国家的事实。长期以来,西方话语被视为世界知识的代表,未被纳入西方知识话语体系的存在就成了非存在。在西方话语下,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就不值一提,甚至是失败的,没有西方“一”的计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不会得到世界的承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10]327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关系到中国成就是否被认可,关系到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理念能否得到广泛传播。
从巴迪欧新本体之真实存在的角度看,中国话语代表的是亿万中国人民以5 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为沃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民族的生存发展而进行的社会实践。中国话语是中国成功实践的真理表达。尽管中华文化一度风靡欧洲,但是伴随着西方科技和资本的扩张,中华文化一度被遮蔽,西方文化操持了对全球文明的计数为“一”的运算,中国成为“属于”人类文明大家庭集合而不被再现的“不可辨识之多”。然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导的历史情势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体中国人民经过长时间艰苦奋斗,实现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功,中国这个“不可辨识之多”以西方人不可理解的方式创造了一个人类的历史事件。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本真存在,其话语是人类知识体系中一个新的真理。
其次,巴迪欧把数学本体论转向事件本体论,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主体的介入,在主体介入下事件得以命名,经过主体的忠实程序,事件生发为真理。这与我国国际话语权建构要求凝练概念,坚持中国特色,把中国成就转变为中国真理的逻辑是一致的。在巴迪欧重建本体论的逻辑中,主体并非人或某个群体,而是一种忠实于事件的程序,在主体程序下,“不可辨识之多”之存在演变为事件,进而从具体的本体存在演进为无限性的真理。主体介入的第一个程序就是对事件命名,命名是一个大二集的集合,既有原情势的知识归类,也有对不可辨识之物的总结。这与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提出和命名是一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命名既要探寻世界现代化运动的普遍规律,也要考量中国现代化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规律。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10]346
巴迪欧认为,真理是主体围绕事件而操持的最后结果,没有主体就没有真理,主体忠实于程序本质上是一种战斗,围绕忠实展开的工作不是专家的工作,而是战士的工作,主体的忠诚决定着真理的诞生。著名哲学家齐泽克说:“在巴迪欧看来,事件是一种被转化为必然的偶然性(偶然的相遇或发生),也就是说,事件产生出一种普遍原则,这种原则呼唤着对新秩序的忠诚和努力。”[11]212巴迪欧的这一思想启示我们,坚守忠实主体程序要像忠实的调研程序那样,区分出关联于和非关联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诸项。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中国特色和九大本质要求的归纳就是巴迪欧事件主体意义上的调研程序。除此之外,巴迪欧还区分了忠实、反动和蒙昧三种主体,我们既要坚持忠实主体的工作,又要注意反动主体,即原有西式现代化的“计数为一”的程序,还要注意蒙昧主体,即其他少数发展中国家偏执于保守逻辑,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遮蔽。
再次,巴迪欧重建本体论的目的在于确保新的真理的诞生,这启示我们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过程中要注意从真理的意义上展开言说。巴迪欧说:“本体论与真理哲学并行不悖。”[1]440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人,巴迪欧所谓的政治真理就是指共产主义的真理。巴迪欧说:“理念以真理的真实性的象征呈现某种事实。这就是共产主义理念如何是革命的政治及其政党刻写在历史意义的再现之中,而它的必然结果则是共产主义。”[12]“为共产主义假设提供一种有力的主体性存在,是我们今天要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完成的任务。”[12]今天,中国式现代化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化在21世纪的成就,象征着开创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本体存在,中国话语本质上传递的是共产主义的真理。
因此,要想有效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使其在世界知识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就需要我们善于利用象征性投射,把中国地域性的真实转化为世界共产主义的象征叙事,让更多的个体转变为忠实于共产主义真理的主体,使地域性的事件类性延展或脱俗发展为共产主义真理,促使原初的西式现代化的历史情势演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起点的共产主义时代的历史情势。怀特海在《观念的冒险》中说,吉本的《罗马战争史》既讲述的是罗马帝国的历史故事,又展示的是18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这一白银时代的种种普遍观念[13]9。“真理之源(origine)就是事件的秩序。”[3]15同理,今天的中国话语既讲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同时也标识着人类迈向新时代的普遍的真理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