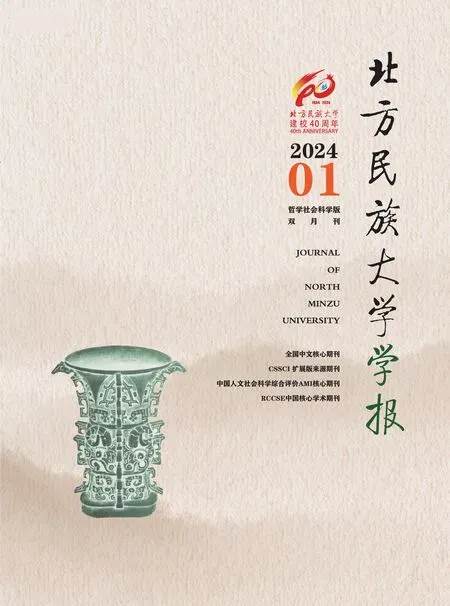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机制
张 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1]如何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逻辑,这是编好用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试用本)(以下简称《概论》)①《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试用本)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撰的教材,该教材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引,以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使命,以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主旨,以“四个共同”“四个与共”为主线,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漫长发展历程为经线,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大维度的共同性为纬线,科学解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重大问题。的关键问题之一。
在《概论》教学过程中,之所以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逻辑问题,这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需要。在如何看待中华民族的问题上,海外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即中华民族共同体也是所谓的“帝国”。有学者指出,许多西方学者和人士普遍存在一种错误的观点,“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近现代国家的成立,都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从过去的帝国如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或者从列强建立的殖民帝国中分离出来、独立建国的结果,那么中国和苏联就曾经是两个少见的例外。而在苏联瓦解之后,中国变成几乎唯一的基本保留其帝国时代疆域版图的现代国家。西方学者中因此有人把这种所谓‘令人吃惊的统一’看作‘中国的神话’。在他们看来,近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努力,很像是在把一件现代民族国家的紧身马甲,硬套到帝国的身躯上去。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政治学家白鲁恂说:‘以西方的标准看来,今日中国就好像是罗马帝国或查理曼时代的欧洲一直延续到当前,而它如今却又在行使着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功能’”[2]189。按照这种观点,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披着民族国家外衣的帝国。言下之意便是,既然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所谓的“帝国”,就应当予以肢解。近年来,西方世界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诸多不实指责,例如,鼓动我国某个民族推动所谓的“民族自决”,又如,把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理解为所谓的“殖民关系”。这些错误言论的根源都在于把“从帝国裂解为民族国家”的特定历史经验普遍化为某种“政治规范”,由此炮制出种种错误言论。应当说,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要想从根本上驳斥错误观点,就应合理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机制,这样才能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所谓“帝国”的本质区别。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有其坚实的物质基础。先从地理环境来看,《概论》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地理条件,“青藏高原隆升导致三级阶梯式地貌,在阶梯过渡带及海陆交接处,形成的西北荒漠绿洲交错带、西南农林交错带、东部海陆交错带、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不同时期人们活动迁徙的地理空间,是孕育复杂多元人文样态的自然环境。这一复杂的地理结构同时孕育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和对外开放的包容性。西部地理结构内聚,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使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东流,生活在西部的人群,向东部大平原发展比翻越高原峻岭向西发展对自身更为有利。北部地理结构开放,草原戈壁连接蒙古高原与欧亚大草原,使得北亚与东北亚的游牧渔猎人群多次南下,中原农耕人群多次南迁北上”[3]30。中华民族形成的地理结构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运动方向,即不断向内凝聚,多元融为一体。
再从经济条件看,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地带相比,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显著特点在于,作为中华民族主体部分的汉族所处的中原地带,在经济富裕和社会文明程度上始终高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四周边疆地区。对此,不妨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在此维度上展开必要的比较。先看西欧文明,西欧文明所在的地中海地区因为地形破碎而生存空间狭小,自古希腊时代开始就已出现“人多地少”的矛盾,西欧只能采取对外殖民的方式,因而西欧文明具有很强的扩张性;再看阿拉伯文明和东正教文明,这两种文明地处生存环境更为恶劣的沙漠或高寒地带,因而不得不对外开拓生存空间。相比之下,中华文明则具有“中原富于周边”的地理优势,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是游牧民族向中原地带索取生存资源,而非中原地带对外扩张谋求生存空间。所以,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看,华夏中心地带与边疆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呈现出“厚往薄来”的鲜明特征。仅此一点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便与所谓的“帝国”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所谓的“帝国”模式中,帝国中心不仅对帝国边缘乃至外部地区在政治和军事上进行武力征服,同时也在经济上进行殖民统治和资源掠夺。相比之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没有武力征服和经济殖民的历史基因。
从历史上看,中原地带之所以不对外扩张谋求生存空间,这是由经济生产方式决定的。我们应当看到,在中国历史上,随着人口的增多,中原农耕地区也不乏人多地少的生存困境,何以中原地带不像古希腊城邦那样对外扩张呢?这不得不从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农耕文明在生产方式上的显著特征在于“地理依赖性”。对中国而言,在自然因素的支配下,农耕文明只能局限在由400 毫米等降水量线所决定的长城以南地区。由于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带无法实行农耕文明生产方式,农耕文明只能在小农生产的条件下“高度内卷”,而不是对外拓殖经济版图。更为重要的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动竟然产生了两种文明在经济上彼此依赖的耦合互补结构,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根基。
一方面,农耕文明在生存空间、富裕程度、发展水平上明显优于游牧文明,因而为游牧文明提供了游牧民族必需的生存资料,而这也正是游牧民族之所以不断南下掠夺生存资源的根源所在。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游牧文明的南下掠夺,给中原农耕地带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安全压力。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凭借着战马资源获得了强大的军事机动性和杀伤力,相比之下,农耕文明由于战马的匮乏而处于劣势。正是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这反而倒逼出了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经济需求,即战马的需求。于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形成了彼此依赖的耦合结构。这意味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动具有深刻的物质循环基础。这一点已经为茶马互市的历史所验证:马对农耕文明而言是军国大计,茶对游牧文明而言则是牧民生计,二者彼此依赖,互通有无。更重要的是,经由以茶马互市为代表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从冲突走向融合,中华民族也由多元走向一体。对此,《概论》意味深长地指出,“任何二分法理论如‘游牧—农耕’‘内亚—汉地’都无法正确描述中国,因为中华文明不是多元文明对立冲突的结果,而是多元文明以融合会通解决对立冲突的产物。正是在这样的文明基础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开始孕育生成”[3]32。
农耕与游牧两种生产方式的彼此互动,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经济共同性上的一个缩影和例证。从总体上看,《概论》准确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的经济基础。“历史上,中原农耕区、西域绿洲沙漠区、塞北草原区、东北渔猎农牧区、西南山林河谷区、东南丘陵滨海区之间生产方式各异,经济互补性强。如游牧区域需要农耕区域的粮食、丝绸、绢帛、瓷器、铁器、茶叶与盐巴,农耕区域需要游牧区域的马匹、皮革、畜牧产品。这些区域之间的衔接地带,形成了河西、藏彝、南岭、苗疆、武陵、辽西、天山等民族走廊。这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通要道、贸易通道与迁徙要道,进一步与北方、西南、海上丝绸之路交会连接,将各区域各族群凝聚成难以分割的经济共同体。”[3]36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基础不仅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等突出特性,也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机制是四周融入中心的向内聚合,而不是中心征服四周的对外辐射。因此,与用武力对外征服的罗马帝国、蒙元帝国等扩张模式相比,中华民族共同体则是聚合模式,具有更为温和的和平性与更为强劲的内聚力。在此意义上,中华民族共同体便不同于其他帝国,历史上的中国尽管存在着封建帝制,但也无法将其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帝国。
四周融入中心的向内聚合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的商贸往来,也鲜明地体现在政治领域中的政权更迭。《概论》意味深长地指出,“中国历史上既有中原王朝继承正统,也有边疆族群入主中原继承中华文化成为正统。历史上,中华文明不是‘中心永恒统治边缘’的帝国模式,而是‘边缘可以竞争中心’的共同体模式”[3]34。自夏以后,出身东夷的殷人建立了更加恢宏博大的殷商文化。源自西北而又与羌、戎部族有着密切关系的周人继之而起,建立了周代,发展影响深远的礼乐文明。周文王便是孟子说的“西夷之人”。曾被称为“西戎”的秦国统一天下建立秦朝,曾被称为“南蛮”的楚人对建立汉朝有极大功劳。秦汉“大一统”王朝正是由曾经边缘却奋力继承发展中华文化的“大夷”完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边疆族群入主中原后都积极维护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4]自秦汉以来,中央集权、政治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政治的主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士族门阀政治是偏离“大一统”体制的“变态”,反而北朝更符合“大一统”主流的“常态”。更为重要的是,北朝从经济军事到政治制度,从编户齐民到人才选拔,都在抑制门阀豪强,回归中央集权。北朝的均田制、府兵制、三长制、考课制为隋唐更高水平的“大一统”奠定了制度基础。无论是辽金西夏的“南北一家”,还是元代的行省制度,抑或清代的“边疆与内地一体化改革”,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对“大一统”制度的创新贡献。在此意义上,以“大一统”为内核的政治共同性是由各民族共同维系的政治共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主流。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传统也决定了我们在处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走自己的路。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5]。
四周融入中心的向内聚合机制使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也能一统天下。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不仅积极维护“大一统”制度,也主动认同中华文化,从而产生了文化共同性。对此,有学者曾指出,当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原地区取得统治地位时,出于用最低成本控制最大利益的理性考量,会主动选择融入中华文明。正如赵汀阳所说,“逐鹿的胜利者们为了保有对优势的精神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合法利用和稳定占用,几乎都理性地选择了周朝创作的天命传承神话来解释自己的王霸故事,将自己的王朝加入以黄帝为始的悠久政治传承叙事中,成为这个长篇故事的一章节,以此解释其政治合法性。这是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最低成本策略,也是最高收益策略,很难想象逐鹿胜利者们会拒绝这种政治神学”[6]49。这段分析大体不差,然而值得追问的是:为何少数民族主动融入中华文明,运用周人创制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观就能获得政治合法性而被中原汉族所认同和接受呢?对此问题,前人早有解答。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这是中国思想正宗……它不是国家至上,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于国家种族,仿佛皆不存彼我之见;而独于文化定其取舍”[7]162。只要少数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融入中华民族,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便由他者转变为自己人。自古以来,既有以夷变夏的现象,也有以夏变夷的现象,不同民族完全可以互相转化而彼此融合,其中的关键在于文化认同,而非种族身份。“夷夏之辨”固然是中国历史存在的客观现象,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主流地位的则是“夷夏之变”,“夷夏之变”的关键在于文化认同打破了族群壁垒。所以,“夷夏之变”进一步推动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由此催生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共同性。
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生产方式到社会生活,从政治一统到文化认同,无不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独特形成机制,即四周融入中心的向内聚合。值得注意的是,四周融入中心的向内聚合机制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集中体现。与中心向四周扩张的帝国模式相比,向内聚合机制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同时,向内聚合也是少数民族主动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越是包容,越能得到认同,越是得到认同,越能维护统一,这又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凝为一体、牢不可破。在维护“大一统”方面,少数民族作出了卓越贡献,从北朝三长制、均田制、府兵制到元朝的行省制、清朝的边疆与内地一体化改革,少数民族让“大一统”制度不断升级迭代、历久弥新,这又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最终,向内凝聚的形成机制确保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分久必合”“衰而复起”,进而保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所以,向内聚合机制具有深刻的中华文明意蕴。
正因为四周融入中心的向内聚合,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始终遵循“合的逻辑”,从“各民族”不断融合为“大中华”;反观西方民族国家,则是遵循“分的逻辑”,从“大帝国”不断裂变为“各国家”。在此意义上,西方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无法解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机制,也就不能随意套用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上。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8]显然,西方逻辑解释不了中华民族,只有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中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实现精神独立性。在这方面,《概论》在许多重大观点上都有类似的尝试和探索,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并认真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