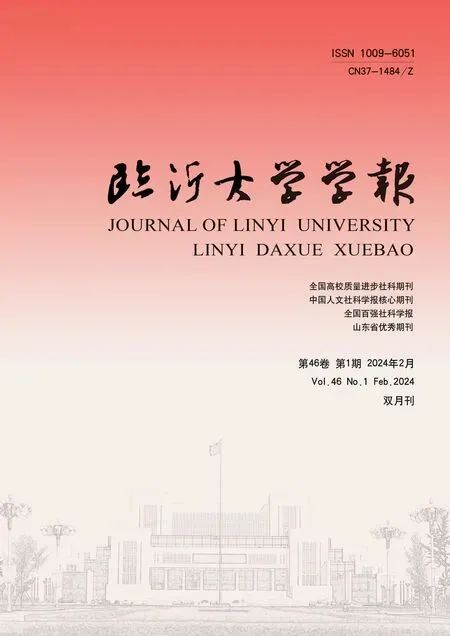明清女性戏曲史的多维度书写
王馨蔓
(太原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中国古典戏曲成熟于宋元时期,明清之际更是达到了巅峰。 女性群体作为戏曲艺术的关键推动者,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回顾戏曲史的书写,女性与戏曲的关系探讨常常存在着逻辑与历史两个角度的纠缠。 学者王宁发现:“在探讨戏曲形成时,多是从构成戏曲的要素入手,从逻辑的角度来研究要素的融合。 这样的研究,可以说是‘逻辑的’而不是‘历史的’。 ”[1]引言4 戏曲的形成原因并非单一,而是复杂综合的,因此,文本之外的活动对戏曲史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女性在戏曲史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女性参与戏曲活动的线索日渐清晰。
明清女性戏曲史的书写不要以“明清女性戏曲史”来定位,最好以“明清女性与戏曲”作为研究对象,才能使研究视野更加开阔,不仅能够关注明清女性生活的文化环境,而且还能具体深入到对女演员与女读者的关注以及对女性戏曲创作与批评的研究。 一方面,这些研究有助于揭示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对于文学艺术的历史书写无疑是一种有价值的探索。
一、文学史中的戏曲史
戏曲史的研究领域有三个核心关键词:朝代或地域、戏曲、历史。 它们分别对应着三个关键问题:首先,需要确定在戏曲史书写中应选择怎样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其次,从史料出发,如何准确理解戏曲这一概念;最后,以何种视角来叙述戏曲的发展历程。
(一)经典戏曲史研究与两个向度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1912)回答了戏曲史研究中的三个关键问题。该著在王国维的戏曲研究中具有总结性,不仅确定了宋元为戏曲成熟时期,还明确了戏曲的概念,对戏曲本体给出了确切的定义。 他不仅提出了“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2]132,更是进一步提出了“后代之戏剧,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2]33。 王国维通过深入研究戏曲的基本特征,为戏曲的歌舞特点准确定性,为戏曲本体正名,并将之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研究;他还特别关注文本,将戏曲中的歌舞形式、内容以及表演故事的歌舞者都纳入研究范围。这些都为戏曲史的书写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尤其是对于文本的重视,更是成为戏曲史书写的典范。
戏曲史书写视角的多样化使得其研究内容更加丰富。 周贻白在 《中国戏剧史长编》(1960)中提出:“盖戏剧本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不比其他文体,仅供案头欣赏而已足。 是则场上重于案头,不言可喻。 ”[3]他将文本“案头”与舞台“场上”并重,并按时间顺序对戏剧的各种体例进行梳理,将声腔、曲调、排场等内容涵盖其中。可以说,周贻白对戏曲舞台性的重视成为戏曲史书写要贴合戏曲本体特征的研究典范。张庚、郭汉城撰写的《中国戏曲通史》(1980)理论性强,将独立的戏曲艺术置于相关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环境中进行研究,宏大、全面而不失细微、深刻。通过精细的史料梳理,该著以一种整体性视角来审视戏曲,将其视为一种综合艺术,以戏曲艺术本身的规律来观照戏曲史,兼顾文学与舞台,用戏曲的起源与形成、北杂剧与南戏、昆山腔与弋阳诸腔戏、清代地方戏四部分清晰地勾勒出戏曲发展的脉络,解决了“戏曲史尤其是通史写作面临结构均衡的难题:宋元之前和清代花部兴起之后都是只有戏而没有文学”[4]21的问题,为戏曲史研究打开了广阔的大门。
戏曲史研究呈现出两个向度:以案头为中心的向度和以场上为中心的向度。前者“以文本为中心,纵向观察戏曲形态与体制流变,横向聚焦剧本结构、文辞、声律,兼论各时期代表性作家及其风格”[4]20;后者“将戏曲视为‘综合艺术’,戏曲的文辞声律之外,还必须考虑到各时期舞台演出的方方面面”[4]22。戏曲本体研究的两个向度加强了戏曲史书写的“逻辑性”,作为戏曲活动行为主体角色的女性自然隐匿其中。
(二)性别文化思想中的女性戏曲史书写
1980 年代中期,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传入我国,该理论以社会性别为核心概念,主张女性与男性生来平等,并从后天及外在因素出发来探讨影响女性社会地位变化的原因,性别文化视角是其实践与研究的具体化。 波伏娃在《第二性》(1949)中揭示了女性之所以处于“第二性”地位是因为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①。凯特·米莉在《性的政治》(1970)中指出:“性别(即从性的类属着眼的人格的结构)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文化的属性。 ”[5]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女性在心理、性格、价值观和地位等方面都囿于性别身份,并把社会对性别的期望内化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中。 基于对性别文化和文化属性的认知,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女性在戏曲史中的地位。
女性戏曲史研究被冷落在文学史研究的角落里。 谭正璧指出,文学史以诗词为主流而忽视戏曲甚为不妥,认为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1916)、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1927)和《中国妇女文学史纲》(1932)都存在偏颇,那就是“未能超脱旧日藩篱,主辞赋,述诗词,不以小说戏曲弹词为文学”[6]自序1。 文学发展循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所胜”[2]98的观点,“自宋而后,小说戏曲弹词居文坛正宗”[6]。谭正璧在《中国女性文学史》(1935)中增加了多位女性戏曲作家与作品,“戏曲如刘清韵之《小蓬莱仙馆传奇》十种,弹词如朱素仙之《玉连环》,郑澹若之《梦影缘》,周颖芳之《精忠传》,映清之《玉镜台》”[7];后又在《中国女性文学史话》(1984)中以“明清曲家”专章对黄夫人、叶小纨、梁夷素、阮丽珍、林以宁、王筠、吴藻、刘清韵等多位女曲家进行了论述[8]。
谭正璧运用中国本土社会性别理论探讨了非主流文学的戏曲以及缺乏社会话语权的女性,并从外在环境、条件等方面对女性戏曲活动进了研究与梳理,实现了与西方社会性别思想的对接,但他仍保留了重文本的传统。
王宁抛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当我们面对明清戏曲史上的经典文本和经典作家时,是否也应该意识到单纯的文学研究相对于立体戏曲史的单薄和局限?”[9]6他认为:“乐妓与戏剧的关系问题,其实涉及的是戏剧演出的‘演艺主体’问题。所以,我们不仅仅可以从角色的角度展开研究,同时,也可以从戏曲形成的角度,来分析探讨乐妓在古典戏曲形成中的作用和地位。 ”[1]引言3-4 王宁对戏曲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仅从性别文化的角度对生活、文学、思想等多层面进行探讨,而是扩展到从演艺技艺的角度对戏曲艺术进行研究,解决了逻辑地或历史地书写戏曲史时产生的矛盾以及案头与场上孰轻孰重的问题。
当女性作为客观存在出现于戏曲本体研究中时,为遵循严谨的逻辑,需将这一元素隐藏,然而,在案头与场上两个向度上,女性作为戏曲活动的主体无法被忽视。 明清女性戏曲史的书写得益于中国戏曲史的构建所带来的启示:一方面,在戏曲文学案头向度,女性成为关键角色,她们所处的社会、思想、文化和生活背景以及所面临的境遇和状态等因素,都对戏曲史的书写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因素成为揭示戏曲历史发展规律的新视角;另一方面,在戏曲文学场上向度,女演员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她们为戏曲艺术的舞台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使得明清女性戏曲史的研究得以突破平面化,且使戏曲在充实舞台元素后更加立体化。 不难发现,尽管各研究者的关注点不尽相同,但在社会性别思想领域,书写者却已悄然达成共识,共同致力于构建一种女性在场的书写体系。
二、文化环境研究维度
探究明清女性戏曲史发展的文化环境,有利于全面了解明清女性戏曲史发展演变过程及其社会动因,实现与传统文学史的平等交流。
明清女性戏曲史关于性别文化方面的研究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不仅得到了肯定和重视,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明清戏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8)特设“妇女与戏曲篇”来展示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其中,华玮的《明清妇女剧作中之“拟男”表现与性别问题——论〈鸳鸯梦〉、〈繁华梦〉、〈乔影〉与〈梨花梦〉》一文深入研究了四部剧作的表现手法与性别问题,不仅独辟蹊径地挖掘出它们的“拟男”特质,还得出与《牡丹亭》形成遥相呼应对话的结论。[10]作为首届“明清文学与性别国际学术研讨会” 的理论成果, 张宏生主编的 《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2002)收录了多篇涉及明清女性与戏曲研究的论文。 其中,顾歆艺的《明清俗文学中的女性与科举》一文列举了诸多实例,包括传奇杂剧中的女性参与科举的故事[11]34-57;刘楚华的《明清传奇中的魂旦》一文深入探讨了魂旦角色蕴含的象征意义,揭示了其代表的人性解放的内涵[11]71-91;孙玫、熊贤关的《晚明剧作中的青楼女子——略论〈西楼记〉、〈红梨记〉和〈三生传玉簪记〉》一文以三部剧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中的青楼女子形象,认为她们不仅是对晚明“尚情”思潮的回应,更具有既背离理学规范又受父权意识形态束缚的复杂特性[11]182-197;吴淑钿的《超越与异化:〈桃花扇〉中李香君的艺术形象》一文回到文学本身,揭示了《桃花扇》的真实面貌,挖掘出李香君形象包含的深层艺术意蕴[11]532-552。这些看似分散的研究成果描绘了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女性的处境与心境。
李祥林从性别文化理论视角关注明清戏曲的著作 《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2001)探讨了戏曲艺术与性别文化的关系。 该著“强调用性别学和文化学的双重目光审视戏曲,旨在将滋生于东方土壤上的戏曲艺术置放在性别学和文化学有机交织的研究网络中进行不同凡响的阐释”[12]1;其上编“戏曲和女性”部分的“从女性文化看戏曲”和“从戏曲艺术看女性”两章剖析了女性与戏曲之间内在的相通特征。 该著从性别文化的独特视角对戏曲艺术与女性文化进行了深刻的解读,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维度。
“在戏曲研究领域中纳入性别意识,从性别文化视角切入戏曲研究,并非出自异想天开的生硬嫁接,而恰恰是戏曲这东方民族艺术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使然。 ”[12]5在性别文化视角下,明清时期的女性与戏曲在逻辑与历史的叙述中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受到文学史研究的影响,明清女性戏曲研究以文学为侧重点,涵盖了对女性形象和女性角色的分析以及对女剧作家性别文化视角的解读。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拓展和丰富了戏曲研究的范围和内容,也深化了其理论内涵。
三、演员与观众(读者)研究维度
明清时期,戏曲成为一种流行的娱乐方式,也为女性所喜爱,从而为女性接触戏曲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她们不仅可以作为演员上台表演,还可以作为观众或读者欣赏戏曲的魅力。
王宁的著作《昆曲与明清乐伎》(2005)指出,戏曲是一种立体的、综合的表演艺术:“戏曲只有当它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才是戏曲。 ”[9]1该著视野开阔、材料详实,以背景、演出、审美和文学四章篇幅对昆曲与乐伎进行了全面研究,充分强调了江南的地域优势,实现了对“活”的戏曲进行研究的目标。王廷信的《市井青楼中的昆曲演出》一文对青楼女子唱昆曲串演戏的活动进行了梳理[13];徐宏图的《明清江浙戏曲家伎及其艺术成就》一文从提升昆曲演唱水平、构建生旦戏表演艺术体系、舞台折子戏的形成、舞台布景艺术的发展等方面详细阐述了明清江浙戏曲家伎的艺术成就[14];厉震林的《论男性文士的家班女乐》一文揭示了男性文人蓄养家班女乐的深层含义,即以性权利的行为来替代政治权利的满足[15];美国学者蔡九迪的《歌唱的礼物:名妓与明末清初的观众文化》一文通过歌伎与文人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赞扬了名妓将表演当作礼物回报知音的行为,并以《桃花扇》中的李香君为例,描述了她与侯方域道别时,承诺不再演唱《琵琶记》,“从那一刻起她将永远不再演出此曲,她要将它呈现给自己的情人”[16]。
明清时期,在性别文化思想影响下的女性戏曲观众研究重点表现在对《牡丹亭》的接受上,其中“共鸣”“化身”“想象”“情迷”成为关键词汇。徐扶明的《〈牡丹亭〉与妇女》一文通过解读《牡丹亭》中人物的生活环境,揭示出读者与女性形象的共鸣:“那时的妇女们,从杜丽娘身上,看到了她们自己的苦闷和命运,也看到了她们自己的要求和理想,所以,既洒同情之泪,又有所向往,尤其与杜丽娘有着同样不幸遭遇的妇女,更会产生强烈的共鸣。 ”[17]117毛文芳在其著作《物、性别、观看:明末清初文化书写新探》(2001)中专辟“杜丽娘的女性阅读”一章,将女性读者视为《牡丹亭》的闺阁解人,以俞娘、小青、叶小鸾、钱宜为例,分析了杜丽娘在女性读者心中产生的疗愈效果,使丽娘成为女性读者自我影像的化身:“女性正在参与晚明以来的一项文化虚构,那就是浪漫情爱的文化想象。 ”[18]高彦颐在其著作《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2005)中特设“情教的阴阳面:从小青到《牡丹亭》”一章,就《牡丹亭》对“情迷”女性的情教意义作了阐述, 杜丽娘成为一个榜样,“这些才女们在丽娘的希望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对她们来说,情、才、德都是崇高的追求,它们可以完美地与女人作为持家者这一惯常的角色相兼容”[19]。 同样谈到“情教”的是谢雍军的《〈牡丹亭〉与明清女性情感教育》(2008),该著将研究与艺术教育相结合,从《牡丹亭》的至情思想、经典阅读、自然感发、感梦身亡、“发乎情止乎礼”等方面对明清女性的情感教育进行分析,指出在阅读戏曲作品的接受中,《牡丹亭》在女性情感教育方面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审美功能和社会效应。[20]
在对明清戏曲女观众的研究上,有研究者试图对女性观剧的限制进行诠释。 赵山林的《中国戏曲观众学》(1990)中的“妇女观众”一章,从妇女观剧的禁忌、观众队伍的顽强增长、闺阁中多有解人三个方面对戏曲女观众进行了探讨。[21]武翠娟在《古代女性观戏禁忌探究》一文中分析了封建时代对女性观戏的种种约束与禁忌,认为“禁忌之多与惩戒之严恰也说明了女性观剧风气之盛。 在‘观’与‘禁’的相互较量之下,我们感受到的是古时妇女参与演剧活动的热情”[22]。 关于女性观众观剧的场所形式,李静在《明清堂会演剧的形式、女观众与狎旦》一文中指出,堂会观戏中的女性观众具有高度的鉴赏能力,她们最终能成为与男性观众平等观戏的观众,正是始于堂会观剧。[23]
在对明清戏曲女演员和观众(读者)的研究中,学者们不仅思考人们对女伶职业的诟病和女伶身份的畸形问题, 探讨女性在家中与户外观剧的限制以及舆论上受责难等问题,同时也对深闺女子们的观剧、读剧行为给予充满人文关怀的解读。 他们将明清女性的戏曲观赏经历从点到面地与演员和观众(读者)的研究相结合,在关注社会文化环境的同时,以剧作《牡丹亭》为焦点从性别文化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
四、创作与批评研究维度
明清女性戏曲创作与批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最初的个别剧作家及剧作梳理到相对系统研究的过程,尤其在戏曲作品的整理方面成果显著。
明清女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可以分为群体研究和个案研究。在以明清女剧作家群体作为对象的研究中,邓丹的博士论文《明清女剧作家研究》(2008)将女性剧作家视为明清戏曲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仅对王筠、吴兰征和刘清韵等女剧作家进行了研究和考证,还从性别文化角度和社会关怀角度对“私情”“情”进行了分析[24];刘军华的《明清女性作家戏曲之社会性别错位现象透视》一文通过七部剧作分析,发现女性角色往往通过“女扮男装”或“换性”方式表达自我理想和抱负。 明清女剧作家个案研究有孟梅的《戏曲〈乔影〉与吴藻的“才子情结”》、任荣的《清代徽州女诗人、戏曲家何佩珠考论》等。 此外,农艳的《二十世纪明清女性剧作家研究述评》一文总结性地描绘了二十世纪学术界对明清女性剧作家的研究轨迹。[25]随着研究的深入,明清女性剧作家的群体形象逐渐明晰,其剧作与相关文化内涵的挖掘也日益丰富。
关于明清女剧作家的数量,学者们考证得出的答案尽管不同,但数值相差不大。郑振铎在《元明以来女曲家考略》提及“明、清二代的女曲家们也寥寥可屈指数”[26],她们也多为散曲家,剧作方面仅提及王筠的传奇《繁华梦》《全福记》以及吴藻的杂剧《饮酒读骚图》(又名《乔影》)。 徐扶明在其著作《明清女剧作家和作品初探》(1986)中考证明清女剧作家有23位。[17]266-280叶长海在《明清戏曲与女性角色》一文中考证明清女剧作家有22 位,且集中于江浙皖等地,尤其是苏州与杭州,剧作达55 种以上②;并在其著作《曲学与戏剧学》(1999)中以“明清戏曲与女性角色” 为题进行了专章探讨, 内容主要涉及戏曲中的女性角色和妇女问题、女作家的戏曲创作、女性笔下的女性角色等[27]。 华玮在其著作《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2003)中考证明清女剧作家有25 位,现存完整剧作19 种。③刘军华在《明清女性作家戏曲之社会性别错位现象透视》一文中考证明清女剧作家有26 位,作品有65 种。④
明清女性戏曲批评研究集中于对《牡丹亭》的批评上,主要有宏观分析、批评文本整理、女性戏曲批评等。 谭帆在《论〈牡丹亭〉的女性批评》一文中针对《牡丹亭》的女性批评者、批评及其特色进行研究,为戏曲批评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11]295-309;华玮、江巨荣共同整理的《才子牡丹亭》(2008)一书充实了《牡丹亭》的批评文本;江巨荣在《〈才子牡丹亭〉对理学贤文的哲学、历史和文学批判》一文中指出了《才子牡丹亭》的思想内涵、评点特色、优缺点[28];华玮主编的《汤显祖与〈牡丹亭〉》(2005)一书收录了学者对女性评点《牡丹亭》的文章;叶长海主编的《牡丹亭:案头与场上》辑录了多篇女性批评研究的文章。 关于女性对《牡丹亭》的评点,有学者质疑作者与内容的真实性,主要集中在“三妇”点评《牡丹亭》上。谈蓓芳的《〈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为吴吴山所撰考》一文,通过考证认为此作为吴山所撰[29];蔡九迪在《梦的分享: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一文中表示:“引起我们对三妇评本真实性怀疑的不仅仅是吴吴山对该版本的广泛参与,还有太多的巧合,太多的完美匹配。 ”[30]这些质疑从另一个侧面点明了女性在戏曲历史书写中的尴尬地位。
在“三妇”点评《牡丹亭》的研究之外,戏曲批评领域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批评群体及其内容的文化解读。 刘奇玉在《明清女性戏曲批评群体初探》一文中,对女性戏曲序跋进行研究,分析了女性戏曲批评的群体特征及其对戏曲文学的理解,丰富了古代戏曲批评的内涵。[31]王郦玉在《明清女性的文学批评》(2017)一书中,对清初至中期“女性戏曲批评”进行了论述,戏曲批评成为批评者表达艺术观点、提升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的载体,进而得出结论:在批评理论上批评者已经觉察到:“戏曲本身所兼具的娱乐性和观赏性,使其对思想性和真实性的要求并不很高,尤其对于观众和读者来说,他们对故事本身的理解和阐释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并非戏曲创作者所能控制和把握。 ”[32]
华玮的《明清妇女戏曲集》一书详尽地整理了散佚严重的剧本,其《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一书对妇女戏曲批评的版本及其情色论、女性意识等文化特征进行了论述。 从《妇女评点〈牡丹亭〉:〈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与〈才子牡丹亭〉析论》起,华玮就从性别文化视角来探究明清戏曲:“她们笔下却透露出一致的女性特殊的阅读角度,诸如对男性钟情志诚的向往要求,以及对女性心理,如母亲疼惜子女与闺秀怜才慕色的反复玩味。她们的批语往往也显示出女性细腻而感性的解读方式。 ”[33]华玮对明清女性与戏曲研究的坚持,不仅体现出一种深深的女性情结,也将明清时期女性的才学气质延伸到了当代。
明清女性戏曲创作与批评研究取得了三项显著成就。首先,经过多位学者的不懈努力,明清戏曲女作家与作品的数量大体得以确定;其次,女性戏曲批评文献得以系统整理与充实;最后,女性戏曲创作作品得以相应整理与研究。明清女性在戏曲中的地位由幕后走向前台,从戏曲史中的隐秘点缀转变为主角。
总之,20 世纪以来,明清女性戏曲史研究既遵循了传统的文学史书写路径,也将原本戏曲史中的女性与戏曲的关联由隐匿转变为显著状态,这不仅赋予其传统文学史书写的特征,即案头与场上并重,还在东西方社会性别思想研究的潮流中展现出东方文化研究的特性,实现了性别主义的东方化——“女性主义”,即“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增强女性气质从而强化性别差异的思想”[34]。 从文化环境、演员与观众(读者)、创作与批评三个维度研究明清女性戏曲史,既使其在内容上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又凸显了女性在明清戏曲史中的重要地位,丰富和深化了我国古代戏曲史书写的研究。
注释:
①“对我们来说,把女人定义为人,是为了在外部世界,为了在人们必须了解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世界探索其价值。 我们将以存在主义理论来探讨女人,对她们的全部生存处境给予足够的重视。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李强译,西苑出版社,2011,第16 页。
②“总计明清两代女剧作家得二十二人,所作戏曲在五十五种以上。 今存有十八种,另残本两种,共计在二十种左右。 ”叶长海:《明清戏曲与女性角色》,《戏剧艺术》1994 年第4 期,第81 页。
③“明清二代,创作戏曲的女性多达二十五位,但至今流传下来笔者亲见之完整剧作只有十九种,另残本两种。 ”华玮:《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第15 页。
④“通过初步努力考证出明清女戏曲家26 人,著录戏曲65 种(不计陈翠娜),其中杂剧计14 种,传奇计51 种。现存戏曲24 种,其中杂剧7 种,传奇15 种,残存2 种传奇。 ”刘军华:《明清女性作家戏曲之社会性别错位现象透视》,《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4 期,第4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