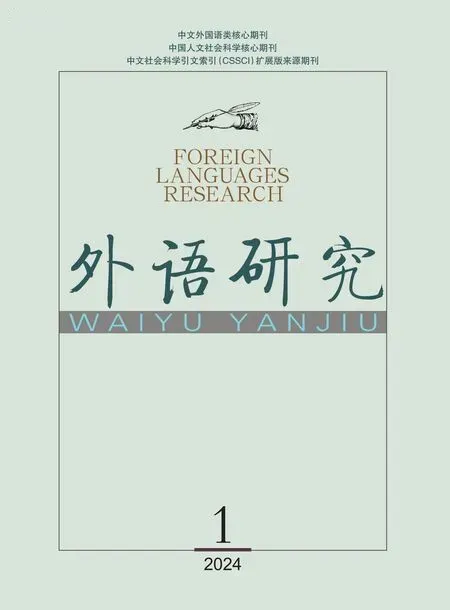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译者群体行为研究*
李正栓 吕 欣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0.引言
毛泽东创作的大量诗和词,是中国现当代诗词难得的佳作。张智中盛赞毛泽东诗词将理想与实践、形式与内容、浪漫与现实、个人情怀与史诗般的宏伟,均融合化入其中(张智中2008:91)。毛泽东诗词浓缩了毛泽东的哲思、情感、意志、诗艺和书法。臧克家说毛泽东诗词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1937 年,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撰写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含12 篇,1937 年10 月伦敦戈兰茨公司首版,两个月内印刷4 次,发行十几万册。1938年1 月美国兰登书屋再次出版该书。毛泽东作为诗人的声誉由此传开。此书一版再版,先后被翻译成近20 多种文字出版,全面、立体、真实地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真正形象。1957 年《诗刊》创刊号发表毛泽东诗词18 首后,在1957 年和1958 年,苏联、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将这18 首诗译成自己的语言出版诗集(李正栓,王心2019:9-10)。毛泽东诗词多语种出版掀起了国际传播热潮。
《清平乐·六盘山》创作前,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分歧以及与国民党追兵的战斗成为这首诗很好的脚注。1935 年9 月9 日,张国焘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并命令陈昌浩率兵南下,同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毛泽东认为继续等待争取张国焘是浪费时间,决定马上北进。果然,10 月5 日,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另立“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
1935 年10 月7 日,毛泽东到达乃家河。途径甘肃固原县(今属宁夏)青石咀时,在一个山头亲自指挥陕甘支队第一总队的一、四、五大队,采取两侧迂回兜击、正面突击战法,歼灭何柱国骑兵两个连,缴获战马百余匹。率领陕甘支队顺利越过六盘山主峰,继续向环县与庆阳之间前进。六盘山作为红军长征时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也被称为“胜利之山”。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提笔抒怀。该词虽以“清平乐”为调,却浩气凛然,表现了革命者的大志和勇毅。徐四海认为本词大气磅礴,雄浑豪放,隽异挺拔,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徐四海2010:96-97)。无论国内外,凡译毛泽东诗词者,鲜有不译此词的,如布洛克和陈志让、巴恩斯通和郭清波、李正栓、黄龙、许渊冲、赵甄陶等译者,都曾译过这首词。
但是,以译者为考察对象的翻译批评却比较少见。其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些译者群体,其译作特征及其成因等都有很多可以研究的素材,值得发掘(周领顺等2014:101)。深入研究译者,对借鉴译者的宝贵经验和丰富翻译文化史都有重要意义。此外,周领顺创造性地将翻译分为翻译外和翻译内两个层次“,翻译外”研究文本之外的务实,即译文服务于社会的程度,应对的是译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翻译内”研究文本求真度,应对的是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主要关注从文本到文本之间的语码转换和意义再现(周领顺2020:52)。从这两个层次出发,基本可以从理论上保证翻译批评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全面性。因此,本文聚焦《清平乐·六盘山》一词,将以《六盘山》一词为文本的译者视为一个群体,并以译者行为理论为指导,探讨这一群体的行为特征,尤其是在翻译内和翻译外两个层次上的共性行为和个性行为。
1.毛泽东《六盘山》译者群体共性行为
1.1 翻译外共性行为
1.1.1 翻译动因
毛泽东诗词翻译历经八十多年(自1937 起),译者遍及全世界。虽然这些译者生活时代和社会环境不同,但却表现出几乎相同的翻译动因。
迈克尔·布洛克(Michel Bullock,1918-2008),自由作家,创作小说和诗歌,从事翻译。生于伦敦,求学于伦敦。1968 年,移居加拿大。关注超现实主义诗歌,自成一派。1969 年,到美国访问,后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州立大学(UBC)创意写作系任教,负责翻译项目。1983 年,退休。1994 年,曾赴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也曾当过教师,编过诗刊,名盛一时。陈志让(Jerome Ch’en,1919-2019),历史学家,生于四川成都,西南联大毕业后,留学英国,并在英国工作多年,后移民加拿大,对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等政治人物都有研究。1965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志让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该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陈志让撰写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占该书篇幅的四分之三;另一部分是37 首毛泽东诗词,由布洛克和陈志让合译,布洛克主笔。诗词部分以Introduction to Mao’s Poems 开篇,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其人其诗,认为他的诗人地位堪比其政治地位。此外,二人在文末对翻译动因做了详细说明,希望以此激发读者对文学的内在兴趣,并对毛泽东所处时代和思想等有所了解。
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1927-),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东亚及中国政治与历史研究专家,生于美国缅因州,青年时代开始写诗,涉猎文学评论,从事翻译,译著颇丰。一生中获得许多奖项。郭清波,中国赴美留学生,师从巴恩斯通,后加入美国籍,也出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1972 年,美国出版了他们两人合译的The Poem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诗词》),获得美国各大媒体好评,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很大反响。该书共149 页,收录诗词35 首。诗词以汉英对照形式排版,诗词注释汇集在译文后面;“附录”包括翻译说明、中国诗词格律和毛泽东手迹(《六盘山》片段)。副文本包括前言和对引用的注释。虽然两人未在书中直接阐明翻译动因,但在前言、后记和附录中还是有所透露。该书后记Richard Nixon and Mao’s Poetry 部分附上了尼克松传记作者与尼克松的采访谈话。采访中尼克松回忆他的访京之旅,尤其是与周恩来研究一首毛泽东诗词的场景。鉴于The Poems of Mao Tse-tung 的出版发生在两国外交新突破时,The Poems of Mao Tse-tung 实际上成为一种外交手段,可视为美国向中国发出的友好信号,以回应1971 年中美两国的“乒乓外交”。此外,前言和附录部分分别对毛泽东诗词创作和艺术性、中国诗歌格律进行了简要分析,表现了对毛泽东其人的欣赏、对其诗的肯定,以及对中国诗歌文化的热爱。
黄龙(1925-2008),中国当代翻译家与翻译理论家,通晓多种外语,曾任中央机关翻译、东北师范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教授,译著颇丰,1980 年出版《毛主席诗词英译(四十首)》,是毛泽东诗词国内最早英译者之一。作为中国译者,黄龙拥有强烈的使命感,专注历史文化研究,并曾以笔为矛坚决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许渊冲(1921-2021),中国当代的翻译家与翻译理论家,一生致力于建构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大局观。他认为文化全球化应该与经济全球化并行,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应与国际文化交流,应与世界文明互鉴(许渊冲2005:23)。毛泽东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的优秀部分理应融入世界。
总之,各译者虽各有身份背景,但都具有良好的学术素养和翻译水平,最重要的是都表现出对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热爱、对毛泽东其人和其诗的欣赏,且都致力于跨文化交际,传播中国文化和毛泽东诗词。这些成为他们翻译毛泽东诗词的共同动因。
1.1.2 读者意识
读者意识指将文学创作和研究的重点放在读者接受度上,即在文学创作和研究的过程中观照读者的感受与接受。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要让读者喜爱与欣赏,只有读者喜欢后才能广泛传播。所以,翻译要为读者服务,对读者友好。毛泽东诗词译者虽在观照读者意识的具体行为上有所差异,但都表现出了高度的读者意识,总体表现在排版、副文本、翻译策略和方法上。
首先,在排版上,除个别译者外,多数译者采用中文在前,英文随后的中英对照排版,以帮助译入语读者比较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更好地理解原文。巴恩斯通和郭清波不仅使用中英对照排版,还给出繁体字书写的中文原诗词,且文字排版采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由上到下、由右及左的传统模式,方便了未接触简化汉字的海外读者。
其次,在副文本方面,译者使用注释、附录、甚至插录的方式,就毛泽东本人、诗词创作和文化负载词进行补充解释,避免译入语读者因缺乏历史文化知识而无法产生理解和联想。以《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中布洛克和陈志让合作完成的毛泽东诗词37 首为例,诗词翻译为该书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中国革命历程的梳理和详细的介绍。由于毛泽东诗词和中国革命的紧密联系,第一部分虽然是历史著作的正文,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第二部分(译作)的背景补充,对于读者理解毛泽东诗词的思想感情至关重要。他们还在第二部分中插入“毛诗导论”,专门就毛泽东诗词特点和地位作了说明,并在每首诗后以注释的方式,解释说明了诗歌创作背景、文化负载词等可能阻碍译入语读者理解的因素,如翻译《六盘山》一词时,文后就有“毛领导的第一方面军在1935 年10 月7 日占领六盘山”一注。除此以外,该书还有毛泽东本人照片及书法。
最后,在翻译策略和方法上,如果排版和副文本是为了满足译入语读者的需求,翻译策略和方法则更多为了适应译入语读者的习惯,主要体现在归化和异化的策略选择和直译与意译的方法使用上,如巴恩斯通和郭清波翻译《六盘山》词牌名时,既直接音译Liupan,又意译of Six Circle 以解释说明,目的是为了降低陌生度,拉近译文和译入语读者的心理距离,是翻译外行为影响翻译内行为的结果,并最终体现为译文的务实度。
1.2 翻译内共性行为
1.2.1 词汇翻译
张智中从毛泽东惯用的词语中总结出毛泽东诗词的语言风格特征,其名词博大壮阔,其动词刚健有力、豪气十足,其数词巨大夸张,口语和书面语相结合,雅俗兼备(2008:239)。《六盘山》的几位译者虽在具体词汇选择上有所差异,但基本都实现了与原词在词汇意义和风格上的对等。
《清平乐·六盘山》全词情景交融,上阕起于远景,下阕始于近景,两阕相对独立,却又紧密相连,“生动地表现了毛泽东及其统率下的英勇红军胜利地登上六盘山后,远望云天,抒发了彻底打垮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坚强决心,发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壮志豪情”(刘鸣泰1993:631)。为了表现这种壮志豪情,词中充满着表现壮阔景观的名词或偏正结构的名词性短语,上阕有“高天”“淡云”“南飞雁”“长城”“好汉”,下阙有“高峰”“红旗”“西风”“长缨”“苍龙”。以“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一句中“高天”“淡云”的几种译法为例。“天高云淡”指天气晴朗,天空云少而高,轻薄而淡。黄龙和许渊冲都使用了high 和light 二词以表“天高云淡”,用词精确。而布洛克将其译为lofty sky, pale clouds, wild geese fly。lofty 大体与high同义,释为巍峨、高耸,也可用以形容高尚的、崇高的思想或信仰,但一般为书面用语,用在此处虽然契合了原词中天高度之高,却不及直接使用high 更贴合原词口语化特点,更加自然生动。pale 与light 极其相似,但不完全相同,pale 强调颜色的深浅,light 则侧重密度的高低。《清平乐·六盘山》作于10 月,正值秋季,并且是甘肃之秋。入秋后大气湿度降低,空气变得干燥,不易形成较厚的云层,因此“云淡”,显然侧重密度的light 更为契合。巴恩斯通则译为dazzling sky 和cirrus clouds,dazzling 意为十分明亮以致目眩,用在此处是为意译,指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同样,cirrus,卷云,高空中一种云层,通常呈现出细长而卷曲的形状,常见于晴朗的天空,属高云族,多呈分离散乱状,色白无暗影,是为“淡云”。总之,四位译者都选用了与原词意义基本对等的名词。
动词和数词的翻译同样如此。“因为阳刚之气盛,毛泽东诗词当中多用动词,特别是表示强力与猛力的动词”(张智中2008:242)。《清平乐·六盘山》中,尤见“何时缚住苍龙?”的“缚住”一词。缚,束也,指用绳子紧紧绑住,此处引申为击败敌人。布洛克译为put bonds upon,巴恩斯通译为tie up,黄龙译为bind fast,许渊冲同样译为bind。就词义而言,几位译者所用词汇都有束缚之意,但就力度而言,put 最轻,tie 次之,bind 最重,因而bind 最能表达诗人必胜的把握和信心。或许黄龙和许渊冲都注意到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Prometheus Bound 被译成《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翻译的互文性借鉴显示了译者的视野与学识。
毛泽东喜用数词,是其诗词的核心词类。若无这些数词,诗词便逊色许多。毛泽东常用数词,尤其是量大的数词,借以夸张表达目光宏远,心胸开阔。“屈指行程二万。”这是何等胸怀,艰苦卓绝的长征,被他屈指粗算,才两万里,表达了“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气概。“二万”概指红军长征至六盘山所走路程,应当如实传译。除布洛克外,其余译者都译出了准确数字“二”。但黄龙将“二万”译为two-myriad li,myriad 意为极大数量,用在这里化实为虚,虽然不精确,却尽显夸张之意。
1.2.2 修辞翻译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这种艺术性的实现与修辞的使用密不可分,修辞所产生的表达效果往往是诗人创作力的表现之一。修辞属于艺术的门类。毛泽东诗词存在灵活多样的修辞:比喻、夸张、拟人、指代、双关、互文等等,这些修辞的应用成就了诗歌的艺术美。因此,翻译中也应转存或再现这些修辞。
《六盘山》词中最具表达效果的修辞是原词最后两句中使用的借喻和设问。
[1]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布洛克、陈志让译文:
Today we hold
The long rope in our hands.
When shall we put bonds
Upon the grey dragon?(1965:337)
巴恩斯通、郭清波译文:
Today we have the long rope in our hands.
When will we tie up the grey dragon of the seven stars?(1972:70)
黄龙译文:
Today we’ve seized hold of a long cordon,
When shall we bind fast the Grey Dragon?(1980:46)
许渊冲译文:
With the long cord in hands today,
When shall we bind the Dragon Gray?(2015:55)
借喻是比喻的一种,直接以喻体来指称事物。由于只有喻体出现,语言更加简洁,却能产生更加深厚、含蓄的表达效果。诗人词中的长缨,意为长绳,这里指代革命武装;苍龙,意为恶龙,指代与共产党和红军为敌的一切反革命势力,包括国民党反动派,也包括日本侵略者。翻译时,应注意避免破坏借喻产生的深厚、含蓄的效果,此时直译反而更得其意。几位译者无一不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使本体更加形象化。值得注意的是黄龙和许渊冲对“苍龙”的翻译。苍龙本就被用来比喻极度凶恶的人,两人大写grey dragon,可视为将其拟人化的一种手段,是在悉数传译原文修辞的同时,发挥译者的创造性,使之更具意蕴。设问不同于疑问,是无疑而问,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有答案在下文中,是为提醒下文而问,称为提问,另一类有答案在它的反面,是为激发本意而问,称为激问。“何时缚住苍龙?”形似疑问,实为设问,且为激问,这并非诗人发出的无可奈何之叹,而是诗人在充满信心和把握的情况下,对消灭反动势力和胜利到来的急切期盼,此句既揭示了全词主旨,又将全词推向了高潮。几位译者也都尽力传译了这一问,翻译时都使用表将来时态的shall 或will,表示胜利尚未发生但即将发生,但shall 与will 相比更加主观,用在此设问句中使得感情或者意愿更加强烈,诗人对胜利的渴望呼之欲出。此外,四位译者出于英语语言习惯,都在问句中添加了主语we,避免了人称指代模糊,不仅照顾了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体验,而且第一人称复数的主语更能给人代入感,甚至有召集、呼吁大众,共克敌人的意味。
2.毛泽东《六盘山》译者群体个性行为
2.1 翻译外个性行为
2.1.1 翻译模式
翻译作为一种劳动,既可以是个人活动也可以是群体活动,因此存在独立翻译和合作翻译两种翻译模式。独立翻译毋庸置疑是指由个人独立完成的翻译活动,而合作翻译可以定义为由两名或两名以上人员共同合作进行的翻译活动,按照合作模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口述加笔受的合作翻译模式、主译加辅译的合作翻译模式、集体分工协作的翻译模式(王正2007:1)。就毛泽东诗词英译而言,既有独立翻译又有合作翻译,且合作翻译多为外国人主导,究竟是何种因素导致了译者翻译模式选择的差异,这种差异最终又分别对翻译造成了何种影响,又该选用哪种翻译模式,亦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西方英译毛泽东诗词基本发生在20 世纪80 年代以前,尤其集中于20 世纪50 年和70 年代,以外国译者群体为主。此时也是合作翻译的高峰,从译者署名上看,他们的合作基本上是外国人主译加中国人辅译的模式,可能与译者个人素养、国内汹涌的政治运动和长期大行其道的正向翻译理念有关。布洛克和陈志让、巴恩斯通和郭清波都是以这种模式合作的。布洛克专于诗歌,兼具语言优势,陈志让精于历史,兼具文化优势,两相结合,互为补充,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翻译质量和效果。巴恩斯通和郭清波同样如此,两人是师生关系。但是这种合作并非完美无缺,由西方学者主译很容易出现原文理解错误或译文过于“本土化”而损失原诗意味的现象。20 世纪80 年代后,中国译者群体成为主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翻译需求剧增,中国本土译者异军突起,此后国内涌现出一大批毛泽东诗词译者,如黄龙、许渊冲、辜正坤、赵甄陶等。这些译者学贯中西,大都有留学经历,任高校外语教师,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天然的文化优势都保障了他们独立且较高质量的诗词翻译。总之,译者选择何种翻译模式是以提高翻译质量和翻译效果为目的,并受到时代背景、文化差异、翻译理念、个人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的结果。
一般来说,译者独立翻译,耗时长,对个人能力要求高,但译文能一以贯之。合作翻译效率高,各取所长,但译文常常因译者主体性差异而产生差异。从理论角度来看,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词汇、文本阐释、语言风格、翻译策略等方面(同上:43),最终导致译文风格的不统一,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合作翻译模式,“诗人译诗,中西合璧”应该是中诗英译的理想模式(李正栓,陶沙2009:108),但要加强合译项目的管理,双方要确实负好自己的责任,探寻更加理想的翻译模式。余光中(2002:66)认为:“最理想的译法应该是中外的学者作家两相合作,中国人的中文理解力配上英美人英文表达能力,当可无往不利。”因此,像毛泽东诗词这类中国传统文学作品,完全可以由中国人主译,外国人辅译或审读。
2.1.2 翻译思想
受时代和个人背景的影响,不同译者总是产生不同的翻译思想。毛泽东诗词英译既有独立译者也有合作译者,这里主要分析主译者的翻译思想。
布洛克早年曾参加布勒东(André Breton, 1896-1966)倡导的超现实主义诗歌运动,其诗作敢于挑战创作的极限,常常将诗歌与音乐和视觉艺术相融合,形式短小,内容简洁,是自然世界与内心世界的结合,既具有超现实主义的潜意识、梦幻等特色,又富有东方神秘色彩。受西方诗学的影响,布洛克采用自由体译诗,不关注诗歌韵脚,并且认为如果毛泽东诗词翻译得过于流畅,节奏过于柔和,是对原诗的背叛,诗中几乎暴力的、明显的断断续续,恰恰满足了人们是对毛泽东“战斗性”个性的期望(Chen&Bullock 1965:319)。因此,翻译时,布洛克主张在语言差异允许的范围内,保留这些特点,具体表现为使用短小、尖锐的句子,同时尽可能地缩短音节。其实,他这种翻译思想导致了他在翻译中对毛泽东诗词诗节形式的严重背叛。形式变了,内容必然随之改变。
巴恩斯通对中国古典诗词颇为了解,在“中国诗词格律”中就中国古典诗词的结构、行长、音调和韵式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此外,他还关注到毛泽东诗词的原型——唐律诗和宋词,并指出毛泽东的诗大多是词。基于这种了解,巴恩斯通在“翻译说明”中,简要说明了具体如何翻译毛泽东诗词。首先,他认为翻译应该紧扣原文,其次,中国诗词非常依赖意象,必须重视意象的翻译,最后,他主张采用增译的方式,尤其是专有名词的翻译,以增加译文的可读性。总体而言,巴恩斯通的翻译更具现代诗特点,注重内容的内涵。
黄龙作为我国当代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他的翻译思想集中体现在1986 年出版的《翻译技巧指导》、1988 年出版的《翻译学》(英文版)及《翻译艺术教程》中,涉及翻译的方方面面(王金波2016:17)。他认为翻译的标准是“信”与“顺”,主张使用直译和意译的翻译方法,以直译达“信”,意译达“忠”,主张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艺术,这种艺术必须讲求文体相称,重视译文的韵律、节奏、音调等特征(黄龙1988:49-83),同时还要传达字里行间的情感,以现“神韵”。此外,黄龙还格外关注翻译的社会职能,即翻译外层面,认为翻译有助于传播革命思想,推动政治改革等重要功能。
许渊冲的翻译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吸收前人思想也总结个人体会,注重实践,把实践当作理论的重要源泉,最终形成了以“三美论”为核心的翻译理论体系。他认为翻译是求美的艺术,而毛泽东诗歌则是意美、音美、形美的集中体现,因此翻译时必须更加坚定对美的追求。这就要求译者充分发挥创造性,将文学翻译“求真”和“求美”的矛盾统一起来,但始终要以美为先。并且,许渊冲充分关注古典诗词格律,主张要“以诗译诗”,是国内“韵体译诗”的主要倡导者。
2.2 翻译内个性行为
2.2.1 词牌翻译
“词牌名作为词学‘文化负载词’或‘文化承载词’(culture-loaded words and phrases),是标志着‘词’文化特有事物的词或词组,反映了‘词’是在漫长的形成过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文学形式的、独特的存在与传播方式。”(王洁2020:173)而且,词牌虽有定,翻译却无定,词牌名因其较强的异质性给翻译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毛泽东诗词以词为主,涉及数十个词牌名,翻译时译者往往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处理这种异质性,也因此表现出不同的译者行为。
《清平乐》源于唐教坊曲名,意为宁静平和的乐曲,每词46 个字,上阕4 行押韵1111,下阕4 行押韵1121,内容以婉约为主,表达爱情、乡情、亲情。宋代时,这一词调沿袭唐时旧貌,后受豪放派词人词风影响,使用范围扩大,感情基调多元。经金、元、明、清各代,其题材扩大,声情愈加丰富。至于毛泽东的三首《清平乐》(《清平乐·蒋桂战争》《清平乐·会昌》《清平乐·六盘山》),其意旨变化更大,描写战争,离唐时旧貌更远,婉约难寻,豪放有加,不仅抒情,而且叙事。词牌名的翻译可体现不同的文化思维。几位译者对《清平乐》词牌的翻译基本可以概括为不译、音译、意译几种。
巴恩斯通、郭清波译文直接省略词牌,只译出了题目《六盘山》,这种不译的方式显然是不可取的。词不同于诗,是一种音乐文学,词牌是标识,类似于公示语,首先规定了曲调,是词音乐性的首要表现。不译词牌,相当于直接放弃了词这种富有音乐性的特殊文学体裁。究其原因,可能源于译者对中国传统“词学”缺乏有效认识或了解不够深入,也可能是译者为译入语读者考虑,直接省略了译入语文学中不存在的成分,避免读者理解困难或产生歧义,又可能是对这一文化现象不屑一顾。但是,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译词却不译词牌,都显得不严谨。布洛克、陈志让译文采用了音译的方式,译为ch’ing p’ing lo,因当时还没有拼音系统,所以采用了威氏拼音法,又在拼音前添加了to the melody of,表明了词的音乐性。这是可取的,采用音译也是正确的,因为毛泽东诗词的“清平乐”不是表现纯净、平和的乐曲,他反映的是波澜壮阔的战争,虽不豪放但绝不婉约。黄龙的译法与布洛克几乎相同,只是使用了拼音系统,译为Qing Ping Yue。用现代拼音,并且每个音独立、首字母大写,而不是连拼(Qingpingyue),非常正确,是一种陌生化现象,外国读者肯定看不懂,但一旦查阅或阅读书中注释便会明白,同时也获取了中国诗歌知识和文化。许渊冲采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他在词牌名前添加tune,与to the tune of 相同,表明了词的音乐性,将《清平乐》译为Pure Serene Music。Pure Serene 意为极安宁、平静的,Music 意为音乐。他如此翻译,契合了《清平乐》表宁静、平和的乐曲的原意,既传译了原词牌的文化内涵,又不影响译入语读者的理解,为将中国词学平和地、平等地传递到其他国家,提供了参考。然而,毛泽东这三首词都没有Pure 与Serene 之意。《清平乐·蒋桂战争》表现的是蒋介石与桂系军阀的战争以及红军借反动派内乱而大力发展的状态;《清平乐·会昌》表现的是红军不畏艰难、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豪气;《清平乐·六盘山》表现了大雁因寒冷而南飞、红军却不畏严寒继续北进直到长城的英雄气概,还有决计缚住苍龙的革命意志。
2.2.2 形式翻译
“所谓诗歌形式,不仅指视觉形式,还包括听觉形式。”(张智中2008:108)视觉形式主要包括分节分阙、字母大小写、诗行的排列与缩进、行数与长短等。毛泽东偏爱写旧体诗词,他认为固定的形式不会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与之相反,固定形式是中国古诗词的艺术结构。翻译时,也必须予以尊重,不得轻易改动。但是,英语诗歌除无韵体、英雄双偶句、十四行等之外往往长短不一,翻译中难免有所损伤,只能尽力传译。《六盘山》原词为双调小令,分为上下两阙。译者们显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译词都分为两节。但除此之外,译者在字母大小写、诗行的排列与缩进、行数与长短的翻译上都表现了不同的译者行为。原词共八行,上下阕各四行,上阕长短不一,下阙都为六言。除许渊冲将译词安排为与原词相同的八行并避免跨行外,其余几位译者都有跨行,使得译词在原行数上有所增加,尤其是布洛克的翻译,他将原诗行拆分为小短句,诗行数因此扩大二倍,变为上下节各八句,如此跨行连续,基本完全改变了原诗行的排列、行数、甚至长短。与这种上下阕行数一致,有规律的成倍扩充相比,巴恩斯通和黄龙对诗行的扩充就略显随意,是自由诗的做法。许渊冲强调诗歌的形美,认为要传达毛泽东诗词的词形需在句子长短和对仗工整方面下功夫,因此他的译词整体形式上与原词最为相似,微观上也最为契合。以译词第一节为例,原诗行长短不一,字数基本呈递增趋势,许渊冲的译词每行音步同样依次递增,在句子长短上不可谓不似。
“诗歌的听觉形式,主要指诗歌的用韵形式”(同上:138),包括尾韵、行内韵、头韵等等,其中,尾韵是汉英诗词共同的、常用的用韵形式,也是诗歌音乐性的集中表现。毛泽东诗词的音乐性除体现在韵式上,也体现在叠词或重复上,《六盘山》中未见叠词或重复,听觉形式就是用韵形式。就尾韵而言,四位译者中有两人译文押韵,且都为中国人,许渊冲和黄龙都采用了aabb 的英语诗歌常用韵式,是译入语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而且这种韵式恰好将诗句两两粘合,也切合了原词的句式安排。相反,布洛克和巴恩斯通受西方无韵风尚的影响,都未压尾韵,音美必定有失。但四人译文皆可见头韵、谐韵等其他韵式。
3.结语
毛泽东诗词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与之相关的翻译研究开展得也越来越广泛,但多数翻译研究关注文本而非译者,译者群体更是被忽视。本文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理论依据,分析以毛泽东《六盘山》为文本的同一译者群体的翻译外和翻译内行为,既寻求作为一个群体的译者的共性行为特征,又寻求同一群体中不同译者间的个性行为特征,旨在能够全面、科学、客观、具体地分析译者群体的翻译行为,并为相关翻译理论、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