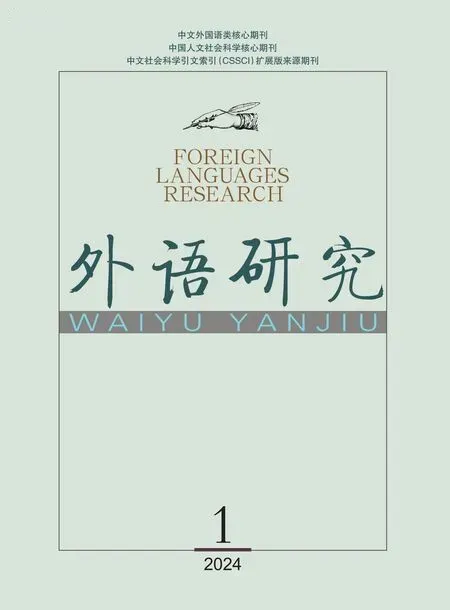《海国图志》概念译介与近代中国世界观建构*
孙一赫 王 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广东广州 510000)
0.引言
鸦片战争的失利和《南京条约》的签订令清廷有识之士认识到中西存在的巨大差异,萌生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促使其积极寻求方法挽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以魏源为代表的清廷开明派认为:要与“洋人”抗衡必须打开国人之视野,让国人看到当今世界之变局,了解西方社会的基本情况,包括制度、社会风俗、文化以及科技等,“悉夷”“习夷”方可“制夷”。魏源以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收集中国广东和澳门以及新加坡“情报”汇编而成的《四洲志》为蓝本,参考当时国内外的世界地理和人文著述,于1841 年编纂发行了50 卷本的《海国图志》。魏源对《海国图志》寄予厚望,希望以此开启民智,让国人“开眼看世界”。在初版后的十年间又派人对《海国图志》进行增补,分别于1848 年和1852 年出版60 卷与100 卷《海国图志》,汇总为80 万字的百科全书,涉及政治、文化、宗教、科技、新闻评论等多个领域,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奠定了思想基础,成为“划时代的历史巨著”(高虹1997:4)。
1.《海国图志》的概念译介
《海国图志》作为近代中国本土首部世界地理百科全书,收纳并译介了大量的世界概念与知识。在译介过程中,《海国图志》分别采用“音译”“概念添加”“语内变形”“引用”四种方式,对世界概念进行转换和呈现,构筑完整的世界体系。四种翻译方法译出的概念及由此展现的世界新格局隐含着内部的间性或矛盾性,即呈现对旧体系“破”与“不破”的双重趋势。一方面,《海国图志》通过音译法和概念添加等译介方式阐述新世界体系和地理逻辑秩序,构筑多元、完整、体系化、平等的世界新格局,打破了中国“天朝上国”的固有理念,让国人以客观、真实的视角看待发展中的新世界,放下历史包袱,虚心学习西方,达到“开眼看世界”的效果。另一方面,所采用的“语内变形”与“引用”的译介方法又使《海国图志》极力靠近中国传统文化与固有世界观,在译介过程中使用大量本土话语和历史话语,让《海国图志》的世界体系呈现“中华中心”的等级化特征,显示了对传统的“守”与“不破”的趋向和心态。
《海国图志》以开拓国人视野为基本宗旨,收纳、整理、译介大量世界新概念,通过“音译”“概念添加”“引用”“语内变形”四种方式,将有关概念予以转换和展现,联通新旧世界与中西文化,构筑了新的世界格局观。
1.1 音译
音译法是保留源语的发音特征,在译语中找寻对应发音的文字直接完成转换的翻译方法。《海国图志》作为百科全书,收纳大量世界概念,而中国与世界脱轨时间长,对世界知识体系缺少必要的认知而造成目标语无法提供对应的概念。音译法直接取自源语发音生成译文,转换效率较高,符合《海国图志》作为百科全书的定位和翻译量,因而成为《海国图志》重要的翻译方法,广泛运用于书中的世界概念译介。
“都鲁机国疆域在阿细亚洲者半,在欧罗巴洲者半”(魏源1998:842)这一段文字介绍了“都鲁机国”的基本地理位置。根据全文内容,此处“都鲁机”指现在的“土耳其(Turkey)”。通过源文译文的对比,魏源在概念译介时以“Turkey”发音为参考,将“Turkey”拆分为“Tu”“r”“key”三部分,并在汉语中寻找语音较为相似的“都”“鲁”“机”,将其组合成为译文。此外,魏源对“France”“Germany”“Austria”等国家名称予以类似处理,分别将其译为“佛兰西”“耶马尼”“奥地里加”。音译法还广泛应用于各国相关概念的翻译,如“都鲁机国沿革”章节中将大洲“Europe”译为“欧罗巴”、土耳其国王“Adam”为“亚丹”及“Alexander”为“阿力山达”等(同上:843)。
但《海国图志》概念体系过于庞大,而中西语言的差异导致音译法下可能产生复杂、冗长的译文,影响读者的接受。鉴于以上两点,魏源在使用音译法时还采用“选择性删减”的方法,仅保留源语的部分语音完成本土化转换,使其作为概念的文字表达符号,以此解决译文混乱和读者接受效率低的问题。在卷二十七西南洋情况介绍中,魏源将澳门著名的教堂“Igreja em São Paulo”译为“三巴”(同上:821),译文保留原文后半部分“São Paulo”中“São”和“Pau”的部分发音,将其转换为中文体系中发音类似的“三”和“巴”,其他部分则全部删去,这种方式缩减译文长度,让译文在形式上符合汉语表达习惯,方便读者阅读和接受。
1.2 概念添加
与音译法的独立使用不同,《海国图志》的概念添加法需要与音译法同时使用,以叠加的方式呈现概念。概念添加是在音译原词的同时添加译语文化中已有的相关概念,从而规定和明确新概念的内涵和指示范围,是一种二次翻译。音译法能够解决翻译任务量大带来的翻译效率问题,但其“保音舍意”的基本特性往往使读者无法理解概念的基本意义和范围指向,使读者对大量“新”“异”的概念译文产生困惑,不利于翻译目的的实现。因此,《海国图志》在某些特定音译概念后添加相应指示词,明确新概念的指示范围,帮助读者理解。
《海国图志》卷三十七“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简要介绍了欧洲的相关情况及各国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让国人首次认识这个陌生的大洲。其中,魏源将Europe 译为“欧罗巴洲”(同上:1092)。从翻译方法上看,魏源首先使用音译法将Europe 的发音特征予以保留并悉数译出。随后,魏源在译文后添加“洲”,让读者能够将“欧罗巴”与本章中涉及的国家、海洋等概念区分开来。“洲”附带的“海上的陆地”的意义还帮助读者明确“欧罗巴”一词的基本指向和地理范围,同时形成地理印象,帮助读者理解与接受。书中所涉及的“阿细亚洲”“阿利未加洲”等也遵循同样的翻译思路。此外,魏源还使用、确立和丰富了“洋”“国”“海”“(群)岛”等概念。
1.3 语内变形
与“概念添加”类似,语内变形法在《海国图志》的译介过程中也并非单独使用,而需与概念的音译叠加形成复合形式。语内变形是将概念先进行音译处理后,利用译语系统的词法特征,对音译概念的文字表达形式进行改动,使之在译文中形成独特的结构和表现形式。《海国图志》的语内变形法往往借用汉语构词法形成新的文字表达来指示某个概念。
《海国图志》第79 卷中将孟加拉(Bengal)译为“孟呀喇”(同上:1934)。由译文词形上看,魏源对该词的译介处理分为两步:首先对Bengal 进行音译,将所有音节译出并呈现在译文中;随后结合汉语造词法,对译文中的“牙”和“剌”进行第二次处理,在这两个汉字的前面加上“口”字旁,构成新词“呀”和“喇”,突出其表音性,再结合起来产生最终译文“孟呀喇”。而将美国(America)译为“咪唎坚”亦是如法炮制。通过语内变形形成的译文是一个整体,没有明确的名称+意义(表音+表意)的组合结构,是利用汉字词法系统创造的概念翻译方法。
1.4 引用
引用法是借鉴本国已有的对应概念的表达方式,让译介的概念能够融入译语的历史文化体系之中,方便读者理解。《海国图志》面向中国社会,考虑中国读者的接受能力与基本认知状况,对传统文化和世界观采用妥协的态度,在部分概念译介中借鉴和引用中国史书及当时汉语体系中已经形成的概念表达,使新概念的译文符合中国传统认知和中国文化习惯。根据引用来源和方法的不同,《海国图志》的引用法包括“历史性引用”和“语言引用”两种方式。
“历史性引用”直接追溯部分概念的历史沿革,从中国史书中寻找其踪迹,使概念实现时空转换,利用概念语义中存在的“历史流”(Steiner 2001:24),减少“在概念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可能形成极为严重的诠释学困难”(王一多2020:64),帮助国人大致了解该国的地理面貌、历史沿革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搭建中西文化、现代与传统的桥梁。在卷二十六第一部分“西印度之如德亚国”的介绍中,魏源写道,“古拂菻国,非大秦也,唐时为隔海之大秦所并,故亦名大秦。元人谓之密昔尔,回教谓之西多尔其,皆古西印度边境,今并入阿丹国”(魏源1998:805)。在这段介绍中,魏源将如德亚国(Jedaea)的古名“拂菻”写明,还结合中国古籍对该国的记载,给出其在唐、元的名称,并将其与古代王国“大秦”做比较,方便中国读者了解其方位,理解该国在古代的状态及其与中国的关系,进而产生一定的印象,构建该国的国别形象。
“语言引用”是借鉴本国当前的语言体系,参考其中的现成表达或理解方式,完成世界概念的译介,在《海国图志》中分为“口头语引用”和“语言体系借用”两类。“口头语引用”直接参考和利用当时国内部分地区对外国的口头称呼确立译名。在卷四十《大西洋》第一节“荷兰及弥尔尼壬两国总计”中,魏源记载:“荷兰俗称红毛番,亦曰红夷”(同上:1168),将“荷兰”译为“红毛番”(“红夷”),这是借鉴当时广州地区的国人对荷兰人的称呼,以转喻的方式用作“荷兰”这一国名的中译名。广州作为清朝严格实行“海禁”政策后唯一可与外国通商的口岸,与外国交流较为密切,在实际交往过程中需要相关的概念和称呼,但原有的中国文化体系缺少相应的概念和称呼,因此广州人依靠外在形象对外国人形成认知和称谓语。为了译介“荷兰”这一概念并构建荷兰人的基本形象,魏源选择接受、利用这个口头交流中的概念,以减少新的译文可能造成的认知困难。同理,《海国图志》中魏源将美国译为“花旗”“双鹰”也是基于国人看到其国旗图案所形成的认知。
“语言体系借用”是在汉语体系和汉语认知方式的基础上对概念进行译介。在卷二十七“西南洋”沿革中,魏源将“Igreja de S.Domingo”译为“板樟”(同上:822),这是以理解为基础进行的概念归化式译介。Igreja de S.Domingo 是中国澳门的圣多明我教堂,以樟木制成的木板为其主要建造材料。魏源利用中国的视像与理解思维,选择基础建筑材料“樟”和基本建造形式“板”两词结合完成对原词的转换,以此表达概念的根本特征。
总之,《海国图志》为了通过译介建构庞大的世界新概念体系,分别采用“音译”“概念添加”“语内变形”“引用”的方法。四种翻译方法及其影响下呈现的译文往往同时出现在《海国图志》之中,没有明确的规定,也缺少区分的标准,译文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相互关系,构成极为独特的多种译法并行的翻译现象。
2.破与不破:《海国图志》新世界观的构建
《海国图志》采用四种不同的翻译方法,构筑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新世界体系,但《海国图志》编译目的和编译思想中也存在对立与矛盾,体现在对概念译介中,呈现出“新”“旧”交互的间性世界观,表现为对原有的世界认知“破”与“不破”的两种倾向。一方面,《海国图志》要重塑国人世界观,通过翻译直接引入世界地理和人文概念,冲击并改变国人原有的世界观,使之形成全新、完整、体系化的世界认知。另一方面,《海国图志》作为士大夫阶层为统治阶级编写的地理知识丛书,不可避免受到正统观念的影响,在译介过程中存在对传统和旧有世界体系的留恋和妥协,翻译中大量引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概念,在部分概念译介中还进行刻意的改写,一定程度上试图维护原有的世界观体系。
2.1 构建完整、多元、体系化的新世界格局
《海国图志》的译介首次为国人构筑了一个完整多元的世界格局。中国自明朝开始实施闭关锁国,到了清朝更为严重,全国仅开放广州一处通商口岸。历时漫长的闭关锁国不仅严重阻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更形成封闭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造成了国人的世界认知在空间上的局限和时间上的滞后。空间上,大多数国人仅了解中国,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不甚了了,包括当时的西方列强;时间上,到鸦片战争之前,大部分国人对世界的认知甚至还停留在中古时代,根本不了解世界随着工业文明的发生早已步入近代社会这一巨大变化。《海国图志》的译介目的就是要直接引入新的概念,拆除国人陈旧的认知框架,重塑国人的世界体系认知。《海国图志》内容极为广泛,从第三卷至第七十卷着力收录和展现世界体系和各国风貌,包括各国的基本状况、地理位置、风俗、兵备、科技发展等内容。面对庞大的世界体系,《海国图志》采用“音译法”快速引入时局发展所需的新概念,在时空两个维度上构筑完整的世界体系,弥补国人对世界认知的滞后。
《海国图志》也首次显示了平等理念,努力构筑平等的世界秩序。中国历史悠久,文明辉煌灿烂,是历史上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之一。在明清之时,中国国力达到鼎盛时期,封建王朝发展到巅峰,这一时期,周边国家纷纷来朝,与中国建立了“东亚封贡体系”(韩东育2018:89),即周边国家依附中国,承认中国的中心地位,得到中国的封赏和保护。这种体系下,国人逐渐形成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随着社会的封闭,民族优越感逐步转变为“自大”和“自满”,最终演变为“华夷之辨”的思想(戚文闯2018:61)。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世界各国的认知始终较为落后,依然沉湎于中世纪的迷梦,认为中国文明独领风骚,是世界的中心——“天朝上国”,而外国则是蛮夷之邦。这种观念导致国人根本不会正视世界体系与格局的变化,更无法看到科技在世界体系和民族发展中的作用。《海国图志》的译介目的就是要打破这种观念上的固步自封,推行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民族自救思想。在翻译过程中使用“音译法”引入大量新的概念。“音译法”最根本的特征是“语音的保留”,通过“保留原文中某些具有异国情调的东西故意打破目标语惯例”(Shuttoleworth & Moira 1997:59),并随着“时间的延续被中国读者所接受和再使用”(唐德根,吴静芬2008),丰富“目的语的语言表达方式”(郭建中1998)。《海国图志》音译法保留了外国语言的部分特征,并借由翻译的形式将外国语言的元素融入汉语之中,将两种语言置于文本层面上等同的地位,打破“华夷文明之别”的固有思想。语言还能够直接影响思维认知,外语元素的保留与语言表达的更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中国文化的自体更新与发展。在封闭的中国旧社会,新概念的引入能够引导传统文化和思想“偏离主流价值观”(Venuti 2001:240),促使国人将目光从人文转移到科技,注意到国外科技发展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进而改变国人妄自尊大的心态,最终实现“师夷长技”的目的。
《海国图志》还首次规定了世界地理系统与格局,构建了体系化的世界格局。中国是农耕文明的代表,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深处内陆腹地,与海洋相隔较远,与世界其他国家接触不多。加上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实行,导致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基本局限在中国及周边国家。而对于世界体系建构,国人存在推己及人的趋向,即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看世界,对世界体系缺少客观、正确的认知。大多数国人的世界概念更多停留在“国”的层面,对“大陆”“海洋”“岛屿”“大洲”等概念并不清楚。这种认知水平难以形成完整的世界观念,无法建立客观的世界地理格局。《海国图志》在译介过程中对不少西方概念采用“概念添加”的方法,在音译法形成的译文后添加汉语概念。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帮助国人理解和区分此概念的指示范畴,还可以形成地理概念群,进而联结成为完整的世界地理体系。如《海国图志》首次规定“洋”的概念,明确概念所指的地理范畴和涉及的学科。在具体编写过程中,《海国图志》采用关联编排法,如在“西南洋”一章之中列举该大洋沿岸的所有国家,进一步明确“洋”的具体范畴及其与国家和世界的关系。同时,《海国图志》还采用对比编写法,如在“西南洋”一章同时引入“海”的概念,让两个地理概念形成比较,明确概念归属与所指,明确世界由“洲”“洋”所构成的基本地理格局。而在国家层面,《海国图志》也明确了国家体制及其概念范畴,形成从城市(部)到国家,包括岛屿、海、洋、洲的一整套地理学概念,由此建立起现代地理学意义上的世界体系和国家体系。
2.2 留恋“中华中心”与“中国至上”的旧世界等级
《海国图志》借用翻译,尝试构建相对完整、平等、多元、体系化的世界格局,让当时的国人看到变化之中的新世界。但《海国图志》产生于相对封闭的中国封建社会,无法完全脱离传统观念的束缚。魏源作为士大夫阶层里的开明人士,其编纂《海国图志》的根本目的是引入现代地理学概念,让国人看到世界全貌,接受现代观念,以便“师夷长技”,而非全盘推翻原有的制度和文化。因此,《海国图志》构筑的世界体系带有极为深刻和明显的传统观念的印记,在编译过程中极力靠近传统文化,以维护原有的观念体系,达到“维持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和文化控制的目的(章晓强,戴秋娟2022)。体系之“不破”主要表现为新世界体系译介的“等级化”趋向,具体包括“中国与世界的等级化”及“外国间的等级化”。
中国历史上的领先地位让国人始终抱有“天朝上国”的理念,在对外关系上坚持“华夷之辨”的思想,以文化界定国家发展的水平(韩星2014)。由此,国人普遍认为中国位于世界文化的“中心”,而中国的统治者——皇帝则是凌驾全世界之上的“天子”(沈传新2022)。这种思想也体现在《海国图志》中对海外各国的译介,比如译者在译文中刻意添加某些概念,表示其在行政、文化的地位上低于中国。《海国图志》虽然承认其他各国的独立地位,音译法的使用也传递了国家间相互平等的意识,但在具体使用中,《海国图志》却又通过特定概念的“添加”维持“华-夷”之等级区分。再比如在对西方国家相关人物概念的译介中,特别是对各国最高统治者的译介,《海国图志》大多选择“王”这一汉语概念,而不是用称呼中国统治者的“帝”这个概念。清朝时期的中国已经发展至封建社会的极限,权力高度集中,皇权凌驾一切权力之上,因而有“帝”之称。“王”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一般指“郡国并行制”中的封国管理者,在政治层级上次于“帝”。在对外关系中,“东亚封贡体系”中的周边政权需要每年向中原王朝纳贡,换取朝廷的承认和保护,谓之“藩国”。其时,朝鲜、越南等国家的统治者一般要接受中国的册封,封号也为“王”。“王”这一表述无形中确立了中国君主“高人一等”的地位,流露出维护和凸显中国与外国的等级差别的意识。《海国图志》还使用了“国”“部”等概念的添加,其中“国”相对于“朝”显得低一等级,而本应与“城市”地位相同的“部”也在等级上低了一等。
等级秩序的维护还体现在《海国图志》的情绪化或戏谑式的翻译上,如将“荷兰”译为“红毛番”或“红夷”、“孟加拉”译为“孟呀喇”等。这些国家大多与中国发生过摩擦和纠纷,如“荷兰”侵占过我国台湾岛,是国人心目中的侵略者,因而在部分地区的口头语或习惯表达中形成情绪化的语言表达形式。《海国图志》承认此类情绪化译文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并在翻译中延用,这是译者意识形态作用下的翻译行为,是一种以民族情绪为导向对某些概念的译文进行主观化表述的结果。这种情绪化翻译在《海国图志》中大多体现在对西方国家的译介上,针对性很强,是“迎合政治潮流”(Venuti 2001:20)而产生的“文化误导”(王金安2008:124),本质上是“中华中心”思想影响下的翻译操控行为。
《海国图志》的等级化还体现在“外国间”的等级划分与维护上,主要体现为对“内亚圈”与“外亚圈”国家的差别译介。古代中国通过“东亚封贡体系”与周边国家基本建立了稳定的外交关系,形成了对世界基本体系的保守和固定的认知。在传统世界体系中,中国将世界所有国家划为“汉字圈”“内亚圈”与“外圈”三类(费正清2010:12)。《海国图志》中的外国等级差异主要表现为“内亚圈”和“外圈”之间的等级分别。“内亚圈”是参与当时“东亚封贡体系”或在历史上与中国有所交集的国家和民族,一般与中国存在政治、经贸、文化的频繁往来,被中国统治者所承认或册封,与中国保持臣服或友好关系,在中国相关史册中大多有记录。这些国家一般为中国邻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国人对这些国家也较为熟悉,认为这些国家接受了中国文化熏陶,是中国影响之下的文明民族。而外圈则是未参与到东亚封贡体系的国家,在历史上与中国交往不够频繁,在中国史册中也没有记录,其中大多是西方国家,包括英国、美国、荷兰等。国人对这些国家了解不多,由于这些国家的人种与文化与中国存在极大差异,国人往往认为这些国家是未能接受中华文明影响的蛮族而产生某种“鄙视”心理。
“内外圈”的认知影响《海国图志》的编辑过程和文本呈现,通过使用“引用法”遵循和维护原有的“中华至上”与“中国中心”的世界等级秩序观念。《海国图志》为贴合中国文化和习惯,从中国史书中寻找相关国家的记载,参考历史上的国家概念进行译介。而中国古代由于地理位置以及科技发展的局限,与当时的西方国家缺少交流,史书记录的国家大多为周边国家,在《海国图志》中内外圈国家在历史引用法下形成的文本差异,造成书中对这些国家的地理形象建构存在极不平衡的状况。对内亚圈国家,《海国图志》引用大量史料,将其纳入中国文化体系之中,形成历史与现代的勾连,让汉语语境中的读者充分认可内圈国家的文明发展状况与对华友好地位,从而形成积极的印象。而对于绝大多数外圈国家,《海国图志》仅采用音译法,结合当代的文献予以介绍,在译介中还对不少国家采用主观情绪化的翻译,误导国人对这些国家的认知和态度,确立其野蛮、侵略性的负面形象,使之与内圈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等级秩序就此建立。但这种等级体系是建立在“中华中心”的世界观基础上的,本身不具备合理性和客观性,也不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事实上,所谓“低等”的外圈国家大多是完成资本主义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令人感慨的是,这种过时的、偏见性的等级秩序观念与其“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的目的有些背道而驰,这也是《海国图志》在当时的中国没能发挥其应有功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在改变中国人的认知方面。
3.结语
《海国图志》是中国第一部自主编写并公开发行的世界地理百科全书。魏源利用“音译”“概念添加”“语内变形”“引用”等翻译方法对新世界的概念进行转换和译介,呈现客观、完整的世界格局,首次构建近代中国的新世界体系。在音译及概念添加方法影响下,《海国图志》的世界体系呈现多元、平等、系统化的特征,对中国人心目中原有的世界认知体系形成了冲击,展示了新的世界秩序。但是,《海国图志》自身的定位、编写目的和读者群体决定其不可能完全背离旧的观念,在译介过程中,通过“概念添加”“情绪化翻译”“典籍引用”等方式,在译文中依然表现出对“天朝上国”及其“内外圈”的世界认知的留恋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