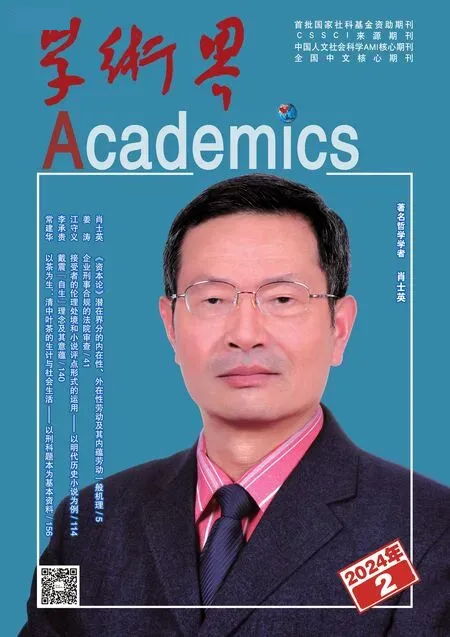再造范式:胡适《红楼梦考证》现代论争的思想史价值〔*〕
温庆新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百余年来关于以胡适《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新红学”之形成、范式、影响及评价问题,学界已有诸多讨论,且尤重《红楼梦考证》的话题创新、融合中国传统考据学与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新方法”及其学术史地位。然而,罕有学者注意到《红楼梦考证》诞生的初期并未获得现代学者的一致认可,更未曾对这一历史情况加以系统的梳理与分析。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学者对《红楼梦考证》进行了一场推崇式肯定与批评式否定相交织的评判。此类长时段热闹存在的接受景象,不仅反映出《红楼梦考证》范式意义确立的艰难过程,亦可讨论20世纪上半叶学术演变的复杂性与多元格局,还原现代学术研究如何基于时势所需而展开以史为鉴与开创未来的艰难探索。
一、作为一种“兴味”:现代学者对《红楼梦考证》的方法认可
早在1923年,梅生《红楼梦辨》就指出:“自从胡适之先生做了一篇《红楼梦考证》,把一般旧红学家的错误,说得详详细细以后,遂引起俞平伯先生的动机,努力研究《红楼梦》,把关于《红楼梦》一书的风格,作者的态度,续作者的态度,续作者的依据……用深刻的功夫,逐一考证和批评。”〔1〕深刻点出了《红楼梦考证》对现代学者关于《红楼梦》研究思路与内容选择的影响。徐文滢《〈红楼梦考证〉的商榷》(1942)进一步敏锐地指出《红楼梦考证》被现代读者正面接受的主要内容,言:“胡适先生以《红楼梦考证》及《红楼梦考证的新资料》二文决定了‘红楼梦的真事是曹雪芹自传’的推论,几年来为公论所钦服,自此不再听到关于这问题的争论。凡有关于《红楼梦》的记载,如《人名大辞典》,各种文学史小说史中,亦均采胡先生的考证为根据,不复有人怀疑了。”〔2〕现代各类文学史、小说史对《红楼梦考证》的采信,即是该文在现代人眼中具有巨大影响力与强烈信服度的最佳注脚。例如,朱剑芒编、魏冰心等校的《初中国文》第4册一书,节选了《红楼梦》第39回至第42回涉及刘老老的部分,名为《刘老老》。该篇文末“注释”直接就说:“据胡适《红楼梦考证》——《胡适文存》卷三——曹雪芹名霑,是前清八旗世家曹寅之孙,约死在乾隆三十年左右。《红楼梦》亦称《石头记》,是一部伟大的言情小说,全书一百廿回,以贾宝玉,林黛玉为书中的主人翁。本篇所描写的是刘老老初进大观园的情形。”〔3〕《初中国文》系“初级中学生”的参考用书,以“新主义教科书”为“卖点”,包括“古语文”与“今语文”两大内容。其直接将《红楼梦考证》的观点当作一种可信的结论,进而向普通学生推广。这些足见《红楼梦考证》的信服力。
现代读者认可《红楼梦考证》的信任心理之所以广泛存在,是因为《红楼梦考证》所采用的“考证”方法契合了现代人的知识结构。朱顼《告研究红楼梦者》(1924)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红楼梦》一书,自胡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两篇文字发表后,一般研究《红楼梦》的人,的确,都有了一种正当的指导,不致误入歧途,再去妄意推测了。”〔4〕“正当的指导”等评价,折射出现代学者对《红楼梦考证》在研究方法(即“妄意推测”)与结论(即“误入歧途”)两方面的认可。这一切出现的关键在于《红楼梦考证》更新了适合现代人知识趣味的“考证”方法。正如顾颉刚《自序传》(1941)所言:“《红楼梦》问题是(胡)适之先生引起的。”又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使人把秘奇的观念变成了平凡,又从版本上考定这书是未完之作而经后人补缀的,使人把向来看作一贯的东西忽地打成了两橛。我读完之后,又深切地领受研究历史的方法”。〔5〕可见,现代学者认为胡适对《红楼梦》研究具有突出的贡献,尤其是“研究历史的方法”的提出被认为有重要的革新意义。顾颉刚所言“把秘奇的观念变成了平凡”,恰恰看到胡适所作的努力即《红楼梦》研究应在贴近现代大众生活的情况下,重新思考该书何以存在的知识特征。
关于《红楼梦》知识特征的讨论,已引起现代学者对该文的强烈阅读“兴味”。例如,1921年6月1日致信胡适的青木正儿曾说《红楼梦考证》“用科学的方法,论调公正,研究精细,真正有价值的一篇考证”;〔6〕其后所撰《读胡适著的〈红楼梦考证〉》(1921)一文,更是毫不吝啬地表达阅读《红楼梦考证》的“爽快”之感,言:“无论何时读胡君之研究皆感到爽快之由,是其一方面不懈于搜罗前辈诸说的同时,却决然不会被牵着鼻子走,总会在基础上建立自己独特所见之处。”〔7〕胡适“自己独特所见”,恰恰是引起青木正儿阅读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又如,毕树棠《书报述要: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胡适作)》(1928)一文指出:“胡适之的考证颇能自圆其说,文笔也不坏”,又说“证据周密考析精详,能到起读者的兴味,因而读《红楼梦》说部是一事,读《考证》又是一事,又另是一种兴趣”。〔8〕此即认为“证据周密考析精详”促使《红楼梦考证》具有特别的文本趣味。可以说,胡适关于《红楼梦》“史料的分析,极其精详”〔9〕等知识特征,促使现代学者认可胡适《红楼梦考证》的研究方法之后,肯定该文的研究结论,进而在涉及曹雪芹的现代教材或通俗读物中反复加以引用。由此增加了曹雪芹与“江宁织造”曹寅、《红楼梦》系曹雪芹“自传”说等观点的权威性。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学者在“红学”史视野下强调《红楼梦》研究从“索隐”到“考证”的变革创造,进而突显“红学”的存在意义,往往存在一种针对彼时“青年”的“阅读趣味”而言的纠偏尝试。〔10〕这使得在现代“考证”之风影响下的“红学”研究及其学术史反思,呈现出教化或启蒙先行的某种批评先见。例如匡汝非《“红学”的闲话》(1926)一文,指出《红楼梦》前几回的“作者自云”所交代的“自况”写作意图已很清楚了:“这全把作者的缘起,合盘托出,是何等的明白!不想有红楼索隐家,猜宝玉是某某皇帝等憶(臆)度之说。又何等多心!关于这种《红楼梦》考的问题,胡适之博士,论的非常详细。请大家看——《胡适文存》第一辑——那就不想去索隐了。”又说:“我很爱读《红楼梦》,前天我在中华书局里买书,有一位专买《红楼梦》索隐的,我虽然不认识他,我知道他也是一个爱读《红楼梦》的青年,同情之感,才使我口哈冻笔,写出来这些话!”〔11〕因此,匡汝非认为后世读者的索隐,并不见得符合“作者自云”的原意;《红楼梦考证》在某种程度契合了“作者自云”中的“自况”之意,故属可信;而针对“爱读《红楼梦》的青年”的“同情之感”,则是否定“索隐”而欲提倡“考证”的体现,从而展开“口哈冻笔,写出来这些话”的说教或纠偏之举。“我很爱读”云云,表明匡汝非对《红楼梦考证》的肯定是建立在其阅读《红楼梦》的实际感受上。其在比较“索隐派”与“考证派”对读者阅读所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对“索隐派”的知识趣味产生了强烈的否定感受。
现代学者肯定《红楼梦考证》的另一种常见方式,是从《红楼梦》演变的“红学史”中,将此文上升为《红楼梦》研究的一大重要“阶段”。原载《时事新报》1946年4月12日第3版的许杰《红楼梦研究的新阶段》一文,即属此中典型。该文首先认为历代关于《红楼梦》研究所形成的“红学”,“几乎蔚成了一种风气”。而“《红楼梦》之被人注意,他的文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时时被人提及,却是几乎跟着时代,不断的在进展着,不断的重新发掘,重新评价的”。在这个“进展着”的过程中,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是以民初的民族思想为骨干,用清代学术的流裔——考据学的方法做出发点”,以至于“他的这种工作,似乎只着重在文艺的政治宣传的意义,而且也有些被歪曲了的嫌疑;如果从学术,或是从文艺的见地上说来,是不见得十分合理的”。到了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系“《红楼梦》研究的新发展”,因为王国维证明了《红楼梦》“是一部人生境界的最高的著作”。而胡适《红楼梦考证》“又是《石头记索隐》和《红楼梦评论》的继续与发展,在《红楼梦》的研究与批评上,自然也是开辟了一个境界的著作”。〔12〕之后,许杰进一步剖析《红楼梦考证》的开创性:一是,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者”,他“虽然不了解进步的科学方法的运用,但用客观的归纳方法来研究学问,却是颇称能手的。因此,他一面承继了《索隐》的启示,用归纳,或即所谓清儒的考证方法来找寻证据,一面又接受了《评论》中的启示,根据作品中作者的自白与材料,因而多方的引证,得出了《红楼梦》的著作,只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的一个结论”。二是,胡适的考证“不但给《红楼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境地,而且也给文学批评史中的考证批评或是历史批评定下了新典范”。〔13〕此类对《红楼梦考证》的学术史定性,仍以“用客观的归纳方法来研究学问”等方法新变作为言说的具体抓手。
要之,《红楼梦考证》被认可的重要缘由之一,在于“科学”的“考证”契合现代读者的知识结构与阅读期待。现代学者认为考证有助于消除对《红楼梦》的种种秘闻索隐,能够启示现代学者探索《红楼梦》研究对现代文学接受与读者日常生活的存在价值。由此引起现代学者在《红楼梦考证》的基础上进行各类关于《红楼梦》的考辨,包括材料的补充与观点的完善等方面。《东方杂志》1943年第2期所载方豪《红楼梦考证之新史料——为胡适之顾颉刚二先生作补证(附表)》等文,即属此类。这就促使现代学者在补充完善的研究实际中,强化了《红楼梦考证》在“小说考证的本身价值是不朽”〔14〕的典型性。甚至,胡适所开创的“新红学”被部分现代学者认为是“红学史”上“最有势力”者,〔15〕进而以“主观偏胜的心理”来赞誉该研究是“有证据的”“科学化”研究的“唯一的正路”。〔16〕胡适本人也被冠以“为人风趣,对《红楼梦》具嗜痴之癖,考证索引,诚如数家珍”〔17〕的另类美誉。
二、范式转向:现代学者批判《红楼梦考证》的本质缘由
我们讨论《红楼梦考证》现代接受的思想史价值,更应注意现代读者针对《红楼梦考证》的种种批判,乃至相关批判出现的历史必然性。现代学者在学术范式、文化意义及事实纠偏等方面对《红楼梦考证》的批判,是现代社会情境的变化对当时学术研究思路及存在意义提出新思考的集中体现,亦是一种与“过去”加以多重对话的经验反思。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大特点。
一是,以《红楼梦考证》为反例,构建《红楼梦》艺术性研究的新范式。
从“红学”史的角度展开《红楼梦考证》评判,除上文列举的赞赏之辞,亦有现代学者从文学艺术与审美价值等方面提出了批评意见。早在20世纪20年代,吕天石《研究小说的正法》(1925)一文就指出,“研究小说最重要的两种方法:(一)考证法,(二)为艺术研究法。”而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研究者“所研究的还是小说的表皮,不是小说的艺术。换一句话说,就是他们没有用一种正法研究小说”。在此类认识上,吕天石指出胡适《红楼梦考证》相较于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等“索隐”研究:“虽是比较的可信,但也是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小说家的著作,虽是常含有自传的性质,但大概一半是自传,一半是想像的事实。……许多小说,大半根据著者本身的经验,本身的历史,或者是著者家庭的历史,加减其事实而成书的。”以至于胡适的研究“只解释《红楼梦》的‘著者’与‘本子’两个问题。胡先生的考证,仍不能助我们研究《红楼梦》,了解《红楼梦》”。在吕天石看来,“考证不是小说研究;研究小说考证,没有研究小说的艺术重要。”故而,尤其需要关注《红楼梦》的“主要结构”与“附属结构”,“小说中所叙述之人物有价值否”等文本内容。〔18〕吕天石的提法是现代小说研究者意图建构“小说艺术研究”等范式转移的结果,并以《红楼梦考证》作为反例来说明小说“考证”并不是小说研究的正途:“作小说往往重事实而不重想像,与艺术不甚相合的。”〔19〕此举必然会对《红楼梦》的审美性与文学性研究予以强调,也是对《红楼梦》的接受提出符合时人知识趣味之内涵建构的新要求,属于小说研究方法的路径之争。
上述路径论争的最关键,在于应将《红楼梦》当作一部“传记”还是“小说”。例如,徐文滢《〈红楼梦考证〉的商榷》一文曾说:“《红楼梦》到底仍然只是一本小说,虽然有着作者自己的灵魂,却不免有许多假设的理想以及搜自他人的故事的组织。而且作者有意让真事隐去,全书敷陈着假话。若拘泥地以为它是一本自传,用来推测曹雪芹一生的遭际,是必酿成大错的。因为小说到底不同于一本传记。”〔20〕从文学创作的过程或小说的存在身份看,现代学者意图扭转《红楼梦考证》拘囿于材料索隐或考证的研究怪圈,更注重“《红楼梦》全书的主题是金玉木石三角恋爱的惨剧,和一个大家庭的没落”〔21〕之类的文本内容。此举带有某种程度的研究范式新构之倾向。尤其是,现代批评者认为时势背景及相应社会情境的变迁,会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思路与存在价值带来新变,以便在革新研究方式中“重提”经典作品的现实意义。
典型之例,即如杨夷《“红学”重提》(1943)一文。首先,杨夷认为《红楼梦》等“中国的旧小说”之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被提倡起来”与“抬起头来,引起全国的惊奇”,是因为“这个运动的先进们,一则为了要找寻民间的文学以与那旧的贵族文学对抗;再则作为西洋资产阶级主要文学样式的小说,这时也已相当多地被介绍过来,这使他们也得去向自己的传统中寻求类似的东西”。同时,“抗战以后,因为我们的‘欧化’的新文学在向民众宣传之前碰了钉子,大家要求着‘中国气派中国作风为老百姓所喜见乐闻’的‘民族形式’的产生,有许多人又迫得回过头去向民间小说学习,于是这本杰作马上又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其次,在分析《红楼梦》被现代学者关注缘由的基础上,该文指出胡适提出“自叙传”在“有了许多证据来作为后盾的。他的方法也合乎科学一点”,以至于“较为可信”。然而,杨夷亦指出:“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作者为要表现出其主题,为了铸造他的典型人物,原是自有其充分选择取舍的自由,不一定是限于亲自经历过的事的。高尔基教我‘语言创造的艺术,创造性格和典型的艺术,需要想像,推测和思考’。……亚里士多德亦曾认为作家的写人物,可以优于实际的人,或劣于实际的人,或恰如实际的人,而诗人模仿的对象,又不外三种:一是事情之确然如此的;二是事情之可能如此;三是事情之必然如此的。所以,除非作家本身之一切经历体验都是确具有典型者,不然则作者断不会斤斤以自身所经历体验之事事为限,而必然还须要加上‘想像’,‘推测’和‘思考’等等要素的。”此类基于“艺术品的创作的过程”等论述,促使杨夷认为“所谓《红楼梦》即作者的自传,贾宝玉即曹雪芹化身之说,殆是未能理解此种创造的过程者耳”。最后,杨夷指出《红楼梦考证》是一种“关于‘实证主义’的贫困的方法”,因为“艺术家的任务,不是描写事物的现象而是要刻画事物的本质,他不是摄影机,而是表现人生,批评人生,创造人生的透视器”。从杨夷的批评逻辑看,其与胡适的分歧由于对文学的创作过程与“本质”的不同看法所致。20世纪40年代的学者更加强调文学创作的典型性与“表现人生,批评人生,创造人生”的合目的性,以至于当时学者认为重提《红楼梦》等传统小说的当下意义时,亦应以“创造性格和典型的艺术”或“表现人生,批评人生,创造人生”的“本质”思想来重新“思考”《红楼梦》的价值,而非仅仅拘泥于“方法”的有意创造。〔22〕此类“重提”系对《红楼梦》的存在意义提出新的“思考”,可谓是从意义“本质”的角度重提《红楼梦》价值的路径之争。
可见,从徐文滢所言《红楼梦》包含“一大部分作者的想像的虚设的组织”,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着各种材料与想像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23〕到杨夷所言的“艺术家的任务”,体现出现代学者重视小说文本审美或艺术研究的范式转向。
二是,反对《红楼梦考证》与“政治问题”相纠缠的艺术意义构建。
现代学者批评《红楼梦考证》的另一种主要原因,是反对胡适将《红楼梦》考证与“政治问题搅在一起”。例如,孙伏庐《致胡适》一信,认为胡适被“大多数人所以敬仰”的原因:“全在先生能做他人所不能做的中国哲学史……能考证他人所不能考证的《红楼梦》,能提倡他人所不能提倡的白话文。”而今却做“‘政论家与政党’一类文章,我知稍有识者必知其不值”。〔24〕这里肯定的是胡适“考证他人所不能考证”或“提倡他人所不能提倡”的学术研究价值,是一种对胡适研究方法的肯定,却批评胡适将学术研究与“政治”挂钩。
相似者,如常乃德《致胡适》一信所言:“读第四期《努力周报》中伯秋傅斯陵两先生对于你们的《周报》的批评我也具有同感,先生的答词我却不敢同意。《红楼梦考证》《基督教在欧洲历史上的位置》一类的东西,实在在这里没有登出的必要,勉强凑进去反令阅者失望。不是说这种东西没价值,只是不应该在这种性质的出版物内出现罢了。先生的答词似乎对于此点稍有含混。要知凡鼓吹一件事情不能不把全副精神集中到一点才能引起人的注意。思想文艺不是不要紧,但是你们不妨另外办一种什么东西来另外鼓吹,犯不着和政治问题搅在一处。我们现在所要求的不是包罗万象的作品,只是要一个又直捷又爽快刀刀见血的东西,否则先生们的文章那一种出版物上不可登,又何必特地摇旗击鼓来办这个东西呢?”〔25〕常乃德亦否定胡适在“思想文艺”的“鼓吹”环节中过于与“政治问题搅在一处”的弊端。常乃德主要提倡“又直捷又爽快刀刀见血的东西”,以便“从思想文艺鼓吹到政治才行”。这是常乃德看到了“民国六年的时代从政治鼓吹到思想文艺”到“只能走这政治的一步”等时势走向,重新思索“思想文艺”与“政治问题”之间何为主导的问题。〔26〕在这种情况下,常乃德对《红楼梦考证》的批评,显然是说此文的撰写意图已无法适应彼时时代变迁之大势。
由此看来,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出发,孙伏庐、常乃德等人反对《红楼梦考证》的根由,在于对文学意义及其实践路径如何顺应时代变迁所需等思考而提出的新看法,最终意图仍是“思想文艺”的艺术意义构建。
三是,学理价值评判主导下对《红楼梦考证》“材料”使用的纠偏。
此类纠正或补充主要是对《红楼梦考证》加以事实纠偏的体现,一直伴随着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例如,梁心在《千岩表》1931年第2期、第3期连载的《胡适考证红楼梦的谬误》一文,重新审视了袁枚《随园诗话》、杨钟羲《雪桥诗话》、敦诚《四松堂集》、敦敏《懋斋诗钞》等材料,指出:“胡先生!请你回头一看自己的所搜集的材料。我暂且不逐条研究。请你告诉我。那一段那一句。是与《红楼梦》撰述的有关系呢。敦诚寄曹雪芹的诗。虽有‘不如著书黄叶村’一句话。究竟黄叶村所著的书。是甚么书。既然引不出证据来。怎能说是脍炙人口的《红楼梦》呢。你的引据功夫。本来是狠着实的。不料这回却蹈空至此了。”〔27〕梁心以《红楼梦》传播史料为中心,一方面尝试正本清源,另一方面则对《红楼梦考证》的研究结论进行辩驳。所言“引不出证据来”“蹈空至此”,表明现代学者对《红楼梦考证》关于《红楼梦》“材料”的使用与解读仍存在不同的声音,甚至大加揶揄。
黄乃秋所撰《评胡适红楼梦考证》(1925)一文针对《红楼梦考证》的主要观点,几乎是逐一地驳斥。如针对胡适“《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等观点,评析道:“余尝细阅其文。觉其所以斥人者甚是。惟其积极之论端。则犹不免武断。且似蹈王梦阮、蔡孑民附会之覆辙。”而后对《红楼梦考证》“其本子之考证”与“其著者之考证”两方面展开详细纠偏。〔28〕对此,暟岚在《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1925年第17期刊载《评胡适红楼梦考证》一文曾概述了黄乃秋的观点,“此文重要点谓:(1)从各方面观之,高鹗之续《红楼梦》四十回,乃系逐渐插入原本八十回之间,将八十回扩充而成百二十回,非于八十回加上四十回,(2)言胡适之谓甄贾两宝玉即雪芹之化身不对,因:(一)与胡适己身立论之根本相抵触(二)立论证据之不充(三)大背小说之原理。末并谓《红楼》为:(一)已经裁剪之人生(二)超时空性之人生(三)契合各理之人生(四)已经渲染之人生,断不能以实际人生相绳。”〔29〕可见,现代学者对《红楼梦考证》的事实纠偏,亦以研究方法的学理价值评判(即“人生”意义)为指导。
三、现代学者评判《红楼梦考证》的思想史价值
从《红楼梦考证》开篇针对《石头记索隐》的批评:“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30〕结尾又说希望“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等论述看,〔31〕蔡元培与胡适的论争表面上是研究意见的冲突,实质却是研究方法乃至范式话语权的竞争,进而导致两人对中国古代小说之时代“命运”的不同研判。甚至,胡适与蔡元培两人对近现代时期“重提”《红楼梦》时的价值内涵,亦有不一样的定位。胡适尝试以“科学方法”取代“附会”,体现出胡适对《红楼梦》以何种面貌存留于“当下”进而通向“未来”学术的凭借何在(即“创造”),提出了一种“科学方法”式的实践思路。这也是胡适《新思潮的意义》(1919)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与“再造文明”等思想所推行“评判的态度”的具体实践。〔32〕
同理,纵观现代学者对《红楼梦考证》的赞誉与批判可以发现:赞同者主要集中于方法范式的认可,反对者意图对《红楼梦》如何适应不断更迭的现代学术及其通往现代社会的存在路径提出不同的意见。现代学者批评《红楼梦考证》的背后,是其认为在“新红学”的“考证”中,有关《红楼梦》故事本身的研究已经降级成为本事考证、作家创作动机的载体,而不是一部自足自立且具有完整审美性、文学性的小说作品。彼时的批评者认为:附加象征意义(即影射××说)或纠结于本事探寻的批评与阅读,会严重干扰《红楼梦》作为小说作品的本质存在;这会导致对《红楼梦》的解读与阐释演变成依照批评者的所见所知,乃至先入为主的目的预设去改造它、解构它。在反对《红楼梦考证》的现代学者看来,以《红楼梦》为典型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需要保持足够的艺术或审美敏感性;更需要基于小说文本所呈现的种种“人生”书写,予以深刻洞察(即契合“为人生”之类的时代主题),保存足够的尊重与真诚且细致的品读热情,方能对《红楼梦》展开“科学”的研究。可以说,从胡适对蔡元培的批评到现代学者对《红楼梦考证》的批评,这是各个时期的学者出于以史为鉴的意图,寻求“科学”构建适应时代价值体系所需的小说研究范式时所发出的各种声音与思考。
进一步讲,现代学者对《红楼梦考证》的各种论争,不仅是关于小说研究方法的路径之争,亦是对小说意义确立路径的讨论,更是对彼时文学发展前途的路径探索。现代学者批评《红楼梦考证》忽略了“传记”与“小说”之间的界限,提出小说研究应当重点关注有关作品的艺术性或审美性。甚至,吴耀祺《论红楼梦考证》(1921)一文认为:《红楼梦考证》“是书浏览一过,觉瑕瑜互见,附会仍所不免,所用科学方法亦未完备”,〔33〕并借此对“科学方法”展开了其所认知的实证说明。许杰亦言胡适“不了解进步的科学方法的运用”。此类意见可认为是现代学者对符合彼时社会情境的“科学”研究方法仍在不停地探索中,亦是对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小说在“当下”环境中如何重获时人认可的“新生”,乃至经典意义的重肯,提出了隐含范式取向的构建实践。因此,此类论争可看作是现代学者与“过去”或传统的多方对话,进而尝试在历史启示的认识语境中重新审视“现实”处境的具体行动。
例如,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之初的村言《红学空波》曾说:“自语文体兴,文艺界益争谈红学。”〔34〕已然看到现代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学术范式转移对《红楼梦》研究风气的影响。后来的许杰《红楼梦研究的新阶段》一文,对上述现象有着更为细致的剖析。许杰在看到《红楼梦考证》诸多开创性的同时,亦辨证地批评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并不太符合当时的文艺思想。其指出:“文艺批评的任务,毕竟不仅是考证或解释,把《红楼梦》确定为作者的自叙传之后,事实上已不过是法朗士所说的‘一切文学作品都不过是作者自叙传’的一个注脚,一个从原则推向个别的例证而已。又那里能算尽了批评的能事呢?”尤其是,胡适的“考证”是“五四以后的产物,他所给与当时的影响,自然和‘评论’有些不同。但是,时代是在进展的,文艺批评的主潮,也不能不跟着时代在前进。现阶段文艺批评的任务,是既然不必强调着政治宣传的作用,而政治宣传的作用,和所谓文艺的政治价值,也不必和艺术价值隔离开来,在艺术价值以外,再找所谓政治价值。同时,他也不肯避免人生哲学的探讨,但人生却离不了他所处的现实社会,人生问题并不一定要和社会问题分开的。至于对于作者身世遭际及□学养等的考证与解释,自然也可以因而触发到作品构成的研究,以及作者在作品中的流露出的人生见解的;但批评的工作却不能局限在这一阶段之上,而且买椟还珠,因而把重要部份(分)丢开,也不能算是明见”。许杰从文艺批评的任务出发,认为批评并不能作为“考证”的注脚,而是一种从作者“所处的现实社会”出发,研究的关注点应包括却不能仅仅局限于“文艺的政治价值”,而应将艺术价值与“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相结合,以便最终触及最核心的“作品构成的研究”。〔35〕从上述批评思路看,许杰对《红楼梦考证》的批评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思路的反思,而且基于“作品构成”重新提出了小说价值的新探索思路。也就是说,20世纪40年代的学者对于小说研究的范式有了一种关注作品结构与艺术价值的显著转向,从而对《红楼梦考证》提出了包含扬弃的反思新见。
从学术史的视角看,现代学者认为社会文化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与此相关的主流思想随之而变,各类主张的碰撞亦在所难免,以至于当时学者对“新红学”的形成呈现出赞誉或批判两种方式并存的态势。以“新红学”为例证所展开的各类学术史反思,在不同时期学术研究的范式变迁及其文化意义的更迭中既有激烈论争,又隐含相互调和之趋向。这种调和之举实际上是不同时期的学者重构学术批评如何在“过去”“现实”(即“当下”)及“未来”之间展开有效传递等隐含历史性意义探讨的体现,皆属于胡适所言“创造中国的新文学”〔36〕的讨论范畴。因此,现代学者有关胡适建立“新红学”的论争,主要是反思“新红学”这一事件形成的历史意义,而不仅仅局限于这一事件本身。其关于“新红学”的反思往往存在这样一个论述逻辑:基于反思者“当下”的知识构建意图,人为地预设“新红学”在“未来”学术衍变格局中的位置,以此倒过来解释“新红学”建立的过去“历史”和现在“影响”。这就导致“新红学”的论争存在着意义增值的无限可能,成为学界构建新研究范式及其观点立意的一种批评凭借。现代学者所言《红楼梦考证》“用的却是新的方法,是归纳的研究方法”,〔37〕这是突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科学性”,亦是批评凭借的具体实践环节。其以此展开的文本品读或解释必然会靠向专门性与专业性,从而促动其他读者在某种特殊化的自觉意识中,不断推进批评行为的发生与理解渠道的革新。而专门性与专业性批评的严肃性,又会灌注现代学者所看重的某种思想或意识。因此,现代学者所展开的《红楼梦考证》批评,是其借助批评(文化)传统的方式来构建某种新的研究思路,进而寄托一定的文化构建目的。它可看作是现代学者对《红楼梦考证》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中尝试“改造传统”与“再造文明”的重要环节(此处借用《新思潮的意义》之话语〔38〕),并最终体现为现代学者尝试指引其他读者采用艺术性或科学方法来阅读或评判《红楼梦》的强烈呼吁。这也是一种以“当下”需求重构《红楼梦》“过去”意义的言说模式,不断诱导世人对《红楼梦考证》的“未来”价值加以新的研判。
要之,现代学者反复强调《红楼梦考证》“对于一切旧文学作品,都能够用一种新目光新方法去研究,不用前人旧说”,〔39〕表明现代学者不仅肯定胡适所提出的“新方法”,亦意识到胡适的主张而导致文艺评价的方式与理论构建须予以深度细究的尴尬。《红楼梦考证》现代批评的热闹景象是现代学者以“新目光新方法”的文艺批评为抓手,努力参与现代社会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然而,现代学者反思时所采用“过去化为现实而得以在场”〔40〕的批评策略,并不见得能够全面理解“新红学”形成初期所面临的各种思想、学术及文化阻碍。因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学者对《红楼梦考证》所展开的一系列批评行为,主要是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当下”身份(或“现代”意义)与接受导向提出新思索而致的。同时,《红楼梦考证》的现代批评是彼时批评者阅读此文而产生一定程度的刺激反应,亦是批评者随之形成或共鸣或批评的心理活动、思想意识诉诸批评文字的集中体现。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胡适经历“向溥仪跪拜的故事,他的‘中国的五大仇敌’的说法,他的‘好人政府’的主张,他对于李顿报告团的歌颂,他在两广异动,陕西事变中发表的言论”等诸多事件后,〔41〕逐渐变得“臭名昭彰”,〔42〕以至于20世纪40年代关于胡适的批评之声更甚于此前。20世纪40年代的学者紧紧抓住“政治问题”来批评《红楼梦考证》的学术价值即是明证。从某种程度上讲,对《红楼梦考证》现代批评的学术史还原,具有解剖现代学术复杂衍变情况的参考价值。因为以时人的论争去梳理现代学术的衍变情况,亦可推广至“整理国故”、现代小说史学史〔43〕等其他方面,有一定的思路启示。现代学术史在衍变过程中逐渐强调的专业化与专门化趋势,使得基于方法范式重构的学术史梳理,逐渐成为现代之人对待各类文化现象乃至具体文学接受的主流选择。在学术史梳理过程中隐含一定的价值重构,亦是现代小说史学史构建的重中之重。因此,“新目光”与“新方法”如何被现代之人加以各种解构与重构,理应成为当今学界客观对待20世纪各类学术史构建的主要评价内容。这样的学术史研究路径,一方面能够彻底还原20世纪学术衍变的文化必然性,另一方面,亦可分析20世纪学术衍变的某些偶然状况,从而在兼顾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批评框架中多维讨论20世纪学术衍变的思想史意义。
注释:
〔1〕梅生:《红楼梦辨》,《时事新报(上海)》1923年4月20日。
〔2〕〔20〕〔21〕〔23〕徐文滢:《〈红楼梦考证〉的商榷》,《万象》1942年第1卷第9期。
〔3〕朱剑芒编、魏冰心等校:《初中国文》第4册,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第67页。
〔4〕朱顼:《告研究红楼梦者》,《时事新报(上海)》1924年2月25日。
〔5〕顾颉刚:《自序传》,《我们的读书生活》,上海:言行社,1941年,第176-177页。
〔6〕耿云志:《关于胡适与青木正儿的来往书信》,《胡适研究丛刊》第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26页。
〔7〕〔日〕青木正儿:《读胡适著的〈红楼梦考证〉》,《支那学》1921年第1卷第11号。
〔8〕〔9〕毕树棠:《书报述要: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胡适作)》,《清华周刊》1928年第30卷第2期。
〔10〕温庆新:《从“索隐”到“开宗”:胡适早期的〈红楼梦〉阅读及范式意义》,《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11〕匡汝非:《“红学”的闲话》,《盛京时报》1926年12月1日。
〔12〕〔13〕〔35〕许杰:《红楼梦研究的新阶段》,《冬至集文》,上海:新纪元出版社,1948年,第79-80、80、81页。
〔14〕叶绍钧、朱自清:《略读指导举隅》,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76页。
〔15〕孙泽民:《关于红楼梦之考证》,《益世报(天津版)》1928年9月2日。
〔16〕补庵:《我读了〈红楼梦考证〉和〈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以后》,《社会教育星期报》1924年第440号。
〔17〕铁汉:《胡适之红学有心得》,《力报》1947年11月21日。
〔18〕〔19〕沈苏约编、陶乐勤校阅:《小说通论》,上海:梁溪图书馆,1925年,第8-18、16页。
〔22〕杨夷:《“红学”重提》,《民族月刊》1944年第1卷第3期。
〔24〕〔25〕〔26〕戴叔清编:《模范书信文选·论文学与政治》,上海:光明书局,1933年,第271-272、273、274页。
〔27〕梁心:《胡适考证红楼梦的谬误》(三),《千岩表》1931年第3期。
〔28〕黄乃秋:《评胡适红楼梦考证》,《学衡》1925年第38期。
〔29〕暟岚:《评胡适红楼梦考证》,《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1925年第17期。
〔30〕〔31〕胡适:《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5、118页。
〔32〕〔36〕〔38〕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51-552、57、558页。
〔33〕吴耀祺:《论红楼梦考证》,《税务专门学校季报》1921年第3卷第1期。
〔34〕村言:《红学空波》,《晶报》1930年10月21日。
〔37〕汪倜然:《怎样研究中国文学》(二),华北文艺社编:《怎样研究文学》,北京:人文书店,1935年,第49页。
〔39〕周侯于编:《中国历代文学类选》,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第228页。
〔40〕赵汀阳:《历史性与存在论事件》,《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
〔41〕胡绳:《胡适论——对于胡适的思想方法及其实际应用之一考察》,《新学识》1937年第1卷第4期。
〔42〕唐德刚、夏志清、周策纵等:《我们的朋友胡适之》,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第103页。
〔43〕罗宁、武丽霞:《鲁迅对“传奇”的建构及其对现代学术的影响——以中国小说史、文学史为中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