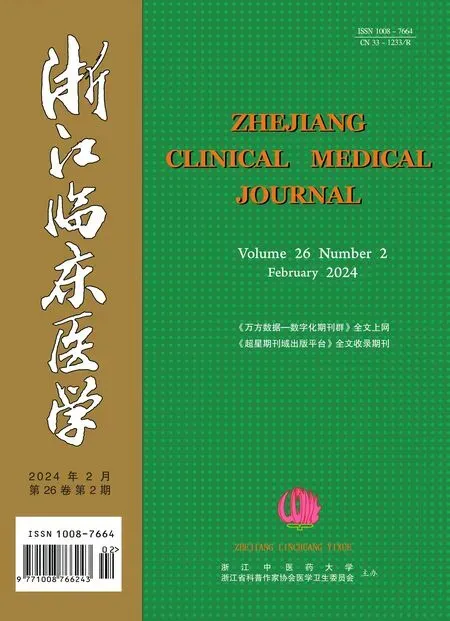肺癌患者发生放射性肺损伤相关危险因素的研究进展
童宇晓 王娇莉* 罗嫚
310003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王娇莉 罗嫚)
在2020 年的全球肺癌新发病例中,约有37%来自中国,且在因肺癌死亡的病例中,中国病例达39.8%。放疗作为肺癌治疗手段之一,在治疗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放疗过程中不可避免会照射到正常的肺组织,严重者可导致放射性肺损伤(radiational-induced lung injury,RILI),其包括早期的放射性肺炎和晚期的放射性肺纤维化。根据不同的评估方法,胸部放疗后RILI 的发病率可达5%~40%[1]。RILI 常是不可逆的,这严重影响了患者的后续治疗及生存质量。因此,早期预防和治疗RILI 对于患者的预后十分重要。本文就RILI的相关危险因素进行了大致的总结,以助于临床上早期发现、治疗RILI 并制定合理的治疗计划。
1 自身因素
1.1 一般情况 目前大多研究尚未证实患者性别与RILI 风险的相关性。临床上数据显示老年患者的发病率高于年轻患者[2],这可能与老年患者自身肺功能降低、一般情况较差、自身存在基础疾病或修复能力较差有关,因此在临床上需警惕进行放疗的老年患者发生RILI。一项研究[3]对吸烟状态和放射相关性肺炎(radiation pneumonitis,RP)风险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吸烟与RP 风险降低相关,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大多纳入的研究均以低等级的RP 为终点,且吸烟者经常咳嗽或一般肺功能较差,RP 症状不明显可能会被掩盖,所以不提倡患者吸烟。
1.2 合并基础疾病 既往研究表明,存在肺基础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病[4]、肺气肿、间质性肺病)的肺癌患者在放疗后发生RILI 的风险更高,对于治疗前的肺功能也会影响RP 的发病率,可以通过一氧化碳弥散量(DLCO)预测[5]。除此之外合并其他基础疾病的也会有所影响。李侠等[6]发现高血压是NSCLC 放疗患者发生RILI 的独立危险因素,他们认为可能是由于高血压与相关炎症因子呈高度正相关,促使发生炎症反应,导致局部组织缺血缺氧、微循环障碍加重RILI。还有研究发现,糖尿病和RILI 的发展显著相关[4],其原因可能是高血糖会引发炎症、内皮功能障碍、氧化应激,这些均与放疗照射至正常肺组织导致损伤相关。因此,基于糖尿病患者自身存在的促炎症环境可能会增强放疗的不良影响。所以在临床上进行放疗方案制定时也需考虑患者本身存在的基础疾病,制定合理的放疗计划。
1.3 肿瘤位置 据研究发现,肿瘤位置与RILI 相关,与位于上肺的患者相比,肿瘤位于中肺或下肺的患者发生RILI 的风险增加。KATSUI 等[7]发现,上/中叶和下叶位置的患者2级RP 的发病率分别为23.5%和55.6%。和瑞莲等[8]也发现发生RP 的患者中,肿瘤部位位于下肺较上肺的多,其原因可能是不同肺区对放射敏感性存在差异,也可能是下肺的肺灌注及通气更好或在放疗时肿瘤运动度增加导致更多正常肺受到照射。
1.4 遗传因素 肺部对放疗的敏感性可能取决于个体遗传表型。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代表了人类基因组中最丰富的序列变异类型,近年来被广泛研究于评估肺的放疗敏感性。PU 等[9]就SNPs 与放射敏感性进行了评估,来自904 个炎症相关基因的11,930 个SNP 被纳入分析,其中1,321 例与RP 显著相关,在验证人群中,9 个SNP 与RP 显著相关。此外还进行了放射毒性的多基因风险评分,发现三个基因(PRKCE,DDX58 和TNFSF7)中的45个SNP 与辐射反应显著相关,DDX58rs11795343 始终与发生RP 的风险增加显著相关。近期的一项研究[10]还发现NEIL1 rs7402844 GG 基因型与RP 级≥2 级风险增加相关。XRCC1 rs25487 AA 基因型与治疗期间严重RP 的风险增加有关[2]。在临床上便可以通过剂量体积和遗传成分(单核苷酸多态性信息)组成的模型来确定每位患者的等风险平均肺剂量(MLD)限值,有助于确定个体基础上可以安全地将多少剂量输送至肿瘤和正常组织。
1.5 生物因子 放疗会诱导DNA氧化损伤促使I型肺细胞凋亡、诱导炎症、血管通透性增加、肺泡内水肿等,过程中会释放: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IL-1、IL-6、高分子量粘蛋白样抗原KL-6、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β(PDGF-β)和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诱导人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化从而导致肺纤维化的关键是TGF-β1 的表达。血清细胞因子水平升高对RILI的发展具有潜在的预测性,但目前的报道结论存在争议。DENG 等[11]研究发现,发生RP 的患者IL-6 水平明显升高,并在放疗期间6 周达到峰值。ZHANG 等[12]对比放疗前后出现RP 患者的血清Ape1/Ref-1和TGF-β1 水平后发现,两者放疗后水平均显著高于治疗前(P<0.05),两者联合使用对RP 的发生具有重要的预测价值。所以在预测RP 风险时将临床因素与生物因子结合,有助于临床上更好地进行分层。
2 治疗因素(治疗方法)
2.1 放疗技术 RILI 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在放疗时不可避免地照射至正常肺组织导致直接或间接受损。目前临床上应用的放射技术如调强放射治疗(IMRT)、容积旋转调强技术(VMAT)、立体定向放射技术(SBRT)、螺旋断层放射技术(TOMO)均有助于减少正常组织的照射。但尽管如此,这些放疗技术治疗下的RILI 的发生仍难以规避。大量研究发现[13]照射剂量、肺平均剂量(mean lung dose,MLD)、V5、V20与≥2 级放射性肺炎的发生显著相关,是RILI 的独立危险因素。近期一项研究还发现[14],如果患者既往无肺部放射治疗经历,在全肺和同侧肺的平均剂量分别小于6 Gy 和20 Gy 时,2 级的RP 可限制在10%以内。此外,在制定方案时需注意每个剂量学参数彼此密切相关。
2.2 放疗联合化疗 既往研究发现,许多化疗药物(如多柔比星、紫杉烷类、博来霉素、长春新碱、吉西他滨等)与放疗存在协同作用,可作为放疗增敏剂来协助放疗。但联合治疗肺癌时,也会导致RILI 的风险增高,紫杉烷类药物诱发的肺炎似乎更高。一项针对接受卡铂-紫杉醇CCRT 治疗的肺癌患者的队列研究发现[15],同时接受化疗的患者RP 发病率可达63%,未接受化疗的患者RP 发病率仅16%,接受卡铂-紫杉醇的患者RP 发病风险更大。近期一项评估不同放化疗方案治疗NSCLC 有效性和安全性的Meta 分析结果也发现与CCRT(依托泊苷+顺铂)相比,CCRT(紫杉醇+顺铂)肺炎的发病率相对较高[16]。
此外近期有研究表明内皮抑素、二甲双胍、尼莫拉唑、替拉扎明等可以改善缺氧环境并增强肿瘤细胞对放疗的敏感性,并有研究表明[17],二甲双胍或内皮抑素联合同步放化疗的疗效明确且副作用少,因此在治疗时可以选择联用这些药物以达到更好疗效。
同步放化疗(CCRT)是不可手术切除的局部晚期NSCLC的标准治疗方案,一般RP 的发病率在15%~40%之间。一项纳入1,600 多例患者的Meta 分析显示[18],序贯化疗与同时接受治疗的患者相比RP 的OR 增加1.6(1.11~2.32),序贯化疗有更高的RP 风险趋势,这可能与辐射的生物效应在最后暴露后仍有持续,化疗及放疗之间的相互作用无法通过一方的停止而消失。另一项Meta 分析显示与序贯放化疗相比,CCRT对总生存期有更显著的益处(3 年生存率18.1%VS.23.8%,5年生存率10.6%VS.15.1%),但序贯治疗并未明显增加RP 风险[19]。所以对于CCRT 和序贯治疗的肺毒性比较,还需要量化放疗与化疗之间的相隔时间和相互作用对RP 的影响。
2.3 放疗联合靶向治疗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s)等靶向治疗由于其高选择性和低毒性而成为EGFR 突变NSCLC 患者的首选。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20]还建议EGFR 阳性的NSCLC 患者在TKI 的同时可以进行局部放疗。目前已有研究表明EGFR-TKIs 可以作为放疗的增敏剂,也有增加RILI 的发病风险。YANG 等[21]通过回顾性分析发现,与同时接受放化疗的患者相比,同时接受EGFR-TKI 和每日一次TRT 的患者更易出现症状性RP。JIA 等[22]也发现同时进行放疗和TKI 治疗的患者与≥2 级RP发病率显著相关,除此之外其还发现当重叠时间≤20 d 时有助于降低这些患者的RP 风险。临床上在治疗时或许可以通过控制重叠时间来降低患者的RP 风险,需要未来更多的前瞻性实验来证明。
2.4 放疗联合免疫治疗 根据NCCN 最新指南,免疫治疗联合放疗在NSCLC 治疗上越来越重要。研究发现对于晚期NSCLC 患者,RT 联合ICI 治疗方案时,PFS 和OS 更长。但与放疗可导致RILI 一样,ICIs 也可导致免疫相关性肺炎,提示我们应重视RT 和ICIs 联合使用的安全性。在KEYNOTE-001 1 期试验的二次分析[23]中,既往接受过胸部放疗的患者比未接受过胸部放疗的患者发生更多的肺毒性(13%VS.1%,P=0.046),但两者对于≥3 级的肺炎发病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一项评估放疗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荟萃分析[24],纳入了1,645 例NSCLC 患者,肺炎的发病率为28.53%,≥3 级肺炎为5.82%,并对比了另外一项Meta 分析的结果,均显示放疗联合ICIs后肺炎的发病率与单独放疗相当,此外还发现在PD-1/PD-L1 抑制剂之前给予放疗可能是有益的[25]。BESTVINA等[26]研究发现同时进行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和SBRT的肺毒性不大于序贯治疗。近期一项纳入16,835 例患者的前瞻性试验[27]还发现放疗在ICI 治疗前90 d(RT ≤90 d)的肺炎发病率为46%,RT>90 d 的肺炎发病率为13%,提出放疗后>90 d 进行ICI 与RILI 的风险增加无关。另一项评估RT&ICI治疗相关肺炎的研究[28]也发现放疗和ICI 之间的间隔<3 个月是发生2 级肺炎的独立预测因素。由此来看,RT 联用ICIs未明显增加发生肺炎的风险,调整放疗和免疫治疗之间的治疗时间有望降低RILI 的风险。
目前免疫治疗除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外还有细胞免疫治疗、肿瘤个性化疫苗。符国奋等[29]研究发现同步放化疗联合细胞免疫治疗可以增强临床疗效,降低化疗不良反应。王虹伊等[30]研究发现同步放化疗下联合细胞免疫治疗的患者ORR 和DCR 均高于未联合细胞免疫治疗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免疫检查的抑制剂相关性肺炎不同的是,目前的文献中对于细胞免疫治疗所致的肺炎的描述较少。CAR-T 细胞治疗后最常见的毒性是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其由于活化的CAR-T 细胞引起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IL-6、可溶性IL-2 受体、IFN-γ 和IL-10)超生理浓度的产生和大量T 细胞扩增,导致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炎症反应[31]。出现CRS 的患者对于肺部的影响可表现为内皮细胞损伤和活化、毛细血管渗漏[32]。这些或许可能会加重放疗所致的RP的风险,尽管目前尚无数据研究表明。
3 讨论
由于RILI 的不可逆性,使其成为了放疗剂量的主要限制因素,这也限制了患者后期的治疗与预后,临床上在治疗方案上的选择与规划变得更加重要。临床上对于不能手术的局部晚期NSCLC 患者,建议同步放化疗,不能耐受的患者可行序贯化放疗,但目前的研究对于CCRT 和序贯放化疗哪个导致RP 风险更大还是具有争议的,因为在放疗剂量上和患者人群上存在偏倚,临床上选择序贯治疗的人群多为有各种合并症的老年患者。对于靶向治疗联合放疗,如EGFR-TKI 可以作为放疗增敏剂增强放疗疗效的同时也会增加RP 的风险,目前的研究提示也许可以通过控制重叠时间来减少RP 发生率,但对于重叠时间的界定尚不明确,仍需更多的临床数据进行验证。
研究发现ICIs 与放疗联合治疗能显著提高患者的PFS 和OS,可能是由于辐射可以诱导肿瘤微环境中的PD-L1 上调、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的增加,抗PD-L1 的给药通过CD8 T 细胞依赖性机制增强了IR 的功效,IR 和抗PD-L1 协同减少了肿瘤浸润骨髓来源抑制性细胞(MDSC)的局部积累,还激活CD8 T 细胞通过TNF 的细胞毒性作用介导肿瘤中MDSC的减少,从而减少MDSC 抑制T 细胞并改变肿瘤免疫微环境的作用[33]。近期研究发现当TP53 基因发生突变时,G1 相阻断导致功能失调,使细胞完全依赖G2/M 检查点进行DNA 损伤修复,ATR/CHK1 途径上调PD-L1 和CD47,与STAT3 转录的激活有关[34]。因此,抑制G2/M 检查点后续可以为存在TP53 突变的肺癌的放疗治疗提供新的思路。理论上辐射对肺组织中的DNA 和蛋白质产生氧化损伤,诱导肿瘤抗原和炎症因子的释放,肿瘤抗原摄取和处理后呈递细胞迁移至淋巴器官,激活其中的幼稚T 细胞成为效应T 细胞。抗PD-L1/PD-1治疗下,进一步释放的活化T 细胞不仅有损伤自身组织的能力,还可以分泌高水平的细胞因子、招募更多免疫细胞进入照射肺区域,进而增强肺毒性。但目前为止发表的两项Meta分析[24-25]均表示RT&ICIs 治疗与单独放疗间的肺炎发病率相当,其中原因也尚未明确。
尽管CAR-T 细胞免疫治疗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上取得了巨大进展和成功[35],但由于肿瘤微环境免疫抑制、T 细胞肿瘤浸润不足以及肿瘤抗原异质性,CAR-T 疗法治疗实体瘤具有挑战性。对于治疗肺癌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找到肿瘤相关抗原或肿瘤特异性抗原,目前虽然已发现一些潜在靶点(PD-L1、B7-H3、EGFR、间皮素等),但仍缺乏相对特异性,在治疗方案及研究上没有化疗成熟,在联合放疗治疗方面由于CAR-T 细胞治疗在实体瘤的研究处于早期阶段,联合治疗的研究较少,难以明确联合治疗的疗效及风险,需要更多的临床数据支持。相信随着放疗及免疫治疗的联合应用和研究发展,将来会有更多探索其机制的研究。
此外由于RILI 的不可逆性,提前确认高风险人群并进行早期干预比后期治疗要好,仅靠单一的危险因素进行评估是不准确的,目前提出的预测模型大多建立在临床因素、剂量因素上,较少纳入细胞免疫因素,有望未来在探究免疫治疗与放疗联合治疗产生的肺毒性的机制时,探索细胞免疫在RP的发生过程起何作用,能否纳入预测模型来提高RILI 高危人群的识别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