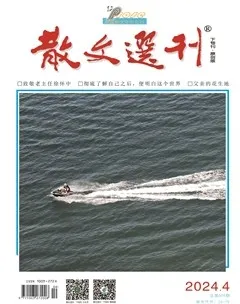我的弟弟
李水兰

弟弟比我小十岁,他出生一两岁,我们就没了母亲,我对他一半是姐姐,一半是妈妈。记忆中,父亲对哥哥和我注重言传身教,历来不愠不火,也从不流露或表达出一星半点的热烈的爱,对弟弟却从小宠爱,每天都和弟弟腻歪在一起。
弟弟六岁那年,一天,他像往常一样赖着父亲不让父亲去上早班,父亲像往常一样哄弟弟乖乖在家等他下班回家,哥哥和我注意到他从自行车的前轮上下来回到了家,于是,我们一起上学去了。没想到,整个上午,爷爷奶奶都没见到他,爷爷到他平时玩的地方找了个遍,没找到,奶奶以为弟弟被人抱走了,哭天抢地了几小时。小时候,最怕听到奶奶的这种哭声,每次听到心就会莫名纠结起来,眼泪不由自主地啪嗒啪嗒往下落。中午过后,弟弟灰头土脸地跟着父亲回家了。原来早上他尾随着父亲一路走到父亲上班的地方,父亲下到矿井底下才发现后面这个“尾巴”。从此,弟弟直到上学再也没有离开过爷爷奶奶的视线。
弟弟带给全家的第一次惊吓是在他两岁左右。那时不知流行一种什么病,村里几个同弟弟一般大的小孩高烧不止,上吐下泻,十几天不见好,已经有两三个小孩相继夭折了。伯父家的小儿子比弟弟大一个多月,和弟弟同一天生了同样的病,终究没有熬过第二十天,翻着白眼走了,伯父伯母声嘶力竭的悲恸声撕扯着我们全家人的心。此时的弟弟奄奄一息,翻着白眼,高烧不退,没什么可吐了,没什么可泻了。奶奶抱着弟弟终日流泪,带着哥哥和我连续十多天,每天傍晚提着煤油灯对着水缸给弟弟喊魂,奶奶喊:“树泉回来啦!”哥哥和我答:“回来哩!”奶奶还隔三岔五用手帕包裹着早稻米给弟弟“揩艰”,实则是从头部到背部和手部沿着经络按摩。那天的夜晚异常漫长和忧伤,我们无助地守着弟弟等候上夜班的父亲回来,马路上救护车呼啸而过,听说矿井崩塌出了事故。按照规定的时间,父亲迟迟没有回来,我们仿佛听到了死神的脚步声,都哽咽着不敢发出任何声音,聆听时钟滴答滴答那么响亮地敲打着时间,担忧、害怕席卷了我全身。突然,父亲进门来的一句呼唤,奶奶猛然爆发悲天悯地的哭声:“崽呀,你终于回来了,可怜啦,造孽呀,你快来看看树泉啊,他好像不行了。”不知到底什么缘由,自父亲抱着弟弟开始,弟弟不翻白眼了,凌晨时分,高烧也退了,弟弟奇迹般的活过来了。
哥哥和我参加工作后,他也尾随着我们跳出了农门,考上了吉林长春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他执意回到家乡父亲身边,成为一名小学教师。单位领导看他踏实肯干,提拔他担任学校的政教主任。几年后,我鼓励他考到县城去,他说:“爸爸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工作。”直到前年,他的大儿子要到县城上高中,小儿子要去县城保育院上大班,弟媳焦头烂额,急得像大火烧到家门口一般向我求助,我动员全家出动,“逼迫”他参加选调考试,终于考上县城甘祖昌红军小学。一年后,他担任学校的总务主任。
弟弟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最久,受父亲的影响最深,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和父亲的性格、为人处世的方法简直一模一样。同村的人说:“你们家一代出一个极其忠厚老实的人,你父亲这一代出了你父亲,事事处处想着别人,巴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你们这一代出了你弟弟,吃得起亏,甘愿吃虧,很会照顾人。”
弟弟有两个儿子,相差九岁,两个儿子从小跟着弟弟睡。除了上班,弟弟空余时间洗衣做饭样样家务都做,两个儿子也由他照顾。弟媳经常向我“告状”:“姐姐,你看树泉带小孩太娇了(溺爱的意思),两个儿子根本不怕他,在他头上‘作威作福。”每次看到弟弟和两个侄子嬉戏玩闹的场景,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带着小时候的弟弟的情景。
哥哥和我在外地工作,家里的事情一般都是弟弟在打理。哥哥老家的房子一楼到三楼重新装修,整整三个月,都是弟弟跟着父亲忙上忙下、忙前忙后。我在老家的房子修缮顶楼楼梯间时,我们因工作走不开,委托泥水匠请小工挑沙和水泥。直到完工结算时才知道,现在农村基本请不到小工,弟弟得知后,白天上课,晚上悄无声息地过来帮忙挑沙和水泥,从一楼挑到四楼,晚上一两点才挑完,还叮嘱师傅不要告诉我。
上半年在南昌给儿子买房时,弟弟说:“姐姐,需不需要我帮忙,家里现金是没有,但我愿意分担点贷款。”
我的亲弟弟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