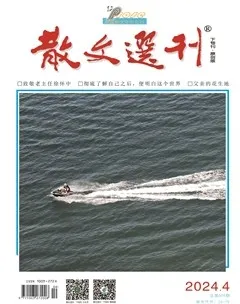从嘉山到明光
周旗

在我的印象中,嘉山起初是和一个白酒的名字相关联的。
在那个年代,真的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了,仿佛你还没有注意,“明绿液”便蓦然花儿般怒放在大众瞩目的那根高枝上。它瑰丽、迷人、风情万种又别具一格,明明是白酒,却如玉的绿,绿得晶莹剔透;若玉的洁,冰清玉洁;像玉的柔,柔情似水;还偏偏又有玉的刚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口“闷”下去,炽烈的热流窜游五经八脉,满腹草长莺飞大地复苏,山川原野郁郁葱葱,春风又绿江南岸了。总之,酒分白、红、黄等色,倘若有绿一族,那么“明绿液”便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作。似乎传统白酒都是由高粱、小麦等粮食作物为原料的,唯独“明绿液”用的是绿豆,它飘散绿豆的色香味,焕发绿豆的精气神,在浩浩荡荡的白酒大军中独树一帜。我不敢说懂酒,只觉得“明绿液”的性情既温文尔雅又如火如焰,静若处子动如脱兔,一旦燃烧起来,火焰上舞蹈着千万粒绿豆的精灵。
初冬的一天,我从嘉山到明光。实际上作为县治的嘉山,在史幕上只投影了短暂的六十二年,在1932 年以前的漫长岁月,这里留下了诸多邈远的州府更迭和稗史轶闻在民间日夜流传,如同淮河的波浪无穷无尽地拍打着两岸。
坐落在柳巷镇的浮山堰就是淮河岸边一截高高隆起的土坡,如果没有人加以解说,很难想象它竟是一千五百多年前世界上最高的土石大坝残存的部分。2022 年初,我第一次走上这座见证了南北朝时期一场战争与一次灾难的历史遗迹。在某种意义上,我今天也是循着去年的足迹再次来到了这里。这是一个阳光灿烂、晴空回暖的日子,而此前的那趟行程则被一场雨水淋湿了。
雨虽在前夜已经停止,云层依然厚重,北风裹携着隆冬的寒意。浮山堰下的小街村街上没什么人,路边有一群觅食的鸡,有兩只狗悠闲地打量这边几眼,地里是一畦畦长势茂盛的蔬菜,村庄沉浸在静谧的日常之中。通往浮山堰坡顶的道路尚在修建,踏上去泥泞打滑,我们一名同行者Y 信步踅进一户人家的院子,讨一点儿水洗刷鞋子上的泥巴。这家主妇大嫂的姓氏冷僻,曰“舌”。舌大嫂热情好客,仅仅因为拉家常时Y 称赞了地里的时令油菜生得葱茏好看,就去拔了一大袋非要塞给这位异乡的陌生人,拦都拦不住。我不禁想起新世纪之初的那年春节,我和几位朋友背着行囊去陕北,路过当地老乡的家门口,他们往往会邀请我们进家里歇脚,煮糜子茶招待,并且临走时一定会塞一包大红枣要你带上。以后光阴荏苒,我不止一次想过倘若再去陕北,老乡还会不会毫无戒意地邀请一个面生的过客进家,款待糜子茶,送你大红枣?二十二年过去,舌大嫂的那袋油菜固然看似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陌生人之间普遍缺失信任感的今天生活中弥足珍贵,它彰显的是人心的纯朴和人性的向善。
听说我这一次可能还会到浮山堰,Y专门托我把其发表的一篇题为《浮山堰的舌婆婆》的文章,以及当时在院子里拍的一张照片带给舌大嫂。
从浮山堰顺流而下即是柳巷的义集乡,义集与隔河相望的泊岗乡各有一条在冬日的阳光下金黄璀璨的银杏大道。如今这两处都成了人文自然景观,银杏树高耸挺立,落叶织就了一层色彩斑斓的地毯,游人川流不息,不少歌舞爱好者特地来到这样的环境里寻找才艺感觉的爆发点,人群中不时有一束束“抖音”的电磁波飞向四面八方。
“抖音”也许是当下最具我们时代特点的一种大众记录和传播手段。如果1952 年“抖音”就出现了,那么在这儿记载下来的则是另一番同样热火朝天的场景——千军万马开挖河道。那时的泊岗,还是嘉山县的泊岗。淮河东流而来,经柳巷后神龙摆尾地围着泊岗绕了一个“几”字形的大弯,每当上游的洪水下来在弯道流缓受托,水位便会抬升,流域的防洪压力骤增。国家决定在这一段改变淮河的流向,挖掘7.5 公里引河将那个“几”字封口,河道取直畅泄,同时在另外三处筑坝拦河,实现内外分流,缩短洪水的流程。四年后为防止堆土区域水土流失,河防部门又组织民众栽种银杏等植物以固河堤。1994 年嘉山县撤销,明光市设立,在淮河的治理史中,嘉山的银杏历经六十余年的风雨兼程,长成明光的金色长廊。在这网红打卡地的欢乐气氛背后,落英缤纷的银杏树不仅是景观,它还仿佛历史的录音机,给今天的人们讲述着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护佑更广大地区城镇的安全、利益,泊岗柳巷等地部分民众抛家舍弃良田,从祖居故土迁徙他乡别处,作出了巨大牺牲和感人贡献的故事。
从嘉山到明光,顺着时间的轴线伸延,直到晚霞的余晖落尽时我才终于再次站在了浮山堰的坡顶。上一趟来攀走的是堰坡泥泞的土径,现在有了步道、长廊、垛墙和碉楼。历史中的碉楼原是为战争准备的,此刻站上去眼界又开阔了很多,河水清且涟漪,宛如风儿吹动一条宽阔的绸缎飘浮在平旷的土地上。那次站在这儿是白日,眺望远处几近迷蒙的地方,连绵的高大树木下是淮河大堤,时逢水位比较低的季节,倘若到了丰水期,这一段河道的水面将向大堤漫漶过去,豁然扩增了几里路的宽度,大河立即变得无比浩瀚壮阔。“金泊岗、银代阳(义集),万年穷不了大柳巷”,耳畔恍若轻轻地回响数百年的民谣,夜色又浓厚了几分,从俯瞰的角度,小街村嬗变成了一幅灯火与屋顶的黑白版画。其实刚才在暮色四合的堰下,我就已经无从辨认舌大嫂家所在的位置了。光阴向前走了两年,这一片土地上的人及人的生活同更广阔更现代的世界又相近相融了两年。记得舌大嫂说过她不识字,然而她的女儿留学去了德国,并在法兰克福组建了小家庭。算起来她的外孙女今年该有七岁了,正是天真烂漫开蒙的年龄。这么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两代或者三代人,东方的浮山堰与西方的法兰克福,从历史到现代、从乡村到世界,丝丝缕缕的联想使我们的思维空间丰富多彩了许多。
胸中似有微澜,酒意般思绪旋绕的微澜。我已多年不沾酒了,举杯邀月留下的其实不过是关于酒的回味。在明光自然会想念起“明绿液”那如玉浴火的绿,但或许今天我们回味的已经不是一种来自绿豆的白酒,而是怀念那云蒸霞蔚的上世纪80 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