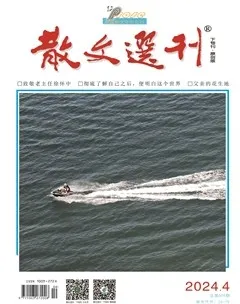忧伤的夏季
顾志坤

小弟1957 年9 月8 日出生,比我小5岁,1969 年我去部队当兵时,他才12 岁,没想六年后,他也应征入伍了,在安徽二炮部队服役,成了我名副其实的战友。他入伍后的第三年,曾回家探了一次亲,在路过上海时,曾专门来我的部队看望我,还住了好几天,我陪着他看望了在上海的好多亲戚,还逛了城隍庙、外滩和南京路等景点,拍了不少的照片。
小弟的个子比我矮,这与他出生时天天吃不饱、营养不良有关。有一年冬天,父亲在上海工作还没退休,小弟才两岁,有一天吃晚饭时,隔壁一位婶婶过来悄悄告诉我母亲,说邻村一个生产队刚种下了油菜,可以去割点回来当饭吃。当时家里的米桶快要“扔炸弹”(即米桶空了)了,能割点油菜回来也好填填肚子,于是天一黑她们就出发了,没想到了那块油菜地,发现为防止有人来偷菜,已经有人在值夜,母亲她们只好躲在一个坟头旁等候,待到半夜里那值夜的人回去睡觉了,我婶婶和母亲才来到油菜地。此时的油菜地,已被浓霜染得一片雪白,朔风也像刀割般刮在她们的脸上,母亲和婶婶便胡乱地割了几把油菜苗就回家了。这时已到了下半夜,我母亲放下油菜后,就到二楼去睡觉,没料一躺进被窝里,发现除了我哥哥和我在呼呼大睡外,還少了一个人,原来是我弟弟不见了。母亲这才慌了,连忙在二楼找,还把我们也叫醒了一起找,谁知找遍了二楼的角角落落,哪有弟弟的身影。母亲这才大叫起来,正在这时候,有一个细细的声音从一楼传到了母亲的耳朵里,母亲连忙冲下楼去,结果在灶间的菜柜下面,找到了因饥饿爬下楼去想找吃食的弟弟。这时候,穿着开裆裤的弟弟已冻得全身发紫,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母亲见状后,连忙把弟弟搂进怀里,号啕大哭起来。这以后,弟弟就落下了严重的哮喘病,一年四季总是不停地咳,连夏天也这样。
没想到了发育时,我弟弟的哮喘病竟被“带出”了,身体还长得十分的壮实,第一年征兵体检就全部合格,当场就被接兵部队首长看中。
小弟有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就是抽烟和喝酒,我劝过他多次,就是戒不掉。一部分原因是他应酬多,尤其在那个年代里,在工作上要得到上级和他人的支持配合,烟、酒的确是其他东西不可替代的。另一原因是他自认为身体好,“连老虎也打得煞”,这是他在我每次劝他时回我的托词。
小弟的病是在2003 年6 月21 日单位例行体检时发现的,其实在身体的症状上,他一点儿也没感到不适和异常,结果体检报告出来后,医生告诉他,在他的胰腺上,有一个很小很模糊的“点”,究竟是什么,他也说不清,为此,他建议最好去上海找专家看一看,以防误诊和采取相应的措施。
6 月22 日,我弟弟拿着体检单来与我商量,问要不要去上海?从他的神情看,似乎并不把这事看得很严重,还开玩笑说,他能吃能睡,连老虎也打得煞,会有什么事?
再说,他也没感到任何的不适。我说这事不要看得太严重,但也不要太不当一回事,我在上海当兵14 年,战友、朋友多得很,在上海的亲戚也不少,找个好医院和好医生应该没问题。但这事我弟弟表示了反对,说现在还只是个疑点,他不想为这事去惊动我的战友、朋友和上海的亲戚们,他甚至不想把这件事告诉单位的领导和同事,至于85 岁的老母亲,更不能把这事告诉她,让她去担惊受怕。待他从上海检查回来后,他再给他们作解释。
我弟弟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认定的事,其他人很难能说动他。就这样,我们通过其他渠道,联系上了上海肿瘤医院的一位专家。6 月25 日下午,我和弟媳朱岳英、弟弟的小舅子朱海根和陈志梅等陪着弟弟,在他单位领导、同事、亲朋好友及老母亲毫不知晓的情况下,来到了上海。
当晚,我们把那位给弟弟看病的专家约了出来,吃了一顿饭。席间,那专家仔细看了弟弟在当地医院拍的片子及检查的报告后说:“东西很小,问题不大,拿掉就行了。”专家也是个好酒的人,他举杯对弟弟开玩笑说:“来,我们俩干一杯,下次等你出院时再喝。”专家的话,一下子把笼罩在我们心头的乌云驱散了。
第二天,医院又重新为我弟弟做了各种检查,检查的结果与上虞人民医院检查的结果基本相符。为了保险起见,专家决定尽快给我弟弟动手术。于是,在7 月3 日的上午,弟弟就被推进了手术室,在手术室门口,我们依次与弟弟打了招呼,弟弟胖胖的脸笑眯眯的,看不出紧张的神色,就像专家说的:“问题不大,拿掉就行了。”但是,当乳白色的手术室自动门缓缓合拢的时候,我的心脏突然发生了一阵猛烈的收缩,就像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攥住一样,有点儿喘不过气来。
我的不良感觉是有预兆的。4 个小时后,当那扇我们望眼欲穿希望它早早打开的自动门缓缓开启时,我们都拥了上去,在一张推出来的病床上,弟弟紧闭双目,面色蜡黄,与4 小时前进手术室时的状态完全判若两人,这时候,就在我旁边的弟媳和志梅禁不住流下泪来。
我弟弟从2003 年7 月3 日在上海动手术,到2003 年9 月16 日去世,加起来不到三个月时间,这短短的治疗过程,可以用难以忍受、不堪回首来形容,但为了活下来,为了能在康复后给那些还蒙在鼓里的单位领导、同事、亲朋好友和老母亲一个交代,为了能实现在将来退休后找个环境幽静的地方去养老,他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一直顽强地咬牙坚持着。直至去世前一周,当他的病情已非常严重时,我提出能否把他生病的情况向他单位的领导报告一下,被他拒绝了,说:“再看看吧。”我知道,当时医院正在给他注射一种新研制的靶向药,他在盼望奇迹的出现。
然而这个奇迹最终没有出现在弟弟的身上。
弟弟于2003 年9 月16 日在上海肿瘤医院去世,终年47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