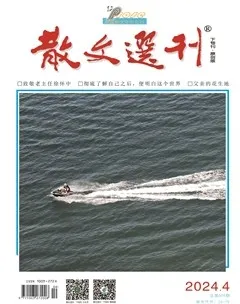燕去来兮
周小盟

是的,那是一群燕子含泥而归。沿着地图的经线,它们在一个个疏离的地名前,找到了陈年的旧居,筑巢,产卵,哺育雏燕。
燕子体型小,羽毛乌黑,翅膀薄而窄,嘴喙短而细,尾羽似剪,主要以蚊、蝇等有害昆虫为主食,是家喻户晓的益鸟。因為燕子的故乡在北方,古人称北方为玄色,所以,燕子又名玄鸟。玄鸟是一种迁徙鸟,冬去春来,秋冬天气转冷时飞往南方,春暖花开之后北归。玄鸟常在屋檐或山洞间筑巢,民间俗语“玄鸟进家门,多福多儿孙”,便表达了燕子屋檐下筑巢能为人家带来福禄兴旺的美好寓意。
回到村子里,三月的暖风吹开寒冬荫翳的薄雾,在院子里打了一个旋儿,然后在屋檐下的燕巢中落脚。母亲把旧年的巢穴保存完好,那位故友,今年又轻啼着我的母语带来远方的问候,飞落在门前的电线上,吟诵着川北春天的一首抒情诗。一词一句,落在故乡的村落,落在每一缕缓缓升起的炊烟里,由近及远,由低而上,伴着鸡鸣鸭叫、犬吠牛哞,把故乡的交响曲带到更远的地方,带到我生存的空间里,簇拥出鲜活的亮光。
午饭过后,母亲推着父亲去院外晒太阳。日光慵懒,在那棵蜡梅花身上耷拉着脑袋,此时新叶已在蜡梅树身上抽芽,未凋尽的花尚在枝头残留。蜡梅是十多年前父亲从外地带回来所栽种在院落的,而今主干如碗口粗,枝繁如伞。父亲坐在轮椅上,居于蜡梅树旁,旁边的矮桌上放着母亲为父亲沏好的茶,父亲读着报纸,困了就倚在轮椅上小憩一会儿。母亲则打理着院落,在簸箕里挑选着饱满的种子,为春耕做准备。直至太阳一点一点从山头落下,冷气逐渐从空气中渗出来,忙活一天的燕子落在蜡梅树上歇脚,翘动着分叉的尾巴发出“啾啾”的叫声时,母亲方推着父亲进入屋内。父亲意犹未尽地望着远山,望着村庄,望着被晚风和夕阳余晖镀上了一层金的燕子,缓缓地随母亲进入卧室休息。父亲自生病行动不能自理后,目光中对屋外的一切有了更深的情感。
彼时,父亲的病已经很深了,我们都清楚地知道父亲来日无多,即将油尽灯枯。而在朴素的乡下,迷信的思想总是在大多数村民的认知里带着神性的光芒。外祖母也不例外,“喜鹊叫喜”“乌鸦叫丧”“燕子叫春”已经在她的思想里根深蒂固。因此外祖母认为,年年有燕子来衔泥筑巢,说明家里一切即将顺遂,父亲的疾病也即将痊愈。一种随季节迁徙的飞禽,是隐居在乡间的神,外祖母用一种最古老和最原始的方式,表达着对父亲的祈愿。
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光,就如同深冬时节的村庄,万籁俱寂,树枝在寒风里晃动着干瘦皲裂的身躯,仅有的一点儿色彩也早已被疾病抽走,被无尽的寒气和疼痛裹挟着,憔悴得像一张揉皱的旧报纸。生命无常,一向健朗的父亲,顽疾给了他重重的一击,那扇我人生中无坚不摧的高墙,仅在一次的春夏秋冬的轮回里便轰然倒塌。随着疾病的渐渐恶化,原本那个健谈、刚毅与豁达通透的父亲不见了,唯剩下一个无比沉默、无比安静的“老人”。
燕子停驻在蜡梅枝头,在早春的旭日和风里缓缓积攒着倦意,“啾啾啾,啾啾啾”,几声鸣叫,把村庄将醒未醒的困意拖得无比辽远。厨房里,母亲在忙上忙下,为我的回家准备着饭菜,暖阳透过纱窗照在她的脸上,把皱纹和沧桑映得绯红,这一年多以来,母亲为照顾病中父亲的饮食起居苍老了不少,满头的白发,就像是一场下了很久的雪。与病魔艰难战斗一年多以后,父亲最终还是败下了阵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那个燕子归去的深冬里。屋檐转角的燕子又飞了回来,叽叽喳喳的声音里还是故土的方言,似乎在告诉着母亲,告诉着我,告诉着蜡梅树旁的父亲,它们已携带春的问候再次回归。而它们不知道的是,春风吹走了寒潮,吹来了千里而外的它们,吹回了外地的我,却吹走了父亲。
今岁的燕鸣多了几分岁月的历练。我也将代替父亲,同它们讲述村庄和故乡。同时,我也将代替燕子,给母亲讲述我在外地的经历和见闻。时光远去,仿佛我也成了芸芸燕子中的一员,归去来兮,故乡和村庄只是停留的一个坐标,冬去春来,寒来暑往,奔波在生存的路上。
离开村庄的车途中,窗外油菜花渐次开放,在蜀中大地写出一篇篇金黄色的散文诗。成群结队的燕子在低空飞翔,一些落在油菜田里,仿佛在为这散文诗写下一枚枚标点,其中的一些,落在我的眼角,模糊了故乡和异乡之间的距离。阳光从远处的山岗上刮过长久的绿意,透过蓝色窗帘的缝隙打在对面一个中年大叔的脸上,胡子棱角分明,满脸写满了困意,见我在看他,他条件反射般冲我笑了笑。我本能地躲过他的眼神,恹恹地望着窗外,熟稔尘世的大叔率先打破了沉闷,他说起自己的来处和去途,描述着自己的身份,讲述着如我这般年纪时的经历,我循着大叔的思绪和语言倾听着,不时地对他的话做出回应。一下午的时间似乎很短,短到我可以听一个素昧平生、萍水相逢的大叔讲述完自己的一生。大叔眼角有些湿润,我不能对他的所有曾经感同身受,但对于我们南来北往的身份,很多话题,都是沉重的。
我跟大叔年龄相差二十余岁,但似乎我们都有极其相似的某种宿命的轨迹。像一只候鸟,在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之间不断地迁徙,抵达而又离去。或许,我们90后与70 后的两个年代的人能促膝长谈,不仅仅是源于我们的一个共同身份——檐下客,有相似的生活与人生心境;更是因为过去我少年意气、桀骜叛逆,一心只顾着自己的生活和娱乐,从不曾与父亲有过深入真切的交谈,而这些年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早已明白父亲这些年在我身上的良苦用心,只是我从未对那些温情做过确切的回应。而眼前的这个年近五十的中年男子,又何曾不是父亲的缩影……
大叔在中途站下车,我们做了告别,而我将继续北上,直抵列车的终点。
列车到达终点,北京通明的阳光倾斜而下,落在每一个身穿不同服饰的人身上。那一刻,曾经内心的很多迷局与困顿,似乎都在慢慢得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