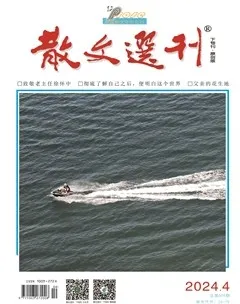鼾声
桑明庆

参加工作后,我第一次见识了鼾声的法力。
那时,我住在机关宿舍,隔壁住着一位中年同事,此兄是个重量级而且带着花腔唱法的打鼾人,每到夜晚,他倒头便睡,随即,“呼噜——啪,呼噜——啪”的雷声便持续响起,震动屋宇,穿墙而过,似乎窗玻璃都抖着颤音。有一次,他去朋友家聚会,晚上12 点多了还听不到隔壁的动静,我顿时起了疑心,便去敲他的门。屋内无人应答,我又给他朋友家打电话询问,朋友说:“酒场早散了,早应该回到单位了!”当晚下着小雨,我急忙找了个同事一起沿路去寻。大街上静极了,很少有行人来往,坑坑洼洼的积水在路灯下明明灭灭泛着光亮;雨点敲击着树叶噼噼啪啪作响,让人感觉浑身一阵阵发冷。当我们走到一条小路的拐弯处,猛然听到了那熟悉的鼾声。我们走上前去,见那老兄竟然双手抱着一棵桐树,身子斜趴在树干上睡着了。接下来的剧情十分简单,当然是俩人架着他回到宿舍继续打鼾了。
医生说打鼾是一种呼吸系统的疾病,尤其是身体肥胖、年老或嗜酒的人易得。
母亲年老后,也有了打鼾的毛病。不过,她的鼾声平缓而节奏均匀,没有什么大的起伏和波折。她晚年卧病在床,我在床前侍候,听着她那从容而又均匀的鼾声,我心里感到无比的踏实、安详,就像我儿时听着母亲的摇篮曲,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深秋的一个晚上,我喝了点儿酒,回家后便上床睡下了。待到醒来,我没听到母亲的呼噜声,睁开眼看到,母亲穿着一身单薄的衣服、佝偻着身子站在床前,正用她那瘦弱的手为我掖被子。我激灵一下坐起身说:“娘!你咋不睡呢?”娘说:“我见你的被子快掉地上了,给你拽拽。天凉了,别感冒了!”说着又去拽我的被子。我赶紧起身把母亲搀扶到床上,又为她加盖了一个小棉袄,直到她又打起了呼噜,我才上床。躺在母亲身边,听着那均匀的鼾声,此时我感觉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不由自主地流下了两行热泪。
终于有一天,母亲的鼾声永远离我而去。
母亲去世后,父亲仍然不肯搬到城里去,十分固执地住在老家,这就需要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轮流回家值班。冬季天冷后,在我们兄弟姊妹们动员下,他才进城与我们住进了暖气房。
新冠病毒肆虐,93 岁的父亲也没躲过去,发烧、呕吐、咳嗽、拉肚子、喉咙肿痛、四肢乏力,所有显性症状都出来了。原本就有高血压、冠心病的他,病情显然加重了。父亲喜欢单独住一个房间,我们夜晚的看护床只能支到外间。父亲也有鼾声,不过声响十分微弱。夜里支应父亲只能和衣而眠,因为要时而起身近距离观察动静。每当我蹑手蹑脚地走到他门前,轻轻扭开门把,听到他微弱的鼾声或看清他胸前被子有节律地起伏着才算放心。在我们的悉心照料下,父亲终于闯过了疫情这一关,身体渐渐恢复。老人久病,床前支应的活儿无疑是辛苦的、难熬的,但每当我听到父亲那阵轻微的鼾声,我都感到无比幸运,都会暗暗祈祷:即使折损我几年寿命,也愿换父亲的百岁之期。
妻子年轻时的鼾声比较轻微,每当夜静的时候,听到身边她那轻微均匀的鼾声,如同一支催眠曲,我酣然入睡。妻子身材比较瘦,又不饮酒,但晚上经常出现轻微的鼾声,是不是她的呼吸道有了疾病呢?但是,除了感冒以外,我从没有见她呼吸道发干、发痒难受过,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啊。我想她的鼾声是劳累造成的。妻子自从走进我们家门后,生儿育女,照顾老人,总是忙得团团转。年轻时,她既要上班又要照看孩子,还要为老人做饭洗衣服。现在退休了,她仍然需要照顾老人,还要带孙女,每天晚上睡得很晚,但只要躺下睡着便有轻微的鼾声出现。因此我断定,她的鼾声是劳累辛苦造成的。随着年纪的增长,妻子的枕头上也鼾声渐起。有时候我跟她开玩笑说:“喂!老朋友,你的呼噜也见涨了呀!”妻子不恼,却回怼一句:“自病不觉,你早就上过呼噜山了,不过是不想跟你说罢了,你倒先嫌了俺。”说罢,四目相视哈哈大笑。其实我平时好喝几口小酒,打鼾的毛病早已有了,只是父母沒说,妻子不言罢了。
夜静了,闻着身边妻子那带有韵律的鼾声我入睡了,一天的疲劳和烦恼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