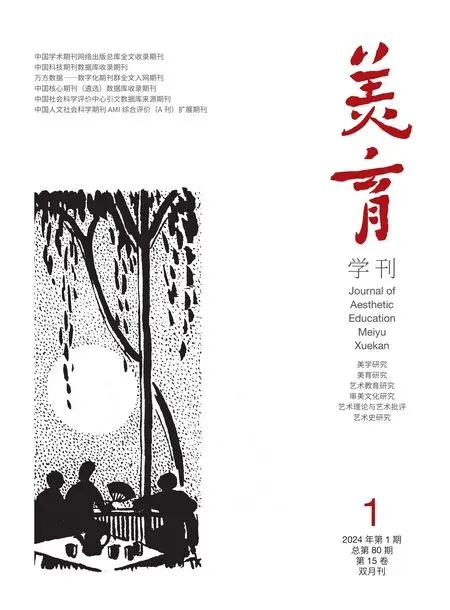区隔与重构:《贵州山民图》中的民族边缘意识
高尚学,魏海心
(广西艺术学院 人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2)
民族边缘的形成,一方面基于不同族群之间语言、文化、地域分布等方面的差异,一方面来源于群体间主观的认同与排异。[1]4清末民初之际,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全国上下都旨在将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之邦与处于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联合,建立完整的国家边界。[1]24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国部分学术机构和学校相继向西南腹地转移,促使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受到了更多关注,相关研究机构在此展开了众多民族学调查。庞薰琹(1906—1985),著名画家和工艺美术家,抗战时期随北平艺专迁至湖南沅陵,后又去往昆明。在昆明期间,他结识了闻一多、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转向了对中国传统图案的研究。1939年,庞薰琹至国立中央博物院工作,负责整理研究中国传统器物纹样,后与民族语言学家芮逸夫赴贵州考察当地少数民族艺术,创作了民族题材作品——《贵州山民图》组画。《贵州山民图》再现了贵州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并将民族装饰纹样融入绘画之中,具有历史性和艺术性的双重价值。此系列作品反映了汉族与苗族之间的文化碰撞,勾勒出了由客观文化差异所形成的传统定义下的民族界限,又因绘画所具有的主观性特征,《贵州山民图》隐含着汉族与苗族不同生态位的互动关系,潜藏着现代民族边缘意识,从中可以管窥民国时期民族边缘的重构踪迹。
一、民族边缘观念与《贵州山民图》
传统民族学观念将不同的族群看作一个个独立的区块,各个族群间以语言、服饰、习俗等显性文化特征作为基本的区分依据,呈现出一元性的区域划分标准。每个族群皆独有某种代表性文化,由此所形成的族群边界亦是相对明晰稳定的。自西方开启工业文明时代以来,民族学研究出现了所谓的“边缘中心理论”,即将民族调查的中心从各个族群的文化特征转移至族群间的社会边缘。挪威民族学者弗雷德里克·巴斯认为族群的区分必须经过排斥与包容的社会化过程,社会组织意义下的族群边界来自“一人以互动为目的,使用族群身份区别于他人”的这一情境中。[2]因此,近代民族学背景下的民族边缘观念形成于各族群间的主观互动,包括强化集体记忆、选择性遗忘、折损他人等,且互动峰值存在于族群边界的接触地带,并且此处尤为可能出现民族边缘的变动。因此,此种观念下的民族边缘不再是地理意义的存在,其形态较为多变、含混,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较大规模的边缘变迁,深刻影响着各族群间的地位关系。
基于上述观点,《贵州山民图》与民族边缘观念之间的关系成为需要思考的问题,二者作为不同领域的客体有着怎样的联系?是否可以用民族边缘观念重新解读《贵州山民图》?从总体时代背景来看,《贵州山民图》的创作时代处于民国时期,此时期的进步民族学者深受西方近代民族学说的影响,皆以科学、多元的方法展开本土民族的研究。李济曾提出:“我们出发点,应该是以人类全部文化为目标。连我们自己的包括在内,我们尤其不应该把我们自己的文化放在任何固定的位置。……我们具体的计划,就是先从自己的文化以民族学的方法研究起。”[3]也是在此种背景下,相关研究机构展开了众多边疆少数民族调查,旨在联合“四裔蛮夷”,消解汉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边缘分隔,构成完整的国族体系。[1]245而《贵州山民图》是以庞薰琹、芮逸夫的贵州苗族考察为背景创作的,画面中的人物、情景、衣饰等都以纪实照片和考察成果为范本,是民族学考察成果的艺术呈现。绘画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更具情感价值和表意功能。《贵州山民图》既反映了苗族的生活状态,又拉近了汉苗之间的情感距离,向居于主体地位的汉族群体展示了西南苗族的真实面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族对苗族的既有印象,促进了汉苗间的社会性互动。从微观角度而言,《贵州山民图》的作者庞薰琹与画面中的苗族表现对象构成了汉苗两族边缘变迁的微焦空间。根据王明轲的观点,民族边界的形成一是源于我者对他者的异己感,一是基于族群成员的根基性情感。[1]4庞薰琹在民族考察过程中参与了当地人的婚礼、丧葬、乐舞欢庆,从异己者转为了同胞亲友。就此而言,庞薰琴作为一个汉族个体融入了苗族之中,在此后绘制《贵州山民图》时,亦是将苗族特有的衣饰、风情融入了中国传统绘画风格之中,构成了汉苗间互动过程的一个缩影,弥合了二者的边缘区隔,与民国时期整体国族观念的建立具有一致性。基于以上所述,《贵州山民图》所传达出的深层意义契合于近代民族边缘观念,解读《贵州山民图》所蕴含的民族边缘意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贵州山民图》中的“自我”与“他者”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历来将满、蒙、藏等视为历史绵长的少数民族,对其有明确的地域界定,但并未明确西南少数民族群体,仅以“苗”“蛮”“夷”等称谓模糊地描述与区分该地域人群。[1]250-251直至近代,民国政府所建立的“族群”概念依旧未能明确划分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边缘。因此,为了深入探究西南地区的地理文化特征,中国近代民族学研究大多集中于此地。[1]251其中包括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等人于凤凰、永绥等地的湘西苗族考察,1934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云南的民族学研究,1939年至1940年芮逸夫、庞薰琹在贵州的苗族考察,1942年至1943年芮逸夫、胡庆钧的川西民族调查等。
此外,在中国传统的地域观念中,西南地区常被称为“蛮夷之地”。尽管自明清起,统治者开始重新审视西南地区的历史文化,但依旧无法摆脱“自我”对“他者”的偏见。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西南部的地域优势才得以凸显,民国政府及学术机构也逐步重视起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派遣众多民族学者对其考察研究,获取资料。[4]虽然中国近代民族学者大多对西南少数民族抱有尊重平等的态度,但在潜意识中依旧存在着“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文化区隔。黄文山在《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中写道:
中国民族之“我群”即为汉族,此为最初组织中国国家之民族,其文化地理,自成一个单位,一派相承,至今不替。“他群”则为边疆及内地之浅化民族,其语言,习尚,乃至一切文化,尚须经若干年之涵化作用,始能与“我群”成为一体者。[5]12-13
据此可知,汉族与边疆民族长久以来的征伐割据逐渐深化了二者间的地位差距,汉民族本位观念深谙人心,影响着民族边缘的构建。近代民族学者虽深受西方科学理论的影响,但仍无法摆脱以汉人视角审视少数民族的观念。他们在民族考察时最为关注的是少数民族与自身相异的文化特征,无意间强化了汉族与少数民族间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差别。
庞薰琹的贵州苗族考察工作以及所绘的《贵州山民图》亦显示出了“他者”的优越性。庞薰琹在贵州苗族村落寻访调查时,以收集当地民族衣饰花边为方式,汇集整理了大量苗族工艺美术成果。[6]虽然这些资料现已佚失,但此后所绘制的《贵州山民图》组画较为真实地还原了苗族的衣饰花纹,并将这些花纹视为独立于其他画面要素的装饰版块。有关文献曾提到,《贵州山民图》中的部分苗民形象是以芮逸夫的摄影作品为蓝本的,庞薰琹几乎完全依照摄影图片等考察记录,精细再现了苗族女子的动作形象以及衣饰花纹。[7]庞氏曾说他笔下的贵州苗民因是艺术形象,并不能以民族学的标准去衡量,但是在描绘他们的服饰时,却尽力还原其本来的面目,像女子绣花一般,按照原样“复制”到了画面上[8]。因此,《贵州山民图》并不是民族志式的少数民族图记,它具备绘画的想象性和主观性。但与一般绘画不同的是,《贵州山民图》中的苗民服饰花纹不是凭画家主观印象草草绘制而成,仅仅用以丰富画面,而是升华为了贵州苗族的“身份卡”,引导观者识别其独有的属性与特点。从这一角度出发,《贵州山民图》通过直观还原苗族在服饰等方面异于汉民族的某些特征,突出强调了苗族相对于汉族的“异质性”。这种倾向根植于长久以来汉人对苗族等边疆民族所具有的猎奇心理与征服欲望,最终的目的都指向强化汉族内部共识。相关研究表明,历史上各朝各代对汉民族边缘的巩固,除了最为直接的武力征战、通婚、贸易往来等方式,还会通过纪念抵御外族入侵的民族英雄、铭记历史中的抗夷战争,以及认识了解边缘民族的奇风异俗等方式,来加深华夏民族的历史记忆,从而凝聚起汉族内部的民族共识。[1]243因此,《贵州山民图》所表现的苗族装饰元素除了具备艺术功能之外,还反映了庞薰琹的传统民族观念,其贵州民族学考察以及《贵州山民图》的创作可视为汉苗间的个体互动案例。
综上可知,《贵州山民图》中的装饰元素因真实再现了苗族衣饰花纹,成为苗族的表征符号,从而具备了民族学意义,并侧面揭示了作为汉人的庞薰琹或仍在潜意识中存有对边缘少数民族的主体凝视,将贵州苗族视为异于自身的“他者”,独立区分了苗族的显性特征。庞薰琹认为社会与生产的发展推动着图案形式的变革,而这些图案形式不仅是民族状貌的象征,还是民族特性的反映。[9]据此,他将苗族的民族特性移植到画面中,展现了苗民独有的民族烙印。此种强调苗族服饰装束、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特异性之行为,于无意间深化了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边缘,进一步固化了二者生态地位的强弱差别。
三、《贵州山民图》对汉苗民族边缘的融合作用
清末民初,西方列强在中国及周边地区施以扩张战略,使我国民族危机不断深化,中国近代的有识之士力图建立以汉族为中心,以满、蒙、藏、苗等为边缘的整体国族观念,抵御外侵。日本侵华后,中国多地相继沦陷,位于中国内陆的西南地区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在抗击侵略、保卫人民等方面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基于此,民国政府在民族学调查之余,也采取了相关措施用以笼络边疆民族,从而凝聚中国各民族同胞,共同抵御外敌入侵。其中最主要的途径之一便是推动少数民族汉化,有资料记载相关政策:
查西南苗夷杂处,种族分类,号称一百种左右,语言、生活、服装、习尚皆堪自为风气,既无国家民族之观念,适足启邻邦觊觎之野心。滇黔边之苗胞,滇省南之夷族,广西之瑶人,川边之藏番,广土众民,监教莫及,兴学传教,人为我谋。东北之沦亡,蒙古之独立,宁夏之回乱,西藏之反侧,如履霜坚冰,谁为厉阶?亡羊补牢,道在同化……凡此设施,皆本救国保民之大职,设政府怀柔之补苴,款款之余,伏乞鉴察,并饬转令滇黔川桂各部,对于同化苗夷工作,咸皆注意。倘能共体斯旨,则三数年后,不难完成民族统一。[10]
另有文称:
要使各区之浅化民族,与比较先进之汉族,如速同化,所谓同化者,即以各族文化为基础,使之吸收汉化及西化,与汉族并进,如此则整个中华民族,可以于最短期间,孕育更善更美之新型文化。[5]22
在此背景下,国立中央博物院开展了众多少数民族调查工作,在充分考察当地的民族起源、文化风俗之外,还致力于推进少数民族与汉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在考察过程中,民族学者与当地居民建立起了身份、观念等方面交汇的桥梁,推动了民族边缘的融合与重构,顺应了民国整体国族观念的内在要求。1939年末,中央博物院派遣庞薰琹、芮逸夫至贵州苗族村落进行了数月的实地考察,所获成果颇丰。中央博物院相关资料记载:
贵州是夷苗聚居的地方,有仲家、花苗、青苗各种不同的种类。风俗习惯,和汉人大不相同,夷苗的服装修饰编织物等,尤其是个有兴趣的问题。本处达滇以后,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在二十八年十二月,派遣庞薰琹、芮逸夫二人往贵州,调查贵阳安顺龙里贵定四县的夷苗村寨六十余处,收集样本,并选择服饰纹样制成图片。[11]
本次民族学考察后,庞薰琹以贵州苗族人民生活为题材,创作了装饰性民族绘画作品——《贵州山民图》系列组画。这系列作品或将人物群像置于浩渺山水之中,表现苗民的习俗活动,或细致刻画苗族女子的衣饰花纹,展现其民族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在创作过程中,庞薰琹采用了毛笔、绢纸和水彩作为主要绘画工具,使画面效果与中国传统水墨画十分相近。例如《黄果树瀑布》一图表现了山崖处一女子眺望远方的场景,与马远的《楼台春望图》有着相似的取材和画面意味。前景处挑着果篮的妇女以背影示人,遥望瀑布山川;中远景山川由实到虚、由深入浅,极具层次感;大面积留白既凸显了人物形象,又生出无限的意境,表现出贵州山水的幽远开阔,深具中国传统水墨画的韵味。《贵州山民图》系列作品皆以毛笔勾线后再赋色,线条婉转流畅,继承了中国古代绘画的美学特征。庞薰琹认为线描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所在,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承载了形与意、虚与实、动与静、刚与柔的多重变化,并认为谢赫“气韵生动”的美学命题可充分诠释中国传统线描的表现技法与意趣。[12]此外,庞薰琹早年虽留学西洋,但他继承并发扬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将画面有无气韵视为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在他看来,艺术家应以“气”作为情感表达的出口,立象以尽意。[13]因此,庞薰琹在创作《贵州山民图》时即以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为依据,将中国水墨画的绘画方式及情感内涵,用于表现西南苗族人民,既呈现出带有文人意味的苗族形象,又开辟了传统人物画的民族新形式,连通了汉族与苗族各自的民族性格。其中,《垂钓》《卖柴》《跳花》等作品墨色朴实淡雅,虚实相生,为贵州苗族的异域风情增添了“象外之象”“景中有情”的画面意味,使苗民形象带有了汉化特征。相关文章曾如此评价《贵州山民图》:“各幅于线条,构图,颜色三项,均卓然成家;而人物之静美尤能表现东方艺画之矜持。”[14]总之,庞薰琹以绘画的形式将汉苗两族的文化特征融为一体,视觉显化了苗族汉化这一民族变迁的隐匿踪迹,《贵州山民图》亦成为民族边缘融合过程的绘画体现。
至此,综合前文可以看出,庞薰琹对苗族群体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矛盾性。这种矛盾的成因,一方面在于《贵州山民图》将苗族的衣饰纹样作为一个独立的表现对象,突出了苗族的奇风异俗,在无形中强调了汉民族本位观念,起到了凝聚汉族内部共识的作用,从而深化了汉苗两族的边缘区隔;另一方面在于他以中国传统水墨技法入画,将苗族的异域风情与文人艺术的淡泊清远相结合,贯通了汉苗两族的文化艺术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苗民族边缘融合的互动过程。因此,庞薰琹的《贵州山民图》对民族边缘进行了区隔与融合的双重构建,将民族视角与艺术视角相交汇,在矛盾中分别体现了民国时期民族学研究的有限性和多面性。
四、《贵州山民图》独特的民族学意义
晚清民国时期,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推动了民族学调研的蓬勃发展,新国族观念也在此时期得以建立。相关民族学者研究梳理了边缘少数民族的起源、变迁、语言、文化等问题,构筑起我国早期民族学发展路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族学研究寻找到了更为有效的发展跳板,也更具现实意义。抗战主线与民族研究支线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我国民族边缘的重构。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虽填补了中国近代民族研究领域的空白,但曲高和寡,此般专业性成果往往主要被研究学者所接纳和吸收,普罗大众作为民族的构成主体,或许无法从中直观感受到少数民族的风土样貌。而以《贵州山民图》为代表的民族主题绘画打破了这层壁垒,将少数民族形象赫然呈现在人们眼前,一篇名为《读庞薰琹的画》的文章曾如此评价此作品: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中国读书人的一句老话,但这句话也适应于现代的艺术家画家,一个写实的画家,却非身历多方现实不可。庞薰琹首先就把这一步做到了。走遍湘、黔、川、滇诸省,和中国边疆区域苗、夷、傜等民族有过接触,于是便采集了这些做了最好的素材,我们住在内地和沿海一带的人,对那边是非常隔离的,但是假艺术家之手,就轻轻的把二者拉拢了。[15]
同时,中国近代时期的诸多民族学考察大致相似,但庞薰琹所参与的贵州苗族考察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因为作为主要成员的庞氏并不具备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等专业身份,而全然是一位艺术家。因此,他的存在为贵州民族学研究规划了新的方向,使研究的目光更多投向了少数民族民间艺术领域,打破了民国民族学研究的局限性。在他的参与下,贵州考察团收集整理了许多珍贵的苗族民间图样,使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研究成果臻于完善。
与国立中央博物院同为历史研究机构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历史、语言、考古与民族学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亦开展了众多民族考察。其所长傅斯年曾在研究所工作旨趣中要求:“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16]不仅是语言学和历史学,与此相关的民族学亦然。作为画家及工艺美术家的庞薰琹便为民族学调查提供了与艺术有关的新方法,即以工艺美术的规律研究苗族的服饰纹样,以窥探中国远古的文化风貌,并将《贵州山民图》作为民族民间艺术的变体形式,使观看者,尤其是距汉苗边缘较远的观者群体更易接受。
除此之外,《贵州山民图》中的民族意识也辐射至此时期庞薰琹的整体创作过程。庞薰琹曾于1946年11月8日在震旦大学礼堂举办个人画展,除了展出《贵州山民图》组画之外,还展出了线描形式的“唐人带舞”。这些线描作品的创作时间略晚于《贵州山民图》,因其与敦煌壁画的飘逸飞扬有几分相像,所以相较于《贵州山民图》更具民族特色。这两部系列作品一个以苗族山民为表现对象,一个以唐衣舞女为主体,分别彰显了苗、汉独有的文化气息,二者虽内容各异,但都统摄于中国传统笔墨之法,亦古亦今,亦汉亦苗,将中国笔墨之古意与边疆民族之灵动巧妙融合。
在中国近代整体民族观念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庞薰琹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所创作的绘画作品多为少数民族题材,并采用中国传统绘画技法,实现了不同民族间风格的交汇融合。其中,《贵州山民图》作为这一时期庞薰琹的代表作品,上承他对中国传统装饰图样的研究,下启中国少数民族绘画的新样式,是庞氏绘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此系列作品诞生于庞薰琹的贵州苗族考察之后,其对于民族边缘的双重作用与近代民族观念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是民国时期民族研究发展历程的缩影。苏利文曾说《贵州山民图》系列作品标志着庞薰琹迈入了其绘画生涯的“灰色时期”。[17]此“灰色”意指此时庞氏的画面的多为蓝灰色调,但对于其整体绘画生涯而言,《贵州山民图》连接了汉苗两族的文化观念,其内核应是独特鲜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