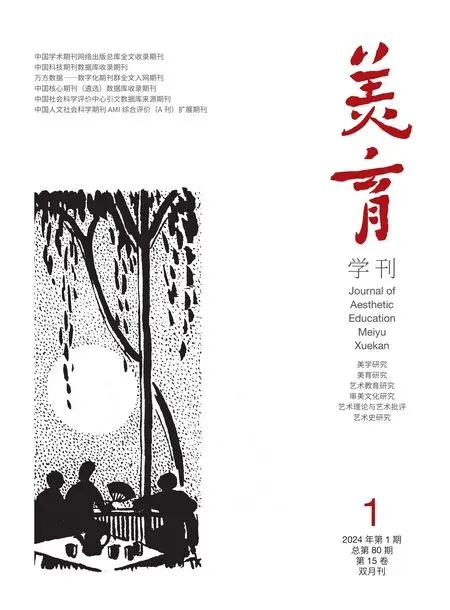论潘菽的美育思想
汪羽佳,刘彦顺
(1.合肥市曙光小学,安徽 合肥 230051;2.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潘菽(1897—1988),又名潘有年,字水菽,我国著名心理学家,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他在心理学研究过程中,一直极为关注美学、审美心理学与美育问题,把美学、心理学、教育学、美育学完全融为一体,有很多独到见解,在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史上独树一帜。
一、整全审美对象观与审美时机、审美同时性
潘菽虽然在专业、职业上属于心理学领域,但他对美学问题一直情有独钟。一方面,他对审美心理学极为关注,比如对实验美学的批评;另一方面,他在美学素养、美育素养、艺术素养上积累极为深厚,眼界开阔。在他看来,美学研究虽然已经有了久远的历史,但是并没有走向通达的大道,而且其现状值得忧虑——许多所谓系统的美学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让问题更糊涂了。潘菽认为,美学的毛病在于概念恍惚、语句浮华、陈述似是而非,看似很有哲理,但其实都是皮相之谈。
就其美学思想的核心来说,他所持的是一种非本质主义的美学观,也就是把美学研究对象设定为主客之间斯须不可能分离的审美生活。这不仅确立了审美生活的构成方式是绝对同时性的,而且其显现状态也是一个奔流着的时间持续体。他说:
美学应该采取动态的观点,一门科学的研究都须要运用动态的逻辑。美学尤其是如此。因为美学的问题在一切问题中是最具有动态性的。所谓美的特质显然有变化万端的表现,并不是某一种东西、某一种性质或某一类形式所能代表。过去的许多美学家都想在客观方面或主观方面找到美的特质所在。有的以为这是一种愉快,有的以为应为保持适当距离的观察,有的以为这是一种情感的客观化,又有的以为这是形式上的某种比例或多样性的统一,如是等等。但这类的说法都把问题说死了。它们在某种情形之下似乎可以说得过去,但在其他情形之下就讲不通。它们的共同毛病是在把美学的问题看成是静态的、机械的而不从动态方面去考察。[1]210
在他看来,之所以要采纳“动态”的方式研究美学,就是因为其研究对象——审美生活既不是纯粹的主观,也不是纯粹的客观,而是审美主体始终指向审美对象的一种时机化活动。尽管潘菽没有对审美生活的时间性状态进行专门的、具体的分析,但是他还是用了最为关键的一个词——“动态”来加以描述,而他不赞成的“静态的”“机械的”美学很显然就是没有时间性的。潘菽进一步分析了审美生活中主客之间的构成方式,他认为:
所谓美大概是主观和客观在某种关系之下的一种表现。既不单独存在于客观现象中,也不单独存在于主观的方面。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是随时变化的,所以必然是一种动态的关系,须要从动态的观点去理解。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人的审美判断是最多变化的,因时代而异,因地域而异,因个人而异,因社会生活而异,因文化水准而异,甚至因一时的情境和个人的饥饱寒暖而异。假如我们不从动态方面去理解,便没有法子把这种形形色色千头万绪的事实都把握在一起。其结果便只能作一种片面的和极不完全的说明,如过去的许多美学理论和美学系统那样。[1]210
在这里所说的变化就是审美生活的绝对时机化。每一个审美生活都是一件独一无二之事,审美主体在变化,审美对象在变,而且审美主体只能以感官直接感受可感的审美对象,因为审美生活作为感官愉悦感不具备回忆与反思的能力,也自然无法把握那些稳定的、不变化的一般性、普遍性之物。审美生活之中主客关系的变化,正是由审美主体能力、欲求的变化而引发的,“随时变化”——其实正是审美主体变化着的能力与欲求促使新的审美生活得以激发、延续,随时并不是随客观之时,而是随感官愉悦感的时机化的需要而变。
在他的《审美判断的研究:熟习的影响》(1934年)一文中,研究的重点就是审美主体对同一审美对象的欲求变化,其实这正是审美生活的常态——审美时机化。他说:
审美判断所包含的因子是极复杂的。但我们觉得其中一个主要的因子是熟习。同一张画,起初认为很好的,看多了便减少其激励我们的力量,同一支歌曲,初听是很悦耳的,听多了也就渐渐生厌,现在所报告的这个试验就是要测验熟习的因子对于审美的判断究竟有怎样的影响。[2]429
审美兴趣既随着相熟的程度而减低,同时兴趣又会在适当的时机再度产生,“熟习的确可以影响到审美的判断。一幅画看得多了,我们便会觉得它引人的力量渐渐减低。不过结果又告诉我们这种熟习的影响是会因时间而渐消失的。社会上对于艺术的兴趣时常变动。所以引起这种变动的原因固然决不只一个,但因熟习而生厌至少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一种旧的兴趣往往经过多少时而复活,这就大概是因为熟习的影响已消失之故”[2]435。在此所研讨的审美兴趣绝不是一种孤立的审美主体心理现象,而是一种有意义的审美意向行为。这表明审美兴趣是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滋生与激发的纯粹时机化作为,从而触发相应的审美生活。
以上所述在潘菽看来才是美学研究的“事实”[1]210,应该对其加以整体把握,而不能致其残缺。对于美学或者一切学科而言,确立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并始终保持其完整性是进行知识体系生产的唯一逻辑起点。潘菽认为,不能把审美对象局限于艺术作品,“更不宜限制于艺术中的某几种,如绘画或音乐或诗歌。艺术固然是人类的审美判断的高度表现。但人类的审美判断的表现却并不限于艺术”[1]210-211。他给出的原因很简单,“在普通所谓艺术的范围之外,人类的审美判断的表现大都是比较简单,比较采用一种原始的方式的。惟其如此,这种表现也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此,我以为美学的研究不仅不应该忽视人类在几种艺术之外的审美判断,并且应该注重这种判断的考察”[1]211。美学在根本上是一种常识性的学问或道理,但也更是一种行易知难的学科,人们往往不顾审美生活的常识而掉进形形色色的陷阱。
虽然潘菽并没有直接指出这种只把艺术作品作为审美对象的美学的渊源与现状,但是很显然,这种美学观念来自西方。自柏拉图、奥古斯丁以来,尤其是自康德、黑格尔以来,已经形成了一条教条式的铁律——美学研究的对象就只是纯粹的艺术作品,而不包括自然空间美、日用品的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美,并滋生出审美超功利、审美只是对形式的静观等主导观念。近现代以来,这种美学对我国的美学、美育理论的消极影响是决定性的、全局性的。潘菽给出的审美生活事实就很简单、质朴:
例如住在茅舍里的人到了过年的时候也要在门上或窗上贴一张花纸或镂花的剪纸;一般妇女都不愿意老是穿着同样的一件衣服(其实男子也是如此);人所用的工具和器皿,不管是精致的还是粗糙的,都要加上一点花饰;小孩子都喜欢听讲故事,即使这故事是毫无意义的;——凡此之类是举不完的,但都是研究美学的人所应该加以注意的事情。最可奇怪的是人的吸烟,味道既不算好,又不怎样好玩,恐怕只有从美学去了解才行。[1]211
最简单、质朴的审美生活事实,恰恰是最雄辩的。因此,潘菽认为,美学研究首先应该回到常理与常识,回到那些自明性的、原发性的审美生活现象本身:
审美的现象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生活中的。恐怕只有最低等的白痴才缺乏这方面的意识。在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找到审美辨别的存在,并且是一个构成部分。我觉得审美判断和人生几乎是同样的意义。所以美学的研究应该从全部的人类生活中去找问题。美学必须能充分说明人类生活的每一种审美现象,然后才能算是成功。假如我们把美学真正研究好了,也就应该对于人生得到了真正的了解。过去的美学把注意局限在几种艺术的范围之内和少数‘高雅’的人的生活表现,所以所见未免不广,因此所得到的了解都是片面的,甚至是浮浅的。[1]211
他不断地、频繁地使用的“生活”“人生”这些术语并不是含混的、含糊的,而是鲜活的、正在兴发着的审美生活之事。
二、“动的心理人格”与美育
潘菽的心理学、教育学、艺术理论是交融在一起的,这不仅显示出他学识、素养之渊博,也凸显出始终把美育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的卓越之处。现今心理学、教育学、艺术理论界限分明,据守各自的孤岛,很难产生像潘菽这样的大师了。他认为,心理学研究对象天然地包含了艺术欣赏与创造,“心理学是研究人类现象的基本原理的。所谓人类现象就是指人的种种特殊的活动。譬如科学的研究、艺术的欣赏与创造、言语的应用、社会化的生活等,都是人类动物所特有或特别发达的现象。研究这种现象所以能成立的基本原理的便是心理学”[2]150。而且,他的心理学研究也极为重视教育学,尤其重视人的全面发展,“自来凡关心于人类的前途和热忱于人类的进步的哲学家,没有一个不是抱有一种政治理想或教育理想的人,或实际就是一个政治家或教育家”[2]217。因此,将对艺术、审美的关注与全面发展的教育相结合,人格发展的理想结果就是潘菽所说“动的心理人格”[2]218。
关于人格,一般的教育学、心理学或美育理论只能设定一个静态的、既成的完满目标,最多也就是纸上谈兵,而潘菽所设定的则是一个时宜时机化的流动人格:“一个人的所以成为一个特殊的人,是因为他所能做的种种行为。一个人和别一人不同,就是因为所能做的行为不同。……儿童变为成人唯一的原因,是在对于环境的反应的增加。所以心理人格的改变不外反应的改变,心理人格的发展也不外反应方式的增加。”[2]218因此,心理学上的人格发展与教育学之中的人的教育就是完全重合的,或者说,心理学与教育学面对的只是同一个对象,只是其侧重不同而已。人格健全的标准在于人与环境之间建立完备的反应关系,“人格的健全与否,以所具对于环境的反应全备与否为标准。假如对于有利害关系的环境只有一部分能反应,其他部分不能反应,这就是反应的不完备,也就是人格的不健全”[2]219。应该通过教育达成一种鲜活的完满人格,始终持一种积极向前、向上的冲动。当其面对不同的对象、环境与信息时,就可以随时做出机敏而迅捷的反应,不壅、不塞、不滞,纯然流畅,直如天体流行,而不是通过空空洞洞的训练与教育而养成的“空洞的观念”。人格不是停留于心中的抽象观念,而是生动的行为,或者说人格的呈现状态正是直观的行为本身。
因此,潘菽一再地强调健全人格的这种奔流性,体现在他的心理学术语上,就是“反应”与“动”。他的观点集中体现在“心理的人格”与“道德的人格”之间的比较,“心理的人格是指一个人所能做的反应的总和。没有反应就是没有人格,反应方式愈多人格也就愈丰富。所以心理的人格只有积极的,没有消极的。寻常所讲的道德人格往往指一种消极的态度而言。如不什么、不什么的人便被称为正人君子、好好先生。这种观念推到极端就是和尚的坐关、道学家的遏欲。人变成了一个打光石卵子,到了‘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的地位,确是无可指摘了,但从心理学的观点看来,也就人格萎缩干枯,差不多等于一个僵人”[2]219。可见,“反应”就是“动”,就是养成积极、健康、敏捷且充满正常欲望的人格,能因应不同的时机且触机而发、奔流不已。
既然心理学、教育学研究的核心对象是“动的心理人格”或者完备的、完满的“反应”,或更准确地说,这才是心理塑造与教育活动的中心任务,那么来自社会的哪些刺激可堪“反应”?潘菽列举了7种重要的刺激,也就是“(1)口语;(2)手势;(3)颜面的表示和身体的表示;(4)身体的属性;(5)文字和符号;(6)制造品;(7)艺术品”[2]298。不难看出,在这7种社会刺激中,至少有3种与审美有直接关系——颜面、身体、艺术品。关于颜面,“至于身体的表示是指身体其他部分种种变化而言。这种变化也和其他部分的变化一样是种种行为的结果。譬如种种跳舞的姿势,磕头鞠躬的动作,轻佻或庄重的态度,挺耸或垂头俯胸的表现,迂徐或匆促的步伐,都可引起他人一定的反应”[2]307。关于身体,“我们的衣着、我们的冠履很可以说是我们身体的第二属性”[2]309。关于艺术,“人类社会的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艺术生活的发达和独立。艺术生活的发达和独立,有赖于优美的和独立的艺术品的创造以造成艺术的环境和刺激。一个社会中有了丰富的艺术刺激,然后能有丰富的艺术生活”[2]313。关于艺术活动作为人的需要,潘菽还强调说:
艺术也和言语一样是和人分不开的东西。我们所知道的最古的人便已有颇发达的艺术。现在世界上最原始的民族也无不以艺术生活为其整个生活的一种重要成分。人不但要吃饭穿衣以免饥寒,并且还要穿吃得娱耳悦目。人造一杆枪以打猎御敌,同时还必在上面雕绘一些花纹或加上一些装饰。人并不是吃饱穿暖以后再以余力从事艺术,而是把艺术的要求和衣食的要求看得同等重要的。[3]
由此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潘菽的美学思想是从审美生活的现实与感受出发的,比如颜面之于身体的美、运动的美,身体之于打扮、装饰的美、嗅觉的美,艺术之于生活的发达、丰富与文明,其范围之广远远跳脱出了中国近现代美学侧重研究艺术,侧重强调审美的超功利性,侧重强调视听感官是仅有的审美感官等书斋美学的藩篱。
潘菽痛斥那些不重视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大学直如猪圈养猪一般:
我们须知艺术是生活的一种主要的要素。没有艺术的生活简直就不能算是生活,不过是猪的生活而已。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社会是否有真实的生活最简易的测验方法就是考察是否有艺术的意味。讲到艺术的空气,我国的大学教育,尤其是中央大学,恐怕又都要打个零分了!仍旧单就我们中央大学而讲,走进我们的校门就看到我们的校地是瓦砾高低,蔓草纵横,好像是一片没有人居的废地。我们的校舍是东一座西一座,甲一个式子,乙又一个式子,没有一定的规划和系统。再可笑的是新砌成的那座宿舍,简直像一个洋灰涂成的大箱子,留几个孔便算是窗子,艺术的意味到此扫地无余了。[4]22
因此,在这样没有艺术空气的学校里接受教育,其生活趣味就会丧失殆尽,“在这样枯燥的空气中生活自难得滋润,要希望生活兴奋焕发那是很难的。这种生活上的残缺和偏枯,我们的大学教育可以忽视而不想法补救吗?”[4]23潘菽对感官愉悦感能力的重视与高扬,对感官感觉能力萎缩的辛辣抨击,的确使人倍感鼓舞。
因此,“动的心理人格”在这样的教育中就自然是脆弱的、单调的、凋敝的。潘菽认为,必须加强包括艺术教育、审美教育在内的生活的训练与陶养,以形成个体的“动的心理人格”。他说:
促进生活的要求,其道唯何?厥唯艺术。艺术是灌溉生活的要求的沃浆,增高生活的要求的火焰的油。艺术足以使人发见人生的真义,刺激人生的冥顽,鼓舞人生的飞跃,解放人生的缚束,指示人生的可能。艺术虽不是生活要求的冲动的一切,但艺术是生活要求的冲动的最高程度的表现。提高艺术的生活要求的冲动,就足以提高一切生活要求的冲动。艺术就是生活,使一切服从于纯粹的生活要求的冲动,这叫做艺术的人生。[1]48
由此努力,就会形成一个“动的社会心理人格”,其特征是强健的、活动的、发展的、有组织的,“中国社会实需要一种根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动力上的改造和加充。这种生活态度改造和生活力的加充是现在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所应该负起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4]24。可见,在对大学生施行全面教育之前,应该首先完成对大学教育者自身包括审美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
三、作为鹄的与手段的美育
潘菽认为不能仅就美育自身来论美育,而是应该从社会、人生、教育的价值与意义出发,得出美育绝不可被替代的铁论。他说:
我们大可以不必非难功利主义和所谓的物质文化,但有一点是很显然的,就是我们在谈教育的人大都缺乏蔡先生在提倡美育中那种阔大的眼光。立在高瞻远瞩的地方去看人生、社会,以及教育,这是蔡先生的美育理论中所包含的精粹。若仅仅把音乐和绘画等等的教育当做蔡先生所提倡的美育,那仍是皮相之谈。[1]117
可以看出,潘菽美育观的视野与心胸极为开阔,他没有为美育价值的独立去非难社会的功利主义与对物质的追求,而是认为这些都是社会与人生的必需,要避免就美育论美育的孤立现象。潘菽美育思想的突出特点,就是对作为手段的美育与作为鹄的的美育的区分。
何谓作为“手段”的美育?他说:“这就是用美育的方法以图完成教育的整个目的。”[1]117虽然这一见解与中国近现代以来诸多思想家、学者的思想没有太大差异,但更深刻处在于他不认同对美育功能的过誉与片面的拔高。他在宏观上认同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又对其有所批评,并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对于蔡元培对美育功能的定位——“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人生不外乎意志,人与人互相关系莫大乎行为,故教育之目的在使人人有适当之行为,即为德育为中心是也”[5],潘菽认为,其偏颇之处在于,“单单的美育却未必能达到我们所期望于它的目的。我现在的愚见觉得蔡先生所说的美育的那种功用是有条件的”[1]118。也就是说,美育的作用与意义是有限的,不宜捧得太高,否则就是滥用美育。他说:
美育并非一定能使我们进于高尚,能使我们捐弃利害,超越死生。在历史上看起来,极高尚的诗人如陶渊明以及极清介的画人如倪云林之类固然不少,但文人相轻,艺人相诟,趋承于势利之门,奔走于嗜欲之市,也是常见之事而并不是例外。所以我们要期望一个受了艺术熏陶的人就能破人我之见,去利害之心,那是不免要常归于徒然的。……我们应该彻底打破一种流行的观念,以为能诗善画的人就一定高尚而靠得住,粗言笨手的人就一定是一肚皮肮脏。事实往往刚是相反的。文和艺亦许正足以掩饰一个人的罪恶,使他更容易自欺欺人。[1]118-119
对美育功能的过誉、对审美超功利性的过度信赖、对诗人或艺术家人格美的幻想、对作者与作品关系简单的对接与对等、某些作品与为人的相反,等等,潘菽对这些现象的反思极为深刻。
美育的功能是提升感官愉悦的能力,未必能够直接使人向善或者向恶。他说:
但美育的功用似乎也到此为止。美育可以促进人的活力,然而却未必能保证所促进的活力一定用在正当的路上。这就像孳孳可以为善,但孳孳也可以为利。必须孳孳然后能为善,但孳孳却未必为善。同时,活力是道德的完成所必须,但活力也可以使人更容易积极为恶。所以美育虽然可以辅助德育,但并不能完成德育。[1]119
可见,在美育与德育之间不存在简单、直接的必然联系,或善或恶,这很难说,而且,潘菽此论的更深刻之处在于:“我们并不能希望于美育中达到德育的目的;有了美育亦许可以使德育比较容易,但有了美育却使德育更成为必须。”[1]119-120在美育理论中,一般会认为美育有助于德育,而且其论据多来源于一些不太足以为信的正面案例,这种论述方式几乎成为美育理论的一种固定的文法或语法,而潘菽却独具慧眼,不仅指出美育之于德育的养成作用是一种没有固定逻辑推导关系的或然关系,而且更精辟之处在于,正是因为美育或许会起到对德育的负面作用,所以,才需要更加强化德育自身,以此来限制美育的这一中性作用与功能。潘菽这一思想在美育理论思想史上是极为独到与深刻的。
潘菽认为,美育虽然往往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却是美丽的饰品与点缀,也是文化发达、教育发达的典型标志。他列举了很多形象的实例:“譬如眉毛有什么用呢?但没有了眉毛的一张脸就未免不成人样,所以一定要替眉毛解释用处的人也可说是不思之甚。又譬如房子,假如造得像狗窝一样,又何尝不可以以居以处,以蔽风雨,然而总不像一个房子”。[1]120此论极为精彩。他还从人的智能、人格全面发展的角度,进一步强化了美育的功能:“美育虽然可以同时帮助别方面的教育,例如德育,但美育有它自己的任务,并不仅是其他教育的奴仆,所以美育和德育、智育等等应该是并立的,并没有上下主臣的关系。美育必须和德育等等携手并进,然后能造成健全的人,只知诗文书画而别方面太要不得人便是有肝无心或有肠无肺的畸形人,要信赖这种人去担负起重要的社会责任,真可说是危矣殆哉。”[1]120潘菽对美育独立价值及诸育之间均衡发展的论述非常形象但也极为朴实。
在论及作为“鹄的”的美育时,潘菽把视野转向了诸育在审美方面的共同方向,把令人愉悦的感性价值赋予智育、德育,“教育的努力须以能做到充分无缺的美育为鹄的,我们要知道,最足以代表人性的不是道德,更不是科学,而是艺术。教育是以发展人性为目的的,所以教育的最主要的内容应该是美育,但这并不是说,德育和智育等等就和人性的发展无关”[1]121。就此而言,美育就成为整个教育的灵魂与统帅,但是,这并不是以美育来取代智育与德育,也不是以美育的手段去促进智育与德育,而是应该发挥美育对德育与智育的“有所领导”的作用。潘菽的措辞极为严谨:“德育和智育等等其实都是发展人性的某一方面所必须,因此也都是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在上面已曾说明教育必须各方面兼顾并重,美育统一,否则便不会教育出一个整个的人。能作这种领导和这种统一的便是美育。”[1]121所有的教育都是为了美好生活,由此当然可以把教育的唯一目的称为美育。
潘菽此论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
第一,在论及美育之于智育的“领导作用”时,潘菽认为科学研究应摆脱纯粹的、冷静的、中立的、孤立的研究方式与态度,回归与强化自身的意义感和价值感——让世界变得更美。他说:
智育使人有知识。但知识本身有什么价值呢?知识的一种价值是在帮助我们增进美好的生活。假如知识只是用来帮助我们互相砍杀,使地球表面变成丑恶可怖,那便是要不得的。所以智育是必须受美育的领导的。知识的其他一种价值是在使我们窥见世界的奇妙、自然的规律,引起我们的惊异赞叹。这时的知识便成为一种艺术性的领略,而培养这种知识的智育也就和美育相通相附而不复有显然的界限了。[1]121
只是盯着知识而不考虑知识所用的科学哲学,其实也就丧失了知识的人生意义,因为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获得美好生活或审美生活。
第二,在论及美育之于德育的“有所领导作用”时,潘菽首先对道德的两种善恶形态进行了区分:“道德的一种价值是在维持良好的社会使个人能顺遂其生活。假如社会中大家都互相欺骗,互相劫夺,有钱有势的人便可以胡作妄为,这便是一个丑恶的社会。因为这种丑恶的社会要不得,所以我们才提倡道德。”[1]121其中所说既包括道德的必要性,也包括道德行为随时而变的特性,所以他把善的道德行为视为美,而把恶的行为视为丑:
不过道德也可以有它的本身的价值。譬如欺骗别人,就社会的标准讲固然是要不得的,但说谎本身也就是一种丑恶的事情。又譬如慷慨赴义的壮烈行为,不被威胁的大无畏行为,谦谦有礼的待人接物行为,节约自制的私生活行为,都足以使我感兴赞美,像看到一件伟大的雕刻或一首好的诗一样。但这种道德可以说是行为的艺术,已和艺术在根源上很相近了。[1]121
把善良行为给人的愉悦感视为审美对象,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优良传统。潘菽说:“德育也是可以由美育统一起来的。不能辨别好丑的人也就不能辨别善恶。”[1]121这一思想与我国古典礼乐教化传统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在美育理论角度的新发挥。因为中国近现代以来,西方的主体性美学与美育理论对我国的影响极大,更多的学者接受了康德在真、善、美三种人生意义之间进行隔绝式孤岛划分的教条,尤其是所接受的康德审美超功利的教条思想更把审美与道德领域之间的交叉、交融、共有之处消弭殆尽,不仅造成视觉、听觉之外的其他审美感官被弱化,而且审美对象——人、空间环境、饮食、日用品等——大规模流失。
第三,在论及美育之于体育的“有所领导作用”时,潘菽认为,体育并不仅仅为了身体的健康与卫生,美育也应该是体育的方向:
现在讲体育的人大都只说它是所以增进健康的。但仅仅为了健康,体育就缺乏充分成立的理由。因此健康也和营养、居处、生活起居,以及公共卫生很有关系,体育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并且假如仅仅为了健康,体育也可以无须种种花样。我们必须认识体育同时是一种美育,然后能使它得到正确的发展,运动场上所常容易发生的丑事也可以希望减少。[1]122
因此,就智育、德育与体育之中向着审美的奋斗、发展方向而言,美育就不再是教育形态之一或手段之一,而是成为整个教育发展的灵魂之一:
无论体育、智育和德育都须由美育领导而统一起来。完全的教育必须包含德育、体育等各方面,不可或缺。但完全的教育也必须是由美育领导和统一的教育,因为美育是最合于人性的发展的,是贯通于教育的各方面的。在美育没有达到完满之前,德育和智育等等决不会先达到完满。这也就是说,没有完满的美育就不会有完满的教育。因此我们所努力的整个教育所达到的完满程度就可以把所包含的美育部分所达到的完满程度为测量的标准。所以我们说,充分无缺的美育是教育的努力的鹄的。但这里所谓美育是属于广泛意义的,并非平常所谓艺术教育所能概括。平常的艺术教育只顾到人的生活的某几部分,而美育则是顾到人的生活的全部分的。[1]122
博学于体育、智育、德育而约于或归于美育,一切教育都是为了美好生活,潘菽这一美育鹄的论可谓对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史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潘菽这种宽视野、高境界的美育思想并不是因为视角、方法的独异,而是来自他对教育现象的充分体察与把握。近现代以来,由于社会分工和学科建制的强大影响,学科门类、专业之间往往孤立发展,“鸡犬之声不相闻”,虽然各自专业得以发展,但也形成了孤立自守的局面,制定了各自领域的评判、考核、奖惩机制,各自为政,互相不干涉、不交叉,这导致的消极后果之一就是:那些完整的宏大领域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其重大意义也就不可能体现出来。这些宏大领域就其自身的构成而言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但在专业和学科过于孤立发展的背景下,它们常常被称为交叉领域或交叉地带,需要使用综合的方法或学科去进行研究。然而,这种研究方式破坏了这些领域自身的完整性。美育学科的发展也是如此。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学者、专家自身做到了全面发展与教育,才能自然而然地获得如潘菽这般的视野与境界——从审美生活的意义与美育的功能角度审视教育的整体价值与意义。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实践与修养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极端狭隘的专业化发展绝不会带来一个完整的意义及宏大的对象,也就是说,那种先在德、智、体、美、劳之间进行专业化的学科发展,而后再进行教育对象的整合的做法,是完全颠倒的。正确的、合理的逻辑是,先确保美好生活这一教育的根本目的,保持教育活动的完整性,再进行所属具体教育形态的发展。潘菽美育思想的贡献就体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