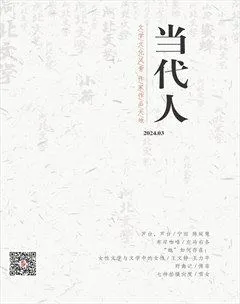书生的远景
因为一座楼,我要谈到两个宋时的蜀人。
一座楼叫远景楼,在四川眉山东坡湖畔。今天看到的远景楼,高十三层,只为纪念两个命名者:苏轼和黎錞。命名者,在宋神宗熙宁年间,都离开故乡蜀地,做了太守。
熙宁年间,苏轼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密州和徐州任职。
黎錞老家在广安军(治所今四川省广安市),离眉州两百公里。两百公里,狭隘一点,还是叫异乡。
两人都是一等一的读书人,也是百姓心目中的贤明。苏轼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与他的兄弟苏辙同科高中,名震天下。黎錞,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进士,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知眉州,官至朝议大夫,是个经学家。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
又说,天下好学之风在蜀更在眉州,好学之人在蜀亦更在眉州。
特别要提到眉州。眉州的水土和人文,相关互动——好学之人培好学之风,好学之风又风化山川名物:“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而大家显人,以门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眉州远景楼记》)
记文中所述远景楼,巍然耸立在眉山三苏祠东北五里地外,一到黄昏,金碧辉煌,老远都能看到。相比“三苏”故乡首席物化遗产——三苏祠,远景楼是个相对独立的个案。它的存在,只因如沐春风一般的自述在:
宋人最初收集东坡先生此文时,也收集了作文的时间——元丰元年(1078年)七月十五日,很明确。
多年后,我在关于先生书画艺术的专题展览中,看到了文章的墨稿,《眉山远景楼记》书写时间却是“元丰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书写地点也有的——乔居之雪寮。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的春天,苏轼贬谪黄州已遇三春,先生的人生尚在涅槃,情绪似乎刚刚获得缓解。那个春天,先生书写了大名鼎鼎的《寒食帖》,也造了“雪堂”,开始了与友人的交往,也有时间思考更大的命题。这篇《眉山远景楼记》,应是先生在书写《寒食帖》后,第一篇纯粹的书法作品。先生抄写了此前在另一个异乡——徐州任太守时的旧文。徐州的功课,应家乡朋友的托付。现在重新抄写,也许应某个朋友之邀,以换取资助的应酬,也许只为纯粹打发闲暇。寒食之后,先生在他的新居,一座简易的茅屋,见到了晚辈米芾、友人董钺,以观音纸作墨竹赠米芾,隐括五柳先生《归去来辞》,并即兴附和董钺的《满江红》。《眉山远景楼记》,跟那几个作品都不一样。至于它为哪位好友而作,不得而知。也许,它留给了自己。从笔意和章法来看,《眉山远景楼记》比之《寒食帖》,徐缓而稳重,在“二王”和“颜体”之间,寻找了一个可以倚重的态度。而题款,更是滴水不漏,但没有提到“雪堂”,只说了“雪寮”。“寮”收“堂”放,个中的些微区别,正好印证了书者情绪的些微变化——
自信已然拐弯,正在重新向上确立。
可以推断,那个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先生已经不再称自己的茅庐为“寮”,而叫“堂”了。于是有了《雪堂记》和“东坡雪堂”的佳话。
黄州重书的《眉山远景楼记》,与徐州初稿《眉州远景楼记》,少了作文背景的交代:“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筑之,作远景楼,日与宾客僚吏游处其上。轼方为徐州,吾州之人以书相往来,未尝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记。”
这个黎侯,就是黎錞。
黎錞是“老苏”苏洵的好友,跟“大苏”“小苏”也有交集,是个做学问的老实人,有个外号“黎檬子”。檬子,就是蜀人说的懵子,憨人的意思,当然是个褒义词。海南也有黎檬子,几年前我在海南儋州的乡场上,见过老百姓卖这玩意,有点像发育受限的小青橘,奇酸难忍,只能切片泡水喝。东坡贬谪海南后,也是见这货,又想起了故人“黎檬子”:“吾故人黎錞,字希声,治《春秋》有家法,欧阳文忠公喜之。然为人质木迟缓,刘贡父戏之为‘黎檬子,以谓指其德,不知果木中真有是也。一日联骑出,闻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大笑,几落马。今吾谪海南,所居有此,霜实累累。然二君皆入鬼录。坐念故友之风味,岂复可见!刘固不泯于世者,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随者也。”
这是东坡先生多年后的记述,个人情感的意味很重。而在远景楼一记中,苏轼对黎太守为文、为人、为事,专门有个客观的简评:“简而文,刚而仁,明而不苟,众以为易事。”
看得出来,异乡为官的黎太守是个做得多,说得少,干实事的执行型地方官员。明眼人会发现黎太守行事风格上似与东坡互补的。这样想,就很有意思了,因为苏东坡写此诗的时候,也是太守,不过在遥远的徐州。
苏轼与黎錞最初的交集亮点,在我看来,或源于一首《寄黎眉州》。这是几年前的事,东坡先生在密州任上。期间,黎錞来到眉州,做了先生家乡的父母官。
好朋友赴任故乡的时候,东坡蓦然就想家了。他的乡情,寄托在能托者身上:黎錞。先生试图通过友人,寄托他于家山瓦屋和峨眉的特别情感:“胶西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治经方笑春秋学,好士今无六一贤。且待渊明赋归去,共将诗酒趁流年。”
这是首鲜为人知的迎送诗,因为提到诗人的老师欧阳修,灵魂偶像陶渊明,提到他的故乡,也是我的老家,如此又不是一首世俗意义的迎送诗。
感叹六一居士,追随五柳先生,要表达的深意,都是浅显明白的。家山瓦屋、峨眉,为蜀中二绝。很多人不知道,也没有去过。苏轼不经意的一句“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一下让天下人都知晓了两山的美。这便是名人的光芒。直到今天,我們还在享受着先生带给家乡的红利。
两个蜀人,各赴一方。一个托付求命名文字,一个赠诗以表胸臆。如此互为寄托,是不是很有意思?
还有更具意思的。两人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踏踏实实做民生,兴文化,而且几乎在同一年,都在当地造了一座地标,黎太守在眉州造了远景楼,苏太守在徐州造了黄楼。
很多朋友认为,可能造楼就是当时为官者的政绩时髦,时间区间的重叠,仅仅凑巧而已。
有一个被大家忽视的时间节点,七月十五。这一天,苏东坡写就此文,他的黄楼要等到九月九日方才落成。也就是说,眉州的远景楼,或于此前业已竣工。先生赶在他自己的黄楼落成前,急就此篇友情文字,这仅仅是时间的巧合,还是东坡特意的构思?
眉州本土的苏学研究者认为,远景楼奠基于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落成于元丰七年(1084年)。这个说法并不一定经得起推敲。元丰元年七月,远在徐州的苏轼已经在考虑为楼赋文了,刚刚经历一个夏天到另一个夏天的抗洪和重建,有暇兌现乡人的友情托请。从东坡的行文中,我们知道了其自熙宁十年(1077年)正月初一赴任徐州知州以来,与乡人的书信互动颇为频繁。这一年,是黎希声在眉州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一年。老百姓也是在这一年对黎太守的为官之道有了比较完整的感受。观宋代士大夫的地方为官生态,要留下什么正面物证,比如造民生名胜之类,大抵会安排在任期的中后期。考虑到眉州老百姓向朝廷请命留任黎太守,此事落地之前,造楼工程或已完成:
“既满将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夺其请。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无事。”
苏东坡很可能是在这一年,徐州抗洪最紧张的时候,得到了乡人关于父母官黎希声的信息和请求,只是碍于民生公务缠身,没有马上启笔。也大抵在年末岁初之交,得到了黎太守留任的确切信息,才得以放下公务,考虑还乡人的请托,不然,以东坡的真诚为人,不会拖到朋友离任。再者,一座三层左右高度的砖木结构楼台,工程若前后拖达七年,这个效率,老百姓满意不满意且不说,黎太守和苏太守两个首先就不会满意。
黄楼于元丰元年(1078年)二月开工,八月十二竣工,三层高十丈。“黄”,取“土实胜水”(苏辙《黄楼赋》)之意,从名字可看出,苏东坡在他乡徐州造楼的目的,也是寄寓民生意愿,抒发抗洪胜利喜悦。苏辙在赋中,还有专门陈述。更有意思的是,九月九日落成典礼这天,苏东坡在黄楼专门设“鹿鸣宴”,大贺刚刚通过秋试的举子,并赋七律《鹿鸣宴》,作《徐州鹿鸣宴赋诗序》,大倡一乡文风。而在此之前的七月十五,他刚刚为远在故乡眉州的高楼作记,又有着怎样的深意?
我试着顺着东坡的行文思绪,做流水的还原。
元丰元年(1078年)七月十五日,苏轼表情严肃,写下了《眉州远景楼记》最开始的几行文字。接下来的叙述,更接近于自言自语:
当初朝廷以声律取士,各地的读书人就此养成华而不实的陋习。唯有眉州的士子,仍以西汉文章为典范,被外地的读书人视为泥古不化。官府的小办事员,也读经书,也习笔墨,他们所作公牍文字,竟然有古文遗风!大户显贵人家,以文章推重门第,甚至还不吝切磋,相互品评砥砺。老百姓与官府里人的关系,好比古时的君臣。官吏离任,还有人为他们画肖像,甚至虔诚地供奉起来。出了成就的,也有人自发口碑相传,一传就是四五十年呵。有心的老百姓还把家里的好东西收起来,以满足官府的需求。读律令条文是经常的事情,谁说读律令条文有什么不对呢?引以为戒。人一辈子哪能不犯一点小过,吃一堑,长一智,有些错误却是怎么也不敢犯的。二月二,龙抬头。庄稼人又开始新的忙碌了。四月初头,野草和禾苗争着蹿长,几乎家家的青壮劳力都上地薅草了。一个村庄都出动了,几十上百人,也没见有谁睡懒觉,打庄稼的迷糊眼。大家伙在田野中央放了个沙漏。有人看沙漏,掌握时辰。有人敲鼓,号令歇晌吃饭,出工收工。有谁要是想“哄”,鼓点没响就收工,或是花着心思磨洋工,会遭致集体的鄙视和唾弃。俗话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按劳分配,秋后算账。谁家田地多,劳力少,别人给你做了工,你就拿出银子补偿。到了七月,草也败了,谷也熟了,鼓和漏也收回来了。买来猪羊酒醴,祭祀田祖,而后酒足饭饱,朝着秋冬睡去……
原谅我,费上这么多的笔墨去复述大师的叙述。它只是一种庸常琐碎的痕迹,但痕迹与痕迹的叠加,一天天往下承传,最后成为某种不可磨灭的记忆链条。它可能与苏东坡的此篇楼记中,所描述的“俗”或“风”有关。
老实说,这不是一篇足够“好”的客套的应酬文字。他的好友,眉州知州黎希声,在眉山的民生城墙上竖了座楼,取名“远景”。据说站在楼顶,能看到十里外的村庄和远山。这是朋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得意之作,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眉州城固态的文化标识。
朋友是百姓心目中的好官——“能文守道不苟随者”;朋友也是知根知底的好书生——“为人质木迟缓”。
为这样的同僚说上些好话,也在情理之中。可苏东坡没有提及朋友的政绩和政绩工程,仍旧是一个人在那里自说自话,讲述他对百姓生活魅力的理解——苏东坡眼里的农耕文明时代,城市和乡村的“远景”。
苏东坡眼里的“远景”,与楼的实际高度和远处物化的风景,并无多大关联。他的远,甚至是一种“近”,或者“向后转”。普通的官吏和百姓——作为个体的“人”,他们也许只能看到“近”,眼巴下的“日子”更为要紧。世界很大,也很遥远,遥不可及。而未来呢?未来是多久?是十年,还是五十年?人一辈子能有几个十年,五十年?还是过好眼前的每一天吧。他不仅是“昨天”“今天”和“明天”,即便是“昨天”“今天”和“明天”,也是“日子”的三个全新版本了。
做官的有做官的修为,管好任上,不昧良心。做吏的有做吏的做派,听从差遣,甘为人下。做百姓的有做百姓的样子,遵受律令,伺候田地。苏轼所谓的“俗”或者“风”,会不会就是这样一种最民间的生存状态——日常的幸福?
只有回到眼下,我们才会感到想象中的“未来”,不再遥不可及。于是,苏东坡在东坡开出荒来种豆,把铜钱一袋袋挂起来计划着花。苏老头在掰着指头过日子的同时,也享用着最世俗最民间最简单最有人气的幸福。在平静中坚守平静,在日常中翻新日常,在琐碎中容忍琐碎,在重复中习惯重复。我们在平静、日常、琐碎和重复中,为我们的“明天”或者“远景”,日复一日地用力,再用力。
这么看来,我们是不是对苏东坡造黄楼作远景楼记,有了另外一层的认知?
它不是一篇世俗意义的应酬之作,而寄寓了超越个体人生风光,关乎百姓幸福愿景的政治理想。其个人的行高,更契合了公共的致远。
于是,故乡眉州远景楼之名,仿佛不可或缺,且有了洞穿时空,点亮今天的意义。
(沈荣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散文专委会副主任,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
特约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