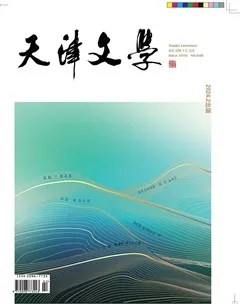小凤
也就在晚会最后剪辑合成之际,有个民办艺校送来了一个舞蹈节目,用民族舞形式表现黎族男女青年的爱情,令剧组所有人都跷起了大拇指。送磁带来的是一位舞蹈老师,其身段和姿色一点也不比京城来的跳舞蹈梢子的美女差,高人在民间,她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呢?华杰先是看到她卓绝的背影就动心了,等到她转过身来,把华杰惊呆了,眼睛一下子直了。熟稔的面孔,柔情的眸子,舉手投足的优雅,不就是在老城结识后不悦而别的心上人吗?是你呀,小凤!
美人乍一看见华杰,开始抿着樱桃小嘴,惊喜地微笑了一下,瞬间晴天转多云,一副娇嗔的神色说,你认错人了,我根本不认识你!便转过身一阵风似的离开了。华杰迟疑,是认错人了吗?还是她不情愿相认?一碗凉水一张纸,谁卖良心谁先死。在老城最初相识时,日思夜想,聚少离多,就那么几回的甜蜜约会,也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或者说还没有达到鱼水之欢的程度。在华杰离开老城时,二人见最后一面,说是在海岛相聚,日后回城省亲再重逢,却因华杰透露了已有相好于丽的信息,吃了小凤一个耳光,从此便断了联系。小凤尽管负气而别,总是没有放弃心向往之的海岛。即使不能与华杰再续前缘,也要独自前往海岛寻找梦中的橄榄树,离了华杰照样可以寻觅到自由和欢乐。就这么,小凤踏上了海岛,应聘到了这家民办艺校当舞蹈老师,尽管寂寞孤独,也自信能够找到幸福快活的另一半。小凤明知华杰供职何处,几次路过挂有招牌的他工作的地方,也从未想去会面,如果遇到华杰的那个相好于丽该多尴尬,索性以为这个当初山盟海誓的家伙死了,心里才干净,不必为一个负心汉挂牵。怎么这么奇巧?没想到来送节目磁带,却鬼使神差地遭遇了。这是真实的还是梦境?
华杰也似乎陷入了纷纭斑驳的梦幻。小凤上了海岛,为什么不来找我?即使没有发生过情人般的关系,作为乡党旧识总是可以会面,相互也有个照应。小凤还在恨自己吗?她来海岛的目的是寻找自由的橄榄树,还是旧情难却,迂回着暗中窥探,找机遇挽回曾经缠绵悱恻的情感?或者,小凤已经另有所爱,双双逃婚到了海岛;也许还是孤身一人,形单影只,像一只美丽的离群索居的南飞雁。她是小凤,一只小凤凰,一只从神话中的凤凰蜕变成现实中的活生生的孔雀。在舞台上起舞,或跳跃着走过大街小巷,都是令人注目的。男人会回头驻足,痴情地凝望着她秀美的背影,直到消失在视线的尽头。也许小凤就是一个略有姿色的女子,情人眼里出西施,华杰的想象又超出了普通人的视角,“诗情画意”了他的审美对象。
恰好,与华杰出双入对的于丽,独自回到青藏高原办理女儿的转学手续,十天半月回不了海岛,无形中给他留下了一个独身的空当。再说,热恋中的男女,总有潮起潮落的时候,亢奋后的平静似乎又形同夫妻,渐渐退却了陌生的新鲜感。不知是肉体牵引着灵魂,还是灵魂操动着肉体,华杰从刚才的梦幻中苏醒过来,又潜入另一番梦境,按图索骥,与小凤约见。小凤也许旧情难却,不便推辞,客气地答应了华杰的约会。
天下河水向东流,海岛上的河流却是从北向南流。跨过南渡江上的大桥,昔日荒僻的海甸岛上摩天大楼在生长,其密集的规模堪与寸土寸金的香港媲美。通向白沙门海滩洗浴场的车队人流,是一道海岛城市的风景线,亲近海水,会释放人们燥热的情绪,洗涤一身臭汗,同时也享受着男女的欢爱。海甸上有一处绿地,静静地泊着一幢庄园别墅,是民国初期修建的。不知哪一位下南洋发了大财的商人,经历千辛万苦,给后人留下了这份财富。追根溯源,其远祖可能是中原人,游荡到福建、江西一带,又来到海岛上,继而南下,越过无边无际的南海,在那片岛屿上淘到了金子。回归到出发的地方,临终修建了这座庄园别墅,没享几年福就故去了。庄园靠海边的崖石上,有一座小巧的灯塔,延年不灭,以熠熠之光为遥远处驶来的船只导航。华杰怎么也想不到,舞者小凤竟然租住在这个诗意而神秘莫测的地方。
这种绝美的哥特式建筑,在海岛上并不多见。尖尖的屋顶,窄窄的窗户,仅三四层高,既小巧玲珑又庄严沉稳。只是它的外观经历了百年风雨侵蚀,斑驳陈旧的灰白色,像一位长了老年斑的长老一样苍凉而凄美。最是海岛红色泥土中无处不在的榕树根,竟然把根根梢梢伸延到了古老建筑的墙壁中,绿色枝叶中冒出的丝丝缕缕根须,爬满了建筑的面孔,似老人的胡须一般。舞者小凤身姿绰约,淋浴着清凉的海风伫立在门前,迎迓姗姗来迟的梦中情人。华杰有点受宠若惊,上前牵住小凤修长白皙的小手,欲将展开臂膀吻抱时,被小凤矜持地推开了。小凤说,不急上楼,我们先散散步,环绕别墅欣赏一下这座美妙的建筑。二人便并行或一前一后,在脚步的缓缓移动中侧身仰望着,像在观瞻一幅巨大的西洋油画。远处传来钟楼的钟声,他们联想到了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也许在这古老的别墅里演绎过一场惊心动魄的爱情,关于一个丑男人卡西莫多与一个绝色美人的故事。说到这里,二人不寒而栗。是的,下雨了,朦朦胧胧,海面上腾起铺天盖地的白雾。
二人推开铁栅栏大门,踏上吱吱作响的旋转式木板楼梯,走进一间卧室,华杰这才意识到这是一座岌岌可危的破楼,像一个苟延残喘的耄耋老人。墙皮剥落,墙壁的缝隙长出了榕树的根须,漏水的水龙头滴滴答答,和着很密的雨声,倒像是一处天然的山水逸情之境。小凤说,你别再笑话我了,名曰庄园别墅,实为贫民窟,但我要的就是这个情调。喝茶还是咖啡?华杰一直喝雀巢,不要干粉伴侣和奶,加两颗方正牌方糖,就最合胃口。小凤打开一瓶白兰地,酒香四溢。二人坐下来呷着咖啡,点燃三五牌香烟,小凤也不用忌讳抽烟有失文静的形象,一起吞云吐雾。白兰地当水一样喝,顿时陷入晕眩。话语有一句没一句,不知从何说起,一个话题刚牵起又戛然而止,怕伤害到对方而引起不悦。双方在揣摸对方的心思,这突如其来的邂逅,如何面对,又如何延续下去,没谱。是猫与老鼠的游戏,是狼与小羊的对峙,谁也不肯越雷池一步陷入情感的泥沼,到头来是谁的错呢?久久地对坐,瞅着对方捉摸不定的眼神,烟抽得嘴唇发干,自觉口里很苦。终于在小凤起身添加咖啡的瞬间,华杰拉住了她的胳膊,转身搂住了小凤微微颤抖的肩膀,将一只忧悒的小鹿揽入怀中。小鹿是瞌睡趁枕头,顺势倒在猎手的枪下,软瘫成了一汪水,任凭猎手宰割。香烟点燃了内心情欲的火焰,血红的咖啡与白兰地酒精如火上浇油,一时忘却了身在何处,与谁在寻欢,管不了那么多,随着动物性的荷尔蒙的冲动尽情狂吻。临到宽衣解带的当儿,却从门口响起急促的敲门声!
谁呀?坏了二人甜蜜中的好事。华杰先是一惊,熄灭了刚刚燃起的情火,连忙整整衣裤和乱蓬蓬的头发,正襟危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支烟压惊。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入了一个坏女人的陷阱?这不是那个老城里日思夜想的舞者小凤吗?不就是那个在剧组偶遇的旧情人小凤吗?难道自己是穿越到了一个险象环生的魔幻之境?不会,不会的,小凤怎么这么快就变了,让海岛的大染缸染成了水性杨花的交际女郎?也许是小凤在报复华杰的见异思迁,马想吃回头草,没有那么便宜。小凤呢,听见敲门声的一刹那,脸色刷地白了,屏住呼吸静了一会儿,朝华杰尴尬地一笑,也不说什么。茶几上的电话是放在一边的,小凤的BP机是关闭的,敲门人只是凭借窗户的灯光,认定屋子里有人,怎么就不开门呢?也许人喝醉了,也许发生了意外,也许是出门时忘记了关灯,电话也搁置在了一边,或者是赌气拒绝开门?无奈,敲门的声音终于疲惫了,隐约听见下楼梯的脚步声,甩了铁栅栏门,悄悄地消失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华杰只是狐疑,并不问个水落石出。倒是小凤动了粗口,骂敲门者不是个东西,为她租了这处住舍,给几个脏钱,就没完没了地纠缠,想让她给他当小老婆,霸占她。他没尿泡尿照照,歪瓜裂枣一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真后悔自己当初答应他租房子,用他的钱,吃他的喝他的穿他的戴他的,就有还不清的债吗?女人喜欢虚荣,大凡有钱的男人投其所好,满足你的虚荣,却很少有不图回报者,那就是占有你的肉体,还口口声声说是什么爱你,只爱你一个,海枯石烂不变心,真是天方夜谭。华杰并不追问这个深夜的敲门者是哪路神仙,姓谁名谁,做什么职业,心想得赶快搭救小凤逃出去,离开这个也许有冤魂萦绕的危楼。好不容易挨到天快亮,华杰和携带不多行囊的小凤趁着黎明的曙色,匆匆逃离了这看似诗情画意的老式建筑,另觅下榻之处了。
这年的春节,海岛遭遇多年罕见的十二级以上台风,轮船飞机交通封闭,电力供应中断,孤岛成了一座死岛。华杰躲在刚刚换到新楼三室两厅的房子里,听窗外的海风在歇斯底里地号叫,尤其是对面民房顶层搭建的铁皮凉棚,被大风剥皮似的撕得噼噼哗哗响。听说琼州海峡的渡船被狂风掀翻,将钢铁甲板像撕纸片似的扯得粉碎,人如蝼蚁,该何处藏身?是人们崇尚的海龙王发怒了吗?它从无比宽阔的水面上集聚伟力,裹挟着大如巨鲸小如虾米的千军万马,以雷霆万钧之势,覆盖了这个小小的岛屿。海边的椰树如沐浴在狂风暴雨中的女子,秀发飘逸,腰肢婀娜,任凭洗礼或者是蹂躏。有的经受不住摧残,被掠去头颅或臂膀或拦腰折断,甚至连根拔起,露出丝丝缕缕的根须。华杰想到了舞者小凤,离开那座西式旧别墅后,与半夜敲门的臭男人断绝了联系,租住在了距华杰新舍邻近的一个家属院的居室。此时此刻,小凤的孤苦伶仃可想而知。正要出门,于丽来了电话,华杰并不去接听,不一会儿听见敲门的响声,知道是于丽上门送吃食来了,也装死不去开门。等门外没有了声响,华杰做贼一样偷偷溜了出来,在风雨中直奔小凤的住处。
好在这里是家屬院,配置有发电机,华杰一眼瞅见了小凤住舍窗户的灯火,一股暖流油然而生。他路过楼下邻居门口,在大风中也不忘摘一枝花盆里的三角梅,上楼轻轻叩响房门。小凤自然喜出望外,伸出双臂搂住了华杰的脖子,说不是北方的风雪夜归人,而是海岛的风雨夜归人,太有诗意了。一枝不起眼的三角梅,插在床头柜的矿泉水瓶里,也平添一丝鲜亮。为什么是三角梅?花期长,开得如火如荼,略带一丝蓝色和粉红,但花瓣的质感干燥,好像粉纸似的,缺少湿润的质地,仍有一缕清香。三角,三角恋吗?想想就好笑。为什么不是一枝红玫瑰,卷曲的团状,鲜嫩多汁,芳香扑鼻。畸形的男女恋情,早已不那么纯洁,不那么完美无瑕,是逢场作戏吗?却也是实实在在的情感的需要,是生理的渴望。居室内弥漫的异性的体香,顿时让华杰身心舒畅。
居室有一张床,一处厨房带洗手间,狭小却也敞亮。小凤为华杰煮了一碗汤圆,黑芝麻馅的,轻轻一吮便有甜蜜滑润的汁液溢出来,真是好味道。华杰对小凤说,多年前从乡下来到老城,第一次吃到这玩意儿,像老家吃饺子一样囫囵吞枣,不知是需要细嚼慢咽的,差点被噎死。这让在汉江边长大吃惯米质食物的小凤笑得喷饭,你真是黄土地的乡巴佬一个。还好有一台旧电视机,轮番播放海岛晚会的节目,华杰虽然在剪辑时看过几十遍,在这小屋里与小凤依偎着一起观赏,还是别有滋味。尤其是小凤送来的黎族风情舞蹈,作为主演的小凤绰约可人的舞姿,虽然比不上京城舞蹈家在帆船上演绎的现代舞那么诱人,却有山野之秀美,自然之纯情。华杰想到,星子他们这会儿也许在京城广厦某一扇窗户内,也在重温自己的杰作,而把讨要酬金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于丽呢,丢失了伴侣,华杰另觅新欢,也实在不仁不义,情何以堪。北方的老城下雪了,一个个落雪的年节,那些往事如过眼烟云。得陇望蜀的华杰,或是乐不思蜀的华杰,除了得过且过,已经无计可施。依偎在臂腕间的小凤,也不免乐极生悲,下床点燃一支烟,站在窗前苦思冥想。窗帘拂动,华杰望见她的肩头在微微耸动,猜想小凤的思绪也一定如一团乱麻。
温柔之乡的梦醒时分,台风停歇了,血红的太阳照在窗户上,从外边传来一阵阵鞭炮声,海岛又复活了。异域的年节,对于华杰和他周围的异乡人,皆是在落寞的心境中度过的。于丽暂且忘却了失踪的华杰,带孩子找乡党聚会去了。华杰似乎也不再避讳什么面子,带小凤去会老友,一打听知道方文离开海岛去了北海圈地,肖阳呢,自从答应离职而不知去向,只好找到了铁军住处。铁军因华杰对他和他媳妇上岛后的关照,怀有报恩的心思,对华杰的到来热情备至。媳妇更是忙前忙后,张罗了一桌好菜。酒席间,铁军只是羡慕老哥好有艳福,平时带的于丽,这回带的是另一个颇有姿色的女子,也不便打探来路。他媳妇本是个多事之人,几番窥探华杰旧人换新人的隐私,华杰默不作声,都被机灵的小凤含糊其词地应付过去了。饭后打了几圈麻将,有输有赢,华杰不动声色,小凤矜持有加,铁军喜怒无常,而他媳妇则斤斤计较,认钱不认人,气氛有点尴尬,索性便散了。
路过一处破旧的居民巷,华杰想到一位艺术馆的乡党石磊租住在这里,媳妇和孩子也到海岛过年,就带着小凤顺路去探望。楼下的主人也不问找谁,打瞌睡的看门狗也不理会来人,二人便登上灰暗的楼梯,爬上了四楼。乡党石磊是画画的,束着长发,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大过年的仍在画他的油画,海边修长且弯曲的椰子树在迎风飘拂。看见华杰上门,不胜欢喜,也不问小凤的来龙去脉,丢下画笔与来客抽烟喝茶。石磊说,本想给媳妇在海岛上谋一差事,在私人开的班车站卖票,因不懂琼语,没干几天便作罢,安心在家带孩子。华杰说,你媳妇是秦腔演员,这不丢了本行吗?小凤搭话说,艺校缺教表演的教师,可以去应聘试试。石磊说,海岛没秦腔,艺校是教琼剧的,连琼语都说不了,咋能唱戏?华杰说,也是。麻利的媳妇很快做了几个小菜,一起坐下来喝酒。男孩子五六岁了,在一旁啃着甘蔗,一边看电视,一边用屁股把凳子撞得咚咚响,也不听石磊训斥。媳妇把男孩哄到了内屋,只听噼噼啪啪一阵响声,接着传出男孩类似杀娃般的号叫。挨了一顿暴打,气儿给放了,男孩脸上挂着泪珠,抽泣着坐下来吃饭。华杰掏出一百块钱,说是给娃的压岁钱,男孩听了爸爸的话,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
隔壁住了石磊的一位女作家同事,也是乡党,被媳妇唤来一起坐坐。年轻女作家属于内向型才女,眉目端庄清秀,不善言辞。会写的人一般都不会说,会说的人把心里的话都说了便不会写。作为人才被艺术馆接纳,稿费靠不住,工资又低廉,只是租住了一间由厕所改建的小屋,茅坑填了,隔挡一拆,就做了住舍。她很高兴认识大名鼎鼎的华杰,答应给杂志写稿,说她的陋室就不请华杰光顾了,便客气地告辞。石磊说,女作家毕业于老城一所大学,轻信一中年男子的爱情承诺,说要和糟糠之妻离婚,便带她到了海岛做情人。谁知男子的妻子随后上了岛,纯情的女作家怎抵黄脸婆的死缠烂打,一场美丽的婚外情游戏就结束了。女作家不再相信爱情,发誓终身不婚,在文学的海洋中畅游,寻找心灵的安妥之处。华杰与小凤感叹,原来来到海岛的男男女女,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写不完的长篇小说。
说话间,一位披头散发的美女撞了进来,也不顾及石磊有客人,抓起饭桌上剩下的一个鸡腿就啃了起来。还埋怨石磊和嫂子,怎么有好吃的不叫她,说是快要饿死了。这是什么人?华杰和小凤有点诧异,面面相觑。美女随手拿起一个白馒头,夹了两片肥肉,咬了一大口,转身说,打扰了诸位,拜拜啦您!便扭着腰肢,一阵风飞旋出了门。石磊说,她叫芳子,也住在隔壁,是从北方来的一个女子,被男朋友抛弃了,只好在歌舞厅做事。经常昼伏夜出,出门时涂脂抹粉,打扮得很妖冶,也醉醺醺地帶不同的男人回来,放浪地狂笑,或垂死般地哭泣。有时也满脸血迹,挣扎着回到住处,不知受到过什么蹂躏和伤害。临过节前,还把一捧九十九朵玫瑰转送给石磊嫂子,感谢对她的关照。石磊说,尽管知道芳子是个欢场女子,但作为邻居在交往中感觉到了她的美丽善良,她生存的不易与无奈。芳子以为,做官千里皆为衣食,来海岛就是为了钱,至于做什么并不重要。有人用权,有人用商,有人用笔,有人用身体,为什么歧视有人用身体赚取生活费?石磊说不过她,只好闭嘴,画自己卖不出钱的画,所谓艺术审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呸!小芳常常这样嘲笑所谓正人君子的文人,满口仁义道德,背后男盗女娼,一肚子的坏水。这话说得,让华杰和小凤如坐针毡,似乎是说给他俩听的。其实,何尝不是说给石磊听的?五十步笑百步。
节后上班第一天,于丽嬉皮笑脸地对华杰说,你终于出现了,我以为你死到哪儿去了,有了新欢给老娘说一声,世上好男人多的是,老娘走开就是了,没必要贼一样躲着。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就像《红楼梦》里说的猫一样逐腥,谁也靠不住。华杰假装忙杂志稿件的事,默不作声,只有招架而没有还手之力。于丽说,你是让那个狐狸精把魂儿勾引走了,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了,你还带她逛街串友,甚至到老乡家里喝酒打牌。华杰听于丽这么一说,知道是被那个恩将仇报的多事女人出卖了,索性解释道,那是在铁军家遇上的乡党,是长得不错,过去也认识,一起吃饭打牌也有错?华杰明显是强词夺理,还假装一本正经,不想就这么摊牌,与于丽断了关系。再说是特殊的同事关系,弄不好会影响到杂志社的利益,缓一缓再说也好。于丽对华杰半信半疑,那就权当信了吧,一切又重归正常,好像不曾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二人又出双入对,同事们一点儿没有觉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裂痕。
和谷,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作协主席团顾问。著有《和谷文集》20卷及长篇小说《还乡》《海岛与故里》《柳公权传》等60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