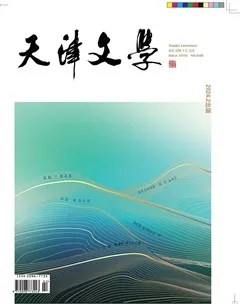北京秋事
1
我至今相信,缘分不是一件患得患失的事儿,无论脚步是快是慢,它的轨迹从未偏移那个即将相遇的地方。就像北京的秋天,一直在等待相遇衍生的惊喜和惊异。
81岁的父亲,因胃不舒服,经历了县市多个医院半个多月的医治和专家会诊,没有发现胃的问题,却发现心脏三根血管正在抗议。左前降支红灯闪烁,提示此路已严重堵塞。另两条的红灯也停在80%处警示。考虑到父亲的年龄,支架手术存在风险,医生建议,马上进行心脏搭桥手术。家里一场地震般的慌乱后,决定立即去北京为父亲做搭桥手术。
北京西三环日坛南路,我的车没能跟随最后一格绿灯冲过路口,停在了红灯的最前沿。导航显示的紫红色拥堵,让我想到父亲被堵的血管。在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333人的首都,每一个针孔里都可能住着一个人。着急是没用的,这时,一位交警随一片落叶一起飘到车前,礼貌地敬礼,标准的普通话。车开到警亭旁,询问进京原因,出示证件,开具罚单,并告知:外地车辆不允许进入三环以内。进京证要七天一审核。他看了看坐在后座的父亲说:走辅路,一直下去就到了。我不知道多少年后是否还记得这个轻描淡写却心急如焚的秋天,但此刻,北京对父亲来说就是再生地。此时我用眼睛去搜寻它与众不同的地方——与我的城市不同的色调;车与行人的密度;楼的高度或云朵的行踪。
父亲住的阜外医院,据说具备国内比较权威的心脏搭桥手术技术。虽然这种手术在很多省市级医院早已成熟,但妹妹还是通过朋友找到了一个在这儿工作的同学,经过电话短信的反复咨询,终于把一家人的希望放在了首都的这家医院。
医院不允许陪床和探视,只需买好术前、术中、术后各阶段所需用品,守候在医院附近,随叫随到即可。入院前的一系列检查一个都不能少,验血、验尿,检查心电图……各种检查后,医生对父亲说:“您是我们这儿有史以来年龄最大但血压最正常的病人,一定要再创造一个奇迹。”父亲笑了:“奇迹是奇人创造的,普通人创造奇迹压力太大。”
父亲表情淡定,脚步沉稳,住院部那扇大门即将关闭。他突然站定,回过头向我挥手,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这一眼,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眼前总是出现父亲站在码头孤单遥望的画面,心里会莫名地疼一下。
父亲的手术从下午1点进行到5点45分。将近5个小时,这是和时间拼耐心的时候。对面墙上的电子屏幕,几台同时手术的病人的名字一个一个在减少,最后只剩下三个。我和家人在等候区来回重复着“踱步”“坐下”“起来”“看屏幕”这几个动作。时间只管嘀嗒嘀嗒敲钟般从我心上踩过,每一声都让我心惊胆战。等待成了我在此时的唯一任务。等待手术的大门打开,等待父亲醒来,等待东方的鱼肚白赶走没有情趣的黑夜。就像儿时,等待父亲从那场震惊世界的大地震中归来。
2
那年的大地震来临时,父亲正在参加省先进代表大会,一群各行各业的先进代表,晚上还聚在一起谈生产谈家庭谈明天,几个小时后,三层的招待所大楼和这些人的梦一起碎了一地。碎砖乱瓦伴着呼喊声四处飞溅。住在一楼的父亲在大楼倒下前的几分钟醒来,大声喊着“快跑”,同时一手一个拽起同屋的室友,借助震波的惯性,被从窗口甩出。最后的一堆砖头,擦着父亲的右脚后跟一起落地。招待所瞬间夷为平地,砖瓦的呜咽和大地哭作一团。一夜的小雨掩盖了尘土的慌张,却让凄厉的呼救声、哭喊声此消彼长。上天的眼泪在天亮时流干了,人的眼泪却串成了剪不断的线。父亲的右脚后跟血肉模糊,他顾不上,他和两个室友循着地下的声音扒着砖头瓦块。可三个人怎么会是三层楼的对手?在钢筋水泥面前,三个血性的汉子蹲在地上放声大哭。
回家的路,漫长又辛酸,一路走,一路救人,捡到一只凉鞋,穿在左脚。捡到一只球鞋,穿到右脚。捡到一块布,裹住身子。没人相信父亲还活着,没人相信会有奇迹发生,包括我的家人和他的同事。35公里回家的路,父亲走了三天。
第三天,太阳怯生生地露出头来,它看到了大地失魂落魄的样子,小心翼翼挪动着身影,从一个树枝到另一个树枝,这是它安慰人间的唯一方式。十一家人的临时帐篷搭建起来,十一家人中已有七人死亡,还有下落不明的父亲。人们的脸上像结了冰。整整三天,我坐在帐篷外的马路上捡石子,这是父亲每天下班回家的路,我相信,石子捡到一百颗时父亲就会回来。
父亲出现时,西去的太阳停下了脚步,光线聚焦在父亲身上,为他镀了一个金身。我迟疑着站起身来,没错,是父亲。迅速跳起来扔掉手里的石子,向着父亲的方向边跑边喊:“爸爸回来了,爸爸没死。”帐篷里的人涌出来,呼喊,流泪,母亲突然双膝跪地,向着父亲的方向……
3
我住在南礼士路的一家快捷酒店。从南礼士路到阜外医院,步行,单向8分钟,着急可以骑小蓝车,符合医院十分钟到达的要求。早晨7点到8点,医院要求家属到医院等消息。7点整,我抓起手机,准时向医院出发。这一个小时,格外忐忑。盼着有01打头的电话响起,又害怕电话响起。电话不响,期待父亲的消息。电话响起,又担心消息的好坏。天亮了又盼着天黑。如坐针毡地熬到下午5点,再来医院等电话,听医生介绍病人病情。等电话的队伍很长,每个家属有两分钟时间倾听和询问。家属按医生点名的顺序站成两排,除了几个熟悉的女家属互相低声询问对方病人情况,沉默者居多,眼睛直盯着引导台上仅有的一部电话,似乎那里装着我们亲人的生死。我站在这个队伍里,这两分钟让我紧张,我忘了自己是一名央企客服部的管理者,可以轻松应对二十多万用户的各种问题。我一遍遍想着该怎样说话更简练更明了,既要省时间又要问得全面。
电话放下的那一刻,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似乎,父亲会因为我的问询加快康复的脚步。
4
“纸上声音书店”的出现对我来说就像一剂安神药。
我是在第三天边走边数路边的电线杆时发现它的,它藏在凹进去的绿化带后面。没人能看到我口罩下面僵硬的笑容,我好像已经忘了“笑”这个动作。我必须去那里客串一个角色,我在北京等父亲,它肯定是在这儿等我的。生活真是有心,它不愿看到我的落寞,便制造了一个惊喜。它知道我喜欢书,喜欢书里意想不到的变化和大千世界的神奇。我对自己说:“要让它站在我的身后,支撑我,看我演练悲喜的表情。”
我是不假思索就走进去的。大门玻璃上粘贴的黄色玩具狗机械而温柔地重复着人的声音:“欢迎光临。”书店有两层,每层六七十平方米的样子,看书的人并不多。上下结构一样,一条不宽的圆形过道,靠墙的书架和中间书桌分门别类摆满了书。夫妻二人各负责一个楼层,女主人负责一层和结账。二层的咖啡屋可以要上一杯拿铁或卡布基诺,坐下来阅读。环顾左右,发现氛围极其匹配“纸上声音”这个名字。寻找、购买、翻阅,全程都在无声中进行。
爱特加·凯雷特的《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就是在那儿吸引了我,我怕它的敲门声破坏了书店的安静,翻看了十几页后便收留了它,以免再响起第四个拿枪人的敲门声。郭文斌《永远的乡愁》在家早已成为我的座上宾,在这儿一眼看到它,觉得它更适合与大都市形成对比来阅读。他说:“人生就像一场刺绣。”他相信缘分,等待缘分。我还没悟透父亲与北京的缘分,我在郭文斌“刺绣”的生活里想象父亲在病床上的煎熬——开胸、缝合,十多个小时醒来后无意识地抓狂,疼痛是父亲在北京的叙述方式,虽然一句他的倾诉我还没听到,但在一个耄耋老人身上完成的“刺绣”恐怕很难掩盖疼痛的痕迹。想象心脏的骤停和电击的画面让我眼神呆滞,停在书的某页忘了移动。我明白,书的很多主人都败给了时间,但文字的力量和教益能让时间惨败,我想我的父亲也会让时间惨败的。
5
我突然发现了街上的热闹。
那些被我忽略的景色随着父亲醒来并渐好的消息聚到了我的眼前。大街上随处可见“美团跑腿”“饿了么”的快递身影风一样闪过。公交车不急不慌地从南北东西驶来,拥堵让它们聚在红灯前调整情绪,然后继续前行。记得有人说过:“如果看见一辆法拉利驶过,你可以骑上一辆‘青桔或‘哈啰追赶一番。不用气馁,在北京,电动车是有机会超过法拉利的。”的确,在北京,快与慢、车轮与脚步,会友好地彼此谦让。
路灯亮时,我坐进酒店外我的车里,关好门窗,陪我的车坐一会儿。我经常用这种沉默安抚我的焦躁,很管用。酒店门口戴着口罩的人进进出出。住进这种酒店的大多是阜外医院病人的家属。操着各种方言,神态焦灼。酒店外狭小的停车场经常停放着一些“鲁B”“豫A”“陕C”等外地牌照的车。车开进来的大多是和我父亲一样病情紧急就顾不上禁行和被处罚的家属。
我也曾站在阜外医院东南的天桥上,像站在码头一样斟酌“阜外”这两个字,我更愿意把它们拆开看。“阜”——可以想象多少年前的码头、渡口,想象舟帆远影,顺着大运河南下,它会在河边遇到我的城市,对一条河来说,北京与我所在的城市是一奶同胞的亲人。这两座城市的人也应该是兄弟姐妹吧。“外”——北京之外,我是把北京圈在里面,以一个外地人的眼光看圈内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仍能看到本地人的自豪。
6
见到那个东北母亲时,我相信了罗曼·罗兰所说:“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医院下午五点半会准时关闭大门,家属不能留宿。一些家属租住在附近的酒店或民宿,因为惦记医院的病人,睡不着时就围着医院散步,我有时也会加入这个队伍。不过,晚上10点以后的北京似乎比白天要热闹些。东北母亲就躺在医院的房檐下,几块红红绿绿的塑料拼图拼成了她的床。汽车的喇叭声、行人的谈论声、附近小饭店飘来的饭菜香,都提不起她的兴趣。她缩紧身体,来回翻身,被岁月抽打过的脸上内容丰富,憔悴、沧桑,心事重重。
她17岁的女儿因为心脏瓣膜手术在监护室已住了一个多月,为了省下给女儿治病的钱,这些天,她一直睡在医院外面的大理石台阶上。17岁的花季却开放在医院,是在母亲心里插了一根针。她随身的布包里放着几袋榨菜、几根黄瓜和几角大饼或烧饼,一个杯子时刻装满从医院水房灌满的水。早晨医院开门,她第一个冲进去,在卫生间胡乱洗把脸漱漱口,便在等候区开始充满希望的一天。
我想着这个东北母亲回到酒店,开始坐在酒店的柜台前跟服务员讨价还价。把有窗户的标间房换成无窗的大床房,把每天398元的费用降到298元。不再去酒店旁的饭店点自己喜欢的饭菜,买个小锅,可以煮面、菜、饺子,煮任何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
我仍旧胡思乱想,想父亲手术时的场景。想各种管子插满父亲的身体。猜测出现各种状况时父亲的样子。想周一出院的那个老人,一见到儿子就抱住他嚎啕大哭,定是以为的生离死别被再次相见的惊喜替代。想那个东北母亲,如果气温再低一些,她会在哪里的夜晚继续等候她的女儿?她的女儿,会不会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正吃着烧饼榨菜的母亲面前,轻轻地说一声“妈妈,咱们回家吧”。其实,我们一直在拒绝说拒绝听拒绝想那个词——死。这是个生活中必有又让人恐怖的去处。我特意去书店找到《我与地坛》,并大胆地多看了几眼“死”。没错,就是在这儿,北京,曾有一个与“死”打过很多年交道的史铁生,他经常把“死”挂在嘴边,他对死的亲近胜过嫌恶,却在有一天对他的长跑家朋友说:“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史铁生尽了最大的努力,活给自己看,活给母亲看。我喜欢他把悲伤堆砌成山包,在山包的顶端让希望拱出头来,然后,一切都被笑容笼罩……
我知道我的父亲也正在努力与命运抗争。他有一群孝顺的儿女,一群乖巧的孙子孙女,一个少有分歧的和睦几十年的大家庭。爱,是这个大家庭亲如一家的营养液,他舍不得丢下。死,是被这个家庭抛在荒郊野外的。
我去了史铁生去过15年的地坛公园,因为我也有了他“做人质”的想法。此刻,我的生活里只有父亲,我把信心抵押给“阜外”这座医院,而这个秋天也作为人质抵押给了我和父亲。
7
父亲出院了。那天是我生日。
父亲让我用一天的时间去转转长安街和北京的胡同,给他拍些照片回来,他要和他去过的迪拜、香港、深圳、海南、杭州比较一下。他说几十年前,他经常来北京出差,最快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车,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天安门和北京的胡同。我步行走过长安街,那天的雨单调、冗长,长安街一片金黄。我告诉父亲我可以找到北京不同的秋天。北京的秋天老舍写过,郁达夫也写过。老舍的秋天用心在高摊与地摊的美食——在小白梨的“皮嫩水甜无虫眼”,在“大酒缸”门外“葱炒羊肉和木槌敲裂蟹脚”。对他来说,北平的秋天就是天堂,甚至“比天堂更繁华一点”。他的秋天里充满年代感,是刚刚可以怯生生地把“繁华”贴到北平的脸上,是享受。这些对于现在的我们,早已是普通的家常便饭了。郁达夫不一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不远千里就是想“尝一尝”故都的秋。他带着时间赋予的饥饿感,想尝透北方秋的萧索和悲凉,他心中有对比,与他南方家乡的对比,与背井离乡人眼中的欣喜对比。“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他说若能留得住故都的秋天“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他对生命的大度无论如何我都做不到,我的父亲已年过八旬,他和病痛斗智斗勇的日子,显然也是绝不想舍掉他最多不过二十年的生命余额。我和家人提心吊胆地徘徊在大厅,等候在酒店,无非是想看到我的父亲健康地走来,一家人围坐一起,享受他该有的天伦之乐。我会在心里为这座医院、为北京戴上一枚名副其实的勋章。
收拾东西时,我在车里发现了进京时交警开具的那张罚单,揉成一团准备和其他杂物一起扔掉,父亲说留着吧,它也有救命之恩。打开,抚平那些褶皱,却发现两个字,那么醒目:警告!没有扣分,也没有罚款。眼泪瞬间滴落。这些天只顾忙着父亲住院,手术一次次签字,买东西,没时间去看一眼这份违章通知单上的字。这些天,我为父亲不知流过多少次眼泪,偷偷地,躲在酒店或某个角落,这一次,是为北京流下的,在父亲面前。
史丽娜,河北省沧州市作协散文委员会主任。做过央企管理、编辑,作品发于《美文》《当代人》《散文百家》《大地文学》《深圳打工文学》等报刊。曾获第四届刘勰散文奖、河北散文名作奖等奖项,有作品入选“中考记叙文阅读指导”,入选“2022年河北文学排行榜散文榜”。出版散文集《散步的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