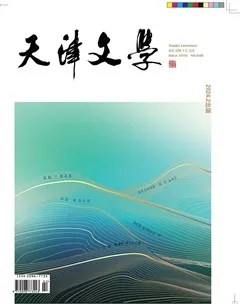富春山的白雪公主(创作谈)
葛芳
有一段时间,我在杭州小住。小区后面是富春山脉,连绵不绝,不远处是淙淙流淌的富春江,于是我经常在黄公望的世界里悠游。黄公望是大师,他传奇的人生经历,常让当下疲惫不堪的人们驻足思考。
黄公望出狱后,已经五十岁了。他穿上道袍,生活虽无着落,但也心宽,他漫游四方,一边摆摊卖卜,一边寻山问水。从此不用再去过问仕途、日常家庭生活琐事,所有这些都和他没有关系了。
五十岁开始学画,从此隐于自然,纵情于山水和艺术。
恐怕当今很少有人可以这样率性地放下焦虑,人临近中年,处处被庸俗和不堪纠缠。
那一年冬天,山上萧瑟,人与人之间充满防备与距离感。我到后山去,荒山野岭上撞见了一个色彩鲜艳的卡通人物——白雪公主,这是个玻璃钢雕塑,其他设施都已呈颓圮荒弃之态。只有她孤零零地翘首站立着,惊愕的表情里露出欣喜、诡异的笑容。她提着竹篮,里面放着蘑菇,她穿着漂亮的裙子,一直是那个样子看着我。我站立很久,她的眼神和笑容,仿佛在向我传递很多很多复杂微妙的东西:山与人,时代与人,古人与今人,童话世界与真实生活……
我凝视她很久,她也凝视我很久。她的目光坚定,始终用一种调侃、荒诞、怪异的目光和我对视。
我坐在书桌前,白雪公主的形象挥之不去。她凝视着我,因为我无意间走进了她的世界,原本她可能已被尘世遗忘、被消费者抛弃,她也就彻底死心了。而我是个闯入者,是个“雌雄同体”的人,我身上有男性的优缺点,也有女性的细腻和力量。她死死抓住我这根稻草。于是我们一起浮游,来凝视从我们眼前走过的形形色色不同的人。
凝视“准中年”。他们有些过早进入衰老,充斥着缅怀与遗憾,有挣扎与不甘。当下,中年人的理想不再是成名成家,而是力求获得轻松、不压抑、不憋屈。
凝视“新生代”。他们有想法,脱离束缚、个性,也带有一定的任性,在自我的空间里纵横驰骋自得其乐。
凝视“边界”。环顾四野,总有某个地方缺失边界感和道德感,一个荒诞不经的院子,可以让某些人仿佛置身孤岛,无视外在的一切,任谁都束手无策,普通百姓虽怨声载道也无济于事。
凝视“女性”。男人有天生的优越感,即使无业、无家、无爱、无性,依然可以用独断、专制、极端的目光审视女性、物化女性,做个赤裸裸的窥视者和跟踪狂。
凝视“男性”。当然整个过程还是由我和白雪公主共同完成。白雪公主积蓄着力量,一口怨气,她要把千百年来贴在她身上的标签狠狠撕去,做个反叛者!
我借用望远镜,借用手中的笔,来完成对中年男性的“凝视”。
“他”是个灰色的小人物,处于明明暗暗之中,虚虚实实之中,有用与无用之中。他有他微茫的理想主义,也有他颓废的现实主义。一个零余人,在一个被金钱、科技、官本位裹挟的社会中,他该何去何从?
这是一个现实困境。如果“他”想得明白,一切也会迎刃而解。
“我也可以把什么都抛开,抛开时代,抛开家庭,一个人,优哉游哉。”
“就在我把一切放弃的时候,我感到了平静。一种奇特又美好的空白。”
“一个人活着,就像一株植物,水、阳光、空气,就十分圆满了。”
物质追求可以降低到几乎零成本,大自然和艺术,也就成了疗救人生的途径。于是,黄公望成了“他”的人生导师,“他”用精神追求慰藉自己,又被庸俗推拥。他在一浪又一浪的富春江上试着去读懂眼前的山,去看透人生的风景。
白雪公主有许多动物玩伴——“瞎猫”“倒退着走路的老狗”“云雀”“戴胜鸟”,它们在山林与市井中穿梭,向她传递着各种稀奇古怪的信息。她,一直站在那里,凝视远方,品味现世。在后山荒弃的游乐园,没有孩子来玩耍,只有山野之风吹过,幸亏,我和“她”遇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