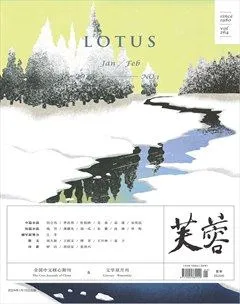在八月的漠南
舒洁
达里诺尔湿地
你美丽之息举起的另一种飞鸟
是我的诗歌,它不会随时节迁徙
它以三种颜色的羽翼深深恋着故乡
天蓝色,白云色,草绿色
它灵魂鲜红的色彩存在于凝望里
它扶摇如鹰,栖落如鹭
遇风如精细的水纹
你也是别致的牧歌
这不像诺恩吉雅,你的边缘
树木青草葱茏,曾经安坐着一座王城
我不愿说告别,或什么结束
达里诺尔湿地,你象征的
我们世世代代的爱与生活
怎么会告别?如何能结束?
在你的纵深,时光何止八千年
西拉木伦河源涓流何止三万年
达里诺尔湿地,遥念无穷无尽
岁岁繁衍的鸟类,在你的托举下渐次起飞
这种隐喻,这层次鲜明的闪现
成为人的无限珍重,娶妻生子
尊老爱幼,放牧牛羊和马群
因为爱
必须深谙你的语境,就从动词开始吧
在介词的过渡中领会某一个名词
达里诺尔湿地,我们匆匆来去
在你的上空,那一时刻的飞鸟
与我的诗歌相伴,飞向云阵最高处
我们已故亲人居住的屋宇
源自呼伦贝尔
——写给孙女舒日莎娜
这个时节
一些孩子在开花的草原上
骑着清香的草捆
他们微笑,身后是远山河流
沿途偶遇他们
我的孙女,我会问起他们的年龄
我想你,我也想让你走向幽淡的自然
让你认识蒙古马、马莲花
在满洲里,我想对你说一说远东
可我不能决定你的旅途
未来也不能。我的祖父
在我出生前就远走天国了
他没有给我留下只言片语
我的父亲,那个早逝的人
曾经为我指了一个方向
我记住了,没有悖逆他的慈悲
再一次重返静地
我的孙女,我发现巨大的改变
可能成为精神的遗址
孩子,我默默接受
我所维护的尊严
是此生的一部分,即使在应昌路
面对被阳光灼烤的石墩
我也会想到先人之语
那源流一样的祝福
依然如迎风而舞的鸟翅
以后吧
我会对你说所爱所得所失所思
写在西拉木伦河畔
祖父的马车
永远停在从经棚至乌丹途中
他把车留在岸边草地
骑马渡过了西拉木伦河
“哀草狂舞
一个年代终结于美丽女子的婚礼上
那辆马车,榫卯结构的车体
象征着曾经的紧密与必然的离散”
那不是迁徙
我的祖父,从北方以北
接回我尚在童年的父亲
在很多年里,我都在想象
我的童稚未脱的父亲
直视金色河流的目光
“歲月的隐语
从不揭示祖先的荣耀
说到养育,这充满尊严的承袭
至今未失平凡质朴的本色”
一个男孩
记住了两条河流,是在塞外
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无论怎样描述
她们都是姐妹,她们远嫁异乡
后来相逢一处,滋养了庞大的族群
我的父亲,在他五十五岁生日那天猝然离世
在弥留之际,他手指燕山泣泪无语
“河流
为什么会成为朝觐之地?
想一想被弃的马车吧,还有破碎的陶罐
你就会敬奉青草再生……”
贡格尔:隐约的手语
我的弟弟在凛冬的厉风中看护着羊群
高高的草垛和贡格尔覆盖大雪
清晨,我的弟弟抽水饮羊
围栏外出现几头黄牛
最老的牧歌在高处
大约在两朵白云之间舒缓飘散
于午夜时分化为银色的星子
那个时候,我的弟弟睡了
千里寂静,炉火正红
“就当是还愿和供奉吧
在那里度过三个寒暑,要心安
要感觉每一滴血里都有母亲浓缩的营地”
我的弟弟曾经描述深刻的孤独
是在夏天的贡格尔,在居中的蒙古包里
他的目光里走来雪季
我依稀看到红衣女子踏雪而来
牵着马匹停留在冰河边
妈就是在冬天出生的
我的弟弟话锋一转,时光就穿过了百年
就是这里啊!我的弟弟说
达来诺日!达来诺日
母亲风雪中摇篮
“一个八月
两个旅者从北部而来
他们向南而去,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室韦的鹰
它怎样飞
都不会在空中划出疆界
额尔古纳河,它展翼下的曲流
从不问世事变迁;在室韦
那只鹰以它的方式出现在天空
在我们记忆深处的一隅
没有留下它扶摇的痕迹
从开始就是错失
室韦的鹰,它的翅羽上承载着什么
当某种图腾让我们联想到
岁月风雨中的危崖
我们就会依恋阴柔
譬如朝露,鹰翅下的额尔古纳河
甚至在夜晚的牌局上
我们都会找到奇妙的组合与平衡
“它确实在那里
远东小镇,清凉的风
在去往界河的路上,有陌生的人群”
它显得孤独
它盘旋在时光之隙,在室韦
它成为我们回望的一点
至今未失真实和生动
也没有任何人说
室韦的鹰,那孤单的鹰
是往昔的魂
“是有幻象
那始终吸引着我们的存在
在辽远的寂静之地等待莅临……”
在上京以西
八月的贡格尔晚霞中现出刀锋
后面涌动着羊群
在被刺破的深蓝里,光焰
托举寂静的王子。入夜
篝火托举暗潮
空间的马以鹰的姿态飞过辽河西源
是一大群,头马洁白
尾马黝黑
你要相信醉酒的高原
有一位孤者在午夜仰望星宇
马鞍上有时间之眼,镶嵌的玛瑙
蜜蜡与绿松石,望着一隅尘世烟火
荒芜处横卧着青铜
信札
心语堆积的高塔顶端落着天鹅
另一只天鹅在低空飞
你能感觉的静止
可能是高原八月之夜的幻境
贡格尔河一再折流
不弃归处
我的孙女
再向西行,就是乌珠穆沁了
霜期将至,回头
我再对你说信札里的文字
如何影响了世道人心
漠南:祖父的叙述
他蹲在雪地
把猎枪口向上抬高半寸
与狼王对视。古老的河,峡谷
一个古老节日的前夜
“来呀!来呀
我的狼性是血
这是你永远也无法撕开的大幕
如果豪饮,我的狼性就是牧歌”
高原峡谷
一面林立陡峭,一面舒缓
风如流沙,狼群蹲伏
狼王的双眼射出蓝光
它嗥叫一声,群狼就跟随嗥叫
“早就该对后人说啦
孤獨坚忍的血背负着什么
节日啊!幻象中的亲人们
围着篝火舞蹈,在那样的星空下
你的视觉中都是爱与慈悲”
父亲!父亲
他大喊两声,狼王后退一步
狼群随着向后移动
父亲!你看这大雪
你看这刀劈一样的雪地上
你温热的眼睛
“难道迟了吗
在族谱最新的一页
美丽的女孩获得美丽的名字
吉祥的人啊!你接受天光洗沐
在蒙古高原的致辞中降生”
我的孙女
最终,狼王带着狼群走了
那个猎人弃枪拾琴
余生都在歌唱雪季
纯粹的追怀
不可问高原上的雨
一大群黑鸟为何有序疾飞
是迷乱,在低空一角
它们的翅膀被风所控
“古歌
支离破碎的花剌子模,残照溅血
最遥远的寄托存在于众公主的舞姿里
忧伤通向希望的路途……”
被消失了
传说中的国度,美丽的人
一场雨,总会有一滴含着踪迹
第一滴,或最后一滴
牵动中亚的光阴和云
“有一种高贵静若止水
花剌子模的王妃没有留下姓名
她是领舞者,她的目光穿透雨雾尘埃
在某地停下,她轻呼一声:我的边陲……”
不可闻箴言的色彩
你可以接近血红,花剌子模的天地
被宠爱的大鹰曾经久久盘旋
那是另一种舞姿
每一片羽毛上都有她们浓缩的身影
她们无语,面向故地
我的孙女
合上史集,急骤的马蹄声就远了
那一切是够久了,叫往昔
二十二年后
——写给我的孙女舒日莎娜
那时
就是你陪我用积木搭建城堡了
我会记得你四岁的想象
你的微缩的花园
那时我少言寡语
我的记忆将反复穿行于那个花园
建筑、门窗、院落与通道
洁白的凭栏上有绿色的装饰
还有你喜爱的十二种动物玩具
也会在明暗的世界里静止
我就守在那里!我的孙女
大概不会是每一天了
是每一年,或数年
我都期盼着你出现
在你我之间
不仅仅隔着自然的山河,所谓远眺
是时间和距离把我们分开
没有疑问,我和你分属不同的年代
我用诗文搭建的桥梁
一端在你幼年的城堡
另一端在我苍老的河边
还有我们的高原呢
我的孙女,我还没对你说
在西去途中,还有消失于
中亚以西的契丹
二十二年后
如果我还活着,我就对你说
飞扬的马尾拖着龙一样的尘埃
马头劈开新的路途
而智者,那个在中亚某地
发出慈悲箴言的人
为何将尘埃描述为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