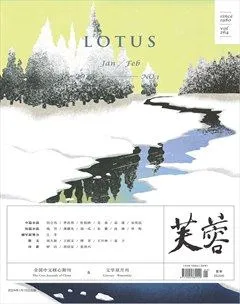东风夜放
风从土坡上滚下来,河边树林稀疏呈白褐色,地上积着碎叶。河羸弱,时流时断,低洼有积水。太阳在积水上晃。风纠缠在树梢叫着,发出鸟鸣声,呜呜呜呜呜。树大多秃头,新叶被风揉得皱皱的,舒展得很艰难。树并不高,窝在河滩上。河是季节河,不足三十米宽,草烂在沙泥上,还未苏醒过来。山并不高,山梁连着山梁,远远看去,如一列骆驼队。山体黄褐色,鲜有直挺的树木,球状的矮灌匍匐在土坡上。一个穿红棉袄的女人站在桥头上,两条路尽收她视野:一条临河,一条通往街上。我向她招了招手,喊了一声:表姨表姨。
赶了一天高铁又赶了半天客车,我第一次来到石炭井。风有些冷涩,但并不会让人针扎似的疼。街上也无人来人往,建筑物破旧,积满了煤灰一样的灰尘。河边一排排低矮的房子,盖着灰瓦,铁门紧闭,锈迹斑斑。这是一个旷大的生活区,给人深深的空洞感和悲酸感,如同进入了隧道。一九六七年,十六岁的表姨留了一封信给她爸,带着包裹,随北上的人流,懵懵懂懂来到了宁夏。一年后,表姨给家里来信,说在石炭井矿务局落了脚。她还寄来照片:站在煤山下,脖子上围着毛巾,一把铁铲撑在胸前,背后是一座荒蛮的石头山,山上落满了雪。她爸看到照片就哭了,泪眼婆娑,喊她:小贞啊,小贞啊。她爸就是我二舅公。
这个爱打猎的二舅公,生活在叫坳头的山区小盆地,买来中国地图挂在厅堂壁板上,每天睡觉前,举着油灯,看“宁夏”,看“贺兰山”。他喃喃自语:得空了,要去一趟贺兰山。可他终究没有去成。他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坳头。一九八一年夏,她爸饮酒过量,酣睡在床。第二天清晨,二舅婆叫他起床,怎么叫也不见他应声。他身子都硬了。家里给小贞拍电报报丧,她寄来一百五十块钱,说,两地相距两千多公里,太远了,事又多,祈求在天的人原谅、保佑。直到一九八三年腊月,表姨才第一次回到江西上饶,带着她丈夫和十二岁的儿子念树、九岁的女儿念水。她提一个圆篮,送来两袋枸杞、四瓶葡萄酒和一袋牛肉干,看望我妈。说起她没能来为父奔丧,她很是愧疚,说:这根刺一直扎在心脏上,怎么拔也拔不出来。
姐夫,我们石嘴山啊,你去玩玩,一点也不落后,光一个石炭井就有十几万人生活,像个小广州呢。表姨对我爸说。
石炭井种得出辣椒吗?没辣椒的地方就不好玩。我爸说。
种出的辣椒还特别辣呢,管你辣得烧舌。表姨说。
长辣椒的地方就是好地方,怪不得你去了石炭井,这么多年也舍不得回来一趟。我爸说。
硒砂瓜最好吃,又甜又脆,瓜浆水足,还不粉。表姨说。表姨用饭碗喝酒,大口大口喝,喝得大汗淋漓。她有着男人一样的魁梧身材,脸色酡红,手又糙又厚又大,腕还粗。她在贺兰山大磴沟挖了三年煤,有了孩子,矿务局安排她去了农贸市场上班。表姨父是河南人,是个支边青年,还在大磴沟挖煤。他不怎么说话,脸黑额宽,剃个圆形平头,高大剽悍,眉宇慈善。表姨喝了一碗酒,表姨父就站起身斟酒满上,也给自己的碗满上。表姨说,在石炭井矿务局工作的,十之八九是外省人,来自全国各地,以河南、山东和东北地区为多,有支边援宁的,有投亲招工的,有退伍复员的。她还邀请我哥去石炭井挖煤,说:挖煤虽苦累一些,环境艰苦一些,但收入高,生活物资充裕,比我们县城强太多了。我哥刚高中毕业,和邻居一起办砖窑厂,对表姨说:汉代,鞑靼人在那一带生活。
我已经读初二,知道贺兰山是宁夏北疆山脉,与内蒙古交界,属于昆仑山脉余脉,横亘六百余公里。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栴的封地在宁夏,一四〇一年,迁王府于银川,留有名诗《贺兰大雪》:北风吹沙天际吼,雪花纷纷大如手。青山顷刻头尽白,平地须臾盈尺厚。胡马迎风向北嘶,越客对此情凄凄。寒凝毡帐貂裘薄,一色皑皑四望迷。年少从军不为苦,长戟短刀气如虎。丈夫志在立功名,青海西头擒赞普。君不见,牧羝持节汉中郎,啮毡和雪为朝粮。节毛落尽志不改,男子当途须自强。
“平地须臾盈尺厚”的贺兰山大雪,让我无比神往。我拽住表姨的衣袖,向她请求:我初中毕业就投靠她,和姨父一起挖煤。直到一九九一年,我还想放弃工作,去贺兰山下养羊,但被我妈狠狠教训: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草没几根,养什么羊?表姨去石炭井,是因为家里穷得没饭吃。
其实,二舅公家族无人去过石炭井探亲,表姨的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结婚,也没派个代表去。表姨也很少回上饶。去一趟石炭井,要不少旅资、物资和体力。村里的李亮彬倒去过好几次石炭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在宁夏当兵,每逢大假期,他就去石炭井,在我表姨家盘桓几天。他说,石炭井是一个很繁华的偏远矿区小镇,有十三四万人,电影院、录像厅、大澡堂、游乐场、溜冰场、旅馆、娱乐场,应有尽有。唯一不好的,是煤灰多,晴天不见日,雨水乌黑黑。每次去,表姨都把他喝得醉醺醺。二○○六年,二舅婆病故之后,表姨再也没回过生养之地。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表姨给我妈打电话,说,大头(表姨父)因糖尿病走了,走得很安详。表姨说得很平静,说着说着,哽咽似的哭了起来。事后,我妈对我说:明年开春,你抽个时间,去一趟宁夏,看看你表姨,几十年了,也没个人去看看她,她嘴上不说,人老了,心里更想娘家人。
远离故地,谁还不会心念故地呢?她在宁夏五十多年,口音也没多大变化,每句话的尾音拖出一个长声调“呀”。
梨花初开,田野多了几分羞嫩与青绿。我去了石炭井。巷口内的一栋二层民房是表姨的家,毗邻石炭井局二中。棕黄的校门被铁栏杆紧锁,空阔的操场黑乎乎,看起来,曾堆放过煤炭。建筑物的外墙被裹了一层灰泥浆似的,黄黄灰灰,剥落了泥片。表姨握着我的手,说:四外甥,我来石炭井五十六年了,你是来看望我的第一个家人。你妈能来就好了。唉,你妈今年八十六岁,能自己做饭吃就已不容易了。过了桥,她大儿子念树从巷子走出来,热乎乎的手伸出来,和我紧紧握手,接过我肩上的背包。屋子里,是一大家子人。念水、念水丈夫、念水的两个儿子和儿媳,念树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念山(表姨三儿子)、念山媳妇和念山的三个女儿。看到他们高兴、赤诚的样子,我眼中一下噙着泪水。表姨虽已七十多岁,但身子健壮,腰板也挺直,脸上皱纹起伏,说话声洪亮,快人快语。十六岁,表姨从江西跑到这个荒野之地,如海棠果落在地里,缓慢且坚韧地扎根,枝开叶散,结了一树的果。树的生命,就是不遗余力地生长。
一九五八年,为支援酒泉钢铁公司,宁夏建设了石炭井矿区,开采炼焦煤。天南地北的人来到了贺兰山下,修铁路、架桥梁,开山辟路,炸石毁沟,掘井引水,筑房建屋,荒芜之地有了不息的人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矿采石的单位达百余家,乱采滥挖、乱开山炸石、乱排渣,生活区聚集了十数万人,人潮汹涌。二○○二年,贺兰山禁采禁挖,石炭井矿务局撤销,划归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管辖,人口外迁,人去楼空,这里再次陷入沉寂。念树一家去了石嘴山市生活,念水随夫在沙湖生活。念山一家去了乌海生活。表姨和表姨父习惯了石炭井,便留守了下来。整个生活区,只有百来个老矿工生活。两家中学、四家小学、一家技校、一家医院、五家银行和邮电所、商场,全部撤离。表姨父在河边种菜、做饭,表姨在十字街口杂货店,卖水果、烟酒、饮料、面包和日用杂货。店很小,只有两个房间,货也很少。南来北往的货车司机走累了,在店门口歇歇脚,顺带买些东西。仅此而已。
落日迟缓,石炭井卧在两道山梁之下。山梁蜿蜒,晚霞壮丽。两条主街道在镇中心交叉,大方砖砌的建筑(大多为两层)墙面,有许多洞孔。砖块黑灰色,给人厚重、苍凉之感。劈立的贺兰山,闪耀着白光。雪尚未融化。这是一座令我神往的神圣之山。余晖之下,贺兰山在奔跑。马群在奔跑。白马群在奔跑。风雪为白马群塑像。
翌日早晨,念树开车带我去沟口。他爸埋在沟口墓园。在S301公路走五分钟,转S314公路,往东走约二十公里,便是沟口。沿途,有好几处荒墓,孤坟或三五个荒坟,黄土堆着,坟头被风铲平,连一根荒草也不长。贺兰山千仞之高的崖石,凌空而悬,被锉刀锉出了骨骼。刺沙蓬黄哀哀。油松矮矮的,近乎伏地而生。一年一场风,从春吹到冬。风凌厉,折断高大乔木,只有矮灌和匐地草本才得以生存。在山梁与山梁之间,被洪水(融化的积雪)冲出裂口,石块压着石块,白白的,如晒干的蝙蝠鱼。沟,在贺兰山,有山谷就有沟。沟寸草不生。一条山沟横冲直撞,撞断了低矮的山梁,河床一下宽阔了起来,终年有了流水,在一个敞斗形的豁口,野花与绿树遍野,故名沟口。墓园在山脚之下,蜀柏葱郁,绿草茵茵。我想起了保尔·瓦雷里的诗歌《海滨墓园》开篇:这片平静的房顶上有白鸽荡漾。它透过松林和坟丛,悸动而闪亮。
只有我和念树站在墓园。那个从河南逃难来的男人,与贺兰山的沙土融为一体。大货车在公路上咆哮。站在这里,可以远眺银川平原北部。那是一片棕黄、土黄、灰绿、浅绿的平原,一片沉静、多变、淳朴、厚道的平原。黄河在平原上漂荡,像一条黄纱巾。黄河就那样流着,从亘古流向亘古。念树说,二〇一七年,贺兰山开始实施生态修复工程,他爸把他从石嘴山招了回来,上山矿坑回填渣土,清理渣堆,种植草木。念树十八岁高中毕业,就跟着车队师傅开大货车。他爸说:贺兰山的煤养了我们三代人,我们挖了几十平方公里的煤山,挖了百条沟,留下了千百道深壑、矿坑,不回填,不种树,就是欠下了后代的债。是债,就要还,我还不了,就你来还,你还不了,你儿子接着还,不能一代代欠下去。念树没办法,开着大货车回到了石炭井。他拉渣土,他爸挖洞种树。
在大磴沟,念树回填渣土,清理渣堆,干了两年。晴好的日子,东沟有千辆之多的大货车在拉渣土。他们大多是原车队的队员。他们熟悉这里每一条山沟、每一道山梁,像熟悉自己的脚板一样。七岁,念树就敢从石炭井走路来东沟了。十来华里长的土公路,走下来,腿也酸痛。他爸就说他以后是个在煤山刨食的人。他爱打架,不爱读书。混到高中毕业,跑车去了。他朋友多,从石炭井到石嘴山再到银川,从乌海到阿拉善到鄂尔多斯,都有他的死党。他说,路上跑的人,没有朋友,半截路也跑不下去。
挖了三年的树洞,表姨父不挖了。他患上了糖尿病。病来自家族遗传。他是握着表姨的手走的。他说:这一辈子,我能做的事做完了,做不了的事留给儿子去做,一代人做好一代人的事,只是苦了你一辈子。表姨用手捂住他的脸,默默流下了泪水。但她始终没有哭出声。在矿山,她见过太多死亡,有被飞石意外砸死的,有落坑摔死的,有被狼咬死的。她自己也曾距死亡一步之遥。她在医院产念树,大出血,难产。她以为自己会出血而死,拼尽全力喊妈喊爸。她多么想那个小脚的娘,想那个拿着竹梢追着她打的爸。喊得筋疲力尽,痛得昏厥过去。醒来,护士抱给她胖嘟嘟的男娃。她喜极而泣。她对大头说:我想爸爸妈妈了,渴了一样,想家乡直挺挺的树,想家乡碧青青的水,想家乡绿油油的山。男娃嘴唇厚,脸大鼻大,嚅着舌,闭着眼。
表姨父一走,表姨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只剩下自己孤单单的一个人。或许这个人世间,本来就是空荡荡的,本来就是有去无返的。
贺兰山是一条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也是草原与荒漠的分界线,扼守着西北宁蒙门户。三月四月,是大磴沟植树的季节。从石炭井开车到大磴沟,约一刻钟。念树去种树,我也跟着去。过了S301与S314公路交叉口,便是碎砂石铺就的山路。大磴沟的沟口新绿摇曳,酸枣、柠条、四合木、沙冬青、蒙古扁桃、贺兰山丁香、裸果木、野大豆、粗穗狗尾巴等植物,从融雪中醒来。它们被东风一遍遍地叫醒。东风在抚慰苍莽大地。似乎这些植物不是长在北疆荒漠,而是长在南方山地。念树说,这个沟口曾是堆渣土的地方,排渣后,人们种下了这片千亩绿园。
山路略显陡峭,很是颠簸,车子七弯八拐,过了两个山坳。念树说:车行走不了,我们走路进去。山洪冲毁了路。三个中年男人用装满沙土的编织袋,堆被水冲刷过的土坡。念树和他们说话。他们相熟。我发现,这些土坡都是用沙袋堆出来的,以做护坡。挖一条浅沟,埋下石头,在石基上堆沙袋,填渣土压实,再堆沙袋,再压实,一层层堆上去,恢复山体。我对念树说:这个堆土回填,量太大了,耗人,机械操作不了。
你以为这是南方啊。不用沙袋装土,沙土被风吹走,储了沙土就种不了树,山体也会塌方。在沟道里的矿渣、削坡形成的高陡边坡,很容易崩塌或者滑坡,一旦遇到特大暴雨,或急速融雪,会引发泥石流,造成的自然灾害是毁灭性的。念树说。他跟我讲起了一件事。二〇一八年五月,有人在沟口的一个山沟放羊,山洪突然暴发,席卷而下,来不及跑走的五只羊被冲走,水浪翻滚着羊。羊溺水窒息。洪水退了,羊搁浅在树桩上,皮肉被石头磨烂,脑壳也被撞裂,血淋淋。一只岩羊也是这样被水浪卷死的。念树说,消除地质灾害隐患是重中之重,修山、治污、净水、增绿、固沙、扩湿、整地,丝毫马虎不得。
山沟因早年的过度开采,成了“天坑”。“天坑”长六七公里,寸草不生,片石嶙峋。脸盆大的碎石,乱七八糟地翻在地面上。我爬上高高的土坡,放眼四望,只见四条“大天坑”纵横。一条“天坑”凹陷了七八个巨大矿坑,深达数十米,积着碧色的天水,看起来,像大地之眼。那是溃烂的眼睛,让人伤心欲绝。贺兰山是会感知疼痛的神奇之山,是父亲之山,眼睛溢出的泪水那么孤独、冰寒、纯粹。
在长约十公里的大磴沟,山峰、峰峦和峰丛被挖采,一眼望不到边的苍凉。黑黑的矿坑,干燥的砾石滩,薄薄的积雪。
风大,凛冽,但有些柔软。北风如刀割,东风如水拂。我戴起了连衣帽。砾石磕脚,我走得不顺。大磴沟的石滩、土坡、低洼,在前两年,已种上了树苗。树吐了幼芽。树苗较小,细如花露水瓶或啤酒瓶,行对行、列对列。种下的树是酸枣、蒙古扁桃、柠条、国槐、刺槐、圆冠榆、山杏、火炬、四合木、沙冬青、贺兰山丁香、沙柳、裸果木、柽柳、紫穗槐、紫花醉鱼木等北方高山植物。这些植物耐旱、耐寒、耐贫瘠。念树体力、脚力都好,走走停停,等我跟上。我也走走停停,驻足四望。数万亩的山地,种满了树苗。
树洞在年前就挖好,有的树种在年前也种了下去。树经过冬季的休眠期,来年春季发育快。往西走了五里多路,到了植树地。这里地势较为平坦,略有起伏。有百余人在种树。有人分树苗,有人铲土填洞。我种过很多树,在北方,却是第一次。我把树洞里的石块掏出来,树苗扶正,踩实沙土,回填沙土,踩实。
午饭是自己带来的,在山上吃。饭都冷了,羊肉冻在一起。我吃不了冷饭。山上没有柴枝,找一蓬死草也相当困难。念树说,平时都是回去吃午饭,这些天,车进不了山,就带饭来了。他叉开脚,坐在沙地上,吃得津津有味。他像他爸,壮实,高大,只是头发早早就稀疏了。他说,开车的人要有一副好胃,热也吃冷也吃,还得耐饥。他爸种不了树了,他接过铁镐铁铲,接着种。与飞鸟走兽、蛇虫一样,草、树是山的活体。山没有活体,就是死亡之山。
在贺兰山,活下一棵树,如岸上活下一条鱼。种下树苗,在夏秋旱季,还要浇水。平均年降水量四百三十毫米的贺兰山,水稀缺得如同黄金。蓄天然水、引山下的水上山,接皮管渡水。皮管长达十数公里,为一片幼苗注入生机。每一棵活下来的树,都足以震撼人心。膜拜一棵树,不仅仅是因为树活得如此顽强、艰苦、卓绝,更因为树是贺兰山的生命之旌旗。苍鹰在盘旋。
打硙口,在当地人的语言中,是指“打凿石磨的山口”。打硙口是贺兰山三十六隘口之一,是宁夏城防四隘之一,与阿拉善、平罗接壤。《嘉靖宁夏新志》录有宁夏巡抚杨守礼七言律诗《入打硙口》:打硙古塞黄尘合,匹马登临亦壮哉。云逗旌旗春草淡,风清鼓吹野烟开。山川设险何年废,文武提兵今日来。收拾边疆归一统,惭无韩范济时才。
打硙口就是现在的大武口。我来石炭井的第一天,念树就对我说:选个时间,我带你去打硙口玩,去爬爬贺兰山。那里有稀有野生动物,运气好的话,可以碰上。
他的话,一下子让我动心了。我来六天了,他还没带我去。我陪他种了三天的树,我不想去了。我就对表姨说,我要回去了,孩子催我了。念树说:还没去打硙口呢,急着回去了?等山上的雪再化两天,就可以安全上山了。我搭了便车,去灵武市水洞沟游玩。
其实,无论去哪里,我都不喜欢卖门票的地方。我爱走野地野滩。野性的大地,即使是荒漠,也给人蓬勃的力量、不可预测的神秘之美,给内心深深的获得感。我迷恋这样的感觉。自然世界是无法言说的。
早早的,念树备好了干粮(馍、卤牛肉)、水、葡萄糖,还带了碘酒、纱布、充电宝。临出门,表姨还抱出一件旧大衣,说:山上冷了,可以防寒。我们走韭菜沟。韭菜沟是大武口的一条斜深的大峡谷,从北武当庙(又称寿佛寺)入沟口,两边是棕黄的山。沟口种了矮灌,抽出了嫩绿的新叶。沟宽阔,陡斜,砾石遍地,水若有若无,在砂石下渗透。因为水的冲刷,沟边山体露出一层层的斑岩,凹坡上长起了梭梭、柽柳、柠条。淡淡的绿意,溶解了满目苍莽。往山上远眺,明长城高耸在山脊,曾熊熊燃烧的烽火湮灭、凝固,化为泥坯石垛。
走了一个多小时,看见一副完整的大型哺乳动物骨架:36个脊椎骨,12个颈骨,4个尾骨,偶蹄,两个棘突,32个牙齿,骨架长约1.1米,头骨修长。念树说,这是马鹿,成年的母马鹿。
有麻袋就好了,我把马鹿骨带回去。我说。
看山,就是什么也不带回去。马鹿生活在高山,也在高山安安静静地归化母土。念树说。我有些羞愧。
雪豹、狼、猞猁、黑熊、貂熊、鹰雕等,是马鹿的天敌。二〇一二年春,念树去额尔古纳的乌兰山拉货,住在山里。第二天早晨,他去林中闲走,看见一只貂熊从树上跳下来,扑在马鹿背上,撕咬不放。马鹿受惊,沿着山道跑,甩不下貂熊,用背猛烈撞松木。貂熊被撞得吱吱吱叫,落下了马鹿背。马鹿直跑。念树说,那是一头母马鹿,皮光毛滑,跑起来很威武、英俊。他又说,幸好马鹿没有跑向雪地,假如被积雪陷了鹿脚,就无法逃脱了。
我没有见过马鹿,也没见过貂熊。念树说,贺兰山马莲口有马鹿群,有两千多头,过几日,我带你去看马鹿。
念树会辨识马鹿粪。韭菜沟偶有动物粪便出现。他捡起一个圆丸似的粗糙粪球,说,这是雄马鹿粪。看到橄榄形的粪球,他就告诉我,这是母马鹿的。圆粪球比橄榄形粪球更大一些。
韭菜沟是他经常走的。这条沟适合徒步,沟宽,植被也比其他沟更茂盛一些,鲜有人来。在韭菜沟,他看见过马鹿、赤狐、蓝马鸡、岩羊。在十年前,这些动物是罕见的。在大磴沟,他也看到岩羊、兔子、秃鹫、蓝马鸡。大磴沟有了树有了草,它们都会陆陆续续回来的。念树说。
登上山脊,仰望天空,我忍不住高喊:苍天啊,苍天啊。天太蓝了,蓝得深邃无比,蓝得无边无际。深蓝,是天空的纯色,也是贺兰山人的心灵底色。
门外就是波浪形的山。表姨跟我说,念树、念水、念山都不怎么爱读书,也没人带他们。他们在街上瞎闯,四处爬山,看到家里烟囱冒烟了,就回家了。十三岁的念树,爬上拉煤的火车,去了新疆,又爬火车回来。表姨父看见浑身煤黑的念树,拿起扫把棍按着念树屁股打。表姨不让。表姨父还要打。表姨拿着木棍,虎着脸说:你试试看,你敢打念树,我就动手打你。表姨父傻眼了。表姨是个不发脾气的人。表姨父手足无措地看着表姨。表姨说:念树天生胆大,像我。有胆色的人,有什么不好呢?
念水的丈夫是青海尖扎人。表姨父很反对这门亲事,说: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地方,鸟都不愿飞过去,你嫁到那里去,坐车都要十天半个月。念水喜欢这个青海人,就告诉她妈,说爸反对她嫁到青海去。她妈说,你愿意就可以。表姨对表姨父说,石炭井去尖扎不算远,比上饶到石嘴山多三百公里。结了婚,念水一家就在宁夏生活了。表姨就对表姨父说:人安排生活,生活也在安排人,很多事情,不用操心。操心了,也是白操心。
三个孩子成家了,她就很想回上饶看看。她出生、成长的坳头村,已搬迁下山,无人居住,菜地也荒了。野猪成群出没。
西北春迟,日落晚。上午九点半,表姨来到小店。这是雷打不动的时间。门口摆了一张小桌、两条长板凳、六个红色塑料凳。塑料凳套在一起,客人随来随取随坐。桌凳抹得发亮。一个油毛毡布雨篷,罩在屋檐。店门正对十字街心。货由配送中心送。《绿皮小火车》《我的父亲焦裕禄》《突击》《山海情》《万里归途》等电影在这里拍摄,随着《山海情》《万里归途》热映,石炭井也被外人熟知。这几年的暑期、大假期,游人如鱼。石炭井又有了旅社、面馆、烤串店、饮料店。主要演员住在农贸市场旧址后面的老别墅,拍完了戏,就在街上散步消食。演员也不化装了,素面朝天。女演员大多精致,也有的是一副邋遢样,头发蓬乱、拖着鞋跟,衣服穿得皱巴巴。表姨很不喜欢这样的演员。表姨爱清爽、干净,就是店门顶上的雨篷,她也是半个月洗一次。瓜果皮、酒瓶、饮料瓶、瓜子壳、硬纸壳等,她每天清扫,用藤筐装起来,可回收的东西就入库,不可回收的倒在河边菜地。腐烂了的水果,她也倒入菜地。这些东西,既是肥料,也是肥泥。肥泥多珍贵,只有生活在这里的人知道。在院子里,她种了六株葡萄,那些泥,是她捂了三年多的菜头菜脚才捂出来的。洗了桌椅、器物的脏水,她也舍不得泼,提到街边浇树。
群众演员住在简易旅馆,有个睡觉、避风躲雨、喝杯热水的地方就可以。他们吃得也简单,一碗面或两个馍就打发了。他们收入非常低,甚至几天都没收入。表姨想不通,好好的年轻人,天远地远跑来石炭井,熬十天半个月,就露一两个镜头,为什么。街边的房子,建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低矮、破旧,很有年代感。美工依据建筑造型,在外观上设计了“炮楼”“红旗照相馆”“老罗自行车修理铺”“门诊大楼”“国营理发店”“火车站”“便民商店”等。表姨和路边其他六户店家,也被拍进了电影。她恍惚了好几个月,不知道自己是生活在电影里,还是仍然处在现实世界。房屋,街道,断了水的河流,风沙跑来跑去的山梁,屋檐上跳来跳去的喜鹊,晚上街角昏昏欲睡的路灯,厚厚的冬雪,过路的大货车,都被拍进了电影。眼中所见之物,成了道具。曾经繁华的小镇,镜头般一晃而过,昙花一现,甚至不真实。她怀疑自己曾经的生活。
在寒冷的冬春,没有游客来了,小镇陷入沉寂。一切恢复了常态。表姨也恢复了常态:坐在板凳上,布裙压在膝盖,望着无人的街道,等着日落。日落了,念树种树回家了。她收拾了店铺,锁上门,步行回家,烧饭烧菜,和儿子对盅,喝上一杯。家,是世界的中心,也是唯一让她感到踏实的地方。
吃了晚饭,她回到街上,街上住着二十多个老矿工,表姨一家一家去打招呼,问个安好,然后回家睡觉。这些老工友,子女都不身边生活。每天早上,表姨也早早去街上,和老工友打招呼。她知道,每年都有三两个,打不上招呼了。招呼一次,也就少一次。也会有那么一天,她上不了门,那一定是她出不了门了。
傅菲,江西广信人,资深田野调查者,《南方周末》书院散文写作训练营导师,专注于乡村和自然领域的散文写作,出版散文集《深山已晚》《元灯长歌》等30余部。曾获三毛散文奖、百花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奖、方志敏文学奖、江西省文学艺术奖,以及《北京文学》《山西文学》《芙蓉》等多家刊物年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