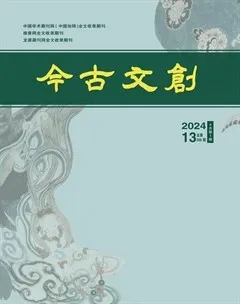黄宗羲君主论研究
【摘要】黄宗羲通过对君主起源、职能、君臣关系进行重新定位以及对人性的探讨,建构起了其独特的君主论。君主源于“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但是在人各自私利的情况下又有人出而治天下,這其中涉及人性的探讨潜在的贯通在黄宗羲君主论建构里。黄宗羲的君主论既是对君主专制的一种理想型的纠偏,亦是黄宗羲基于两朝经历的一种突破性的政治畅想,而其对于人性的形而上的思考亦能反映理学在明末清初的一个发展向度。
【关键词】黄宗羲;君主论;人性;自私自利;圣王之治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13-006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3.019
黄宗羲一生经历了明末专制集权下朝廷是非不明、阉党把持朝政的黑暗统治,目睹了明朝的灭亡,经历过抗清复明的失败,以致后来对整个封建君主专制集权产生了怀疑和否定,毅然建构起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本文意图通过黄宗羲的相关著作为依托,分析黄宗羲的君主论思想,试图呈现黄宗羲君主起源、职能、君主起源背后的人性立论依据等观点,在理论上梳理黄宗羲君主论和其人性论的一贯性关系。
一、黄宗羲对君权起源、君主职分及君臣关系的厘定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1]2。在最初的人类社会形态下,每个人都只着眼于自己的私利,无暇顾及其他。天下的公利没有人去振兴,公害也没有人去消除,长久以往,祸乱穷困就会产生。出于兴公利除公害的需要,需要“有人者出”,为天下兴利除害,君主即由此产生。
黄宗羲在《孟子师说》说:“天地之生万物,仁也。帝王之养万民,仁也。宇宙一团生气,聚于一人,故天下归之。”[1]90天以仁生万物,必不会让人被私情所蔽,流于自私自利而最终导致祸乱争夺,所以天生“聚一团生气”的人为圣为王,使之治理天下,使民皆各得其所,各得其利,万民也会归顺他,这便是君主的起源。虽然这个君主的合法性最后也是依托于天,但是黄宗羲显然更偏重其职能设立——即是君主是为了替天下兴利除害而设的。
君主的起源决定了君主的职分一定是以天下万民的公利为中心的。是以黄宗羲说“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1]8;“嗟乎!天之生斯民也,以教养托之于君”[1]11,黄宗羲认为,君主是为教养百姓、为天下兴利除害而立的,设立君主的初衷要求君主毕世而经营不怠的应当是天下之事,所以为人君应当比天下千万之人要勤劳,而又不享其利,故古之人以得天下为不可摆脱的桎梏,恨不得断臂而去之,认为人君之位“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人人能让君主之位而不会眷恋。所以“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真正明白君之职分的君主,当知道人主受命于天而明白治乱天下的艰难,必当剥去自己的人情私利而经营天下,行仁义之道以教养天下。古之君王能以教养天下为己任,故能制井田、学校、兵车、封建、丧葬、祭祀、礼乐以养民,其所为之事,所立之法,所养之兵,所制之刑,皆以民之利为出发点。后世君王则与之相反,一切所谓,为己而不为民。
黄宗羲认为,后世之君不明君之职分,导致了一系列后果:一是“以天下而养一人”(《孟子师说》卷六),将君民的关系恶化为相仇、对立的关系;二是将君臣关系恶化为主奴关系,造成君道不明,则君臣同为民之大害的局面;三是“行非法之法”,导致天下大乱;四是其“私”天下的行为让其他人以为为君就可以享受至上的权力和快乐,故人人都图之,从而频繁引发战乱。此可见,君主是否是一个合格的君主,关键在其能够明白自己的职分,并毕世去经营,究极而言则在于其为己或为民也,为民,乃君之当为也,私己是君之当去也。
鉴于后世主从君臣关系所导致的后果,黄宗羲对君臣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一是打破君主臣从的角色定位。明确君臣皆是为天下而设。《原臣》篇曰“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以群工”天下治理任务繁琐,仅君主一人是完成不了的,所以需要设大臣和君王分治天下,这是臣的来由,侧面也说明君、臣的关系是平等的。《置相》篇曰:“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1]8就目的而言,君臣同为天下而设,不存在主从关系,就如张岂之所言:“‘君臣应是共同负担人民公共‘利害事务的人员”[3]“为臣者轻视斯民于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为臣者不能解决百姓水火之难,即便能辅佐君王得到天下也是对臣道的一种背离。二是打破君父臣子的纲常。黄宗羲认为“臣不与子并称”,君臣之间并不是君父臣子的关系。《原臣》篇有言:“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1]5,父子是同气连枝的关系,子得父之精血而生,父对子有生养之恩,所以尊敬爱顺是为人子所当为。然而君与臣,一无血亲之情,二无侍奉之义,只因治理天下之责联系在一起,若非为治理天下,则君、臣无甚干系,相互为路人而已,不能担“父子”之名。臣道非为子之道,君与臣终不能以父与子称之。
二、黄宗羲君主论的理气论依据
黄宗羲的“君主论”建构,与其在形而上层面的思考紧密相关。黄宗羲认为“天地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1]60“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4]609也就是说,气是天地万物得以存在的根本,是万物之源。气动静而有阴阳,黄宗羲说:
气本一也,而有往来阖辟升降之殊,则分之为动静,有动静则不得不分之为阴阳。然此阴阳之动静也,千条万条,纷纷轇轕,而卒不克乱。万古此寒暑,万古此生长收藏也。[4]609
气阖辟升降的过程分为动静,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而阴有阴之动静,阳又有阳之动静,这千条万条的动静就是气生物的过程,气之流行运动而有寒暑交替,春则气化而生物,冬则消敛而收藏,如此,四时得以行,百物亦得以生,这是气生物的过程,而无论寒暑消长,皆是一“气”。气是变动不居的,要认识这个动的气只能通过“理”来见气。黄宗羲对“理”做出了自己的界定,黄宗羲言:“夫所谓理者,气之流行而不失其则也”[5]511“圣人以升降之不失其序者,名之为理”[6]438。气不是静止不动的,但又不是乱动,气之升降阖辟皆有其条理、秩序,故气化生万物而能不乱,黄宗羲把气的这种升降不失其序称为“理”,说“理”更偏向对气之流行而不乱的状态描述,而言气更强调天地间只是一团和气,这也可以对天地之间万物各自生长而不会混乱做出解释。黄宗羲认为“理气是一”的,关于这个“一”,可作两解,一是理气是一物两名,二者是对气的不同描述;二是理气统一于一体上,有气必有理,人由理见气,理气不离。关于第一解,黄宗羲有言:
理气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则谓之气;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则者而言,则谓之理。盖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也。[7]1061
也即是说之所以有理、氣两个称名,升降沉浮的是气,而气升降浮沉而不乱称为理,理、气所指称的是同一个东西。
关于第二种意义也即是说理是气之理,有气而有理,并非气之外另有一个理存在,理是气流行所表现出来的,所谓:“道理皆从形气而立,离形无所谓道,离气无所谓理。”[6]40理依于气而立,又附于气而行,从气的升降变化才能见理之流行,气流行而不失其条理、秩序便是理,故通常来说理不是单独存在的,只有气流行才能见理。理气二者不离,也可以说气是偏向动而理偏向静。气动而有条理,气动而生成什么是定了的,理亦是定了的,然气不动,亦不存在流行而生人生物,人也不可见理,所以理只是气的流行,没有离开气而存在的理,理气不离。气聚则理聚,气散则理散。
“气”为生万物之本,气理是一的,黄宗羲从“气理是一”推出了“心性是一”。关于气、理、心、性的关系,黄宗羲是这样描述的:
天地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是气以生,心即气之灵处,所谓知气在上也,心体流行,其流行而有条理者,即性也……若有界限于间,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见,见之于气;性不可见,见之于心,心即气也。[1]60
气是“一本”,气化生物,人物皆禀此气以遂其生,而人物又各有不同,是为万殊,而人得气之灵以为心,《孟子师说》有言:“知者,气之灵者也。”故人心有知,感于物而动,当恻隐自然恻隐,当羞恶则自然羞恶,这个心体流行出来而不失其序便是性,心为体,性为用,如果心体不流行,我们无以见性,性是心之性,心与性之关系一如气与理的关系。气、理、心、性并非四个不同的东西,同是一气,“心即气之聚于人者,而性即理之聚于人者”(《明儒学案·师说》),所以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气、理是一,心、性是一。
心是动的,性相对来说是静的,在人这里“其变者喜怒哀乐也,已发未发,一动一静,循环无端者,心也;其不变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梏之反复萌蘖发见者,性也”[8]22。心是变动的,心自然而然动出的东西是确定的,这个东西就是性。黄宗羲曰“性者生而有之之理,无处无之。如心能思,心之性也;耳能听,耳之性也;目能视,目之性也”[1]78。性无处不在,无物不有。如理不会失其序一样,性亦是历然不能昧的,黄宗羲说:“人受天之气以生,只有一心而已。而一动一静,喜怒哀乐,循环无已,当恻隐处自恻隐,千头万绪,轇轕纷纭,历然不能昧者,是即所谓性也。”[9]408-409人心中所有,亦只是一性,有条理而不能昧此性之发见。
三、黄宗羲君主论的人性论依据
人同禀气之精者,得气之灵而为心,则人心中所有之性,莫不是一团和气而无有一恶,黄宗羲是由理善来推性善的,黄宗羲有言“理无不善,气则交感错综,参差不齐,而清浊偏正生焉。性无不善,心则动静感应,不一而端,而真妄杂焉”[8]23。理本身就是条理粲然无有不善的,而理之具于人而为性,亦无不善,正如黄宗羲所言“满腔子是恻隐之心,此意周流而无间断,即未发之喜怒哀乐是也”,是故人性本来是善也。恶是心动出来才有这个区分的。关于恶的来源,黄宗羲是这样解释的:
夫不皆善者,是气之杂糅,而非气之本然。其本然者,可指之为性,其杂糅者不可以言性也。[8]755
黄宗羲强调,气动而自然流露出来的才是性,而气之杂糅则不能算性,气动而有条理,理是善的,人得理而为性,故而性是善的。性之善就像寒必冬,暑必夏一样自然;恶之生就像偶尔冬而暑,夏而寒一样,虽偶有反常,然而万古冬寒夏暑终是恒常不变的,是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才是常道。虽气之本然是善的,然气在流行过程中,不能无过不及,此无过不及所形成的杂糅偏胜之气,才是有可能致恶的原因。而大多数的常人由于此杂糅偏胜之气所成的形质而呈现出善恶交杂的状态,然其中体未尝不在,也即是人性未昧也,所以即使气质有偏,人只要能看到并抓住那个中体,亦能去恶而全其善,人心所有,无非善之性已,恶则是因为有“过不及”。
虽常人有善恶交杂的状态,然而天生人不是只生常人,圣人得其“中气”而生,故没有过、不及之差;常人则是“杂糅偏胜”之气所化,故而有善恶夹杂之弊。故需要圣而王者,养民教民,所谓“天地生万物,仁也。帝王之养万民也,仁也。宇宙一团生气,聚于一人,故天下归之,此是常理”[1]90,也就是说天以“仁”生万物,必不忍万物堕于“杂糅偏胜之气”而不可自拔,故诞出集“中气”而生的圣王来治天下之乱,得天地那一团生气者,当圣而王之,天下万民自然尽归于其下,教养万民是君王之责。在理想的状态下,天生圣王而治天下,君王的合法性是天来保证的,但是黄宗羲限定了前提,必须是得天地中气而能治天下者,才是当君王,得天地之“中气”圣而王者去治理天下,这便是黄宗羲理想的圣王之治。
总之,黄宗羲的君主论是基于肯认人性善的潜在前提下建构起来的。黄宗羲的君主论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其实是基于对三代以后君主专制高度集中、高度发展导致的系列问题、弊端的一种试图性的纠正,不管是他对君主起源、职分、君臣关系、天下之法等等的重新界定,还是他对后世君主振聋发聩的批判,他都并没有突破君主制度的樊笼,而是基于肯认君主制的前提下对封建君主专制的一种改良和纠偏,意图把导致后世君主私天下的“私”欲去掉。黄宗羲君主的立论起源是因为人有“私”的部分,人人“私”則没人去兴公利,除公害。他所阐述的有生之初的“自私自利”更偏向一种原初社会状态的描述,“是人类产生初期的社会状况的一种概括”[2]163也即是一种“中性”的描述,在原始的社会形态下,人人自私自利,但是这个自私自利是出于一种生存本能的需要,并未造成什么祸害公共利益的后果(这个黄宗羲也并未提及),只不过是这种自私自利的状态下,天下公利无人兴,天下公害无人除,但是并不意味着这种自私自利就是非正当的、不合理的,反而是应该得到保障的。而事实上,在黄宗羲君主论的阐述中,他也寄希望于圣王,渴望或者畅想圣王之治,但是他也不把全部的希望放在不知何时才会出现的“圣王”身上,而是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治法对在君王之位但是没有“圣王”之德的人君进行制约和框束,期望能最大限度内保证君主是为天下万民兴利除害而服务,这也是黄宗羲对中国传统贤能政治的一种突破。
参考文献
[1]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一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2]张岂之.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J].人文杂志,1980,(02).
[3]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三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4]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二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2008.
[5]黄宗羲.黄梨洲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
[6]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四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8.
[7]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七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8]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八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9]张师伟.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陈文艺,女,贵州毕节人,宝鸡文理学院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明理学与清代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