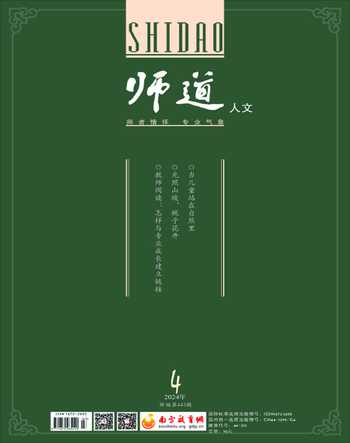当儿童站在自然里
吴鸽

20世纪初,杜威在《儿童与课程》中指出:“作为教师,他考虑的是怎样使教材变成经验的一部分,他自己的教材知识怎样可以帮助解释儿童的需要和行动,并确定儿童应处的环境,以便使他的成长获得适当的指导。”[1]杜威强调了教师的课程主体意识,认为教师不能是教材的附庸。
很庆幸,2002年我进入通师二附小工作。二附小是“情境教育的发源地”,情境教育创始人李吉林老师在这里躬身耕耘60多载。一直以来,学校将李老师开发的“学科情境课程、主题性大单元情境课程、野外情境课程、幼小衔接过渡课程”四大课程作为重要的情境校本课程体系,聚焦“蕴含丰富情感、蕴藏着潜能的、活生生的儿童”,为“学习者中心”赋予了独特的内涵,创造了有效的实践路径。
多年来,在情境校本课程体系中孜孜汲取营养的我,跟随李吉林老师和学校的前辈们,从起初认识情境课程到成为一名合格的课程实施者,看到在课程牵引下教师专业成长的速度,看到儿童因情境课程而洋溢的勃勃生机。逐渐地,我从“课程实践”迈向了“课程自觉”。
校本课程下的班级面孔
李老师在指导老师们做教科研时经常说:“实践有一个过程。光靠摸索做不深也做不长,只有把学习理论和探索的实践结合起来,才会产生新的认识。产生新的认识以后再去进行新的实践,如此反复才能进入一种新的境界。”那么如何把这些年学习的情境课程理论和符合班情的教育实践相结合,从而拥有情境课程下的班级面孔呢?
首先,这种课程的探索应是自下而上生长起来的,核心是学生,立足于班级学生的发展需要,着眼于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其次,必须注重情境课程在班级层面的个性化传承、拓展和延伸;最后,借鉴其他课程理念,如斯滕豪斯的“教师成为研究者”、施瓦布的“教师作为课程实践者”等,相互印证。
在深入学习后,我发现情境校本课程体系中的野外情境课程是一大亮点。裴新宁教授在《为了儿童学习的课程》一文中这样评价:“野外学习是独具特色的非正式学习”,“野外学习这种方式调用了儿童学习的感知维度,体现了对儿童首先是生命(生物)主体的尊重,对生命力给养源泉的恰切理解。”[2]诚然,儿童是自然之子,儿童需要自然。野外学习,是到自然中去学习,符合孩童的天性、智力和生长规律。儿童去看自然中的青山绿水,听鸟声蝉鸣,在自然的引领下和日月星辰对话,和江河湖海晤谈,和每一棵树握手,和每一株草耳鬓厮磨,才会顿悟宇宙之大、生命之微、时间之贵。
此时正值新教材、新课标全面推行,语文教学面临着新的改革。部编版教材采用双线组织单元结构,努力建构适合中小学的核心素养体系。新课标明确提出:“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培养的核心素养,是学生在积极的语文实践活动中积累、建构并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表现出来的,是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的综合体现。”而大自然就是丰富辽远的“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是野外学习的非正式学习方式,是课堂之外儿童最佳的学科实践活动场域。
于是,我构想:以大自然为课程本源,以语文学科为主体链接各学科,在班级层面实施“大自然+”情境微课程,将儿童带入充满诗意和生命活力的真实生活、真实情境中去,指向儿童综合素养的培养。
从儿童立场出发
学习二年级下册的一组童话,从《枫树上的喜鹊》《沙滩上的童话》到《我是一只小虫子》,孩子们的想象被文本中有趣的情节和灵动的语言完全激发出来了。学习完《我是一只小虫子》这一课,孩子们下课围着我叽叽呱呱地说:“我喜欢当一只小虫子,我要做会唱歌的蝉!”“我要做穿绿裙子的纺织娘!”“我要做一条会吐丝的蚕,我喜欢吃桑叶!”……听着这些充满童心童趣的话,我问道:“你们只知道虫子的名字,大致知道它的样子,但是你们有过认真观察一只小虫的经历吗?”“认真观察是怎么观察?”一个小男孩抓抓脑袋问:“是像法布尔那样观察吗?”“是啊,就像那样,仔细地观察,做个小小研究家才棒呢!”我知道,班级里有不少孩子读过彩绘版的《昆虫记》。看着孩子们被勾起了探究的兴致,我想,何不顺着学生的兴趣,开发一个关于“虫子”主题的“大自然+”情境微课程呢?
“教学事件”是课程诞生的起点。从理论上讲,一个完整的课程建构包括内涵、特征、核心元素、建构路径等部分,如果教师的课程开发必须把这一切都想清楚,可能刚刚升腾起的想法瞬间就会被浇灭。概念重建主义课程观的代表人物派纳曾提出:课程不仅仅是一个名词,还是一个动词,课程不再是预先制定的外在于师生的学校材料,而是师生在共同的教学实践中生成的教学事件。万伟老师在《课程的力量》一书中也这样表达:“课程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我经常引用著名学者吴宓的一句话:‘把我自己——我的所见所闻,我的所思所感,我的直接和間接人生经验中的最好的东西给予学生。这就是一位教师的课程意识最经典的体现。我们可以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优势特长、爱好兴趣,给学生提供课本外的、更丰富的学习经验。”
儿童体验“事件”的行为过程就是实施课程、产生课程价值的过程。当“课程建构”从高深、抽象的理论话语中跳脱出来,当我从儿童立场出发,有意识地抓住“教学事件”——它“不仅是教育活动内容的主要载体,更是教育价值的重要载体”[3],“‘你好,小虫语文情境微课程”应运而生(见上表)。
我们以课程目标为引领,以任务活动为推进,使得大自然成为生动的课堂。学生在其中观察,跨学科阅读,组建小组开展昆虫研究,组织昆虫发布会、小虫创编表演等,在语文学习基础上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的、社会性的运用。“你好,小虫”语文情境微课程将知识、活动、审美融为一体,以有序的实践活动改变了学习方式,使一只小虫的符号知识和儿童的生活感性、思维探究相融合,让与情感伴随的学习愈加立体、丰富。
教师的研究力决定课程的内蕴
“大自然+”情境微课程让儿童在自然中打开,“打开”的方式考验着教育者体察儿童的敏感力,还要求教育者拥有“具体化”的实践智慧。教师的研究力离不开阅读,关键是如何向“阅读”借力,用江苏省特级教师曹勇军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将阅读转化为教学资源、教学思路和教学眼光”。同理,教师也可“将阅读转化为课程资源、课程思路和课程眼光”。
做“大自然+”南瓜主题情境微课程时,我们以语文学科为核心联动各学科,设计了11个学习活动。在“寻找通城南瓜王”活动中,学生走进乡野田间、农贸菜场,找寻最大的南瓜。回到学校,我没有第一时间组织学生评比最大的南瓜,而是让他们先聊聊各自的寻找历程,说说眼前这一个个南瓜被带到教室的过程。学生有按寻找地点交流的,有围绕寻找时的趣事交流的。两个孩子的交流很有意思,一个说他在南瓜地里寻找时,想到我给他们读过的文章《最大的麦穗》,文中场景好像在生活中复现了,他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做那个空手而归的人,挑到自己认为最大的那一个就是胜利;另一个孩子说,寻找南瓜让他累坏了,他和家人去了很多地方,总认为眼前的南瓜不够大,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第一次去的地方,结果那个大南瓜被切开,分批卖出去了。交流结束,孩子们用笔写下了寻找南瓜的过程,并附上一两句自己的思考。
在交流的基础上再去评选“南瓜王”,学生对“最大的这一个”有了动态的感性认识,它不再是作为一个符号被定义,而是“在学生的话语表述与行为中,具体地展现活动中的学生的个性的观点、风韵、成长与潜能”(钟启泉語)。这个看似常态的学习实践,其实不是随意设计或填数般地出现在课程中的,它暗含课程的意义——“意义”以课程实践来传达,而这一点,正是我在阅读钟启泉教授的专著《课堂转型》之后获得的启迪。一本本专业书籍的阅读,使得我在微课程设计时摒弃仅凭“经验”的习惯做法,而尝试在专业理论的指导下,让课程设计逐步走向专业化。在阅读和实践中我愈加深入地理解了“课程研究”对教师的作用——它是老师研究力的深耕与外化,是在儿童立场上对教育的理解和选择。
走向哪里——
过去一年,“大自然+”情境微课程在班级层面上共实施了8个主题。在实践中我不断思考:它要走向哪里?它将引领着我和儿童走向哪里?教育的目的应当向人传递生命的气息,这是我对教育本质的理解。而“大自然+”情境微课程就是要引领学生和大自然建立亲密关系,让儿童走出封闭的课堂,走进蕴含真、美、思的广远情境,以具身学习的方式激活儿童创造性的潜能,让儿童在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和生活中,尽情伸展生命的灵性,成长为精神明亮的人。
如是,向前。
参考文献
[1][美]杜威.杜威教育论著选[M].赵祥麟、王承绪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57.
[2]裴新宁.为了儿童学习的课程——中国情境教育学派李吉林情境课程的建构[J].教育研究,2011,(11):94.
[3]刘剑玲,文雪.关注教育事件:教育研究的复杂性思考[J].上海教育科研,2005,(1):8-11.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责任编辑 黄佳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