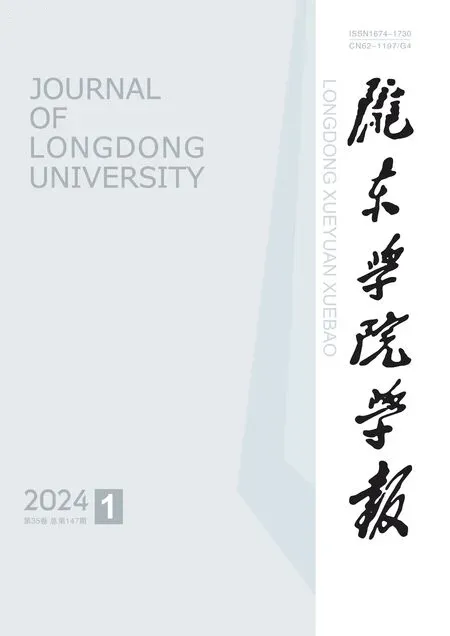陈端生与浙江精神
徐 晓 芳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浙江历史源远流长,山川秀美,人才辈出,孕育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精神品格。浙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务实”“开放”“创新”“自立”“诚信”等特质已经为大家所熟知。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更是对浙江精神进行了准确概括和阐释:2000年,提炼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16字的浙江精神;2005年,又将浙江精神提炼为12个字:“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尤其是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G20”杭州峰会期间,把浙江精神概括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这种精神品格洋溢在浙江美丽的山水间、灿烂的文明里,积淀在浙江人民深层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中,薪火相传,历久弥新[1]。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或著书立说,或亲身实践,对浙江精神作出了自己的解读。无论是王充倡导的“疾虚妄而归实诚”、南宋事功学派的“义利双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还是龚自珍的“不拘一格降人才”,都以男性话语为主导,女性的声音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以至于说起浙江精神,鲜有女性的身影。事实上,女性在浙江历史上虽然出镜机会不多,但是有限的几次出现在公众视线中所显现的地域精神和动人风采,足以照亮男权社会里一直被人忽视的角落。东晋谢道韫的丈夫王凝之面对战乱独自一人逃逸被杀,她却提刀站立家门口迎敌,反而赢得孙恩的敬重并赦免其族人;唐朝陈硕真在浙江发动农民起义,成为中国历史上女性自称皇帝的第一人;元代管道升写下“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吟风弄月归去休”这首《渔父词》,劝丈夫赵孟頫不要贪恋功名,充分体现了浙江人低调务实的精神;南宋朱淑真“娇痴不怕人猜”的爱情自主意识和“女子弄文诚无罪”的男女平等意识让人眼前一亮,仿若现代女性穿越到了理学兴盛的南宋;明清浙江才女文化群体所凸显的女性意识和权欲渴望彰显了江南女子的才华和自立;鉴湖女侠秋瑾“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的英雄气概更是如同闪亮的彗星绽放在星空中,用生命实践了吴越之君“轻死易发”的传统……在众多女性中,作为清代浙江才女文化群体中的佼佼者陈端生,以其对女性敏锐地观察和特立独行的姿态,挥毫写下的弹词小说《再生缘》犹如一颗闪亮的珍珠镶嵌在浙江的小桥流水中,发出耀眼的光芒。由小说改编的戏曲《孟丽君》早就在民间活跃多年,越剧、黄梅戏、锡剧、淮剧、祁剧、闽剧、京剧、扬剧、粤剧、歌仔戏、琼剧等多种剧种都演绎了这段女扮男装的传奇故事。
《再生缘》讲述的是元代兵部尚书孟士元之女孟丽君许配云南总督皇甫敬之子皇甫少华,因遭刘奎璧逼婚,女扮男装离家出走,高中状元并成为当朝宰相。父兄翁婿同殿为臣,而此时的孟丽君却希望像男性那样挣脱家庭桎梏成就一番事业,拒绝相认。终因酒醉暴露身份,皇帝要她三日内入宫为妃,否则以扰乱朝纲之罪论处。孟丽君既不愿意嫁与皇甫少华为妻,也不愿入宫承宠,进退两难,忧闷郁结于心,口吐鲜血不省人事。至此第十七回,陈端生掇笔,《再生缘》成为未竟之作。杭州女诗人梁德绳所作续本三回给了小说“大团圆”结局,最后孟丽君被封为保和公主,嫁给皇甫少华。这部沉寂数百年的作品引起了陈寅恪的共鸣,他在《论〈再生缘〉》一文中说:“玩味再生缘文词之优美,然后恍然知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而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2]陈端生在作品中抒发的悲愤和不平不仅仅是对女性或个人人生境遇的感慨和伤怀,而是“对整个传统思想乃至社会政治的怀疑,这种反叛意识贯穿整个作品”[3]。而这种怀疑精神、反叛精神正是和浙江精神一脉相承的。
一、出走故事的编织:勇立潮头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这是北宋大诗人苏东坡咏赞钱塘秋潮的千古名句。千百年来,钱塘江以其奇特卓绝的江潮,倾倒了众多游人看客。自古以来,浙江人不仅仅喜欢观潮,而且还将在潮水中奋力搏击演变成一项刺激的运动,成为钱塘秋潮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南宋周密在《观潮》中曾经写道: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每年八月中旬的钱塘江弄潮活动在南宋时非常盛行。“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宋代潘阆《酒泉子》),奔腾不息的钱塘江吸引了勇敢的浙江人面对汹涌澎湃的潮水毅然踏浪而行,不为富贵不为名利,只为实现自我价值。“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唐代李益《江南曲》),唐宋以来女性对于勇敢的弄潮儿的推崇和敬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浙江人不惧艰难险阻的冒险精神。浙江的“水文化”特征不仅“激发和培养了浙江人的智巧”,而且还濡养了浙江人敢于创新、锐意进取、不墨守成规的文化品格[4]。浙江素有“鱼米之乡”之称,但是由于北方连年战乱,经过永嘉南渡、安史之乱、靖康之难,中原汉民的大量南迁导致人口不断增加。“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理环境使得浙江的人地矛盾日益尖锐,“穷则思变、自强不息”的生存理念贯穿于浙江人的日常生产活动中。明清的浙江读书人不留恋故土不贪念天伦,放下考取功名的执念只身到全国各地官府入幕,形成了“无绍不成衙”的独特现象,“绍兴师爷”也成了历史上浙东地区典型的地域文化人群。
陈端生十七岁时开始写《再生缘》,故事的架构选取了当时最为流行的桥段——女扮男装。“衣服不只是社会和性别秩序的标志,它还创造并维护了社会秩序和性别秩序。”[5]中国古代的男女服饰制度要求男女各守本分不得僭越。在现实生活中女扮男装会遭到谴责,然而在文学作品中却因为其情节新奇灵动而深受大家的喜爱。女扮男装的故事出现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可以追溯到南北朝的《木兰辞》。唐传奇中也有一些女扮男装故事,如《虬髯客传》《谢小娥》等。女扮男装题材真正密集地出现是在明清时期,不仅男性文人书写了许多作品诸如《玉娇梨》《三美图》《雌木兰》《女状元》《女驸马》等,而且女性弹词作家承担了最为齐全的女扮男装故事的编织任务如《玉钏缘》《再生缘》《昼锦堂记》《榴花梦》《笔生花》《金鱼缘》《子虚记》等。在诸多女扮男装的女性形象中,《再生缘》中的孟丽君形象可谓个中翘楚,影响深远。孟丽君因为不堪忍受刘奎璧的逼婚,不顾前途迷茫、命运叵测,女扮男装离家出走,从一个锦衣玉食的千金闺阁变成艰苦谋生的平民百姓,经过种种磨难,终于高中状元,位列宰相。孟丽君的大胆叛逆和智勇双全完全颠覆了男权社会中女性谦卑柔弱、贤惠顺从、温柔痴情的形象。而这正是女性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从最初的对儒家忠孝思想的践行,到其作为主体的意识的不断觉醒,再到争取与男性同样的权利,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女性从“附属品”到“单独个体”的精神演变[6]。而陈端生之所以能刻画出一个栩栩如生的独立、刚烈、坚强的孟丽君形象,与浙江地域文化所蕴含的浙江精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陈端生所处的时代和地域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江南社会。家住杭州勾山樵舍的陈端生,其祖父陈兆仑系雍正进士,其父亲陈玉敦是乾隆举人、曾任山东登州府同知、云南临安府同知,从小家境优渥,其母汪氏和其妹陈长生均为饱读诗书的才女。明清时期浙江经济发达,杭州凭借着繁忙的运河和多年的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大都市。另外浙江又出现了丝绸、茶叶等贸易为主的工商业市镇,如濮院和南浔是专门的蚕桑市镇,菱湖和乌镇是以丝织产业而闻名的小镇[7]。根据史料记载,明朝以后,浙江市镇数量迅速增加,杭州、湖州、温州等地均辖有几十个市镇,小者千户,大者万家以上,成为商业、手工业集聚地[8]。经济的发展导致思想文化的变迁,明中叶王阳明“心学”的出现使得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有所改变。李贽、唐甄、冯梦龙、李汝珍等都从不同方面对当时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提出异议,袁枚和陈文述更是不顾世俗的反对招收闺阁女弟子并帮助其结社吟对、出版诗集,大大提高了社会对于才女的认同感。许多人认为女性较高的文化修养能够提高子女的教育水平乃至整个家族的兴旺发达程度,有些人甚至把女子的才华当成婚嫁的筹码。正是由于社会对于才女的推崇,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对于自我身份、地位以及命运的审视使得闺阁女性希望能像男性一样走出家庭,通过自己的努力建功立业、成就辉煌。孟丽君形象一经问世便广受欢迎,尤其是闺阁女性,不是续写就是自己再塑造能为女子代言的女扮男装离家出走女性形象,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反抗。因此,以抒写女扮男装出走的女性形象为主的清代女性弹词小说作者大多来自江南。勇立潮头、不畏艰险的精神给浙江人带来了机遇,改革开放以后草根浙商走出家门、不恋家园、四海为家的从商之路和陈端生小说中塑造的女扮男装离家出走谋求功名的女性形象具有传承性。
二、女性权欲的追求:义利双行
“浙江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大胆突破了几千年被统治者奉为基本国策的重农抑商政策,形成了‘讲究功利,注重工商’的传统。”[9]中原文化安土重迁,提倡仁义道德、忠孝两全,浙江文化重视“事功”学说。南宋浙东学派中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和当时的主流学说——程朱理学不同,主张义利双行。叶适从事功观点出发,对“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提出质疑。他认为追求物欲是人之本性,同样是伦理道德前提,但是这种本能要与道德结合起来,而且受道德约束。道义与功利是一体两面不可分,伦理道德也是以物质条件作为基础,义应该同利结合起来,而不是相互对立[10]。在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看来,“义”和“利”抑或“天理”和“人欲”,在人类社会活动中向来就是并存的、统一的。明中叶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肯定主体精神和人的自我意识。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更是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理论。商业活动的频繁带给人们思想巨大的冲击,富庶繁荣的江南孕育了先进前卫的理念。民间对于经商的态度迥异于中原文化,“经世致用”的思想为人们经商、发展商品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尤其是明清时期,浙江地区形成了诸多商帮如杭州帮、宁波帮、绍兴帮、龙游帮、南浔帮等。杭州有“杭民半商贾”之说,湖州南浔由于蚕丝业的发达使得经商者超过大半,龙游商帮更是在明清被列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宁波由于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使得唐宋时期就成了浙江连接日本、朝鲜的中转站。人们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在浙江变得合情合理,这势必影响到文学创作中。
陈端生写《再生缘》的动机是为了娱乐消闲,打发冗长的闺阁时光,不但在自己家里与母亲和妹妹唱和,而且还与当地潜在的女性阅读群体交流互动。《再生缘》还没有写完就已经流传开来,“惟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遍相传”,可见当时这部弹词小说有多火爆。大多数闺阁女性认为自己在结婚前的时光是幸福快乐的,有许多闲暇的时间进行文学创作,但是嫁人后就身不由己,就算夫妻和睦家庭美满,也需要操持家务、侍奉公婆,难得有空闲时间。正如陈端生多年后在大家的要求下续写十七回的时候说:“尽尝世上辛酸味,追忆闺中幼稚年。姊妹连床听夜雨,椿萱分韵课诗篇。”正因为结婚后的日子不但琐事缠身,而且有些甚至要为生计发愁,所以当时的闺阁女性最渴求的就是像男子那样洒脱地走出家门,施展自己的满腹才华,美名传扬千秋万代。因此,陈端生给了孟丽君在古代读书人心目中最为成功的头衔——金榜题名、位列三台!最让闺阁女性心动的还不止这些,背后的经济独立才是梦寐以求的。孟丽君当上宰相后,面对皇甫少华早已没有了当时离家出走时愿意为未婚夫守节的忠贞,而是沾沾自喜于自己的独立自主,正如她自己所说“宰臣官俸嵬嵬在,自身可养自身来”,所以,再也不愿回归家庭和婚姻了。同时期男性文人也创作了大量的女扮男装题材的小说,如《玉娇梨》中的卢梦梨因为对苏友白一见倾心便女扮男装托妹自嫁,《宛如约》中的赵如子为寻佳婿女扮男装……他们塑造的女性形象虽然也是才华横溢姿容绝艳,但是大都以寻找如意郎君为最终归宿。和大多数弹词小说不一样,《再生缘》在弹词小说中,女扮男装不仅仅是女性要求男女平等的诉求,更是女性饱满的权欲意识在作品中的喷发,“义”和“利”从来都统一存在于人的梦想之中。
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孟丽君这样的人物,但是艺术来源于生活,明清社会之所以出现这么多女扮男装离家出走的女性形象,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不少女性开始通过生产劳动挣得了经济收入获得了经济自立。浙江纺织业发达,一个辛勤纺纱的农妇除了可以养活自己,还能养活子孙,成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塑造了姚芷馨和薛蘅香两个女性人物,她们一个善于养蚕一个擅长纺织,都能补贴家用。在现实中,松江的妇女几乎个个都会纺织,依靠女性手工业支撑了明清经济的半壁江山[11]。此外,社会上还存在女性文人群体,那就是专门给富家千金小姐做教师的“闺塾师”,被人称作“流动的女性教师阶层”[12]。出身书香门第的浙江嘉兴才女黄媛介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导致流离失所、家境窘迫,然而她并不躲在闺阁自怨自艾,而是勇敢抛头露面,辗转江南各地或鬻书画或师闺塾,不但得以养家糊口而且受到了当时男性文人的尊重。清嘉庆年间的杭州才女沈善宝被生活所迫,也做过闺塾师,也通过售书卖画来维持生计,她在《登舟叹》一诗中写道:“少小耽吟咏,东抹与西涂。既而学丹青,聊复自写娱。岂知陶情举,翻作谋生图。”甚至,清代中后期女性弹词小说作者通过编辑出版书籍营利,如南京的香叶阁主人侯芝曾经对《玉钏缘》和《再生缘》进行修订,然后交给书商出版。在重视封建礼教的明清时期,浙江的社会氛围对于女性从事生产劳动、经商等活动还是比较认同和理解的。正是在这种“农商并重”“义利同行”的文化思想熏陶下,义乌人在物资匮缺的年代用鸡毛换糖的方式,将拨浪鼓摇响全国的每个角落并最终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义乌小商品市场。陈端生作品中所体现出来女性对于经济独立的憧憬和浙商对于财富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
三、不甘世俗地反抗:敢于挑战
自古以来,浙江人民择水而栖、择江而居。从八千年前的跨湖桥文化开始,其后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以及良渚文化,浙江人一直在和水打交道,浙江的治水文化也在不断演进和发展。浙江先民在水患面前积极应对、努力拼搏,养成了冷静、机敏又颇具冒险精神的性格。大禹治水历经13年,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三过家门而不入”,率领民众,从鲧治水的失败经验中汲取教训,变“堵”为“疏”,与自然灾害中的洪水斗争,最终取得胜利。大禹这种一心为公、顽强拼搏、科学创新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的故事无疑最能体现浙江人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从性格特征来看,越人勇敢善战。《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13]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练成“三千越甲可吞吴”,灭吴称霸,完成了复仇计划。勾践也成为流传千古的刻苦自励、发愤图强的楷模形象。浙江人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精神有目共睹,无论是宋室南渡后岳家军“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豪情壮志,还是明清易代之际江南人如火如荼的抗争,都让人印象深刻。“江南是中国自由精神的传统所在,是对暴政和压迫最有反抗精神的地方,是中国最有骨气的地方之一。”[14]在江南文人潇洒自如、精致典雅的表面下,往往掩盖着桀骜不驯、向往轰轰烈烈的个性。明朝的于谦作风廉洁、为人耿直,坚决不给执掌大权的宦官王振送礼,并声称只有“两袖清风”;明朝学者方孝孺反对并拒绝与朱棣合作,不屈而亡,被诛十族;张苍水坚持抗清斗争20余年,在杭州被处斩决,临刑前赋《绝命诗》……
陈端生在《再生缘》中塑造了三个女扮男装的女性,分别是孟丽君、卫勇娥、皇甫长华。这三位女性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均为出生于官宦之家,被仇人所迫女扮男装离家出走,而且都才华卓绝并且开创了一番成就,但是为什么只有孟丽君形象让人记忆犹新、流传广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卫勇娥以及皇甫长华思想的发展以及个人的成长和孟丽君截然不同。卫勇娥智勇双全,做了山寨王,有了自己的王国,并且还有了“部前将士心俱服,都说道,定要真龙夺假龙”的宏伟目标。皇甫长华巾帼不让须眉,才能远在她弟弟皇甫少华之上,做了女将军。两位女扮男装的将军一起征战朝鲜,但却因为婚姻立刻归于平淡,再无事业上的建树。卫勇娥不得已嫁给了将军熊浩;皇甫长华虽然当上了皇后,但是爱情生活并不圆满。孟丽君虽然在刚刚离家出走的时候只想着逃婚,最终的目标是和皇甫少华夫妻相认以及与父母团圆。然而,当她做了宰相以后,内心却开始挣扎。尤其是自己能得到皇帝的重用,大展宏图,事业上的成就感和心理上的满足感让她不想再回归家庭和婚姻,不愿再雌伏,女性意识已经被完全唤醒。孟丽君的思想和行为已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因此当她被人揭穿为女子身份,被皇帝、父母、未婚夫所逼迫时,她口吐鲜血。陈端生写到第十七回的时候,戛然搁笔,《再生缘》成了一部未完成的小说。虽然梁德绳续写了大团圆结局,但是已经违反了作者的初衷。陈端生无法为孟丽君安排一个圆满的结果,在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女性对于自己的命运无力掌控。然而,这正是这部小说的意义所在——勇于反抗和敢于挑战的精神贯穿始终!
陈端生自己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闺中时光幸福安逸,嫁给浙江秀水的范菼,夫妻幸福和睦,但是好景不长,范菼因为科考案被流放发配到新疆伊犁,在陈端生病死后才归家。在丈夫被发配的十多年间,陈端生忍受了种种磨难,但还是“强抚双儿志更坚”,可见作者和她所塑造的孟丽君形象一样意志坚强、不甘屈服。同为杭州人的孙德英在弹词小说《金鱼缘》中塑造了一个类似孟丽君的人物冯淑容,也是女扮男装成就了一番事业,但是却选择终身不复装,而作者本人也以事亲为由不嫁,再现了当时女性对于婚姻的逃避心理,并且表现出初步的反抗意识。在明清朝代更迭之时,江南文人所表现出来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令人难忘。黄宗羲虽然跟明王朝有杀父之仇,但在清军铁蹄践踏中原之际毅然举旗抗清,历经十年艰辛矢志不渝。晚年著书立说,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这样振聋发聩的思想观点。他主张君臣应该平等,正如他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说:“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15]“一部民国史,半部在浙江”,浙江的革命党人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王金发、陈其美、朱执信和章太炎、蔡元培等,以及作为三大革命团体之一的光复会,都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浙江辛亥革命在全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具有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16]。“敢于挑战”的浙江精神不仅表现在战斗中,更多的是表现在日常的生产活动中。浙江人多地少,自然资源贫乏,但是浙江人敢干、敢闯、敢于挑战。作为早期浙商典型代表的温州商人,在浙江乃至中国改革史册上,向我们展示了众多的“第一”和“首创”:全国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全国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第一个探索“挂户经营”……[17]无论是陈端生笔下的孟丽君的反抗叛逆还是她本人的生活经历都与“敢于挑战”的浙江精神一脉相通的。
四、结语
2005年7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上的报告上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18]文学作品虽然是作家想象的产物,但也是现实生活的映照。对于古代文学作品进行深入阐释可以帮助我们更好观照当下,对于古代女性的抱负和理想进行细致解读则可以让我们更加全面体会地域文化和精神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