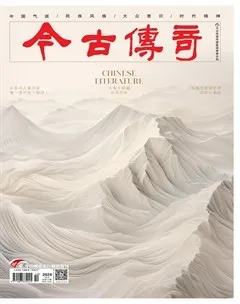将疼痛化为诗歌的心跳
诗人进入诗歌的方式多种多样,没有统一的模式,有以听觉进入的,有以视觉进入的,有以嗅觉进入的,有以味觉进入的,有以触觉进入的……以何种感官方式进入应该是因人而异的,即使是同一位诗人,他进入诗歌的方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何况还有第六感官(直觉或伏觉之类)。但不少诗人和读者认为,诗歌要写出诗人内心的疼痛,给人疼痛感,甚至有人直言,没有疼痛感的诗歌不是好诗歌。能将诗歌写出疼痛感,已经成为不少诗人的追求。疼痛感,源自拉丁语中的“伤害”,是引发疼痛的刺激从受创部位或者病灶部位发出并传导至中枢神经、使人产生疼痛感知的过程,这是一种生理上的触觉反应。而诗歌的疼痛感主要还是心理或者精神上的反应,它源于诗人对生活的深切体验与感知,诗人将它写入诗中并艺术地呈现出来,然后传导给读者。著名诗人蒋楠在《“诗歌之乡”与“疼痛之上”》中说:“我坚持认为,有什么样的‘痛感,就有什么样的思想和语言,在诗写者的笔端流淌。”读了诗人章洪波发表在本期的诗歌,我产生了一种明显的疼痛感:一是其每一首诗歌几乎都用到“疼痛”(或相近)一词,二是其诗歌的意蕴都与疼痛有关。他的诗歌疼痛点究竟在哪里?他是如何表现这种疼痛感的?下面以诗歌文本为例,来具体分析一下。
《像一道闪电》的疼痛点在于人生的无常与生活的不易。诗歌以其独特的语言和深邃的意象,向我们展示一个人在疾行于山间时的复杂心情。诗人用闪电般的比喻,表达内心的幸福、疼痛、光芒和爱。“把自己走成了/一朵乌云”,形象地描绘了人在行走中的孤独和沉重。乌云象征着内心的忧虑和困扰,而行走则象征着人生的旅程。诗人通过这种比喻,表达了人在行走中内心的复杂情感。“偶尔,穿出一两只小动物/与他对视,又匆匆走开”,表面上是写动物,实际是写人,写生活,写人与自然的微妙关系。对视是短暂的,留下来的是相互关注,同时人性、诗性的一些美好也体现出来了。“多像一些亲人忙于/生计,只用眼神道别/牵挂,祝福……”则表达了诗人对亲人的思念和牵挂,以及对人生无奈的感慨。“疾行于山间。他知道还会遇到/很多熟悉的事物”,这一句承上启下,向读者表明他在生活中不断地遇见并不断地感悟。最后,“但他必须像一道闪电……交出……”是全诗的高潮,诗人用祈使的语气和形象的比喻来表达内心的幸福、疼痛、光芒和爱。闪电象征着瞬间的美丽和力量,也象征着对未来的期待和希望。诗人通过这一比喻,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生命的热爱。诗中人物在“大雨将至”时的疾行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生的过程,需要我们不断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变化,同时也要付出生命中的美好和力量。
《被落日追赶的人》的疼痛点是人生的磨难与短暂。通过对主人公被风、雨、闪电、雷声追赶,以及被落日追赶的描绘,展现了人生的苦难与挣扎,以及在困境中寻找希望和归宿的主题。诗中的“他”其实就是诗人自己,不用第一人称是为了叙述更客观、更理性。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人,他经历了种种磨难,但却从未放弃。他的内心世界充满对生活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期待。开头两行,“体内的风声”与“残缺的青春”相关联,表明他曾经拥有过美好的青春岁月,但因为种种原因,它们已经残缺不全。他试图“赶在暮色降临前”交出内心诸如月光、灯火、潮声和浪花等一切美好,表达他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向往。诗中的比喻和象征手法也十分出色。落日、流水等意象,不仅描绘了主人公所处的环境,也暗示他的内心世界。這些意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人感受到了主人公的孤独和无助。最后两个“是不是……”,诗人运用疑问的口吻,引导读者一起思考人生:当落日追赶一个人时才会觉得余生不多、遗憾似群山飞来;当生命遇到困境时,不要放弃希望,而要勇敢地面对一切,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美好。无论何时何地,家都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这里的家更多是指我们内心的归宿感,是诗人内心精神的栖居地。这首诗表现了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和对未来的热情期待。
《东鲁山》的疼痛点是失去亲人的伤痛和对他们的怀念之苦。诗中的东鲁山,坐西朝东,仿佛是人间的“风水宝地”,其实它是一块墓地,“住着我的亲人”,它的魅力在于它的静谧与温情,同时也因为它能“救赎”我们曾经救赎过的一切。第二节中的两个“救赎”,将生与死、爱与恨、过去与现在、自然与人生融合在一起,透露出一种深沉的人生思考。每一份痛苦,每一份经历,都成为诗人成长的力量源泉,从而构成一幅人生的多面镜。“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东鲁山是亲人的安眠之地,也是诗人内心唯一的情感依托。清明扫墓,是“我”和亲人沟通、交流的特殊方式,也是“我”弥补亲人的唯一方式。在“我”眼中,东鲁山就像是一座精神的山,它可以洗涤过去,甚至改变着现在,麦子和高粱不见了,只见墓碑。在“我”看来,东鲁山是高于草木花朵的。这里没有物质的喧嚣和争夺,有的是温热的土地和宁静的山谷。诗人的这份宁静是经历了风风雨雨、酸甜苦辣之后才获得的。这里“住着”亲人,“他们的名字紧挨着名字”,仿佛“在尘世取暖”并相互“问候”。然而,东鲁山也“拒绝”麦子和高粱的生长,只生长“悲伤”,这里的“悲伤”是对亲人的怀念,也是自我救赎的一种力量。东鲁山不仅是人间的风水宝地,也是“我”心灵上的一片净土。诗人的表达方式朴素而真挚,字里行间充满了情感的力量。
《父亲的钢笔》的疼痛点是父亲的“英雄气短”。这支钢笔是父亲留给“我”的一件精神财富,它静静地躺在“残旧”的笔盒里,现在可能已经坏了,写不出文字了。但诗人睹物思人,仿佛看到一位“迟暮的英雄”。诗人通过描绘父亲使用过的钢笔,以及那些被他写过的事物,以物喻人,传递了对父亲的敬仰和怀念。首先,诗人在开篇就通过生动形象的比喻,将父亲用过的钢笔比作一位迟暮的英雄,这种形象化的表达方式让读者能够更好地感受到诗人的情感。同时,诗中也运用“尘埃”这一意象,进一步强化钢笔的“残旧”和“落寞”之感。其次,诗人通过描述那些被父亲写过的事物“已成为历史/成为残缺和疼痛”,诗人将父亲的手迹与历史、残缺和疼痛联系在一起,表达对过去岁月的感慨和对父亲的敬仰之情。最后,诗人又想象如果拿起钢笔写下现实,“那些虚构的/美好,将荡然无存”,这里诗人以钢笔作为引子,对过去与现在进行对比反思,体现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对父爱的珍视。
《马头琴》是一首充满情感和深度的作品,其疼痛点是马作为生命的消逝。它通过马头琴这一艺术形式,将马的坚韧、隐忍、热烈和奔放等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诗不仅是对马的赞美,更是对生命的凭吊。首先,诗中的描述让人感受到马的坚强和高贵。当一匹马应声倒地,它的头颅被雕刻成马头琴,这个过程既体现马的坚韧不拔,也体现马的无私奉献。接着,诗人进一步强调马的骨骼和精神内核,将其融入马头琴中,象征着生命的精髓和内在力量。在马头琴的演奏中,诗歌通过生动的比喻和想象,将声音赋予了生命和情感。那些竖起耳朵的动物和人,那些垂下头颅的草木,虽然都感受到了马头琴的魅力,但方向感是截然不同的,动物抬头是对琴声的聆听和共振,而植物垂下頭颅是对琴声的感知和缅怀,通过对比产生一种情感张力,进而生发出生命的悲悯力量。在诗的结尾,诗人用“马头琴啊!其实你是一匹马的/灵魂”来总结全诗,将马头琴与马的灵魂紧密相连,强调了马头琴所蕴含的生命意义和精神力量。同时,诗人也提出一个问题——“谁能唤醒一个人内心的苍凉/和波澜壮阔的悲痛”?这个问题既是对生命的思考,也是对人类的关怀,唤起人们对生命的敬畏和珍爱。
另外几首诗也是有疼痛点的。“谁能比它更锋利,更轻易就划开我与故乡/久治不愈的疼”,《七月的叙述词》的疼痛点是远离田野的疼痛。“请允许我说出爱,久藏于内心的/红扑扑的爱”,《请允许我说出……》的疼痛点是爱而不得的落寞与苦闷。“仿佛暮色一合拢,父亲就将/离我而去”,《催眠术》的疼痛点是父亲走得太匆忙的遗憾。“像一株植物,遗忘在夕阳的背影里”,《需要一场雨水》的疼痛点是生命缺乏爱的滋润。“它是一个人内心的/灯盏,被风提着/在旅途中,明明灭灭”,《低处的阳光》的疼痛点是底层对“阳光”的渴求。“它落下的/重量,足够压住尘世一切的/轻浮、荒芜和绝望”,《汗水的重量》的疼痛点是劳动的艰辛。“它把一个人轻轻摁进春色里/仿佛把幸福和疼痛,摁进/生活的骨肉里”,《三月的风》的疼痛点是青春易逝与人生无奈。“它羞涩的歌声/把月光下的子夜,捻得又细又长”,《子夜的小村》的疼痛点是思念之苦。诗人将这些疼痛点,通过语言的多姿多彩和结构的起承转合等手段艺术地表现出来,也引发读者阅读的疼痛感。章洪波认为好的诗歌要“有血,有肉,有骨头”,因而他的诗歌注重构思的精巧、语言的锤炼和内涵的厚实,特别讲究修辞手法的出新出彩。
章洪波从小热爱文学,学生时代深受艾青、徐志摩、戴望舒、北岛、郑愁予等诗人的影响,在多种文学样式中独爱诗歌,他喜欢诗歌的语言、哲思以及直抵人心的力量。章洪波诗歌的疼痛感来源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感知,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现实的警觉与批判,并不是子虚乌有、空穴来风,它是有真挚的情感基础的。疼痛是他诗歌的词根,更是他诗歌的心跳。“疼痛”一词在他的诗歌里出现的频率较多,这恐怕与他成长的经历、经受的生活密切相关。据了解,他比同龄人经历过更多的风雨、苦难和伤痛,过早地体会了人情冷暖、爱恨情仇、生离死别,但恰恰是这一点让他更透彻地感悟人生,更深情地热爱生活。当然,一首诗光有疼痛感是不够的,他的诗中更有幸福、期许、甜蜜、忧伤,与真切的体验交织在一起,使主题更加丰盈、饱满。他说:“幸福并疼痛着,让我在尘世时刻保持冷静的思考,穿透一些事物的表相,看清它的本质。我并不因疼痛而厌恶生活,相反更爱生活。”在坚韧的人生历练和自觉的诗歌实践中,他正在不断探索,以日臻成熟的审美追求力争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疼痛诗学。
李汉超 湖北应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应城市作家协会主席。已出版诗集《岁月无尘》《大地之灯》和诗评集《诗海逐浪》《静下心来读好诗》《荆楚诗韵》等11部。
(责任编辑 蒋茜 74050215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