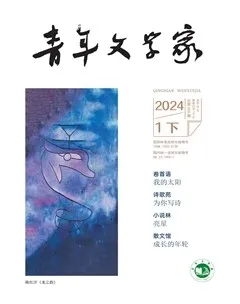书灾
沈惠勤
冰心在《忆读书》一文开首说:“一谈到读书,我的话就多了!”是的,我想不只是文学大家一谈起读书“话就多了”,每一个热爱读书的人都会有话想说。我此生虽热爱读书,但一路走来,由于能力浅薄,心思朴拙,并没有竭尽护书之能事,导致了一场场书灾,这实在是羞愧的。
一、书荒
我出生在一个渔村,父母虽识得些字,但他们对读书能改变命运的认同感并不强烈。老实巴交的他们拿不出一本像样的书做我的精神食粮。
我偶然见书是在邻居家,那个小邻居正在生炉子,欲用满目灰尘的连环画做引火纸。这是一本与柴火混在一起的弃书,它们犹如被打入冷宫的嫔妃一般凄惨,甚至可以说比柴火之流的命运更惨。它们被随意丢弃在柴火堆中,显得不伦不类,然后生生地被欺压在下,变得面目全非。小邻居把它抽出来时,如同扯着一个不情愿的孩子的臂膀一样,一不小心,就扯下了衣袖。小邻居扯下一页连环画纸,大概嫌当引火纸太单薄,索性将整个所剩不多的几页在手里揉成一团,开启了它烟火生活的第一幕—生炉子。现在想来,用书纸当引火纸着实够奢侈的,但我当时只觉得好奇,因为从未好好见识过书的我很想看看里头的字画,然而它们太脏了,实在不堪入目,而且它们已然接上了“自来火”。火苗伸出滚烫的舌头风卷残云地饕餮着书纸,腾出一些火星,犹如火魔喷吐的哈喇子,一场生活的烟火活生生地吞没了曾经抚慰过人的精神食粮。
我对此原本是毫不在意的,毕竟这本书已经破破烂烂,勾不起我一丝好感。
不过,这场残酷的烈火吞噬,仿佛在我心上也燃出了一个洞,至今我对这样一本连环画中间的任何一个文字,以及任何一幅画都难以描述,它们构成了我对这本人生所见第一书的空洞见识。
我正儿八经地拥有书是在20世纪70年代,走进小学读书,与许多老百姓家的孩子一样,拥有的是一本普普通通的、透着油墨香的语文教科书,这股油墨香气在老木疙瘩一样的课桌上异常突兀地透进我的鼻翼,引诱我读书。它是我人生中极为金贵的第一书,我本应好好珍惜它,但懵懂幼稚的我对它竭尽恶作剧,让它接纳了少不更事的主人的众多“馈赠”:指甲的抓印、铅笔的描画、小刀的刻痕、铅灰的涂抹……可它却像一位慈祥的奶奶一样,任劳任怨。
而我,自从开始读书,就读一本,扔一本,从未懂得收藏。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一本教科书完不完成使命不重要,只要一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它便基本听从两个命运:一是当柴火烧,可以暖身心;二是当作废纸廉价变卖,可以换油盐。我早已记不住它们坎坷的命运,然而它们在无形中化为精神食粮融入了我的血液,并一直指引着我行进在读书的路上。
二、穷读书
在我读五年级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表姐家看到了大我整整一辈的老姐夫的几本书。他是农村中学老师,我十分羡慕小我一辈却与我年纪差不多的外甥女,因为她间接拥有她爸爸的这些书。趁着表姐忙于家务,我借来一本《吕梁英雄传》,因为受到时间的限制,加上见识的浅薄,我生吞活剥地看完了书,像煮了一枚蛋,因为太过烫嘴和饥饿,竟然在吃完后食不甘味,并未真正引起心灵的共鸣。我明白,书不是自己的,该按时归还,这严重地限制了我对一本书的解读。
不曾真正拥有自己的书,读来始终是窘迫的。我对书也没有那样强烈的占有欲,没有像梁晓声那样,为了一本《青年近卫军》,特意到她母亲工作的厂房去要钱买书。不过,当梁晓声在逼仄、潮湿、闷热的环境里见识到母亲的辛苦后,他也沒能用母亲揉皱的钱买下那本心心念念的书。毕竟,穷读书是一场于心不忍的考验。
在进城读师范的日子里,我的书也都是借的。虽然学校的图书室也计时归还,但毕竟没有人情约束,所以看书也就变得舒爽起来。彼时,写篇日记还是错字连篇的我要看完一部名篇巨著还是水平严重不足的。所以,我同时买了《现代汉语词典》和《中华成语词典》来提升自己的水平。后来,那本《中华成语词典》被我反复翻烂了。在恶补的同时,我与那些稳步前进的城里学生相比,总有几分狼狈,所以不敢声张自己在读什么,基本是悄悄地读。我看中国的《四世同堂》《小二黑结婚》《野火春风斗古城》还能差强人意地记住些内容,但看《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那样的外国文学作品,真的有一种深深的欠缺感,总是不能卒读里头大段的描述性文字,就基本是跳跃式地翻阅过去。
不管是速读、跳读,还是细嚼慢咽地读,都算给自己的青春时光补充了精神食粮。但这些书依然不是自己的。我很佩服一种理念:分享一个苹果,只能我一半你一半,而分享一本书便会变作N份的知识。图书的借阅让许多人在穷读书中也能分享到其间的“黄金屋”和“颜如玉”。
三、迷你书房
参加工作后,我延续着师范时期的读书习惯,仍想着要读书。这个时期,我会把一部分钱用于置书。后来,我自己也很快建立了一个小家庭,巧的是,我先生也是一个喜欢置书的人。我们正儿八经打造了一个书橱,将彼此的书籍合二为一,整合共享。书橱里塞满了各种书,有一边工作一边进修的书籍,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伟人著作,有文学读本,也有订阅的报刊……书籍逐渐增多,像栽培的苗圃一样,需要一些精心的伺候了。
当我们拥有一套镇区的蜗居房后,也不忘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我们硬是在东北角的小阳台里打造了一个迷你书房,房里仅供放置一把摇椅的空间,然后把所有书籍全部垒于简易书架上。通常是谁先霸占领地谁就能先享受读书时光,而另外一个就只能算“二等公民”了。这是成为城区居民最初的惬意。
随着日子的推进,我们奔波在人生路上,与书渐行渐远。生活的油盐酱醋味渐渐地弥漫了整个小屋,书卷之气一再被排挤着。孩子长大,独霸了迷你书房。那些可怜的书籍经常惨遭小刽子手的屠戮。等我洗刷完毕,常常在那里见到乱书一堆,都已经是“缺胳膊掉腿”的了,悔之晚矣。
在狭小的空间里做事,往往是局促不安的。渐渐地,生活杂物越来越多,它们粗暴肆虐地侵占到了一方书香之地。所谓的迷你书房,慢慢退化成藏物间了。那些书籍已然不可能再享受高贵的待遇,它们渐渐被堆叠的杂物掩盖了真容,或许在后面只能“长太息以掩涕兮”了吧。
后来,我们以小换大,购置了一套底楼,奢侈地打造了一個书房,书桌、书橱应有尽有,靠墙列成一排。那些书籍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陈列在书橱里了。我颇为自得地美其名曰“书斋”,也颇为浪漫地设想着在此享受读书时光。可最终并没如愿,与吃喝拉撒睡这些日常用度比起来,这个所谓的书房是最不受待见的。首先,它的格局小,处于东侧,狭长的一条;其次,它兼具通向南边小园子的廊道功能,往来杂沓的步履声让人心神难以安定。我从未在里边安下心来看过一本书,我宁愿在某个周末,走出这个书香之地,到室外小花园的石桌边、花草边,坐享一段神清气爽的读书时光。我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让这个所谓的书斋发挥作用。那些书籍排列在橱间,看我晃进晃出,晃过了许多匆匆光阴,该是满肚怨气的吧。
四、书灾
女儿渐长,为人父母者不得不重新考虑购房,又借又贷,双管齐下,购置了一套二楼平层。面积是大了,可面对家里上下几代人的用度,终于将所有能利用的小空间全部装修成卧室,没有给那些书籍留下一个独立的空间,它们四散各处,家人各取所需。我先生占据了阳台位置,在晾衣竿下摆了书法桌,将欧阳询、颜真卿、王羲之的书帖混搭成山。而我占据了卧室一角列了一个书橱,文学书籍层层叠叠。家中廊道一头儿贴墙做了一个公用书橱,陈列《中国旅游大辞典》《年鉴》《辞海》等大本书籍,厚重而又精致。如此支撑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些书籍在各处堆叠成长,犹如一片片长年不经伺候,终至杂草丛生的田土,乱象频仍。后来,随着家中第三代的降生,那些书籍的位置越来越局促,孩子的玩具像肆虐疯长的草儿一样,声势浩大,掩盖了家中最后一点儿可怜的书香领地。那些书籍躲在盒装玩具的背后默默地承受着房屋老化带来的严峻考验。
一日,一个小球滚落至书橱脚下,我不得不翻箱倒柜,历经一番腾挪转移,找到了小球。我也看到了橱脚下躲藏着的蓬头垢面的那些精装书,我心有戚戚,提起一本,里边的一截儿竟已潮湿霉变。我恍然明白,书橱是贴着卫生间的墙壁打造起来的,当时为了省钱,没有进行丝毫的防潮处理,所以水汽一点点洇过墙壁,渗进书纸,濡没文字。一场灾难降临到这些书籍头上,它们像得了风湿病的老人,不堪一击。我急忙给它们掸去黑灰,抹干湿气,堆叠到书桌上。书桌原本也是一块巴掌大小的地儿,对于新纳的书籍成员,它们总是默默地承载,渐渐地失去了书桌的功能,彻底地变作一头驮书的老牛,现在一下子又接纳这么多书籍难民,书桌危如累卵。
而此时,卧室里那只纸板书橱也早已不堪重负,弯下了每一根承重横板,终于有一天倾斜垮塌,我想了个办法让它再支撑一段时日,可最终书橱还是分崩离析了,那些书籍也滑落一地。我终于明白,书这精神食粮,也并不是可以任意处之,而无视它们的物质存在的,知识借助纸张的形式存在着,是实实地拥有沉甸甸的分量的,它们不只是精神的食粮,更是不容小觑的物质啊。
我费了整整一天工夫,把书堆叠于地上。此时,我又犯了一个低级错误,靠墙、贴地对于书籍来说,都是毁灭性的灾难,书是不能如此赤裸裸地陈放的。待到我这愚人清醒过来时,这一堆书的底层又成了重灾区。
我救治书们的唯一办法是,把一只废弃的电视柜挪来,专门用来堆叠书籍,书们在上头累累叠加,以最小的空间密度紧紧相贴,换得一份暂时的安全,可是它们全然变作了一堆书山,煤矿再好,也难以开采了。
我常常为不能掏出沉压其间的书而烦恼。一次,我想起毕淑敏的一句话,可是无法翻阅,又一回想重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霜冷长河》,可又苦于不能深挖而作罢。我像一个山民,仅能在山地表面做些开垦,实在难以深入山中去做一个开采的矿工,有时我还极为懒惰,当在山地表面淘不到宝时,就弃了耙子,绝了念想,那堆旧书山终至沦落为无人问津的荒岭。后来,干脆重新购置读物,那些埋在山里的书成了一个久远的念想。书不能随手拈而读之,那与一堆废纸又有何异呢?
五、大书房
我一直期待着拆迁,其目的之一便是与年轻一辈分而生活,一定要把那些委屈的书移植到新居,为书开辟一堵墙,让书们占据最广阔的墙面空间,彻彻底底地还书以尊严,让它们好好地长出生命,像一墙绿意葱茏的爬山虎般。我的这一观点与先生不谋而合。
拆迁新居到手,最着急慌忙要向装修师傅表明的就是打造书墙的意愿。书墙不在于多好,而在于实用和牢固,装订满墙的小橱格,让它们各有所负。这一劳永逸的储书之策刚刚敲定,孩子就念叨起来:“爷爷奶奶,我也要几个小格子,摆放我的书,以后来你们家,我就有书读了。”那是当然,一墙的书格够每个人承包了。
乔迁新居在即,我把旧屋中的书山一层层地挖掘开来,如同意外采得一座金矿。我欣喜地将书分门别类安置于新居的贴墙小木格里,这是家中最大面积的一堵客厅墙。为了给书谋得这一席之地,我们也做了割舍,这里不能安放沙发,改放一张长条形的书桌,格局似乎有点儿另类。然而,我们为书安心,我们把客厅打造成了一个家人共用的大书房,每天可以随心与书会面,而书友也竭诚效力。孔子、孟子、庄子等诸子百家来了,三毛、张爱玲、铁凝、王安忆、迟子建等作家来了,他们温文尔雅地赠书与我,我读之、问之、笑之、爱之,随意自在。
数十年来,我向来是生活至上,书虽然一直是我心头所爱,但与日常所需相比,它们一直在默默地退让牺牲。书在我这样爱而无力的人手里是受罪的,有的虽然忠诚地跟随了数十年,但被暖暖地捧于手心实在是难得。待到老矣,终于能好好地归置它们,让它们列在大墙的格子里,等待着我空来的安抚。可是,待等觉醒时,一个人的电量已经所剩无几,眼睛昏花了,脊椎酸痛了,与书们的对话大打折扣了。
个体处于世间,如微弱尘埃。所求知识更是微乎其微,如若还要不好好善待而淹没那些书籍,便是对人类智慧的大不敬。虽然所求无多,但还是要尽己所能善待这些请到生命里的每一本书。
一日,我与学生一起阅读一篇名叫《保护书籍》的短文。文中说:“书籍面临着危机。据估计,美国各图书馆有近1/3图书的纸张已严重老化。……1850年后出版的书籍,平均保存寿命为50年至100年,有些书籍只能保存25年便化为尘土。”
书,承载的是智慧的结晶,却托付在沉重而又脆弱的纸张里。书的物质生命是短暂的,但精神应该不朽。
我只是一名书籍的普通读者,从来没有梦想也没有能力做藏书之功,心间只求对得起人生匆匆几十年,既然我认识了这些书友,那么,在人生步入老年之际,让我好好善待之。
人生本苦短,与书对话,去除孤寂,日子便会温暖些,有此精神食粮,不亦乐乎?
在短视频占据人类耳目的时代,我不觉得为书们布局一堵大墙是一种违逆,我依然坚信《记黄鲁直语》中黄庭坚说过的一句话:“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
不读书就会变得面目可憎,那么读了书是否就会变得面目可爱呢?读书虽然无法创造出回春之术,让老之将至的我返老还童,但书籍一定是能让人安然的。那么,为了做一个安详的老人,读读书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