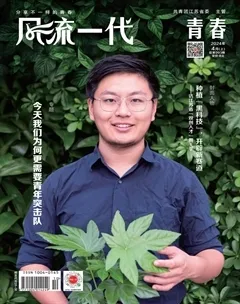我的大学
作者简介:薛永忠,男,1969年出生,泰州市高港区政协主席。
1
高中学习对我来说似乎没那么紧张:集邮、集古钱币,读金庸、王朔、梁羽生的小说,读《读者》《知音》《故事会》各种杂志,还痴迷上了吉他,左手指尖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与隔壁班的同学合办小报《牛虻》,针砭时弊、讽刺学校、挖苦老师。
当时的我毫不怀疑自己有充足的后劲冲刺全校第一。然而,春节后开学不久,我摔断腿了。手术出院时,离高考还剩三个月。
腿上打了钢钉躺在家里不能动,每天都有同学把当天的学习笔记带给我。毕业考试,舅舅驮着我进了考场,成绩出来,离“第一”仅一步之遥。虽然不久后的高考没有考好,但也达到了一本线。我原谅了自己:无所谓,向前看,前程远大着哩。
从7月底到8月底,一批又一批同学都收到了录取通知书。直到9月,我还是没有收到录取通知。国庆期间,老爸用自行车驮着还拄着拐杖的我,找到一位在省教育报工作的同乡,这才得知:今年录取工作全部结束了。
9月,同学们陆陆续续、欢天喜地走向天南海北,我只能拄着拐杖仰头看着天上行色匆匆的云。
年底,市里出台政策,城镇户口高考落榜生有机会参加工作。我想赶快逃离漫长而无望的等待,那种氛围真的让人窒息。于是,果断选择参加工作。
2
劳动局大院里,报名的人潮涌动。政策规定,按高考语数两门总分排名录取。我数学108分,超过很多人的总分,第一个选岗。迈着刚刚摆脱拐杖的腿,我一脚踏进了机械冶金工业供销公司,成了一名全民劳动合同制职工,工作岗位:供销员。
上岗之前,在商校集中培训了3个月,我结交了一些新朋友,原本灰暗的心情逐渐阳光起来。培训结束,正式上班了,憧憬从此天南海北跑供销,见识各式各样精彩的人和事,暗暗给自己立下目标:奋斗五年,成为这里的经理。
当时正值“十亿人民九亿商”,供销公司物资公司炙手可热,线材、圆钢、铝锭、锌镍铜……一天一个价。不断有人发财了,有人“进去了”,每天上演着精彩纷呈的人间故事。然而,正如刘若英《给十五岁的自己》唱的:“不确定自己形状,动不动就和世界碰撞。”我没有能去供销科,而是进了综合科,而且是先去看仓库。第一天,和刚参加工作的几个培训生一起去西郊石化厂拉煤气罐。回来时,站在堆满煤气罐的一路颠簸呼啸的卡车上,寒风凛冽,我的头发和心情一样凌乱,想着一个具体且现实的问题:怎么离开这里?
苦苦思索了两个月,苍蝇撞到玻璃上——有光明、没前途。一天,有个比我大两三岁的朋友告诉我,他正在参加自学考试。他说,自考很难,但文凭很硬,国际上都承认,考过十门就拿大专学历。他已经过了两门。高考关上了一扇门,自学考试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我突然间看到了光,先拿个文凭再说。
考试还有一个多月,最多可报 5 门。我报了5门,谢绝了所有活动,一心一意备考。上一年在病床上自学的经验派上了用场。到教育局拿成绩单,居然5门全过!
1989年,我拿到了自考大专文凭;又过一年,通过了自考本科。
3
拿到了大专、本科文凭,加了两回工资,自学考试奖励了两个一百元,请同事们到富春饭店美滋滋地吃了两回早茶,但我没有一点读过大学的感觉。既没憧憬中大学生活的浪漫,似乎也没有多少真才实学,感觉就是高三之后读了个高四高五。本科考完之后可以继续拿学位,但这时,我已被借用到公司的主管局——机械冶金工业局,我的目标已有点宏大:不但要当经理,而且要做企业家。
当时的机械冶金工业局是全市最大的工业主管局,下辖春兰、林海等30多家企业和包括我原单位在内的 3 家物资供销公司。春兰正呈蒸蒸日上、一飞冲天之势。全省机械系统正在轰轰烈烈开展“学春兰、学小天鹅”活动,作为主管局唯一的小秘书,我成天跑企业、写材料,几乎每天都在近距离聆听企业大咖的对话,一次又一次受到思想的激荡和鼓舞。有一次,全系统书记、厂长会在春兰总部召开,气氛宽松而热烈,年轻的总经理陶建幸豪情满怀地畅想下一步产业布局,感慨“中国市场到处都是机会”。三十岁左右就当上林海一把手的局长继续鼓动:“到处是黄金,看谁眼睛尖!”我听得热血沸腾:我要做企业家,像陶总那样。
当时泰州的很多厂长、经理都是从主管局中层岗位派出去的。陶总就是从局技术科长到春兰当厂长的。很多企业的一把手是我原来朝夕相处的同事科长。成为企业家必须先当科长。所以,“当科长”成了我当时人生目标的最紧要一步。为了“当科长”,我拼命写材料、跑企业、学本事,比对付自学考试投入了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
1992年,改革大潮奔涌,开放是最热门的话题,中国恢复GATT(关贸总协定)地位在即。局里成立了外经科,正物色人才。
我立即决定:学外语!学外经!首先订阅了英文版的《中国日报》,虽然看得吃劲,但我每天还是硬着头皮读,然后把一些不算新闻的新闻讲给同事尤其是领导听。接着,报名参加省外向型经济培训班。不久,又从报纸上看到南京大学商学院的招生启事: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修完课程可申请硕士学位。软磨硬泡,领导同意我报考。我考了,真的考上了。
可只上了差不多一个月,商学院的老师突然来和我们这个班商量:让我们国贸班并到MBA班去。好多人同意了,但我不同意,因为单位让我来学习,是要培养一个外经人才。
商学院最终给我提供了一个方案:你考国贸专业正式的研究生。只要过了笔试,复试好商量!
正式的研究生,一下子复活了我的大学梦。尽管单位领导得知情况后打来电话,暗示我回去,不上学,一样可以当科长。但在上大学与当科长之间,我果断选择了上大学,决定全力以赴,放手一搏。
离考试还有三个月,研究生考试有5 门,政治、英语原本会一些,专业课厚厚4本教材:《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更要命的是要考《高等数学》。我自考学的是中文,没有数学,距上一次摸数学书已经过了整整6年。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想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更重要的是不给自己留下遗憾。之后的每一天,我都在南大校门东侧的自习室度过。我对4门专业课越来越着迷,也发现了自己真正的爱好。《高等数学》初看如天书,但好歹把微积分啃下来了。至于线性代数、概率论,只能翻阅一下了。政治和英语,实在没时间了,听天由命吧。
放榜了。两个消息,一好一坏:好消息是考了313分,超过南京大学国际贸易研究生单独考试录取线,完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坏消息是英语49分,而国贸专业最低要求是50分。找到了校领导,最终答复是:这是一条硬杠子,你英语多考1分就好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微笑着的,心无波澜、了无遗憾。因为和上一次与大学失之交臂不同,这一次,我是有选择的,而且是我自己的选择,并且我为这个选择认真地努力过。
我的大学,从此道一声“再见”。
50岁生日那天晚饭后,一个人在房间里循环播放《给十五岁的自己》,仿佛是和少年的自己对话。我最大的感慨是,感恩和庆幸自己人生的这50年,恰逢中华上下五千年最好的五十年,每个平凡的普通人都拥有了选择的权利,越努力,选择的机会就越多,人生就越精彩。这些无数个毫不起眼的微小选择的涓涓细流,最终汇聚成了时代前进的奔涌大潮。
(编辑 郑儒凤 zrf911@sina.com,采采绘图)
- 风流一代·青春的其它文章
- 小林漫画
- 青问青答
- 我为什么不会和自己相处
-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 江南三月
- 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