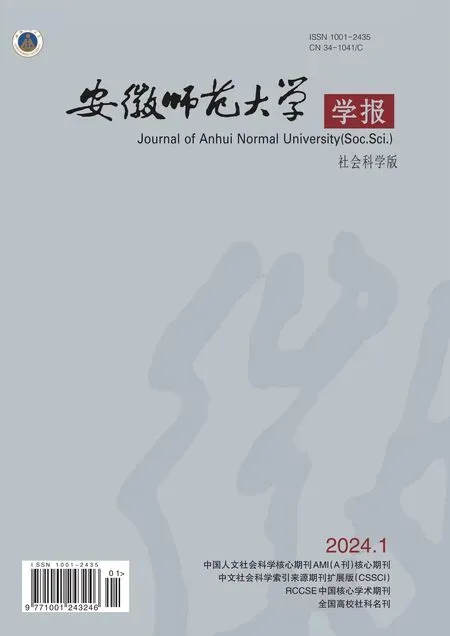葛兰西与福柯:两种治理观的比较*
熊伯能,何 萍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 430072)
治理问题是当今时代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和实践问题。就治理的内在逻辑而言,关键是要回答“什么是治理、治理什么、由谁治理、怎样治理”等基本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哲学家福柯曾提出社会主义治理合理性的问题,引起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关注和思考,联系到20世纪初葛兰西对治理问题的探讨,从而更加突显了葛兰西的治理理论的当代价值。但是,福柯的治理理论与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家葛兰西的治理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葛兰西的治理理论是围绕着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而展开的,它的核心范畴是文化霸权,力图在政治哲学框架中揭示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提出现代国家治理的方案,本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治理理论;福柯的治理理论是围绕着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治理问题而展开的,它的核心范畴是生命权力,力图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中揭示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提出现代社会治理的方案,本质上属于新自由主义的治理理论。尽管这两种治理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因它们都是从权力关系入手来研究治理问题,又形成了一种理论上的对话关系。正是这种对话关系,可以引发对当代治理的深层次理论思考。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分析福柯和葛兰西在治理的本质规定、权力基础、历史主体、未来图景等问题上的异同,来思考治理理论的基本特性,并借鉴他们的思想资源,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治理理论。
一、从文化领导角度理解的治理与从统治技术角度理解的治理
治理的本质是什么?治理和统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是研究治理问题必须首先解答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福柯与葛兰西都强调治理不同于统治而有自身的特点,但在如何理解治理的特点上,福柯与葛兰西又有着全然不同的阐释。福柯和葛兰西在这个问题上的同与异向我们展示了治理理论的产生及其走向。
福柯和葛兰西强调治理与统治之间的不同,是基于他们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认识。19世纪80年代,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之初,就有了国家政府机构和议会机构两个部分。从这时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就开始思考治理问题,展开了有关统治与治理关系的探讨。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是列宁与考茨基关于统治与治理的争论。考茨基以西欧资本主义的现状和第二国际的议会斗争形式为根据,认定阶级只能统治,而治理应该由政党来实施。列宁以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为根据,指出无产阶级既能统治也能治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种治理方式。列宁与考茨基的观点虽然是对立的,但让人们看到了统治与治理的区别,从而引起了人们对治理问题的关注,也拓展了人们对治理问题的认识。
进入20世纪20-30年代后,资产阶级国家产生了新的职能,这就是来自市民社会的组织形式。葛兰西就是在对这一组织形式的研究中,看到了资产阶级国家结构的变化。在《狱中札记》的“政治和宪法”一节中,他写道:“按照传统的宪法,它(指政党——引者注)在法律上并不统治或治理国家。它具有‘实际的权力’,执行领导功能,保持‘市民社会’不同利益的力量均衡。但在实际上,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互相交织,所有的市民都认为政党既统治也治理国家。我们不能根据这个事实创造传统的宪法,因为事实总是不断变化的;只能制定一套原则,宣称国家的目标就是国家的结局、国家本身的消亡,也就是政治社会再次被纳入市民社会。”①[意]葛兰西著,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狱中札记》,河南大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16年版,第208页。在这段话中,葛兰西动态地描述了统治与治理的关系。在他看来,统治和治理分别代表了国家的两种权力:一种是政治权力,这是统治的权力,这种权力通常是由统治集团来行使的,它采用的方法是暴力专制;一种是社会权力,这是调节市民社会不同利益之间关系的权力,这种权力通常是由政党来执行的,它所采取的方法是领导。葛兰西一方面区分了统治与治理,强调两者是根本不同的东西:统治是采取武力、军事、司法等强制手段的权力形式,是镇压性、直接性的权力行使过程;治理是在道德、伦理、精神、文化等方面实行领导的权力形式,是非强制性、非暴力性的权力行使过程。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这两种权力形式并不是完全割裂的,不是有前者就不需要后者,或者有后者就不需要前者,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但在不同时期两者的地位不一样。在资本主义初期,前者地位更为重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后者的作用将越来越大,甚至逐渐取代前者的地位。
历史地看,葛兰西对治理的强调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自19世纪末开始,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统治地位逐渐稳固,市民社会也由原来的经济基础上升为国家的形式,执行国家意识形态的职能,这就为资产阶级巩固自己的统治提供了新的场域。于是,资产阶级不再采用单一的暴力强制、武力镇压等高压手段进行统治,而是同时采取改革选举制度、扩大普选范围、实行社会保险、发展国民教育等途径,希望通过所谓福利政策来软化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斗志。葛兰西认为,正是后者,构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治理手段。资产阶级国家把这种治理手段包裹在民主化和平等化的外衣之下来迷惑无产阶级,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置于资产阶级统治的羽翼之下,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法超出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的界限。这样,葛兰西就通过剖析资产阶级国家的内部结构和行使权力的方式将统治与治理区分开来,强调治理在资产阶级国家的作用,尤其是在阻止无产阶级革命方面的作用。他在区分统治和治理的社会基础上,对资产阶级国家内在权力结构的剖析是十分深刻的。正是这一方面的思想,成为当代思想家们研究现代国家治理和国际社会治理的重要思想资源。
与葛兰西一样,福柯也坚持治理与统治的区分。他指出,“治理(gouverner)与统治(régner)是不同的东西,也不是命令(commander)或者‘制定法律’……治理也不是要成为君主、宗主、领主、法官、将军、地主、师傅或者教师,治理有其特殊之处。”①[法]福柯著,钱翰、陈晓径译,《安全、领土与人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2页。那么,治理的特殊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在他看来,16 世纪前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统治权问题,统治权模式的基础是“统治者—臣民的轴线”②[法]福柯著,钱翰、陈晓径译,《安全、领土与人口》,第82页。,统治者可以采取杀人、暴力等形式,也可以采用法律、规章等手段,这是全景式的压迫和控制模式。但是,随着人口的发生和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治理艺术逐渐成熟起来,最终突破了统治权理论的阻碍,而成为相对独立的权力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有可能建立这样一种关系,“不是一味地顺从,而是让协作发挥重要作用”。③[法]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2页。福柯在这里所说的协作的权力关系,也就是治理的权力关系。
但是,在对治理本质的理解上,福柯与葛兰西是根本不同的:葛兰西的治理理论把治理理解为社会权力的变化,而福柯的治理理论是把治理归于一门技术。在福柯看来,国家的治理不能仅仅关心作为公民的人的权力,还要关心作为生物存在的人的权力,并且随着现代国家的发展,后者是越来越重要的方面。福柯指出:“因为治理一词本身……我曾经,今年我仍然只从这样一个角度,并且只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考察对人的治理,即它作为政治主权之运转。”④[法]福柯著,莫伟民、赵伟译:《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在这里,福柯不是一般地谈论治理,也不是关注任意一种权力关系,而是关注国家的治理技术。他认为,“治理术对国家来说如同隔离技术对于精神病学来说那样,以及规训技术对惩罚体系来说那样,生命政治对于医学制度来说那样”。⑤[法]福柯著,钱翰、陈晓径译:《安全、领土与人口》,第156页。应该从治理技术的角度来看待国家,把国家理解为一种治理方式,看成治理横生出来的“枝节”。在他那里,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有三层意思:首先,它是“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计算和策略构成的总体”⑥[法]福柯著,钱翰、陈晓径译:《安全、领土与人口》,第140页。,这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其目标是人口,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技术工具是安全配置;其次,“治理”作为一种比主权、规训等更加重要的权力形式,由此发展出一系列治理机制和知识体系;再次,治理术“还意味着一个过程,或者说是这个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中世纪的司法国家转变成15、16世纪的行政国家,逐渐治理化了”。⑦[法]福柯著,钱翰、陈晓径译:《安全、领土与人口》,第140页。这三层意思表明,福柯关注的核心是治理实践的技术维度。他曾批评人们对阶级斗争概念中的“阶级”关注过多而忽略了“斗争”,强调“要研究权力的策略、网络、机制和所有决策赖以实施并迫使其得到实施的手段”。⑧[法]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24页。可见,与葛兰西重视权力的政治层面相比,福柯更加重视权力的技术层面,从技术的角度来审视治理问题,在他看来,治理正是借助具体治理技术得以获得其现实性。
福柯的治理理论与葛兰西的治理理论的这一区别,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他们的政治立场造成的。葛兰西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资产阶级国家持批判态度,因此,他把治理研究的重心放在社会权力的变化上,提出的是批判的治理理论;福柯是一位后现代哲学家,对资产阶级国家持肯定态度,因此,他把治理的重心放到治理的艺术上,代表了当代技术政治学的研究向度。如果将两者综合起来,我们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治理既有政治层面的内容,也有技术层面的内容。
二、治理的权力基础:是文化霸权,还是生命权力
治理的权力基础是从权力分析角度对治理问题的追问。在这个问题上,福柯和葛兰西都不满足于从宏观的政治层面上研究治理问题,而是深入到微观的机制层面上研究治理问题。他们的观点是:国家不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在国家之外有另外的权力来源,这些权力对于治理来说至关重要。葛兰西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仅仅是政治社会,在政治社会之外还存在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拥有道德和智识上的领导权。要想顺利实施治理,除强制权力之外,必须发挥文化霸权的作用。福柯指出,不能把权力局限于国家机器、把它看作是唯一的权力工具,国家不是所有组织的权力源泉,现实中每个个体都拥有一定权力,都是权力运行的载体。“不仅要追踪以政府形式出现的权力,还要追踪亚政府形式或超政府形式出现的权力。”①[法]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36页。“所有不直接经过国家机器的权力机制和效应……在维护国家方面比国家自身的机构更为有效。”②[法]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176页。这意味着,治理除依靠传统的国家力量外,还要借助于微观权力,这些权力的作用比国家机器还要大。但是,福柯与葛兰西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对微观权力的规定也不相同。
因处在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葛兰西继承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传统,从政治和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来规定微观权力。在葛兰西看来,微观权力就是市民社会的权力,但这里的市民社会不是马克思时代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而是基于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建立起来的文化活动,即“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包括学校、教会、文化机构等。这些活动构成了政治国家之外的伦理国家。据此,葛兰西提出“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即强制力量保障的霸权”。③[意]葛兰西著,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狱中札记》,第217页。葛兰西这里所说的“强制力量”是宏观层面的政治权力,而他所说的“霸权”是微观层面的文化权力。列宁在俄国革命中使用过霸权概念,强调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结盟,发挥工人阶级对农民阶级的政治领导作用。但列宁的霸权概念指的是宏观层面的政治权力。葛兰西提出霸权概念最初受到列宁的影响。1926年在讨论南方问题时,他首次使用霸权概念,指的是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结成联盟。随后霸权被他赋予独特的内涵,不只是指政治上的领导,更多的是强调文化上的领导。他认为,无论对暴力手段的垄断,还是生产地位上的优势,都无法解释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在思想上的认同,这种认同只能被理解为由精神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力量所导致的。这种力量在西方的市民社会中获得了自己的基础,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必须先在市民社会行使领导权,在掌权后也必须继续实行领导权。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发挥领导作用,只能依靠强权直接统治,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失去了维护政治地位的力量。在他看来,“阶级冲突的真正战场不在别处,而在于是否有能力提出一种独立的、广为传播的世界观”。④[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主编:《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第113页。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暴力与文化的关系,即在强制的政治权力与软性的文化霸权之间,前者是工具性的,后者更具有根本性。这样,葛兰西就把政治问题与文化问题加以融合,把意识形态作为治理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和手段。对意识形态的治理,就是对人的治理,而无产阶级政党治理意识形态的路径,就是一方面创造出改造社会的集体意志,另一方面制定和传播新的世界观,把被领导者团结和聚合在自己周围,开辟了西方文化政治的理论取向与实践道路。
与葛兰西不同,福柯生活在一个反人道主义的时代。受他的老师阿尔都塞的影响,福柯对意识形态持拒斥态度,把意识形态斗争称为“虚假的政治化”。⑤[法]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90页。他反对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理解治理,否定那种旨在通过扭曲个人信仰而实施对人影响的意识形态权力观。①和磊:《葛兰西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3页。对他而言,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政治经济学,都不应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理解,而应从人的生命权力的角度来理解。在他那里,微观权力不是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而是人的生物性的生存权力,即身体的生命。基于此,他提出了生命权力的概念,指出:“权力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压抑。权力压抑自然,压抑本能,压制阶级,压制个人”②[法]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190页。,“在权力网络所及之处,正在形成的我不认为是意识形态。……我认为更多的是知识形成和积累的实际工具。”③[法]福柯著,钱翰译:《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7页。在1978年“安全、领土与人口”系列课程上,福柯明确提出,所谓生命权力,就是将构成人类的基本生物特征纳入政治分析和权力分析,“把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本生物特征重新纳入考虑”。④[法]福柯著,钱翰、陈晓径译:《安全、领土与人口》,第3页。他认为,权力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系列机制和程序。他提出法律、规训、安全配置三种权力机制,其中安全配置是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这是与统治权模式完全不同的权力布局,自由是安全机制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这就把自由纳入权力技术的范围中去理解,权力被理解为让每个人自由运转而进行的一种调节。人口最早用来指人口繁殖运动,后来众多的人口被认为是统治者力量的体现,重商主义者认为它是国家和统治者力量的源泉,而重农主义更看重人口的自然性。在功利主义看来,由于人口具有自然的欲望动机,可以通过欲望来产生集体利益,不应限制欲望,而应刺激和鼓励欲望。正是从这种立场中,福柯发现了人口治理的可能性。他反对从法律主体的角度来定义人口,认为不应根据地位、住所、财富、职务等区分人口,指出:“人口就是这样一个延伸广阔的东西,从物种的生物学本源直到通过公众的概念所提供的可控制的外形。”“现代政治问题是完全与人口紧密相连的。”⑤[法]福柯著,钱翰、陈晓径译:《安全、领土与人口》,第94-95页。在他看来,人口是现代权力机制的对象,它重塑了权力技术与知识类型,成为治理的目标和手段。与君主统治相比,治理越来越具有优势,变得比统治更加基本。所以,福柯眼中的治理其实是对人的生物生命的管理,就是生命治理。⑥何萍:《风险思维与21世纪的生命政治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1期。
联系时代的变化来分析福柯与葛兰西对微观权力的不同说明,我们看到的是治理对象和治理内容的变化,即现代治理已经由对人的政治的、社会的生命的治理进入到了对人的生物生命的治理。
三、政党和知识分子能否承担起治理主体的责任
治理的主体,是治理理论中的又一个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葛兰西把政党和知识分子作为治理的主体,强调政党和知识分子的先进性,而福柯则对治理的主体,尤其是对政党持批判态度。这两种观点看似对立,在其背后却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这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国家的极权主义,强调治理的目标是使人获得自由。
葛兰西把政党和知识分子作为治理的主体,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议会选举、政党轮流执政等制度时,强调“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0页。,国家越来越变成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工具,“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即使像美国等民主共和国,“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他们提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4-55页。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作为治理主体的意义,认为无产阶级是历史上的进步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成为治理的主体,才能实现人的自由。葛兰西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但他不是在社会地位的意义上定义无产阶级,而是在文化批判的意义上定义无产阶级。所以,在谈治理的主体问题上,他没有采用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概念,而采用了历史集团或社会集团的概念。他指出,“现代君主也是神话的君主,他不可能是真正的人或确定的个体。他只能是一个有机体,一个复杂的社会要素……那就是政党”。①[意]葛兰西著,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狱中札记》,第92页。在这里,他明显受到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影响,借用了《君主论》的核心概念,尽管当时意大利确实是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但此处的“现代君主”并不是指现实中的国王,毋宁说,它是对治理主体的一种象征性隐喻。在他看来,每一政党都是某个社会集团的代表,代表相应社会集团的利益。“阶级产生党派,党派组成国家和政府的人手,即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领导。”②[意]葛兰西著,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狱中札记》,第183页。这就是说,政党是与市民社会相联系的,它行使的是领导的权力。政党在行使领导权力时,通过新世界观和思想体系去教育广大群众,组织起人民的民族的集体意志,从而推进社会革命等重大政治行动。但是,政党不是直接地行使市民社会的权力,而是通过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来行使这个权力。他说:“某些社会集团的政党不过是它们直接在政治和哲学领域而非生产技术领域培养自己有机知识分子范畴的特定方式。”③[意]葛兰西著,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狱中札记》,第10页。在这里,葛兰西厘定了政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政党的基本职能是培养有机知识分子,并通过自己培养的有机知识分子去领导和组织市民社会的活动,将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上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使治理由理念变成现实的活动。
如果说葛兰西是通过对无产阶级政党和有机知识分子的历史主动性来说明治理主体的责任,那么,福柯则是通过批判政党来说明治理主体的责任,这主要是受到了阿尔都塞的影响。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在于它被赋予一种结构和功能,“主体”是被意识形态构造出来的,“意识形态把个人呼唤或传唤为主体”。④[法]阿尔都塞著,陈越译:《哲学与政治(下)——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7页。受这一思想影响,福柯并不关注治理的主体问题。他指出:“我确实相信不存在独立自主、无处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体。我对那样一种主体观持怀疑态度甚至敌对态度。”⑤[法]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15页。在他眼中,主体建立在特定文化氛围的基础上,不存在拥有自主权力的主体。重要的不是“谁拥有权力”的问题,而是“权力如何运作”的问题。没有人是永远的权力主体,主体只是由权力关系构建出来的。权力结构比权力主体重要得多,权力机制内在于生产关系、家庭关系、性关系等关系中,与它们构成互为循环的因果关系,由此治理表现为治理子女、治理家庭等多种形式,这些治理形式与国家治理在内在根据上是相通的。与这一观点相联系,福柯对政党持批判态度,是因为他看到了西方国家政党出于自身利益相互倾轧,造成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为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提供了条件。据此,他认为,把政党作为治理的主体,是西方国家治理体制的失败。他强调“我们开始进入政党领导的政府统治的时代,这是要冒风险的,对此我们切不可疏忽”。⑥[法]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42页。极权国家和法西斯主义是对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自身功能的弱化,其根源不在于国家机制的内部,而应该从非国家的治理术方面,也就是到政党的治理术方面去寻找。他把政党称之为“非同寻常的、非常奇怪的、非常新颖的组织方式”⑦[法]福柯著,莫伟民、赵伟译:《生命政治的诞生》,第254页。,指出政党的治理化不是加强国家治理,而是会弱化国家治理。因为随着西方政党制度的成熟,国家权力逐渐被政党所掌握和垄断,权力的重心逐渐由国家转到政党手中,政党事实上成为国家治理的决策者和操纵者。
对比福柯和葛兰西对治理主体的态度,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治理需要政党和知识分子,但政党和知识分子能否承担起治理的责任,则取决于政党和知识分子的性质,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有机知识分子是能够承担起治理的责任的,而腐败的政党和传统的知识分子是不能够承担起治理的责任的。
四、治理的未来图景:“治理有方的社会”与自由主义社会
治理的未来图景,实际上是有关治理方案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福柯和葛兰西一样,都采用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方法,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经验原型,提出他们的治理方案。但是,由于他们选择的具体的经验原型不同,所以,他们提出的治理方案也不相同:葛兰西选择的经验原型是处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环境下的意大利,他提出的治理方案是如何走向“治理有方的社会”①[意]葛兰西著,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狱中札记》,第212页。;福柯选择的经验原型是处于新自由主义环境下的德国和美国,他提出的治理方案是如何完善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对比这两种治理方案,对于我们认识资产阶级国家的治理现状,思考当代全球治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葛兰西提出“治理有方的社会”,是对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一种批判性反思。在葛兰西看来,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究其客观原因,在于它的国家结构不同于俄国的国家结构。俄国的国家结构是典型的东方社会的国家结构,这种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国家就是一切,国家等于政治社会。这种国家结构使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能够直接击中国家的政治社会,获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与之不同,意大利虽然在经济上落后于英、德、法等国,但在国家结构上,还是属于西欧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不同于俄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市民社会得到充分发育,并已经演变为更加复杂的结构,成为与政治社会相互补充的国家形式。这样一来,市民社会就成为一种能够抵御经济危机等直接经济因素冲击的力量,就像“现代战争的堑壕配系”一样,“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②[意]葛兰西著,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狱中札记》,第193页。意大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因为受到了这个强大的堡垒和工事的阻碍而不能直接击中意大利的政治国家,而遭到了失败。由此决定,意大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不能走俄国暴力革命的道路,而应该走一条首先进行文化革命,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和其他阶级的领导,然后再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建立起苏维埃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前景就是走向“治理有方的社会”,即马克思所称的共产主义。在这一分析中,葛兰西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结合起来,建构了考察国家演变的三个维度:过去讲的是传统国家,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国家等于政府,国家等于政治社会的阶段,后来阿尔都塞把它称之为镇压性国家机器;一个是现在的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国家等于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完整的国家”,用阿尔都塞的表述就是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国家;一个是未来国家,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治理有方的社会”。这三个维度既是历史的,也是结构的。说它是历史的,是指国家从最初的强制性组织,到最后趋于消失,专制和强迫干预的因素越来越少,而精神的、伦理的、文化的因素不断增加,直到最终政治社会融入市民社会,表现为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说它是结构的,是指以“治理有方的社会”为标准来对当下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治理展开批判。葛兰西借用拉萨尔的“自由国家”和亚当·斯密的“守夜人”国家概念来定义“治理有方的社会”,指出“治理有方的社会”才是真正达到“国家成为守夜人”的阶段,进入“根本自由的时代”。③[意]葛兰西著,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狱中札记》,第218页。这是马克思所定义的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社会虽然目前还没有到来,但是它作为解决资产阶级国家治理问题的方案,对于现代国家和国际秩序的治理起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葛兰西的治理理论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治理理论。也正因为如此,才得到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传播,成为各国思想家分析当代国际政治、批判国际霸权主义和大众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
与葛兰西相比,福柯提出的“自由主义社会”的治理方案只具有认识论的意义。说它是认识论的,是它只是在过去和现在两个时间维度上反映西方治理术的演进。在福柯看来,当代的治理观念来自基督教牧领制度,教会牧领建立了完整的指导、控制、操纵人的权力体系,其核心是对人的灵魂进行治理,“必须在这个方面才能找到治理术的源头、形成和建立之处,找到它的胚胎”。①[法]福柯著,钱翰、陈晓径译:《安全、领土与人口》,第143页。在15、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出现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和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矛盾不断加深,治理越来越成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对灵魂的治理逐渐过渡到对人的政治治理,经济和舆论成为与治理相关的两大现实场域,出现外交-军事技术和“治安”(police)两套新的治理技术。对于福柯而言,治理呈现出反本质主义的倾向,它是力量关系的布局,重在保持平衡的力量关系。18世纪治理从基于国家理由的治理技术过渡到基于自然现实的自由主义,社会、经济、人口、安全、自由成为治理术的新元素。自由主义关心的根本问题是“在一个由交换决定了物品的真实价值的社会中,治理及其所有的治理行为,它们的效用价值是什么”。②[法]福柯著,莫伟民、赵伟译:《生命政治的诞生》,第61页。这种治理需要自由也消耗自由,既产生自由又限制和摧毁自由。人们采取经济干预主义来保障民主自由,在自由主义危机的基础上发展出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德国新自由主义确立市场经济作为国家的原则,通过市场经济来改造国家和控制国家,“应该为了市场而去治理,而不是因为市场而去治理”。③[法]福柯著,莫伟民、赵伟译:《生命政治的诞生》,第166页。美国新自由主义把劳动纳入经济学分析,提出人力资本理论,打破了资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同时利用市场经济来分析破解一切非商品关系,以成本和利润来评判所有公共活动,创造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模式。总体来看,无论是基督教牧领制度,还是16、17世纪国家理论,或是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根据福柯的观察,当一种治理术面临危机时总能根据需要产生出新的治理术,但他并不认为这个过程可以无限下去。他指出,从18世纪直到现在都是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时代,虽然自由主义曾经面临危机,但是在自由主义基础上产生的新自由主义挽救和发展了自由主义。尽管他强调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不是一回事,但谁也不能否认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而产生的。他认为不存在社会主义的治理术,社会主义只能嫁接到自由主义治理术上,“在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内部以及在与其嫁接中生长并且切切实实发挥了作用。”④[法]福柯著,莫伟民、赵伟译:《生命政治的诞生》,第116页。这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福柯虽没有像福山那样明确表示历史将在自由主义中终结,但从字里行间能看出,他所设想的治理其实就是自由主义治理。然而,2007-2008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连续不断地爆发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战争危机和公共健康危机证明,福柯的“自由主义的社会”治理方案既不能使人类走出当下的危机,更不能解决他所主张的生命治理问题。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福柯的治理理论中有价值的内容。福柯提出生命政治学,要求把人口、人的生物生命的生存权力纳入治理的范围之内,是我们建构当代治理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问题是,我们不能像福柯那样,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下来谈生命的治理,而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的框架下来谈生命的治理。在这一方面,葛兰西的治理理论应该成为当下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政治学的重要思想资源。这就是本文对比研究葛兰西的治理理论与福柯的治理理论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