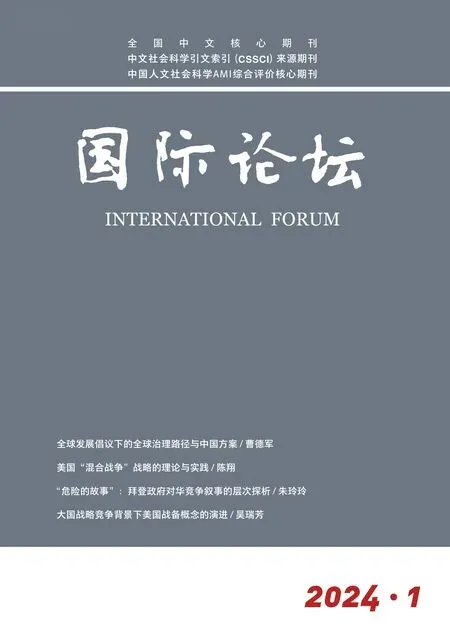全球发展倡议下的全球治理路径与中国方案*
曹德军
【内容提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与能力显著提升。在全球治理的格局转换阶段,中国具有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意愿,全球治理的中国时刻正在到来。传统的霸权稳定论回避了霸权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负面功能,忽视了新兴大国主动供给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动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丰富实践,反驳了霸权稳定论与“金德尔伯格陷阱”叙事逻辑,为建构新兴大国的全球治理新路径提供了坚实支撑。全球发展倡议的普惠发展模式超越了“南北发展援助”模式的局限,既是对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全球提升,也是中国“南南发展合作”的最佳实践,有助于建设性促进国际发展多边机制提质升级。长期以来,多层次、有步骤、凝特色的中国外交实践,诠释了全球发展倡议的普惠包容理念。中国秉承“授人以渔”的内源性发展哲学,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援助、分享发展模式与经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智慧”致力于寻求最大共识,秉持增量改进原则,以亚投行为依托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升级扩容、以全球数字治理为抓手进行模式创新,塑造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力。
全球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是为全人类做贡献、谋福利的过程,作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发展经验为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繁荣提供重要借鉴。①《中国式现代化为他国发展提供借鉴——访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阮春强》,新华社,2022 年10 月27 日,http://www.news.cn/world/2022-10/27/c_1129082473.htm。展望“两个一百年”战略蓝图,创造性供给全球发展治理的中国方案,既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所谓“达则兼济天下”,强起来的中国希望用自己的成功发展模式,为解决全球难题贡献特殊力量。当今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怎么办,成为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新时代之问。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需要进一步将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经验与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以超越传统不平等的全球发展体系。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后发赶超之路,这些不平凡的发展道路积累的独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经验,是支撑新时期全球发展倡议的关键。
化解新时期全球治理困境,需要创造性供给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自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治理格局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趋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②习近平:《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448—449 页。在此背景下,2021 年9 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中国创新性参与全球治理开辟出新路径。全球发展倡议有助于实现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仅对解决当前国际难题具有现实针对性,而且更从长远的战略角度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提出的国际公共产品,对促进人类整体的永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本文基于中国外交实践,提炼中国发展经验对国际发展的理论意义与启示,回应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叙事,为构建中国特色全球治理理论奠定基础。
一、中国发展路径超越“金德尔伯格陷阱”
在全球治理领域,新兴国家如何供给国际公共产品是一个重大的现实与理论议题。当新兴国家崛起,大国权力竞争将塑造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政治基础。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提出“霸权稳定论”,认为供给全球治理方案是大国霸权的基础。①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p. 307; 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5, No.2, 1981, pp.242-254.他指出,20 世纪30 年代衰落的英国缺乏全球治理能力与意愿,而新兴大国美国则推卸全球治理责任,从而引发国际秩序危机。②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p. 307; 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5, No.2, 1981, pp.242-254.基于此,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指出,如果新兴大国不能扮演全球治理的“稳定器”角色,那么国际秩序必将导向混乱,从而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③Joseph S. Nye, “The Kindleberger Trap,” April 1, 2023,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china-kindleberger-trap-by-joseph-s--nye-2017-01?barrier=accessreg.这种历史类比逻辑认为,若美国缺乏能力且中国缺乏意愿来承担21 世纪全球治理责任,那么国际秩序必将陷入危机。④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29—1939 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洪文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第12—20 页。该论点将全球治理责任推卸给新兴大国,不仅有失公平而且有违事实。
(一)反思“金德尔伯格陷阱”叙事
“霸权稳定论”视角突出霸权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正面功能,却忽视霸权国的负面作用。⑤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p. 9.历史经验表明,当新兴国家的实力开始接近霸权国时,权力转移带来的敏感焦虑,很可能让霸权国成为国际稳定的破坏者,通过组建权力联盟压制与破坏新兴国家供给的国际公共产品。⑥Benjamin J. Co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73.即便霸权国单方面供给国际公共产品,这也并非仁慈施舍,而是维持国际领导地位与霸权优势的政治手段。面对潜在的战略竞争者,霸权国完全有可能将国际公共产品私有化,建立排他性的消费门槛,或利用其他国家的不对称消费依赖进行剥削、压制或威胁。⑦Stephen D.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28,No.3, 1976, pp.317-347.由此,当相对衰落的霸权国无力继续供给国际公共产品,却又不允许新兴大国供给时,就会产生一种逆向的“金德尔伯格陷阱”。换言之,是霸权国对新兴大国的压制,而非新兴大国的不作为,引发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赤字。
第一,霸权国并非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全能冠军。即便霸权国拥有结构性的权力优势,但并不能在所有议题上具有供给优势。随着国力或竞争态势变化,公共产品的数量与质量都可能发生改变。有些由霸权国供给的国际公共产品不仅不能发挥公益作用,有时甚至会破坏全球协作,成为公共危害。例如“北约”与美国的亚太联盟网络在冷战期间发挥了所谓的“均势制衡”功能,但是在冷战结束后则成为霸权的私有物,变成干涉打压他国的工具,制造区域动乱与冲突,其原本维护和平的公益性质发生异变。随着霸权国的合法性衰落,其他国家可能联合绕过霸权国集体供给公共产品,降低对霸权国的战略依赖。
第二,霸权国会转嫁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成本。霸权稳定论指出,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本与收益是不成比例的,大国需要“照顾”他人和“牺牲”自己才能供给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但霸权国的供给动机会随时间而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免费乘车者期待其供给更多更优质的公共服务,霸权国也不堪重负。在还没有出现真正的挑战者之前,霸权国往往通过分享权力,让两个或更多的国家共同分担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成本。例如,在冷战中后期,美国面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危机。为了缓解战略压力,美国允许德国和日本扮演稳定全球货币的领导角色,与之共同维护西方世界经济稳定,最终逐步扭转西方阵营的经济衰退局势。可见在霸权衰落之后,霸权国依然可以利用国际制度分摊合作成本。①参见:Jonathan Kirshner, American Power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4; Helen V. Milne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eyond Hegemonic Stability,” Foreign Policy, Vol.110,No.1, 1998, p.112。
第三,霸权供给模式并非国际关系史的主流。霸权稳定论假设“世界经济要稳定,就必须有一个稳定者”。但20 世纪30 年代的历史教训表明,霸权国有时难以扮演世界经济与金融稳定的“稳定器”角色。②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305.实际上真正由霸权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时间并不长,主要集中在1890 年至1910 年英国的金本位制与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如果着眼于长时段,可以看到国际关系主流是“无霸权”时代,例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与凡尔赛体系是多极协调的产物。而且历史上,霸权国的存在本身就增加了全球治理的成本,诸多国际系统的弊端有时恰恰是霸权国造成的。综上所述,新时期的全球治理需要跳出英美崛起经验,反思霸权稳定论与“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叙事逻辑,重视新兴大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
(二)全球发展格局下的中国能动性
在全球治理的格局转换阶段,新兴大国具有充分的治理能动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丰富实践反驳了霸权稳定论与“金德尔伯格陷阱”叙事逻辑,为建构新兴大国供给模式提供了坚实基础。“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关键不在于新兴国家是否愿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在于国际社会特别是霸权国是否相信与允许新兴大国承担全球公共责任。中国具有强烈意愿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经验,也注重区分不同的国际发展需求领域,结合自身比较优势,形成多层次、有步骤、显特色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路线图。这种独具特色的全球治理方案赢得了国际社会认可,以实际行动超越了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中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能动性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基于强烈的全球责任感,吸引他国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逻辑认为,由于缺乏国际强制力量,各国更倾向于“搭便车”而非主动提供公共产品,这将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①吴志成、李金潼:《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视角与实践》,《政治学研究》2014 年第5 期,第111—124 页。但实际上,中国反复表示愿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2014 年7 月,习近平主席承诺“我们将更多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②习近平:《推动中拉关系实现新的更大发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311—312 页。在11 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③习近平:《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448—450 页。供给国际公共产品让他国消费,将有助于增加国际社会对供给者的认可与信任,这构成了国际领导力的合法性来源。基于五千年的光辉历史、新中国70 多年的奋斗历程、40 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奇迹,中国有强烈的全球大国担当。因此,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论忽视了新兴大国强烈的国际责任感与政治抱负。
第二,立足比较优势,供给“最佳”方案。担任国际领导者角色不仅需要雄心和意愿,还需要有承担全球责任的能力。从供给路径看,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是多元的,美国学者杰克·赫什利弗(Jack Hirshleifer)等人总结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四大模式,即累积加总、权重加总、最佳供给与最弱链接。④Jack Hirshleifer, “From Weakest-link to Best-Shot: The Voluntary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Public Choice, Vol.41, No.3, 1983, pp.371-386.其中,“最佳供给”模式由最大贡献者的努力决定,允许和默认其他国家“搭便车”。尽管霸权国具有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实力,但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可能难以赢得合法性认同。例如,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阻碍中国供给新型国际公共产品,拜登政府提出“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计划与“重返更好世界倡议”(B3W),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中国展开竞争。①毛维准、戴菁菁:《对冲“一带一路”:美国海外基建“蓝点网络”计划》,《国际论坛》2021 年第5 期,第55—75 页。这种零和竞争的霸权压制行动不仅违背国际社会对中美合作的期待,而且也会降低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因为中国的治理方案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充满吸引力,也符合国际社会对优化全球治理格局的期待。
第三,保持战略远见与创造性介入,提升中国方案的认可度。供给国际公共产品是展示领导红利、吸引他国支持与认可的重要方式。领导者的贡献只有被国际社会认可时,才能产生影响力。换言之,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不是简单的物力与财力的投入,而是一个关于角色、期望和观念的塑造的过程。中国的全球治理展现出创造式领导力特点。这是一种面向未知挑战的领导力,领导者能够打破常规,为群体成员带来新的发展思路或供给新的公共产品。富有创造性的领导者秉持有远见、有激情、有动力的领导风格,以共享、互惠的方式将不同国家整合起来,为全球命运与公共事业持久奉献、供给符合国际发展所需要的新型公共产品。②Robert J. Anderson et al., Scaling Leadership: Building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and Capacity to Create Outcomes that Matter Most, London: Wiley, 2019, pp.5-10.以认可度为前提,中国的全球治理蓝图展示出基于相互尊重、和谐包容和共商共建共享的愿景,致力于扩大现有国际体系的包容性。2017 年1 月,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系统阐述了摆脱全球治理困境的新理念。③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37—540 页。基于广泛的共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当年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为全球治理奠定新的规范基础。
由上可知,“金德尔伯格陷阱”的责任在于霸权国而非新兴大国。霸权国的战略疑虑和压制,导致新兴大国的供给潜力难以充分释放,最终形成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缺位。新兴大国不仅要考虑全球社会的治理需求,还需要顾及霸权国的感受与反应,在这种平衡过程中新兴国家的供给能力与意愿会受到一定制约。但鉴于新时期全球挑战加剧、全球治理赤字加剧,中国不失时机地供给新型国际公共产品,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选项,有助于超越西方国家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叙事逻辑。
二、全球发展倡议下的普惠包容发展新模式
当前全球治理的重大挑战之一是南北发展失衡,解决发展质量差异、跨国阶层不平等、公有和私有财产分化严重失衡等问题,需要探索全球普惠发展模式。基于“共同富裕”试验区经验与全球南南合作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多层次发展经验为普惠发展提供新思路。长期以来,西方价值观主导的当代国际发展援助面临发展目标异化问题,部分西方国家将援助与政治挂钩,使援助沦为一种政治利益交换的工具。与传统援助模式不同,中国引领推进的新南南合作模式关注自我增长与发展赋能。随着中国在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其彰显出的发展理念、对外援助模式和路径独具特色,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秉承“授人以渔”理念,中国的技术援助、发展模式和经验分享,将为南方国家带来摆脱对发达国家依附困境的新机会。①Shaquille I. Gilpin, “China,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Aid System: A Challenge to (the Norms Underpinning) the Neoliberal World Order?”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58, No.3, 2023,pp.277-297.
(一)自主发展道路与能力建设
发展是实现民生改善的关键,发展合作是超越国界的公共产品。传统发展援助忽视了国家建设的独立性与主动性,而全球发展倡议则着眼未来,建立更可持续的自主发展能力。作为最具发展活力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未来设计与探索将深刻影响南南合作与南北关系走向。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一方面要提炼中国经验的知识体系,形成系统性的原创知识和叙事架构,为当下世界各国疫情后经济复苏重建提供理论支撑,诸如“要致富多修路”的基础设施实践,自由贸易区、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等经济特区发展模式,“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试验逻辑等。另一方面应创造性地将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经验与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以超越传统不平等的全球发展体系;立足新南南合作平台,建构全球发展伙伴网络。例如在全球农业、减灾、扶贫等领域,突出特色,发挥倡议构想者与方案起草人作用、切实推进全球发展援助理念与体制的优化改革。
“授人以渔”的内源性发展哲学,成为中国帮助南方国家进行自主发展的核心原则。任何外部激励都需要经过自身内因转化,促进内源性发展,才能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2011 年中国发布的第一份对外援助白皮书将“南南合作”视为援助的核心,通过积极分享中国知识与经验、促进技术转移与资金合作,实现对方国家的自力更生和全球发展能力建设。2021 年中国发布第三份对外援助官方白皮书,第一次使用“国际发展合作”取代传统的“对外援助”,修正和拓展了西方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概念,更加重视南南合作的新模式,促进援助、投资与贸易三者有机结合,实现更加平等多元的国际发展合作机制。①中国发布的三份对外援助白皮书,参见:《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 年4 月),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1 年4 月21 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11-04/21/content_2615780.htm?ivk_sa=1024320u;《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 年7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4 年7 月10 日,http://www.scio.gov.cn/ztk/dtzt/34102/35574/35582/Document/1534198/1534198_2.htm;《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2021 年1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21 年1 月10 日,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44691/Document/1696699/1696699.htm。进入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参与对外援助主体的多元化,对外援助治理模式逐渐从传统的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垂直管理模式转变为纵横交错的多元主体互动模式。②于浩淼、徐秀丽:《“双轨制+”:中国农业多边对外援助治理结构探索》,《国际展望》2020 年第4 期,第132—148 页。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双向互助,体现了“发展合作”的平等性、互助性、互利性。2018 年中国成立“国际发展合作署”没有用“对外援助署”命名,体现了对受援国的平等地位与国家尊严的关切,致力于全面提升国际发展合作质量。当前,中国发起了众多重大国际公共产品倡议,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非发展基金、南南发展基金、丝路基金与“一带一路”倡议等。以全球普惠发展为目的,传统援助、对外直接投资、主权财富基金、出口信贷、基础设施贷款,都可以成为新型国际发展合作的工具。对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而言,找到潜在比较优势并通过产业规划和基础设施投资来激发与启动深度结构转型,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发展。
全球发展倡议包含的普惠发展模式,避免了西方国家的南北援助模式存在的不平等局限。传统援助模式展现出的是居高临下的“垂直范式”,使得援助国与受援国存在不平等的施舍关系,北方和南方国家的地位存在明显差异。中国探索的新型援助模式,则是南南合作的互惠互利援助,更具有“水平范式”特点,关注和尊重被援助国的心理感受与主权独立。③庞珣:《新兴援助国的“兴”与“新”:垂直范式与水平范式的实证比较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5 期,第31—54 页。换言之,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援助忽视内生因素,依靠外部力量主导的援助模式会造成不对称依赖,损伤受援国的独立自主发展能力。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白人的负担》一书中曾指出,发达国家在提供发展援助时给受援国带来巨大的成本压力,导致援助的效力降低。①参见威廉·伊斯特利:《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总是收效甚微》,崔新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年。与西方传统的援助理念不同,中国始终坚持以自力更生作为立足点,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将“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目前中国政府正式发布的三份白皮书(2011、2014、2021 年)对中国外援助及国际发展合作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其中展示的国际发展合作理念致力于突破传统模式的局限,注重对援助过程与合法性认同的意义,促进国际发展话语从援助有效性向发展有效性转变。②Jonathan R.W. Temple, “Aid and Conditionality,” in Dani Rodrick and Mark Rosenzweig, eds.,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5, Amsterdam, Oxford: Elsevier, 2010, pp. 4415-4523.
概言之,发展是全球南南合作的核心目标,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为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发展知识分享提供了新思路。进入21 世纪,南方国家迅速崛起,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发展的经济社会结构。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与南北垂直差异的发展经验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南方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发展制度的重要性,发起了新南南合作模式。③南南合作金融中心:《迈向2030: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角色变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30—31 页。作为全球南方最大的国家,中国长期扮演全球南方国家与全球北方国家之间的“桥梁”,扩大和深化全球技术与知识转让。中国传授国际发展知识,在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和权利平等的基本原则下与南方国家开展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经验传递
历经百年艰辛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超大人口规模社会的第一次现代化,是共同富裕与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国家与国家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为人类历史文明提供了新选择。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大坐标中,方可发现其独特的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意义。全球发展治理创新离不开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最佳贡献,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方案的期待不断上升。中国式现代化很好地诠释了自力更生与合作发展的关系。“发展是硬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要解决的不仅仅是14 亿人口的善治问题,更需要将全球问题引入地方试验区,探索未来人类发展的新模式。在全球治理的国际发展领域,中国丰富的发展合作实践经验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提供重要参考。④FAO 组:《中国设立第三期中国—FAO 南南合作信托基金》,农业农村部,2020 年9 月25 日,http://www.moa.gov.cn/xw/bmdt/202009/t20200925_6353306.htm。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为完善全球治理供给新方案。新时期全球挑战加剧、全球治理赤字加剧,中国式现代化有意识地嵌入全球普惠发展机制之内,通过内嵌式发展进行“增量改进”。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权力转移进程加快,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开始顺应时代需求,尝试构建普惠包容的发展新模式。新时期中国创造性地通过构建亚投行、丝路基金、“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世界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通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升级扩容,打造周边安全共同体,增强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融资与第三方合作,凝聚新兴经济体的力量;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做出重要贡献。当前,中国成立了各种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例如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家文创实验区、国家传统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一带一路”综合改革开放试验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都致力于中国经验的累积与全球多元发展路径的探索。
第二,促进国内国际发展相结合,探索全球发展新规则。从国内规则角度探索未来全球发展新方向,其中创建贴近国情的政策试验田就是一种独特的实践智慧。2013年3 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在上海建立自贸区的设想,表示“要用开放扩大内需,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①鲁楠:《“改革促进开放”抑或“开放倒逼改革”》,《文化纵横》2013 年第6 期,第74—76 页。这是国务院第一次提出建立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方略。随后国务院公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关注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有机结合,其强调的指导思想是:“紧紧围绕国家战略,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先行先试,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2017 年3 月31 日,国务院印发了《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上海自贸试验区进入2.0 时代。方案提出,要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要服务全国改革开放大局,形成更多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②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的通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7 年3 月30 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7-03/31/content_5182392.htm。从制度创新上看,经济特区试验是孵化具有中国经验与实践特色的改革发展模式,根据自身国情为全球治理探索有效方案。③郑永年、王璐瑶:《全球经济新规则下的自贸区试验》,《文化纵横》2013 年第6 期,第60—67 页。
第三,突出比较优势,发掘与激发自主发展潜力。中国发展实践表明,立足自身国情建立特殊经济功能区,有助于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协助增强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塑造能力,挖掘发展潜力。中国的工业园区发展经验,有助于培育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力。例如,被誉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明珠”的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通过信息分享、项目支持推进能力建设。①Ana Cristina Alves and Celia Lee, “Knowledge Transfer in the Global South: Reusing or Creating Knowledge in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Ethiopia and Cambodia?” Global Policy, Vol.13, S.1,2022, pp.45–57.自21 世纪初以来,中国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模式开始“走出去”,在“一带一路”倡议规划下建设经济走廊,成为南南合作的新平台。例如,埃塞俄比亚东部工业区(EIZ)和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SSEZ)就是中国智力援助的新代表。这种局部试验区合作,不仅可以展示中国发展经验,而且有助于渐进式地让受援国提升自主发展能力。此外,在合作路径选择上,中国不断搭建“1+N”集体磋商与合作平台,诸如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17+1”合作机制。②罗建波:《中国对外援助模式:理论、经验与世界意义》,《国际论坛》2020 年第6 期,第39—63 页。以全球普惠发展为目的,中国发起了众多重大国际公共产品倡议。
基于“自力更生”实践哲学与“授人以渔”内源发展理念,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更注重知识积累与经验传递,以自主发展为最终目标。2015 年9 月,中国宣布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 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 年后发展议程。此外,为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与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7 年5 月,中国向“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提供20 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 亿美元,在共建国家实施100 个“幸福家园”、100 个“爱心助困”、100 个“康复助医”等项目。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2020 年12 月),2020 年12 月21 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0-12/21/content_5571916.htm。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基础,很好诠释了自力更生与合作发展的关系,为南方国家树立了典范。④FAO 组:《中国设立第三期中国—FAO 南南合作信托基金》,农业农村部,2020 年9 月25 日,http://www.moa.gov.cn/xw/bmdt/202009/t20200925_6353306.htm。
三、完善与创建国际发展的新型多边机制
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了推进国际发展目标的机构框架,该框架以联合国安理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政治机构为支撑,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最初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简称IBRD)两大国际金融机构为抓手。国际发展机制的建立对新独立国家的发展给予了制度性支持。然而进入后冷战时代,传统国际机构有较强的路径依赖与发展滞后性,在应对新的全球治理挑战中往往捉襟见肘,灵活性与前瞻性不足。新兴国家的发展经验需要被吸纳进国际多边机制中去,全球发展治理也需要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多元模式。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世界政治意义在于,跳出冷战时期的“东西”秩序之争与“南北”秩序之争,对国际发展的多边机制进行了建设性的完善升级。
(一)传统国际发展制度的局限
传统国际发展机制包容性不足。长期以来,国际多边发展机制反映了欧美国家的利益与价值观优势。自由制度主义学者指出,美国在自己建立的国际秩序中遵守国际制度的约束,通过供给具有全球合法性的公共产品,换取其他追随国对其全球领导力的认可,因此传统的国际发展机制成为服务霸权国领导力的平台。①G. John Ikenberry,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4, No.2, 1998, pp.147–177; G. John Ikenber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3, 1999, pp.43–78.但是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反思,全球治理没有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尤其对新兴大国的包容性不足,削弱了传统国际发展机制的合法性。对此,中国、巴西与印度等新兴国家呼吁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要求进行国际机制改革,改革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机制的投票权重。②Phillip Y. Lipscy,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Policy Areas, Outside Options, and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9, No. 2, 2015, pp.341–356.为完善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额重新分配改革被提上日程,新兴国家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也促使全球治理的主要协商平台从八国集团转变为了二十国集团。③参见:Jeffrey M. Chwieroth, Capital Ideas: The IMF and the Rise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尽管部分西方舆论将中国倡议创建的亚投行视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竞争者,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并非“另起炉灶”。④Daniel W. Drezner and Kathleen R. McNamara,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Global Financial Orders and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11, No. 1, 2013, pp.155–166.传统国际发展机制存在显著的局限性,难以满足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诉求,也难以应对更加复杂多元的全球化现实。因此,关照全球普惠发展的诉求,对传统国际发展机制进行系统性反思与改革则成为新的时代趋势。
西方国际发展机制带有意识形态偏见。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国际制度网络,并将西方意识形态植入其中,形成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通过社会化劝说和社会互动传播美式价值观,建构了成员国的身份偏好。①参见:Peter J. Kazenstein, Robert O.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然而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的多元化趋势也强化了意识形态冲突。例如,国际体系中的自由主义含义是有争议的,关于什么是“自由”,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共识。欧美发达国家倡导的“自由主义”关注普遍的个人权利和开放的市场,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认为社会稳定与民生发展才是最大的自由,主权独立是个人人权的前提。意识形态竞争还体现在多边联盟和国际机制的建设过程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之初便承诺,在发展问题上对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秉持“不干涉原则”。因此与世界银行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相比,亚投行在发放贷款时并不将借款国的国内人权与民主状况与之挂钩,这种不干涉原则非常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②Erik Voeten, Ideology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1, pp.8-10.
传统国际发展机制成为霸权国私有化的政治工具。国际公共产品往往具有半公共性或半私有性特征,霸权稳定论的逻辑也常常成为霸权干预和压制他国的借口。“霸权稳定论”的前提是霸权国具有战略自觉,进行自我克制与约束,然而并非所有霸权国都有这样的战略自觉。在最极端情况下领导国家不仅会搭便车,还会制造全球公共危害。例如,美国是二战后在全球范围干预他国内政和制造战争最多的国家,尽管其借口为自由和民主而战,但实际上却展现出偏狭的地缘利益与单极傲慢。此外,美国也是二氧化碳排放累积最多的国家,其人均碳排放量常年居世界首位,甚至曾带头退出《京都议定书》。冷战后美国单边主义在中东、非洲等地加剧了族群内战与国际冲突,其长臂管辖与强制性制裁外交,也让不少国家从道义上批评美国的“强权主义”与盛气凌人的霸道干预缺乏合法性。例如,2022 年3 月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因俄乌冲突对俄罗斯采取制裁,部分国际公共产品沦为西方国家打击对手的权力政治工具,呈现私有化特征。“七国集团”将部分俄罗斯银行踢出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利用全球生产链优势对俄进行技术封锁,强制将部分国家排斥在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范围之外。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霸权国强制与威胁行动则会进一步伤害其全球领导力的合法性。
(二)中国供给新型国际发展机制
在冷战结束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全球发展治理的制度建设曾一度陷入停滞,有关国际发展机构的改革呼声不断。对于国际多边机制而言,吸纳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最成功的南方国家,是展示其合法性与包容性的重要方式。对于崛起的中国而言,嵌入国际主流机制平台是发挥比较优势、作出独特贡献的关键路径。因此中国倡议创建的新型国际机制与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之间并非对立零和关系,而是在合作共赢框架下完善与互补的共生关系。
其一,以渐进方式弥补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不足。推动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系统,是中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目标之一。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真正成为了国际公共产品的“核心贡献者”,创设了新型国际多边发展机制,展示了“增量改进”的可行性优势,同时用高标准的多边开发银行进行良性竞争与建设性补充。例如,亚投行更多聚焦基础设施,传统国际发展机构重点关注的知识银行、开放数据等暂时不是其关注重点;同时对成员国资格保持高度开放性,如亚投行的成员资格向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成员共同开放,而新开发银行的成员资格面向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开放,优势互补为全球治理的渐进改革和普惠包容奠定基础。
其二,专注基础设施比较优势孵化新型公共产品。新型国际发展机构高度重视治理的平等性。亚投行在既有国际机制基础上进行创新,随着新成员的不断加入而调整股权结构,使投票权更为平等,同时实现公共产品供供给的优势互补,避免与传统国际发展机构发生替代性竞争。①张春:《新型国际发展机构与新时代的全球发展治理》,《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 年第2 期,第118—128 页。在亚投行成立之初,习近平主席就曾指出“亚投行应该结合国际发展领域新趋势和发展中成员国多样化需求,创新业务模式和融资工具”。②习近平:《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上的致辞》,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年,第120 页。此外,“一带一路”倡议辐射区域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基础设施陈旧老化、道路交通不完善、电力供给不足、通信设施匮乏等问题。牛津经济研究院《全球基础设施展望》报告估计,2016 至2040 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94 万亿美元,而同期世界基础设施投资缺口达到19%。③Oxford Economics, “Global Infrastructure Outlook: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Needs 50 Countries,7 Sectors to 2040,” pp.3-4, https: //www.oxfordeconomics.com/publication/open/283970.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够帮助弱小的经济体更有效地参与一体化,补足网络中的薄弱一环。④保尔·科利尔等:《中低收入国家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探讨》,《世界银行经济评论》2016 年第3 期,第134—166 页。亚投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正为应对此类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与跨区域公共产品。①郑永年:《“一带一路”是可持续的公共产品》,《人民日报》2017 年4 月16 日,第4 版。
其三,以包容性发展模式升级全球治理体系。基础设施作为一项公共产品,其长期收益相对稳定可靠,着眼长远而言其产生的“溢出效应”会对整个区域发展产生显著的辐射带动作用。中国从一开始就希望亚投行成为一流的、具备21 世纪高治理标准的开放式开发银行。中国反复表示,亚投行并非仅仅服务中国国家利益,而是为所有成员国利益服务。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援助及贷款重点方向是社会平等、消除贫困、健康改善与绿色发展等,大多偏向“软性”发展因素。而亚投行的重点则聚焦于亚太基础设施、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等,相对关注“硬性”发展因素。亚投行致力于成为高标准、高质量、高起点的新型多边发展银行,为全球治理未来探索新模式。②何兴强:《龙之印迹:中国与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218—219 页。中国无意彻底改变全球秩序,甚至没有能力这样做,它旨在提供一条可行的发展道路,让全球南方超越西方模式限制,多一种发展选择。③Hong Liu, “China Engages the Global South: From Bandung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lobal Policy, Vol.13, S.1, 2022, pp.11–22.
概言之,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方案核心在于,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合作理念,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作为全球化受益者,中国希望提出包容性全球治理框架,普惠公正展示和谐的全球发展前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智慧”体现为,柔性引导与协调相关利益者关系,寻求各方最大共识;扩展开放合作的平台网络,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普惠全球。④《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新华社,2021 年11 月16 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四、数字时代的普惠发展与中国实践创新
数字平台通过创造新的全球市场,使全球化成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进程。全球数字化模式有助于全球发展更加包容均衡,数字信息跨界流动打破地理与时空界限,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微型跨国公司赋能。在数字经济时代,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合约等颠覆性技术,有助于在“去中心化”的全球治理行动中提供每个节点的参与度。①李彦等:《新时代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数字化技术创新理论研究》,《世界环境》2021 年第3 期,第68—70 页。面向未来,“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性逐渐提升,中国特色的全球数字公共产品的供给将为全球发展赋予新的动能。
(一)塑造全球数字普惠发展理念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为全球普惠发展提供新的抓手。作为全球数字大国,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竞争、合作与治理,不断提升数字领域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彰显数字经济治理的公平互惠原则,需要一方面弥合数字鸿沟,特别是要提升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技术水平,增加对落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援助;另一方面要推动建设更加包容开放的全球性数字经济规则,既兼顾数字经济发达国家的利益,也要尽量减少部分发达国家的高标准对发展中国家构成“发展壁垒”。当前中国积极促进数字时代的全球新基础设施建设,在“数字丝绸之路”框架内致力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和包容的全球化格局。
首先,积极引领全球数字规则制定。当前,世界大国争夺数字经济制高点的治理竞争,集中体现在网络基础设施供给以及不同治理理念模式的竞争。立足比较优势,可以尝试在有优势但缺乏国际标准的领域提出新标准倡议。2022 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加快建设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发展、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②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21 年12 月12 日,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671108.htm?eqid=aaec7d8b0001 34ba000000056458aaf3。通过建设数字“一带一路”,中国在战略性数字产业链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涵盖了互联网、电信、金融支付、大数据中心、海底电缆和云计算等。2015 年,第一个国家标准计划《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致力于推进中国标准“走出去”、提升标准化基础能力、实现关键领域的标准化工作突破,让中国发展成为世界“标准大国”。③国务院办公厅:《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5年12 月30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5-12/30/content_5029624.htm。“中国标准2035”战略指出,要通过“一带一路”和“数字丝绸之路”等海外投资进行标准化实践,同时在国际标准治理事务中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其次,搭建新型数字贸易全球治理系统。数字平台除了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跨国陆地和海底电缆网络、光纤电缆网络、卫星导航网络(北斗)、数据中心和相关云服务。其中数字平台可以让国际社会从数字基础设施网络中获益,共享全球数据信息,并进行低成本全球交流。例如,“世界电子贸易平台”(简称eWTP)寻求扩大全球贸易、旅游、培训和技术方面的数字网络,可以有效降低全球贸易成本,为中小型企业发展赋能,获得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经济论坛(WEF)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认可。2017 年第一个“海外电子枢纽”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数字自由贸易区建成。除马来西亚外,中国已在泰国曼谷(2018 年4 月)、卢旺达基加利(2018 年10 月)、比利时列日(2018 年12 月)和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2019 年11 月)建立了电子枢纽。2018 年2 月,首届全球跨境电商大会通过了《北京宣言》,确认“eWTP”是电子商务的重要国际机制,旨在塑造全球数字贸易的实践,为供给新型国际公共产品奠定基础。
最后,探索全球数字货币与新型金融模式。全球性数字货币作为跨境交易和投资决策所使用的货币,是一种潜在的国际公共产品。然而这一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往往是主权国家,存在全球消费与供给的错位。当前,美元依旧是全球主要外汇储备,美元在外汇交易、全球支付和贸易方面仍保持中心地位。全球金融市场高度依赖美元,很容易造成国际公共产品的私物化或工具化。为探索全球普惠金融与新型货币,中国成为首批发行主权数字货币的国家之一。2021 年1 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与环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SWIFT)成立合资企业,升级跨境人民币支付和结算系统。在2021 年3 月的国际清算银行(BIS)创新峰会上,中国提交了关于全球数字治理的提案。数字人民币建设实践为全球数字金融孵化规则,这种数字货币和数字支付网络是一种新型国际公共产品。①“China Proposes Global Rules for Managing Sovereign Digital Currencies,” Dezan Shira and Associates, April 4, 2021.
(二)供给全球数字发展型公共产品
在新一轮“再全球化”进程中,南方国家的新理念与新经验将为全球治理带来新方案。②王栋、曹德军:《再全球化: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2 页。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引领者之一,有望将国内技术创新与发展经验外溢为区域性、国际性与全球性公共产品。“云治理”加强了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有助于数据共享,打破“数据孤岛”困局。通过整合碎片化资源,将各部门的数据孤岛转化为单一的信息“云”,促使信息在整个平台共享流动,从而改善跨部门之间的协调,提高总体治理水平。这种云治理模式若在全球推广,则可能建立一个外向的、分散的、协商的全球治理新范式。
第一,顺应数字全球化趋势,构建全球基建新格局。“数字丝绸之路”(DSR)是中国建设连接世界的复杂基础设施网络的全球倡议,已经扩展到第五代(5G)移动网络、物联网(IoT)、人工智能(AI)、大数据、智慧城市、数据中心和数字经济时代的云计算等前沿领域。标准连接是数字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5 年10 月,《“一带一路”标准联通行动计划(2015-2017)》指出,标准化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并且概述了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促进投资和贸易、支持基础设施联通的10 个优先领域。①《我国发布〈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2017)〉》,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5 年10月22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5-10/22/content_2952067.htm。在2017 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论坛上,数字经济被正式纳入议题。2019 年4 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要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共同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②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2 页。当然,全球标准竞争涉及地缘政治,当前世界大国为抢占前沿技术战略高地,在全球数字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相互挤压,致使全球数字治理格局碎片化。
第二,促进包容性全球数字治理,破解南北“数字鸿沟”。南北发展不平衡是长期困扰全球的突出难题之一,而全球南方与北方国家在数字准入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发展中国家的移动宽带普及率约是发达经济体的一半,而固定宽带普及率则仅为发达经济体的三分之一。不同地区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差距仍然显著,及时缩小“数字鸿沟”的需求十分迫切。③罗雨泽:《数字技术革命为南南合作注入新动力》,《中国经济时报》2021 年9 月7 日,第1 版。中国近年来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为推动缩小数字鸿沟作出积极贡献。例如,通过援助肯尼亚国家光纤骨干网项目,中国推动了肯尼亚及其非洲邻国的信息通信产业集群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大幅提高网络速度的同时,降低通信成本,促成了电子商务的兴起。为使技术能够真正落地、产生实效,中国面向东盟、南亚、阿拉伯国家建立跨国技术转移中心,通过技术对接、示范培训等,推动先进适用技术转移转化。为探索构建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数据治理体系,雄安新区加快创建全球领先数字智能城市、打造高质量发展“全国样板”,基于此可为全球数据治理积累独特的中国经验。
第三,搭建多边机制平台,优化全球数字规则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以G20 为核心。2016 年G20 杭州峰会则率先制定数字经济政策,发出全球首个多边数字政策文件《G20 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标志着世界数字经济发展正式走上全球治理议程。①Samm Sacks, “Beijing Wants to Rewrite the Rules of the Internet,” Atlantic, June 18, 2018,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 archive/2018/06/zte-huawei-china-trump-trade-cyber/563033.2021 年8 月,中国网络空间局在数字创新论坛上提出了中非互联网合作倡议,与非洲建立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连通性,比如为塞内加尔建造国家数据中心提供资金,为非洲联盟建设区域性数字经济框架提供大力支持。此外,中国以东南亚为关键节点,重点建设中国—东盟数字中心与“数字命运共同体”,基于此加快境外建设跨国数字共享平台的建设。②Karen M. Sutter, “‘Made in China 2025’ Industrial Policies: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ugust 11, 2020.数字基础设施巨大的正外溢效应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其外溢效应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更在于政治收益和国家形象提升。
综上而言,在数字治理方面中国正成为全球参与者和引领者。作为数字大国,中国积极致力于促进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合作理念,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产品供给实践,将为数字时代的全球治理供给新路径与新模式。立足增量改进原则,中国致力于打破数字鸿沟,确保互联网接入的可负担性、可靠性以及可及性。同时依托G20 等多边发展机制,提出全球数字发展的新规范与新倡议,为创设全球数字公共产品探索新规则。
“道者,自然也”。中国自身的发展是一种顺应全球化潮流的“道”,如今促进中国倡议、分享中国智慧更是展示大国道义的重要方式。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普惠发展的重要启示体现在:一方面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时代潮流,提升大国外交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与塑造力;另一方面,跳出西方国家主导的发展话语叙事与传统观念制度框架,为人类社会发展提出创新性解决方案。尤其是,自2008 年全球金融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面临困境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发挥能动性,倡议创设了多个新型多边发展机制与倡议愿景,致力于完善和改良全球治理模式。在功能分工上,中国倡议的新型多边发展机制更专注于基础设施发展和民生改善,通过接纳本地区以外的成员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展示出显著的包容性。③Ian Tsung-yen Chen, “China’s Status Deficit and the Debut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The Pacific Review, Vol.33, No.5, 2020, pp.697-727.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智慧”致力于寻求最大共识,搭建开放合作的平台网络,让中国发展的成果普惠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