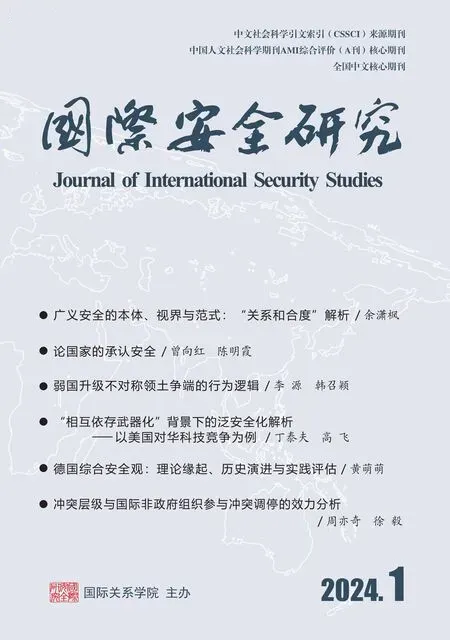广义安全的本体、视界与范式:“关系和合度”解析∗
余潇枫
【内容提要】 基于中国关系本体论对安全的本体和视界进行解析,并且建构中国的安全理论范式,是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的重要方面。安全是一种什么样的“实在”,这是十分重要的本体论问题;而以什么样的“视界”考察安全,则是非常棘手的认识论难题。“关系和合度”解析为“广义安全论”视域下的安全本体、视界与范式提供了哲学诠释。安全是“关系性实在”,是和合状态的共享性秩序,是呈现人与世界“广义性联系”的“关系和合度”。如果关系的和合程度是安全获得的程度,那么安全就是以“关系和合度”为自变量的函数,广义安全便是呈现人与世界“关系和合度”的安全,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广义安全凸显“关系和合度”的适然性,安全之境即是保持优态共存的“适然之境”,是当下所发生的一切关系的总体性和合,这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全球安全观提供了理论支撑。广义安全观是集成与整合诸安全构成要素与安全领域的大安全理念,是“场域安全”思维的完好体现,是多重时空关系状态与多种活动性质特点的融合。
建构安全理论,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角与层次的选择,但“广义安全论”可能是最不可或缺的。如果要用一句话概述何为广义安全,那么其便是呈现人与世界“关系和合度”的安全。
人类的发展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特征,但人类安全算法总体上呈现战争、竞争、竞合、和合的“升级”特征,每一次安全算法升级即是人类文明发展阶段的提升。①余潇枫:《人类安全算法“升级”:战争-竞争-竞合-和合》,《国家安全论坛》2023 年第2 期。“广义安全论”视角下的安全是一种“场域安全”意义上的“类安全”,由于人和世界的关系是“全域性”的,物理世界、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都在这一广义的“全域”中,因而广义安全是人类整体意义上的总体安全,是基于“关系和合度”为考量的安全范畴,既包含个体安全,也包含集体安全与人类安全;既包含国家安全,也包含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全球安全,甚至还扩展至星际安全以及人类与非人类间的类际安全。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广义安全是对安全在三个维度上扩展的结果:一是指涉对象维度上的不断深化,超越了国家安全作为唯一的基本单元或中心;二是领域设定维度上的不断拓展,低政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进入国家安全的高政治议题中;三是价值整合维度上的不断融合,“安全与发展”“安全与平等”“安全与正义”“安全与解放”和“安全与自由”越来越成为安全理论研究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和哲学等相关联的复合性议题。
那么,“广义安全论”为安全的重新解读提供了什么样的本体论前提与方法论视界?如何基于这一特定的前提与视界探讨广义安全的理论范式建构?这是本文将要讨论的主题所在。
一 本体:安全是“关系和合度”的函数
安全是一种有待于理论解释的复合性“实在”。何为“实在”?人类在探索世界之初,往往把世界的“本体”之物视为实在,然而人自身处在世界之中,又如何能确定所看到的“本体”即是实在?康德为了解决这一认识论悖论,把世界分为“物自体”与“表象世界”,世界便是人为自然立法意义上的“表象世界”。现代科学从分子、原子、亚原子粒子一层层剥离进去,以探究世界内核的基质性实在,发现组成任何粒子的“能量子”(量子)居然是无定形的非物质存在,于是对世界本体的物理性解释取代了经典物理学的物质性解释,物理性包含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信息与能量),于是现代物理学得出的结论是:所谓的“实在”只是量子场域中波函数坍缩时的瞬间显现,“实在”的本质是非定域的概率。因而,要探索安全是一种什么样的“实在”,需要确立“广义安全论”视角,对安全作出超越经典物质实在论的全景式分析,从不同维度对安全的实质性含义进行探究。
(一)“安全实在”的主客观维度考察
安全是“客观性实在”,是呈现客观上无威胁的“外和合度”。仅仅从人的感性经验出发,我们能够认可,安全威胁是外在的、客观的和可观察的,即当我们面临某种来自外在客观的安全威胁时,如火灾、水涝、空气污染等威胁着我们的生存,“不安全”便成为一种全然的“客观性实在”。这些威胁实实在在地存在,对所有人都造成伤害。在客观维度上,“客观性实在”源自个人对外在客观威胁的经验性感知,呈现的是人与客观世界的某种关系,安全便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的外在和合性程度(外和合度)。由于人的客观生存环境中永远存在不同层次与类别的外在客观性威胁,因而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安全,安全永远只是一个相对性范畴,客观环境中的“安全度”就是由人与客观环境关系的和合性程度即“外和合度”所决定的。
安全是“主观性实在”,是呈现主观上无恐惧的“内和合度”。我们观察客观世界时,我们自身恰恰又处在这个世界之中,因而对“客观实在”的认知是相对我们观察者自身的,在绝对意义上它又因基于我们的“观察”而是“非客观”的,这就是“观察者悖论”。即使在经验层面,被当做“客观实在”的威胁出现时,我们也不能排除经验主体自身对这一安全威胁的主观感知的某种“参与”甚至“建构”。假如人感知不到安全威胁,或者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自身脆弱性,那么人可以是处在一种对于他人是不安全而对于自己是安全的境遇中。这就产生了因主体的感知或脆弱性不同而差别各异的安全判定,进入一种具有“安全中的‘不安全’”与“不安全中的‘安全’”的特殊情景。可见,安全威胁作为一种外在“客观实在”,除客观性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该威胁能否被感知、如何被感知以及是否针对特定脆弱性而造成真实的威胁。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旦主观“感知”因素介入安全研究,因为主体的脆弱性程度与“观”的角度不同,主体本身会直接受到安全语境的影响,所谓安全就必然包含“客观”与“主观”两种因素,这时绝对的、全然的“客观安全”就退隐了,代之显现的是主观感知认定下的相对的、或然的“主-客观安全”。再进一步,当主观感知介入安全时,如果再把感知分为“外感知”与“内感知”,安全的“实在性”不仅变得相对模糊,而且“威胁”就可被分为相对于主体的“外在性威胁”与作为想象对象的“内在性威胁”(如“假想敌”之类)。于是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外在性威胁与内在性威胁是外在于人的“客观性实在”,还是内在于人的“主观性实在”?
“主观性实在”源自人对内在主观恐惧的体验性感知,呈现的是人与自身内在世界的某种关系,安全便是“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当我们讲“客观”的时候,任何“客观”都是一种主体参与其中的“观”,因而探究安全是何种“实在”时主观性是占主导的,于是观察者悖论导致了客观性悖论,任何“客观”都是与主观的“观”相关联的。然而,人是一个有限性存在者,其主观感知难以达到全维意义上的绝对程度,主体内在心理的“安全度”也只能是用人与自身关系的“和合度”即“内和合度”来表示。因而在主观维度上,安全是基于语境(场景、情景与前景)的具有概率性的“景象判断”,这种判断既有赖于主体的脆弱性对外界的投射程度,也有赖于主体的能力对当下威胁的回应程度。即使处于同样的客观环境或面对同样的客观威胁,不同的主体也会呈现不同的心理映射和对安全威胁不同能级的应对,使得同一环境中不同主体的“内和合度”具有差异性。
(二)“安全实在”的话语、意向性维度考察
超越主客观维度考察安全的主要有主体间性、意向性维度以及融合所有实在性诠释的关系性维度。如果我们把威胁的来源置于社会场域的特定关系中,那么对安全威胁的考察就更趋复杂而有意义,除考察安全的“客观性实在”和“主观性实在”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它是基于主体间关系建构的何种“话语性实在”,或是一种基于“安全场域”特定语境中的“意向性实在”,抑或是统合所有实在判定的“关系性实在”。不管这五种判定对安全威胁有着多少种不同的描述,至少这五种安全威胁的实在类型都是安全本体论与认识论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
安全是“话语性实在”,是呈现主体间关系和合的“群和合度”。在主体间性的维度上,“实在”源于人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相互感知、认同与互构,呈现的是人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特定关系,安全便是社会场域中主体间建构的、呈现“主体间不存在冲突”的和合状态。这种和合取决于话语建构,其本身是对主观与客观的超越,构成话语的言语行为是当下显现安全与否的关键因素。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安全研究的首要问题是把话语安全与客观安全、主观安全区分,安全作为言语行为自我指涉的实践,“话语”才是安全的依托,因而“国家安全不再是简单的分析国家面临的威胁,而是分析特定‘国家’的具体身份是如何产生及再现的”。①巴里·布赞、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余潇枫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154 页。矛盾运动是宇宙存在的基本方式,由矛盾导致的冲突永远存在,安全与否是由行为体间的认同相互建构的,安全只是一个体现主体间关系的相对性范畴,其中具有社会建构性的“话语”起着关键作用,通过话语而实现的任何冲突的弱化、消解、转和与趋合等才是主体间安全性获得的标志。由此,安全作为“话语性实在”,是社会场域中行为体间的和合性程度,即“群和合度”。
安全是“意向性实在”,是呈现“类意识”与“类安全”的“类和合度”。在意向性(intentionality)①“意向性问题”涉及现象学哲学与量子社会科学讨论的范围。在现象学中,意向性特指意识对其对象的共时发生的指向性,“意识意向某对象”则意味着某对象向意识显现自身。在量子社会科学中,意向性指意识的涌现(emergent)特性,因物理性与心理性不相容,所以意识是经典世界观下的“反常”性奇迹。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意向性所指的是,诸如信念、愿望、意涵这些心理状态内在都是‘关于’或指向超乎其上的事物,无论是世界中的真实客体、人们心灵中的想象、或是他人的心灵。……只要制度被理解为集体意图,那么意向性便也同样存在于宏观层面。”“如果我们在经典物理学约束的框架下进行社会科学研究,那么意向性现象在我们的研究中便没有任何地位。……如果意识不能与经典世界观取得协调,则意向性问题便不存在于用经典方式所构想的社会科学当中。”参见亚历山大·温特:《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祁昊天、方长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14-15、19-20 页。维度上,“意向性实在”是人与客体世界长久交互而形成的,源于人的“类意识”,即在特定语境中的先天性感知。这种意向性感知涉及现象学研究,呈现的是人与客体世界的某种先在的本质性关系。人类之所以有“类意识”,是因为人之为人具有其独有的作为“类存在物”的类特性。首先,人的类特性与物的类属性有着根本区别。物的类属性是固有的本然性,是一种限定性概念,而人的类特性是一种超越性的概念,“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273 页。其次,人类的类特性与动物的种特性也有着根本区别,类特性正是基于对种特性的否定而生成的。种特性刻画的是动物的存在属性,即本质先定性、无个体性、与生命活动的直接同一性等。例如,蚂蚁会做各种类似人类的修路、制定交通规则、进行流水线工作等事情,“但蚂蚁之间的和平取决于其无与伦比的征战和屠杀本领,而单从数量上来说,蚂蚁因战争带来的伤亡超过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事件。”③马克·W. 莫非特:《从部落到国家:人类社会的崛起、繁荣与衰落》,陈友勋译,中信出版社2020 年版,第413 页。蚂蚁的“外交政策”可被概括为:永无休止的侵犯、武力夺取地盘以及尽其所能消灭邻近群体,如果蚂蚁掌握了核武器,它们很可能在一个星期内毁灭世界。④Bert Hölldobler and Edward O. Wilson, Journey to the Ants: A Story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9.与种特性相反,类特性刻画的是人的存在属性,即本质的后天生成性、个体性、生命活动的自我否定性等。人类的类特性表明呈现“类和合度”的“类安全”才是安全的本质,因此安全还有比“客观性实在”“主观性实在”和“话语性实在”等更为深刻的内涵。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从量子理论视角给出安全是“意向性实在”的判定,认为“国家是一个社会体系,一方面由围绕特定语言形式(公民身份、属地、主权等)组织的社会结构构成,另一方面由参与这一话语体系的人(公民和外来者)的无数实践构成”;“国家是一种波函数,被数百万人非定域地跨越时间和空间共享,但就其本身而言,它只是一种潜在的实在,而非确定的实在”;“国家是一个意向性客体或概念”。①亚历山大·温特:《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祁昊天、方长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306、314 页。因此,对国家的意向性认知体现着人类的“类意识”程度。“类意识”是人类在自身演化过程中升华所成的类生存意识,因而安全具有代际传承性的意向性范畴,行为体在类意识中的和合性程度就是具有本质性意蕴的“类和合度”。
(三)“安全实在”的关系性维度探究
安全是一种“关系性实在”,是呈现人与世界“广义性联系”②狭义性联系是指小范围的、与自身直接相关的联系,广义性联系是指大范围的、与自身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由此可以理解“人与世界的‘广义性联系’”是一种总体性、整合性、全网式的联系,就如一汪水,不是只与自身所处的溪流、湖泊相联系,而是除溪流和湖泊外,还与江河、海洋、大气、生态圈相联系。的“关系和合度”。人类对安全的认知经历了从客观性“外在”、主观性“内在”、主体间的话语性“同在”,再到类范围的呈现“类意识”的意向性“共在”的不同逻辑阶段,其具体的演进过程比较复杂,需要通过一部专门的安全演化史阐明。但不管是何种类型的“安全实在”,从关系主义本体论视角看,安全总是作为一种“关系”而呈现。关系主义本体论是相对于实体主义本体论而言,前者以“关系”为世界存在的终极假定,强调“凡一切实存的事物都存在于关系之中,而这种关系乃是每一实存的真实的性质”,③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281 页。在国际关系中即使是无政府的世界也是“有秩序”的;后者以“实体”为世界存在的终极假定,强调不同“实体”单元构成世界,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就如同一堆无序的实体性“弹球”,在无政府世界中相互随机碰撞,无常涨落。
中国有着丰富的关系主义本体论的思想资源。“天人合一”是中国对世界最典型的整体性关系视角的解读;一贯三者为王,所谓王者,是天、地、人关系贯通之人,能统摄天、地、人秩序的便是“王道”;同样,仁者,二人也,遵循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便是仁者,“仁者爱人”是中国人对社会最典型的伦理性关系视角的解读。以围棋为例,“布满棋子的围棋棋盘很像是一个儒家心目中的世界,每一颗棋子都与其他棋子联系在一起,相互关联的棋子和棋盘共同构成了一个围棋的天地。围棋和其他棋弈游戏最大的不同是,围棋的任何一颗棋子在下子之前,亦即放在棋盘上面之前,是没有任何预设身份的,也没有任何先在的属性和特征。所有围棋棋子看上去都是一样的,只有黑白之分,没有具体特定的身份……但棋子一经放入棋盘,就根据与其他盘中棋子的关系具有了身份和角色,获取了自身的意义。围棋是一种游戏,但反映了一种思维方式,反映了一种宇宙观,也反映了一种对个体身份和角色的理解和诠释”。①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173 页。为此,与西方将世界视为一个由“原子式”个体构成的实体弹球组合不同,中国人将世界视为一个“共在先于个在”的关系网络,整体不可分割,关系建构了实体,个在不重要,只有个在之间形成的“共在共生”的“关系和合度”的获得即安全的获得,才是重要的。
再以国家、国家关系、国家安全为例,国家安全的认知源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关系判定与国内社会关系中的角色定位,引发冲突并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本身的是国家在关系上的“非兼容性”。国家的本质与人的本质一样,“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56 页。彼得·瓦伦斯滕(Peter Wallensteen)在研究国家关系与国家冲突相关性时指出,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因地缘关系邻近性程度高的国家之间更容易引发紧张状态和战争;从现实政治角度看,处于结盟中的国家更容易参与到联盟的国际冲突中,甚至结盟关系有时会超越地缘关系对国家利益的诉求,成为主要冲突因素;从理念政治角度看,民族主义国家与非民族主义国家、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关系较为难处,它们之间会有更多的紧张与冲突;从资本政治角度看,已完成工业化与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之间,会因为产业竞争、商贸竞争乃至整体的工业化竞争而引发更多的国家间竞争、冲突乃至战争。③彼得·瓦伦斯滕主编:《和平研究:理论与实践》,刘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48-67 页。在国家发展的动态结构中,国家的“施动”,如持“赞成”“反对”或“弃权”态度,都表明国家对于某种“关系”的判定与选择,进而影响国家自身的身份确定与安危。可见,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不仅有客观性因素(土地、人口、文化传承等)、主观性因素(如对国家身份认同持有的信念以及相应的制度设定、时局判定、国际体系中的角色确定等)和社会建构的话语性因素(如话语结构、言语信息传播与言语行为施动等),也有根植于类意识的意向性因素(如国家的象征符号意向、以国家或其他单元为认知单位的“我们感”、非法律意义上存在的“国家感”、跨越时空的“集体自尊”向度、人类共同体、地球村等),这些不同维度的因素统合于一体,其所凸显出的总体性“关系和合度”才是国家安全的实质。
基于关系的视角,对上述不同安全本体的实在性判定作一统合,凡客观的、主观的、话语的和意向的实在及其不同组合均可被归入不同层次与类型的广义关系之中,或者说“广义安全论”秉持的是“关系本体论”,安全的实质是“关系”,安全的本体是“关系性实在”,其关系的和合性程度即安全所能达到的程度,由此可以推论:安全是“关系和合度”的加和。其表达式为:
或者更确切地说,安全是以“关系和合度”为自变量的函数,其更抽象且简约的函数表达式为:
其中:S(Security)表示安全,H(Harmony,或为汉语“和合”拼音hehe的首个字母)表示“关系和合度”,F(H)是以H为自变量的函数,其中H = Σ(h1+h2+h3+h4),h1、h2、h3、h4分别代表外和合度、内和合度、群和合度、类和合度。
安全是“以‘关系和合度’为自变量的函数”,正是“广义安全论”对安全本体探讨的重要理论贡献所在,它超越了以往对安全的消极界定(安全是一种客观威胁的不存在,或是一种主观恐惧的不存在),进而凸显了安全是一种与“危态对抗”相反的全然积极的优态共存状态。以中美关系为例,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上把中国定为头号“竞争对手”,中国则强调中美关系不应是“竞争关系”,而应是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的“良性竞合关系”;美国提出要与中国全面“脱钩”,中国则反对所谓的“脱钩”“断链”,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同时,主张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美国从太平洋“东进”构建三条岛链和新“印太战略”以压制中国,中国则向世界发出“一带一路”倡议,谋求世界各国共同推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为全球发展开辟新空间;等等。中国寻求的是通过超越“危态对抗”以提升“关系和合度”,构建优态共存与普遍安全的世界。
二 视界:安全场景性、情景性与前景性
理论的视界决定对事实解释的深度与广度。何为“视界”?视界是观照研究对象所企及的范围,或者是一个学科性的独特范畴所能表达的构造性“场域”。柏拉图《理想国》的视界是“理念论”以及整合哲学、伦理、教育和政治等的“城邦正义”,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视界是以“政治理论与政治体制”为要的“城邦政治”。研究安全理论首先要对安全视界进行探究。
(一)“和合度”与“场效应”
安全作为“关系性实在”,是总和共享的“关系和合度”,因此可以给安全下一个描述性的界定:安全是呈现和合状态的共享性秩序。和合状态、共享、秩序是解读这一安全界定的关键词。“和合状态”表明系统中的要素在根本上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融合的;“共享”表示“无危无缺”的某种程度;“秩序”表明行为体间存在共生关系,意味着系统内部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在一个情景中某些事情比在其他的情境中发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其他的事情更不可能发生或者是根本不可能发生,有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把这种情景称为‘有秩序’的”。①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 年版,第84 页。由“秩序”而形成的安全系统具有结构性与生成性,安全实质上是呈现镶嵌互构的安全场域中保持和合状态的共享性秩序,其和合有序性程度就是安全的实现程度,“关系和合度”是安全程度的总体性标示。
“关系和合度”的获得与行为体所处的场景、情景及前景有着紧密关联。安全不仅有客观性与主观性交织的时空“场景”,而且有主体间性建构的文化“情景”,还有与意向性关联的未来“前景”,或者说安全是自然-文化-未来三维一体化的关系场域,这其中的“未来”是超越自然羁绊与文化边界的意向性未来,是呈现人类“类性”的意向性图景。解读好安全的“场”与“景”,透彻了解“安全场域”的“场效应”与演进趋向,有利于深入理解广义安全的要义。
天地万物、人间万事无不处在“场域”之中,极宏观的有宇宙场(万有引力场),极微观的有量子场。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的存在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不可逃避的命运“在场”。按“场有哲学”解释,生命是一种“场有”。①唐力权在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基础上提出“场有哲学”,强调生命现象是一种“场有现象”。参见唐力权:《周易与怀特海之间:场有哲学序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那么,安全与生命一样,其实也是一种“场有”,是一种“场域”或“在场”中的关系聚合。从“场域”的视角审视作为“关系性实在”的安全,安全是基于“共生”前提的和平、和解、和好、和谐与和合的“在场”,或是风险、威胁、危机、灾难与灾祸的“不在场”。
“场”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出现频度较高的用词,其含义一是指空间域,如场地、场所、体育场等;二是指时空融合点,即特定时间点的空间情景展示,如开场、出场、闭场等;三是指价值网,即人们出于价值追求需要或出于价值规范约束而为之去从事和投入资源的关系网络,如商场、官场、情场等。物理学中的“场”是表达事物在特定空间与时间中具有某种关系特征与状态的称谓,如“电场”“磁场”等。物理场的特征:一是场的分布状态延伸至整个空间,有“全空间”特征;二是场作为一种动力系统具有无穷维自由度,有“多变量”特征;三是场是一种其量值因时空而变的强度存在,有“量值性”特征;四是场还可以是与时间变动相关联的函数关系,具有“时变性”特征。以上四点,构成了物理运动特定的“场效应”。
在安全研究中引入“场”与“场域”的范畴,可以很好地揭示以“关系和合度”为变量的各种安全状态。社会领域中多用“场域”来替代“场”概念,表明除了场的物理特征与状态外,还叠加了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的专有性质,因此更能具象地反映出安全作为社会关系范畴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场域”范畴较之“场”的概念更好地表征了安全要素构成的社会关系的集合特征与和合性程度。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对“场域”的界定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网络,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②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第134 页。可见,关联着众多行为体的安全不仅是一事一物的没有危险或威胁“可能”的持存状态,而且是与众多事物相关联的没有危险或威胁“关系”的持存状态,是基于场域的总体性“关系和合度”的达成。
对场域的安全性考察关涉物理、文化、价值等多重时空关系。有学者认为,“场域”代替“环境”“语境”和“社会背景”等话语,为寻究经验事实背后价值博弈的潜在模式和关系性逻辑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①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年版,第138 页。“安全场域”与“场域安全”这两个重要范畴不仅使得安全是一种“关系性实在”在现实中得以成立,而且还使得场域中各要素在安全互构中形成不同和合度的“场效应”。借用现代物理学的“希格斯场”比喻,能够较确切地说明“广义安全论”的图景:“在宇宙之初,所有的粒子都没有质量,电子、夸克还有其他所有粒子都像光子一样没有质量。随着宇宙的演变,粒子通过所谓的希格斯机制‘获得了质量’,”“宇宙发生了膨胀,无质量的粒子集合体冷却,在发生自发对称性破缺后出现了希格斯场,粒子开始表现得仿佛是有质量,然后我们人类也产生了。”②理查德·A. 穆勒:《现在:时间的物理学》,徐彬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 年版,第181-182 页。同样,安全行为体作为独立要素而存在时,没有进入“关系场域”,并没有任何安全问题,一旦进入某个“关系场域”,便获得了相对其他参照物的“安全性”,在场域各要素间的镶嵌与互构作用下,呈现某种“关系和合度”的安全“场效应”便产生了,众多安全行为体聚合成塑造安全的力量,奏出跌宕起伏的安全“场效应”之交响曲。由此在广义安全的视角中,万事万物的演化都是在场域关系语境中的演化,所谓安全就是呈现“场效应”的“关系和合状态”,和合度圆满状态即是最安全状态。
(二)安全的场景、情景与前景
基于场域理论,从物理时空、文化时空和价值时空③余潇枫:《哲学人格》,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第161-166 页。的角度对安全进行深入分析,可揭示安全的“场景性”“情景性”和“前景性”特征。
从物理时空考察安全,安全显然具有特定的物理“场景性”。场景(setting)分析是源于戏剧理论的一种重要方法,每一个场景都具有超越个体的时空独特性,在戏剧理论中“场景”是基于社会建构性的“客观状态”。人们如果通过客观性途径认识安全,那么基于自然灾害与人类战争的种种体验,会把安全更多地关联于客观存在的处境、条件与状态,安全即一种客观上可视可闻的时空“场景”。两次世界大战的时间与空间的场景性特征就十分明显。“无论何时,当我们把社会场景理论化为一种双方互动时,在一开始结构性特点很小,通过互动而产生了额外的结构。”④尼古拉斯·格林伍德·奥努夫:《我们建构的世界:社会理论与国际关系中的规则与统治》,孙吉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160 页。全球化时代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也有不同类型与层次的场景性特征,如近些年主要发生在欧洲的移民难民潮,移民问题的“安全化”使得欧洲安全的“和合度”大为下降,成为欧洲面临的重大非传统安全挑战的特殊“场景”。
从文化时空考察安全,安全还具有特定的文化“情景性”。情景(context)一词来自拉丁文contexere,含义是连接与合并。如果场景强调的是物理时空属性,那么情景强调的是社会文化属性。有人类学家认为,情境曾是考古学的重要话语,强调“物器”可以在不同类型的情景关联的文本中“说话”,脱离情景的文本将无法清晰表达其意义。①伊恩·霍德、司格特·哈特森:《阅读过去》,徐坚译,岳麓书社2005 年版,第146-149 页。人类安全维护是人自身参与其中、选择其中和建构其中的实践活动,安全维护方式与人的文化存在方式和文明发展程度紧密关联。早期人类学家关注的“安全问题”多是原著民生存环境中的社会结构与功能以及确保其种族延续的内在机制,为此人类学家提出了“文化”概念以揭示其情境,“文化”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后来被称为“安全研究”的最早的重要概念。②Philippe Bourbeau, ed.,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Liberty, Fear and the Stat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2.人类发展至今,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也不是发生在时空以外的纯粹事件,而是发生在具体时空的文化情景中的历史事件,因而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带来的安全问题不仅有其“时空场景”,也必然有其富有文化意蕴的“时空情景”(spatio-temporal context)。“把社会分解为各种情景的聚集体,所有这些情景都是社会性的,它们都具有两个行为体,在一个不同的固定的环境中互动,无论是建构性的,还是解构性的。”③尼古拉斯·格林伍德·奥努夫:《我们建构的世界:社会理论与国际关系中的规则与统治》,孙吉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160 页。以恐怖袭击为例,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是恐怖分子一种滥杀无辜的“变态复仇”情境,而美国在九一一事件以后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则是另一种以“武力反恐”为标志的复仇情境。俄乌之间、巴以之间本是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关系,但在特定的安全场域中却反目为仇,酿成你死我活的复仇情境。所以,安全威胁不仅存在于物理时空的场景中,还表现在特定文化时空的情景中。
由上述的安全“场景”和“情景”的组合,有学者提出的“景观安全”(spectacular security)成为安全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如果说“生态景观安全”是指生态景观中潜在的位置与空间关系构成的安全格局,称为生态安全格局(Security patterns),那么社会景观安全是指社会场景中潜在的区位与文化关系构成的安全格局。社会景观安全主要包括大型节日、庆典为主的“节事安全”与大型会议、展览为主的“会展安全”两大块。以往人们参加的各类节事的庆祝活动或者举行大型会展(竞赛、庆典)活动,都是呈现为大规模的喜庆场景与愉快情景,但自从恐怖主义袭击以及大规模群体事件频频选择在这个特定的时空点发生,呈现特定时空-文化的社会景观却成了时刻带来灾难阴影的“火山”,随时有爆发的可能,于是“景观安全”也就成为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景观情境”的新安全领域。
与物理时空相区别的文化时空、历史时空和语言时空等都是价值时空的具体化,它们之间具有时空的复合交错性。价值时空凸显的是时空的“关系性”而非“实体性”,如果基于相对论原理,时空的特性是由物质的“运动”特性决定,并且在运动特性支配下的时间与空间可以互相转换,那么作为一种“实体”的时空就变成一种作为“关系”的时空,这也正是相对论导致人类时空观念变革与范式转换的关键所在。与此相应,社会运动的特征支配社会价值时空的特征,“价值时空扬弃了自然时空的自在性、可分割性的特性,生成了价值时空自身的自为性、总体性和发展性的特性,从而使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在自身的实践活动中超越了自然物理时空的有限性,进入一个富有强性的有限与无限相统一的社会价值时空,使人的超生命本质得以充分的发展、延拓成为可能”。①余潇枫:《哲学人格》,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第164 页。因而从“价值时空”考察安全,安全还具有基于“意向性”的呈现未来向度的“前景性”。“价值时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安全的维度。如果说物理时间的矢量方向是过去-现在-未来,那么价值时间的矢量方向是未来-现在-过去,物理时间的起点是在过去,价值时间的起点却是未来,经典物理的“因果论”在价值时空中转换成量子物理的“果因论”。当人们为未来的理想而奋斗时,未来的理想便成了人的价值时间起点。以未来为价值起点更多反映的是人类的意向性本质,也就是说真正的未来是意向性的,是一种超越场景性与情景性现实边界的“前景性”或“前景化”指向。
广义安全的“前景性”或“前景化”研究具有“未来反求”的重大意义,甚至会帮助我们重新建构乃至改变安全的残缺现实。“前景化安全”(foregrounding security)概念是对语言学中前景化理论的借用。巴里·布赞认为,安全指涉对象的建构具有“前景性”,并且安全以指涉对象为轴不断深化,如果将安全以“领域”为轴进行扩展,那么就使一直被战略研究所重视的军事安全得以扩展至经济、政治和生态安全领域;如果将安全以“地域”为轴进行扩展的话,那么共同安全就超越了国家安全范围和军事安全中心,所以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单个国家,而是整个国际社会共有的全球性问题。①巴里·布赞、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余潇枫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7 页。
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三个维度是自然、文化和未来,而安全场景、安全情景和安全前景正是三个维度在安全研究中的立体架构与整体化图景,并且构成安全研究的新视界,“关系和合度”则是安全“三景”一体化的价值性尺度。
(三)“安全场域”与“场域安全”
安全场景、安全情景与安全前景都关涉安全是否“在场”。如果说“安全化”与“去安全化”是安全议题的“在场化”与“不在场化”,那么“在场安全化”(insecuritization)则是安全场景、情景与前景相融合下的“在场”。
对“在场”安全进行“场域”性考察,是安全哲学的一种抽象,也是安全研究的一种整体化努力。安全是特定的“场有”状态。“场域安全”是指与安全相关联的、具有特定活动性质的、没有危险或威胁的关系状态,它强调的安全不是一种线性的、技术性的安全,而是非线性的、价值性的安全。“场域安全”强调反映在安全问题上的社会活动的复杂关系,突现多重“时空关系”与多种“活动性质”在安全问题上的叠加、复合与交织。提出“场域安全”的目的是,强调运用“场有思维”的方式来考察安全,把安全看作一种具有整体性、交织性、强弱性和动态性的“场效应”,继而对安全的维护也会具有更为合理与有效的筹划与实施。②余潇枫:《非传统安全治理能力建设的一种新思路--“检验检疫”的复合型安全职能分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 年第9 期,第85-86 页。
这里需要区分“安全场域”与“场域安全”。“安全场域”是对安全的特定场景、情景与前景的总括,可被理解为能够影响乃至决定安全态势的特定语境,如地缘场域、利益场域与社会心理场域。西方学者认为,“安全场域”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空间,有磁场、战场、统治场和“模截场”(transversal field)四个特点:磁场是将不同感知、观念和利益同质化;“战场”是那些给事件贴上“不安”标签的管理专家需为争夺意义而进行斗争;“统治场”是通过形成主导意义的体系界定安全、威胁和政策;“模截场”是揭示安全可以相互影响和渗透。③参见C.A.S.E. COLLECTIVE, “Critical Approaches to Security in Europe: A Networked Manifesto,” Security Dialogue, Vol. 37, No. 4, 2006, p. 458。转引自袁莎:《“巴黎学派”与批判安全研究的“实践转向”》,《外交评论》2015 年第5 期,第147 页。
而与语境化分类的“安全场域”不同,“场域安全”则是对安全“特定语境”或“关系网络”本身进行再抽象,是对安全本质属性与能力的概括与提升,是对场域中的安全问题的“系统性特征”的强调。“系统”本身具有两种重要含义:一是作为整体主义的隐喻,“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二是作为功能转换的隐喻,“整体异于部分之和”。第二重含义不仅否定了还原主义的思考路径,而且强调了系统的“突现属性”,即“当单元通过互动构成系统时,系统会具有与单元明显不同的特性”,“即使组成部分是非对称的、非平和的和不稳定的,整体也可能是对称的、平和的和稳定的;不可靠的要素可以构造出可靠的系统”。①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李少军、杨少华、官志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第8-9 页。因此,“安全场域”突出的是局部安全的“场域性”,而“场域安全”突出的是系统全域的总体“安全性”。“场域安全”重在反映安全问题上的社会活动的系统复杂关系,凸显多重时空关系与多种活动性质在安全问题上的叠加、复合与交织(多重时空关系包含主体、区域、层面、领域、阶段和代际等要素,多种活动性质则关涉主体、结构、要素、样式、功能和价值等不同方面)。
当用“场域安全”对安全现实进行深入理论观照时,安全事件只是一种作为研究对象的现象或表象,其背后关联着安全互构的复杂关系。可见,在“场域安全”分析中,安全不仅是一种状态,还是一种条件、能力与愿景;不仅是一种事件,还是一种趋势、互动与建构;不仅是一种情势,还是一种关系、结构与语境。这一切均反映着“场域安全”的整体性、交织性、强弱性和动态性的本质。
三 范式:广义安全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
那么,如何对广义安全作出明确的界定?以往人们对安全的界定多基于经验与学理两个维度。若以人的直接经验感受概括,安全可以被描述为没有“五害”的状态:身体上没有受伤害、心理上没有受损害、财产上没有受侵害、社会关系上没有受迫害、生存环境没有发生灾害。若以学理的研究分析概括,安全可以被刻画为没有“四危”的状态:客观上没有危险(威胁),主观上没有危惧(恐惧),行为体间没有危情(冲突),类意向上没有危感(本体不安全感)。
(一)广义安全凸显的是“关系和合度”的适然性
尽管从经验与学理上都可以概括出被人们认知的安全的基本状态,但不同的主体、不同的立足点、不同的层次有着不同的安全理解,不同的理论与学派对安全也有完全不同的界定。作为一个重要的基本概念,“安全”并没有得到像“权力”“利益”和“财富”概念那样透彻的研究,甚至还远远没有形成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定义,特别是当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凸显和蔓延时,安全与和平开始分述,追求“世界和平与安全”成了新的命题;安全也开始与发展相关联,除了“生存安全”,“发展安全”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于是安全的界定更为复杂多样;尤其是“人的安全”被提出并广泛运用后,“人”是“人类”“人民”的抽象指称,还是“个人”的还原式理解,一直存在理论争议。“安全”甚至被认为是一个“模糊而又充满价值”、①David A. Baldwin and Helen V. Milner, “Econom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Henry Bienen,ed., Power Economics and Securit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2, p. 29.“不发达”和“有待深化”②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Second Edition), Hertfordshire: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p. 3.的概念,因而也是一个“最为棘手的研究对象”。③巴里·布赞、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余潇枫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19 页。
至今关于安全的定义,总体上有三类不同的界说:一是强调安全不可定义,“安全”在根本上属于争议性的概念而难以统一,或者说安全是一种给出性的条件,恰如健康和身份一样不能简单赋予其确切涵义,甚至还可以说安全是没有任何精确意义的“模糊的符号”;二是认为安全问题太复杂、层次太多而且不同层次的安全实质完全不同,因而不可统一而论,只能根据不同层次或范围作出不同的定义;三是认为安全可以明确地定义,强调安全的内涵虽然看起来模糊,但还是可以在最基本的层面做简约化的理解与描述。④Terry Terriff et al., Security Studies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pp. 1-3.如伊恩·贝拉尼(Ian Bellany)明确认为,安全就是“摆脱战争的相对自由”,⑤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Second Edition), Hertfordshire: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p.16.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则把安全概括为“获得价值时威胁的不存在”。⑥Terry Terriff et al., Security Studies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p. 2.
布赞对安全概念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强调安全关涉三组关联的概念:第一组是补充性概念:把安全引入更具体、更具限定性的问题中,如威慑、战略、遏制等。第二组是平行性概念:把安全引入政治理论或更广义的国际关系研究框架,如权力、主权和认同等。第三组是竞争性概念:针对安全引入一些可替代的概念,如和平、风险、紧急和危机等。而“引入三组与安全相关联的概念框架的有利之处是,我们可以对安全进行结构性的概念分析,这对解读那些在安全概念不清晰情况下进行争论的国际安全研究文献特别有效。这些文献往往是‘概念上沉默’的,因为它们采用的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概念,并以直接经验的方式来叙述,忽视对概念本身的详尽讨论,引用的是缺乏‘安全’概念争论的学科材料。即使没有一种路径清晰地讨论过安全的概念化,而现在通过引入补充性、平行性或竞争性的概念,就可以探究国际安全研究视角所形成的‘三角洲’,进而对‘安全’涉及的要素进行‘元对话’(meta-conversation)。”①巴里·布赞、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余潇枫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16 页。但巴里·布赞只是指出了缺乏安全概念研究的问题所在,并没有对三组概念本身作深入诠释。
当我们对安全的本体与视界有了较好理解后,就能更为合理地对安全进行界定。首先,安全本体的解析为“广义安全论”视域下的“安全本质”提供了哲学解读。安全是“关系性实在”,是呈现人与世界“广义性联系”的“关系和合度”。在社会场域中,安全与伦理中的权利/权力、哲学中的正义、政治中的自由、经济中的保障、社会中的平等以及生活方式中的人类文明阶段均紧密关联,所以在安全哲学上可以对安全实在性的不同判定作一统合性的把握,把上述关于安全的不同类型包摄进去,即安全在本体论意义上是一种“关系性实在”。
其次,安全视界的解析为“广义安全论”视域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提供了理论支撑。广义安全观是“场域安全”思维的完好体现,是多重时空关系状态与多种活动性质特点的融合。在广义安全观视域下,离散的、局部的、本位的、传统的安全理解被超越和提升,复合的、整体的、技术与价值相融合的安全理解被认可与重视;安全是一种跨越边界的状态,是一种相互关联的结构,是一种整合关系的场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条件,更是一种普世共享的价值。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广义安全观在国家安全场域中的运用与创新,基于广义安全观确立起来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创设了这样一个“安全之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统一了发展与安全的对立,统筹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两分,统合了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的对开,统合了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的两难,从而实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融合。②余潇枫、章雅荻:《广义安全论视域下国家安全学“再定位”》,《国际安全研究》2022 年第4 期,第11-12 页。由此,以广义安全观运用于全球安全场域而建构的全球安全观则必然是这样一种安全理想:坚持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国际无政府逻辑,以“和合共生”的本体论立场、“和合共建”的方法论路径、“和合共享”的价值论目标去勾画人类安全前景与破解全球安全困境,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识,形成安全互助的良好态势,促成安全互保的战略环境,建成安全共享的治理体系,最终实现人类持续和平与世界普遍安全。①余潇枫、王梦婷:《“全球安全倡议”:人类安全的“前景图”》,《国际安全研究》2023 年第1 期,第4-25 页。
在广义安全的本体与视界论证的基础上,安全范式可作如下建构:无论是关涉生存的安全,还是关涉发展的安全,它们都是一种关系性和合状态的呈现,也就是说安全作为一种“关系性实在”,基于和合目标的适然性在场是其根本特征。适然性是一个与必然性和应然性相对应的哲学范畴,必然性强调世界的自在性、客观性、本然性,因而“不安全”与“地球必亡”一样是人类的宿命;应然性强调世界的自为性、主观性、或然性,因而“不安全”与“人类末世”一样是人类的另一种宿命;适然性强调的是相对于人的当下合理性和“属人世界”的真理性,“适然世界”是一个在人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统一了人的主客观矛盾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价值世界”,因而也是一个获得了“关系性实在”与“当下合理性”的安全世界。
(二)广义安全揭示的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
前面我们已经给出过关于安全的若干界定:安全是“关系性实在”,是和合状态的共享性秩序,是以“关系和合度”为自变量的函数。那么如何来表述“关系和合度”的适然性?“适然”是介于“应然”与“必然”之间、又统合它们两者的价值定位,而基于和合共享的优态共存正是适然性的最好表达,所以也是广义安全的本质含义所在。从适然性观之,安全之境即是保持优态共存的“适然之境”,是在一个当下所发生的一切关系的总体性和合。这里的优态共存状态就是总体“关系和合度”实现的适然状态。
如果用优态共存范畴来表达安全的这一本质状态,那么广义安全的定义就是:广义安全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
“优态共存”是一个相对于“危态对抗”的概念,也是一个超越狭义安全界定的范畴。危态对抗是指,行为体之间的状态是“你安全我却不安全、你不安全我却安全”或者“确保相互摧毁”。危态对抗表明安全即消除存在着的“威胁”,而在现实生活中,威胁是一个警戒性很强的词语,它总是被人们关联到生存危险的生命体验与生死存亡的国家历史中。在安全理论研究中,威胁除了可用数量关系表达客观实态外,还可与境遇中行为主体的主观状态相关联,再加上“话语安全”的影响,这使得安全问题更为复杂化。一旦人们把因生存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可预测性而导致受到的威胁和内在恐惧均纳入安全范畴,安全问题会更加严重。于是,对威胁的过度防范与抗衡恰恰在现实中会强化威胁的程度,使得人们陷入某种无休止的恶性循环。如果我们只承认安全是“威胁的不存在”,就会在现实中寻找威胁并努力消除之,进而使对抗与复仇成为未来资源投入的首要领域。人们所寻求的“威胁的不存在”将变成无可达成的虚位状态,甚至使“危态对抗”代代相传。①余潇枫:《从危态对抗到优态共存:广义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战略的价值定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2 期,第9 页。
优态共存是指行为体间的状态是“你安全我才安全,我安全你也才安全”。以生存优化状态为安全的目标,相应的安全梯度可以标示为优化状态、弱化状态、劣化状态和恶化状态等四个层次。这样以生存状态来观照安全和体现安全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安全的理解更加广义,并且生存状态的四个层次本身构成了一个有序的安全梯度。而安全作为“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相对于行为体来说,“优态”是其最佳适然之状,强调具有独立身份行为体的生存能力与可持续发展生存境况的相称。如果把“优态”作为对象的安全置于发展国际关系最基本的前提,就使得安全研究的主题从“战争-和平-安全”拓展到“发展-和平-安全”。这不仅表明国际关系理论从源起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考转向了和平与发展,也表明当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普遍化,和平并非等同于安全,不科学的发展也同样会带来不安全时,对于和平与发展的思考又将转向基于全球国际关系或后人类国家关系视角的发展与安全的思考,从而标示出安全所要达到的更广泛深远的价值目标。
“共存”是安全获得的互惠性条件,强调行为体追求安全的共生性、平等性与交互性,并在此基础上延伸出共建、共享与共赢的适然目标。在全球体系中,无论哪一个层次的行为体,若要获得安全,其基本立场与途径都只能是通过互惠共建达到共存共优,这就需要国际关系任何一个层次中的自者与他者间的共同努力。所以,广义安全的实质是从利益共同、责任共担走向以命运共同为目标的安全共享,广义安全的价值目标是“优态共存”。
“行为体间”是安全实现的关系性条件,强调安全实现的关系本位与过程互构的适然性。值得强调的是,这里的“行为体”(actor)不仅仅是“主体”(subject),而且是比主体涵义更广的能够影响安全的一切独立要素。在“广义安全论”中,对行为体的解读也是广义的,它包括人类行为体和非人类行为体。前者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后者包括有生命行为体如动物、植物等,还包括非生命行为体如知识、技术、设备、文档(如报告、白皮书、会议记录)等,特别是安全知识、安全技术和安全工具一般被视作新兴行为体的非生命行为体。①Richard Freeman and Jo Maybin, “Documents, Practices and Policy,” Evidence & Policy: A Journal of Research, Debate and Practice, Vol. 7, No. 2, 2011, p. 156.由是,以优态共存界定安全,作为“广义安全论”的核心范畴,安全的可能性边界就拓展到了安全建设的双方甚至是多方,其安全就有了某种适然的价值意义。特别是在应对各类跨国乃至全球非传统安全威胁时,人类共存于一个被称之为“地球号”的“太空救生艇”上,安全是共生、共建和共享的,优态共存才是最佳的生存与发展之道,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是优态共存的现实诉求。
其实,作为广义安全的优态共存状态就是总体“关系和合度”的适然状态,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相关性与等值性。我们将“优态共存”(Security Coexist)简写为SC,这样可以用“广义安全是以‘广义关系和合度’为自变量的函数”的表达式来表示“广义安全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的界定:
广义安全(优态共存)仍是以“关系和合度”为自变量的函数,只是用S'和F'(H)取代了S 和F(H),或者说“关系”的含义进一步扩展,这里的关系是全域性而非以往的非全域性关系。安全的“本位”转换,安全不是“我”的安全或者“你”的安全,而是“我们”的安全。广义安全揭示了安全的真正本质,使以往的狭义安全需要被修正与超越。这样,作为广义安全的“优态共存”和“关系和合度”既呈现了安全作为“关系性实在”的本体性,又凸显了安全场景、情景与前景三者统一的“元视界”,进而达成“整体性适然”与“总体性和合”的生存性境界。
(三)“广义安全论”的普适性
“广义安全论”是基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范式“和合主义”的安全理论。和合主义范式的理论普适性决定了“广义安全论”的理论普适性。正是和合主义与“广义安全论”作为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研究的中国式理论,对主流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理论特别是占传统主流的美国学派提出了挑战。相对于人类的安全场域来说,任何一个演化系统,在根本上都是对立统一、共生交融的“和合体”。“和合”逻辑的合理性在于场域中关系各方都具有共生性,这种共生性是相互交合的,也是相互包容的。和合主义与“广义安全论”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意义论上,都是对西方现有理论不同程度的扬弃与超越。
与西方本体论传统的实体理性不同,和合主义与“广义安全论”的本体论前提是关系,“关系性实在”是世界的本体,实体只是关系的一种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先有关系,再有实体,整个世界由不同的关系组成,本质上都是关系的和合。
与西方认识论传统中的原子主义不同,和合主义与“广义安全论”的认识论框架是整体(关系)主义。与原子论强调“个在先于共在”相反,其强调“共在先于个在”,进而形成世界万物的“共生论”。中国认识论传统的根本特征是,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关系是构造世界图景的本源。
与西方方法论的二元对立不同,和合主义与“广义安全论”的方法论特征是中庸,即以中庸达成和合。《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①陈晓芬、徐儒宗译注:《论语·大学·中庸》,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289 页。中,是稳定天下之本;和,是为人处世之道。故而中和、中庸、中道都是达到整体平衡与天人合一。
与西方意义论的“唯我”有着根本的不同,和合主义与“广义安全论”的意义论指向是“共享”。既然世界处在关系之中,共在先于个在,中庸为达成和合的最佳方法,那么意义寻求必然要超越“唯我”的个人主义而实行“天下”的普世主义。只有共享才是人类持久和平与世界普遍安全的终极意义所在。
和合主义与“广义安全论”的核心价值范畴是类生存、类伦理、类安全,理性原则是社会共有、权利共享、和平共处、价值共创和安全共享,目标指向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实现途径是和合共建。近些年,有不少学者试图建构各种与和合主义视域相关联的中国学派理论,形成了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研究的特有理论群。如国际共生论、海陆和合论、生态制度论、文化中国论等,强调共生与共存是先在于国际关系现实的,故和合价值具有先在性;如道义实力论、关系过程论、创造性介入论、文化过程论等,强调因国际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故过程语境中的和合便是关键所在;再如新天下体系论、社会演化论等,强调不管国家之间差异如何之大,人类必定有一个共同的和合未来,世界终将从国际安全共同体、全球安全共同体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②余潇枫:《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国际安全研究》2014 年第1 期,第26-30 页。
和合主义与“广义安全论”蕴含着中国整体论、共存论的重要思想,吸纳了现代系统论、相互依存论的知识图谱,是关于“国际关系和合”“人与世界和合”的理论体系,为全球“和合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核心范式,其理论的普适性还可以从国际比较中得以进一步证明。
如现实主义的人性假定为“恶”,强调战争、权力的争夺与国家间的权力-体系特征,重视国家短期内的绝对获益与相对获益,提出过威慑与核威慑论、地缘政治论、权力均势论、安全博弈论、安全困境论、霸权稳定论等安全观,面对异质性冲突不是强制就是独断;而和合主义的人性假定是“非恶向善”,把安全的本体视作“关系性实在”,重视国家在长时期中的相对获益,以和而不同、兼容共存的方式消解异质性冲突。
自由制度主义将国际主体由民族国家拓展至国际组织,认为国际主体间的合作、互惠互利建立在理性算计与博弈论基础之上,强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提出过相互依存论、制度共建论、民主和平论等安全观,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帕累托最优;而和合主义以整个世界、全人类作为分析单位理解世界政治,认为世界是一个共生、共存和共联的复杂网络体,只有互惠互利才能促进个人、国家的利益,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孔子最优”,即在让整体变得更好的前提下,才使得自己变得更好。
建构主义以敌人、对手和朋友定位来分别对应来自霍布斯、洛克和康德式的国家间文化,坚持自者与他者、中心与边缘、霸权国与挑战者等指称国际关系二元叙事的模型,提出以社会认同与共有观念为安全变量的认同安全观,认为“自助和权力政治都是制度,它们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特征,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①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37.进而用理念、规范、文化和认同来排斥国际关系中的物质和权力;而和合主义则建构了国家间的第四种文化,即似亲族(sibling)关系文化,以普遍包容的价值观消解自者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关系共生的基础上兼容物质与理念、权力与规范、制度与认同等对立性范畴,呈现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和合性与共享性。“与建构主义排斥物质、权力不同,和合主义在关系共生的基础上既强调现实主义的物质、权力的现实性,也强调自由主义的合作、制度的合理性,还强调建构主义的观念、规范、认同的主导性。和合主义是一种兼容并包的概念,体现的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和合’,鲜有排他性。”②余潇枫、章雅荻:《和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7 期,第68 页。
可见,较之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安全研究范式,提倡“和合安全观”的和合主义与“广义安全论”更具有历史过往的解释性、现实困境的超越性与未来发展的包容性。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视和最有能力以“和”为本位来维护安全的国家之一。即在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和合治理”仍然可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和合治理”以“和合”为核心价值取向,以共商共建共享为重要原则,通过在实践中形成“和合体”“聚合体”和“竞合体”等不同治理类型,凸显其治理行为体的包容性、治理结构的多元性、治理过程的开放性以及治理价值取向的公正性,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①章雅荻、余潇枫:《和合治理:中国特色全球治理理论建构》,《国际观察》2023 年第2 期,第42 页。事实上,以和合主义与“广义安全论”为范式的“和合治理”,正是人类探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秩序所需要的价值引领,它不仅为一个流动多变的世界提供了独特的价值尺度,而且为人类未来走向展示了美好图景,为世界发展与普遍安全的实现揭示出一条“和而不同”的坦途。
结 论
安全本体论与安全认识论是“广义安全论”建构的重要前提。安全是一种什么样的“实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本体论问题;而考察安全又需要什么样的“视界”,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认识论难题。安全是一种关系性实在,关系的和合程度就是安全获得的程度。广义安全便是呈现人与世界“关系和合度”的安全,亦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西方与中国对安全的解读有着不同的历史渊源,西方人以理得义,中国人以象取义,都对安全作出了非常有意义的解读。不同的“场域安全”视界建构不同的安全场景、情景与前景。广义谱系中的安全,是一种关系性和合状态的适然,是呈现和合状态的共享性秩序,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如果说和合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为“广义安全论”建构提供了元范式,那么“广义安全论”是以和合主义为价值取向并帮助人类实现和合境界的安全理论,这一理论以和、和合、和合度、和合共生、和合共建以及和合共享等范畴为核心内容,力求实现人类自身的和合、人类与未来社会“超人类”(智能机器人或人机一体化行为体)、“非人类”(有生命的物质)乃至“外人类”(外星文明行为体)间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