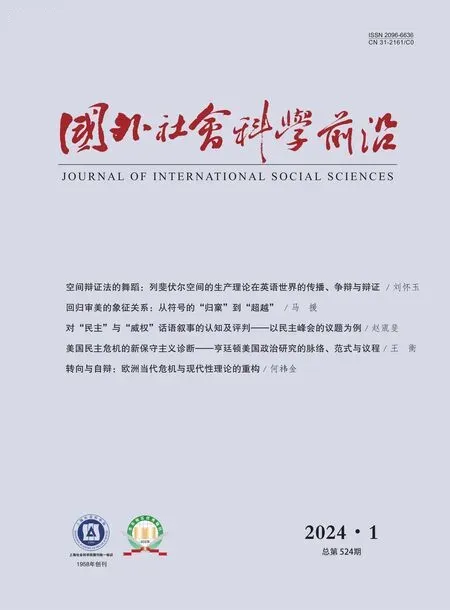回归审美的象征关系:从符号的“归窠”到“超越”*
马 援
象征是美学的一种标记,不只是因为象征作为一种常见的艺术手法,而且在于象征代表着人类社会关系的重要秩序,它承载着一定文化群体中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建立的意义关系,以及由此所展示出来的文化精神气质。因此,象征是与民族文化、集体经验、地方式沉浸联系在一起的。审美是一种感知与体验,它需要激活人浸润于艺术对象之中的情感涟漪。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强劲发展,这种审美与象征的贴合关系,逐渐随着文化一体化生产趋向离析与解体,这也意味着审美与象征秩序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关系的脱节。正如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指出的,“工业技术对象征控制的把持”①[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张新木、庞茂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1 页。造成了“象征的贫困,作为美学参与的丧失,孕育着一种心理和力比多的贫困”。②[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张新木、刘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36 页。原先审美接连的象征秩序,审美自然而然所流露的人与自然、人与现实生活的亲近,随着象征的贫瘠,源自象征秩序的审美情感受到了阻隔,也意味着人的审美力的感性独特性的遗失。
当代符号学家特别是受到“语言学转向”③参见马援:《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转向”及21 世纪新发展》,《哲学动态》2022 年第12 期。的影响,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等,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接壤,关注到了美学中的象征问题,“反思语言与社会历史的关系”,④Rosalind Coward and John Ellis,Language and Materialism,Routledge &Kegan Paul,1977,p.2.以符号学的独特视角,追问象征的价值和回归象征的意义。他们拉动符号与象征之间的关联,分析原始象征秩序的符号系统与现代性社会符号编码秩序之间的本质区别,以象征关系的新变化洞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矛盾,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借用同一性、同质化和相对主义的符码操作,对来源于礼仪、风俗、习惯和风尚的象征秩序形成破坏。为此,他们力图以符号学重返象征秩序的母体,超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限制,恢复象征的审美驱力,搭建符号栖息的理想家园。本文正是围绕着这一主题,从符号的“归窠”到“超越”,阐明符号与象征被分离之后的复归路,在符号学介入中分析象征秩序如何招致破坏、又怎样使之复原和重塑,进而重新构建符号意义系统的真正价值秩序,追回审美感知之中的象征关系。
一、以符号介入象征与审美的连接
“象征”与“符号”无论从词源学还是从生成过程来看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在西语中“符号”常用“symbol”来表达,而“symbol”也可指“象征”。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现代符号学者也正是在符号具有象征意义的关系中谈论符号的,而非将符号作为“sign”记号或者标记来理解,凸显了符号与象征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符号”“象征”“审美”一直以来就是无法相互绕开的词项,艺术作品通过具有象征意蕴的符号来显示其美学价值。例如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H.Gombrich)在《象征的图像》⑤贡布里希的《象征的图像》以图像志的方式,在对曼泰尼亚《帕尔那索斯山》、拉斐尔的签字厅壁画、朱利奥·罗马诺建造的茶宫中风神厅等的解释中,把神话、占星术、宗教、寓意结合在一起作为构成文艺复兴时期象征体系进行了探讨。——作者注中,以图像志的方式阐释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与象征的关系,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置于当时庞大的象征符号集合中去考察,可充分地感受到“符号”“象征”“审美”之间的内在接连性。又如解释人类学派的创始人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在对符号与象征关系的论述中指出:“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①[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11 页。他将文化作为连接符号与象征关系的通道。然而,符号作为“symbol”的象征意义正在被瓦解,逐渐靠近“sign”记号的意义和功能,同时,美学构成中的符号也随着符号与象征关系的断裂而失去了象征性。
因此,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现代符号学在接连象征与审美的关系中首先恢复了符号与象征的关系。它所具有的人本主义符号学②现代西方符号学发展主要有两大支脉:一支是以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为代表的具有人本主义特征的符号学,另一支是以皮尔斯符号学为代表的具有实用主义特征的符号学,前者关注于符号的社会属性,后者强调符号的生物属性。人本主义符号学的焦点不是纯粹逻辑导向的符号,而是侧重研究符号的社会功能。——作者注的特征将符号与象征关系置于社会关系之中,以符号与象征关系透视社会关系的变化,实现从文本符号向人的符号化对象世界的转换,从而以象征与符号的关系释义“符号”和构建符号学理论。人本主义符号学在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为源头“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特别在历经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开启下,巴尔特、克里斯蒂娃、鲍德里亚、詹姆逊、威廉斯、伊格尔顿在具有象征意义符号的释义中,一方面以符号学切入对“文学理论”“文化研究”“话语理论”“精神分析”和“叙述学”理论交互的思考,另一方面以“符号化对象”“人的符号化活动”和“符号化世界”对“消费社会”“身份”“权力”和“认同”作出观照现实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现代符号学在复原符号与象征的关系中,走出了索绪尔“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形式”与“内容”二元对峙的格式塔语言符号学,将作为抽象语言的符号、作为文本语言的符号拓展到广泛的符号化的世界,借助“符号”作为洞察社会历史变迁的微缩镜。在反思索绪尔建立系统内差异性的符号理论的基础上,他们将符号从封闭内在系统转向与对象世界和现实世界相关关系的研究,注重符号在“对象世界”与“观念世界”“现实物”与“意义之网”“历史真相”与“文化表征”之间的嫁接作用,也就是彰显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解释。他们不仅将符号学作为思考人类社会结构的重要工具,显示其方法论意义,而且将符号本身视作构成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在基础,以人的符号化实践活动彰显符号学本体论和价值论的意义。因此,他们探讨的美学并不单纯指向某种技艺或者技法的美学,正如威廉斯对美学的论述中指出的,“特别在19 世纪,美学从一种关于感性的理论变成了一种新式的、特殊的,关于‘艺术’(其本身是把技艺重新概括为‘想象’技艺)反应的表述”,③[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156 页。而是在于注重美学中关于感知、意向和行为的多样性,强调源自人的符号化对象世界的审美创造性想象和审美反应,为艺术理论打开了与人的丰富的符号化世界相连接的场域。审美的驱力并不仅限于作品的自律性,而是在文化意义模式的象征关系中,将人现实的符号化活动作为符号象征关系的来源,强调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在人的社会活动和符号化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审美感知。
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现代符号学对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解释蕴含着两条思考路径:一条是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符号意义,诠释社会历史运动中结成的符号象征秩序;另一条是符号学原理的考察,从结构和层级关系上对符号象征关系的分析。他们以符号一体两面“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强调在意义关系中谈论符号的形式,同时,嵌入在一定结构关系中呈现符号展开的内容,从而展现对符号具有象征意义的释义。
第一,在社会历史的延展中呈现符号象征关系。巴赫金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在符号理论的分析中,强调符号生成的物质基础以及符号活动客观现实的运动条件,即符号勾连了对象世界与意义、物质与意识、现实与观念的通道,彰显了具有象征关系的符号内涵。符号的象征形象依附于符号的物质形式和符号的材料,符号的象征关系生发于有机自然秩序的土壤。符号不是简单的标记,而填充丰富的内容,刻录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巴赫金打开了人本主义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接壤方式,引起了克里斯蒂娃、詹姆逊和伊格尔顿的关注,他们从不同视角批判索绪尔把符号作为封闭语言系统“记号”的唯心主义符号观,指向了符号生成的物质材料、现实环境,以及符号与现实世界相互作用的现实场域,展开了对符号与象征关系的研究。
他们认为符号代表着人类文化的凝合,以符号的方式传递着具有历史意义的制造物、社会设置和信仰系统,作为延续仪式、宗教、观念和精神气质的意义系统,因此,符号不能单一用来作为对象世界的记号,而是深入在社会历史之中,根系古老文化而拥有象征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激活符号的象征关系,珍视象征所意蕴人类社会与自然母体的接连,珍重现代文明与孕育着以血缘、民族和种族为纽带的古老文明的联系。他们认为,符号不仅具有象征性,而且其象征性具有秩序感,而符号象征的秩序感源自人与自然的贴近关系。符号的象征秩序是内生于自然规律之中的人造秩序,体现着人对自然界存在规律的发觉和遵循。
例如,鲍德里亚在对“象征”的阐释中调用了另一个语词“交换”,象征交换秩序的变化表征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人类社会交往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价值秩序的变化。在原始社会存在着“库拉”和“夸富宴”的象征秩序,传达着氏族、仪式、膜拜纠结在一起的复杂社会体系。原始的象征关系代表了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紧密联系,就其中鲍德里亚所谈的“死亡”来说,指向了原始社会在交换中溶解“死亡”的“秘传仪式”,这种象征交换关系建立了人与自然馈赠与反馈赠的流通,以及在此基础上结成的各种社会组织关系。
伊格尔顿借用莎士比亚《冬天的故事》中斐迪南搏击巨浪的这个象征性隐喻,表达了人类文化活动与自然关系的张力,反观走向与“自然”相对的人类中心论,强调自然关系中的文化生成。他以历史文化语义学恢复“文化”(culture)与“自然”(nature)的词项接连关系,指出“文化的原始意义是耕作,那么它既暗示着规范,又暗示着自然生长”,①[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3 页。而符号象征意义正是在人类对自然文化的活动中,在文化符号的实践过程中得以组建和展开的。符号象征关系内生于自然世界中,体现了人类依循自然规律而产生智性运动的过程。
第二,符号学理论框架下的象征问题。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现代符号学借助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不同视角在观照符号象征意义与现实世界关系的同时,进一步从符号学系统分析符号在表意过程中的位置结构,以“历时”与“共时”的共变关系彰显符号的象征意义。其中,代表性的探讨包括巴尔特的“象征层”、克里斯蒂娃的“象征态”,以符号结构的层级关系和符号运动所处的状态推进符号象征关系的分析。
为了显示符号的象征意义,巴尔特对符号在展开过程作出表层信息和意指、表象与象征的分层考量,对符号结构进行了三层级划分:第一层是所指与能指关系层,也就是符号的信息层和传播层;第二层是意指层,也称为象征层,即向象征科学开放;第三层是意指活动层,即多余意义的理论。②参见[法]罗兰·巴尔特:《显义与晦义》,怀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42 页。他指出:“象征意识在符号的深层维度上看待符号。”③[法]罗兰·巴尔特:《文艺批评文集》,怀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248 页。巴尔特所展开的包括文学符号学、文化符号学、图像符号学和叙事符号学都指向了符号的象征层,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在这一层关乎人的想象、信念和理想之类精神的东西才能被释放出来。
克里斯蒂娃以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进入符号学,结合了符号产生的心理机制和社会基础,形成了意指过程中符号态与象征态的辩证张力,分析符号过程中充满社会象征秩序与主体阐释的双向构成关系。她以“意指实践”洞察处于“子宫间”具有“断裂”“破坏”“分裂”特征的符号态,与置于社会历史秩序拥有“相似性”“联合”和“交换”特征的象征态之间的运动关系,用“镜像”“菲勒斯”“俄狄浦斯”和“阉割焦虑”一系列精神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内在心理活动与社会象征秩序,即符号态与象征态,不可分离构成了符号的运动。
二、符号象征秩序的“归窠”:对资本主义符码操作的审美批判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现代符号学从象征秩序观察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征,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以“同一性”“均质化”的符码操作,篡改了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使得符号从象征关系落入消费关系。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符码操作产生对象征秩序的干扰与破坏,使现代社会与根系传统价值体系的原始秩序发生“断裂”,人类古老文明遭致鲸吞,原先古老的审美圣坛也遭受到了摧残。为此,他们借助符号象征秩序的“归窠”,瞄准现代资本主义的诟病进行深度批判,具体呈现为:
首先,以符号的象征“归窠”,介入对现实社会的观察。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现代符号学反思现代社会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符号竞技场,揭示资本逻辑编织的符码秩序,在具象化和现实的社会场域凸显符号象征关系的变化。他们以符号面向现实、折射现实和参与现实的过程,接连“符号”“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的关系,为符号学打开了聚焦社会现实问题的场域。
例如,巴尔特在对符号学的阐释中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历险”,他认为符号学并不是怎样的一种科学,而是记录“个人性”但又“非主观性”的“遭遇者”①[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历险》,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3 页。在纷繁复杂的符号能指链中的各种历经。巴尔特正是以符号学的“历险”或者是“遭遇”的方式,去呈现消费主义符号的逻辑秩序,揭示资产阶级利用对符号象征关系的篡改,将具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隐蔽性地编译和转码成理所当然的普遍常识,从而打造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大众消费审美。又如,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以符号变体对比分析了资本主义工业时代前后工人阶级文化生活方式的变化,揭露20、30 年代充满“有机”“鲜活”“富有特质”和“内生与生活之中”的工人阶级文化符号,“让位于”五六十年代之后以“棉花糖的世界”“新大众艺术”和“失去行动张力的流行文化”的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消费市场,这样一来“‘普通人民’的城市文化被摧毁”,②Richard Hoggart,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class Life,Chatto &Windus,1967,p.10.工人阶级习以为常、口耳相传和照例下去的风俗礼仪和道德准则被腐蚀,具有工人阶级特质的符号象征秩序遭受“断裂”,沦为琳琅满目大众文化的审美娱乐。
其次,以符号的象征“归窠”,对比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与原始社会的符号秩序。其中,鲍德里亚、克里斯蒂娃关注社会人类学家像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所建立的社会象征与语言符号关系的探讨,认为象征关系接连原始社会秩序的基础,符号的象征秩序赋予事物特定的象征意义和分配着社会象征的角色。他们借助符号象征秩序对原始社会秩序复原,对比资本主义社会的符号序列。
例如鲍德里亚就以“死亡”与“象征”的关系对比分析了原始秩序与资本主义秩序之间的区别。他借助莫斯的交换与馈赠的观点阐释象征的意义,指出“象征不是概念,不是体制或范畴,也不是‘结构’,而是一种交换行为和一种社会关系”。他认为,象征构造真实与想象之间的乌托邦,它消解了灵魂与肉体、人与自然、真实与非真实、出生与死亡的二项分离,而现代资本逻辑脱离了原始思维中的死亡意义,造成生与死的失联,人在异化、无馈赠、无交换的死亡中与自己对峙,失去了符号的象征秩序。又如,克里斯蒂娃以“献祭”的符号象征关系回溯了原始社会秩序的建立过程,“献祭”方式使得“所指”找到某个单独位置的“能指”获得稳定的社会关系,实现对象物、自我意识和社会契约关系的确立。她认为,资本主义改变了原始社会以“献祭”建立起来的社会象征关系,以资本逻辑的想象关系构建其秩序,原先直观的“所指”与“能指”的象征秩序被隐秘的资本主义秩序所替代,“所指”与“能指”的关系没有相遇而被分裂。
再次,以符号的象征“归窠”,揭示符号象征秩序滑落于消费主义的符码生产。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现代符号学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运行逻辑不仅是对生产秩序的操控,而且侵占了人与对象世界黏连的精神秩序,符号的原始象征秩序被遗弃,资本主义符号秩序表现为消费主义的符码生产。
比如,巴尔特对文化意指的阐释特别表现在对消费社会中时装消费的分析。他将时装消费的典型特征——“流行”放置于语言文字符号编绘的“流行体系”中,揭示消费社会如何用服饰符号与修辞系统的接连造就了流行体系的经济学,也就是以“流行神话”簇拥之下大众的盲目消费。
鲍德里亚用“丰盛”“全套商品”和“节日形象”勾勒了消费社会的景象,揭示在消费主义主导的社会中人与物的关系已经从单纯的使用关系转变成由广告、商标等组合而成具有“集体隐喻”符号意义链的消费逻辑,符号从“物体系”转向了“消费品的象征符码意义”。也就是“消费的主体,是符号的秩序”,①[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226 页。整个社会关系包括物品、等级、消费、需求、享受、娱乐都落入了消费符号的秩序。与此同时,大众传媒簇拥符号消费不断膨胀式发酵,以动机、诱导和欲望驱动人们在看似节日一般的消费社会中沉沦。
詹姆逊指明现代资本主义虽替换了符号象征的内容,即原始象征秩序,但保留了象征的形式和神秘感,将象征关系转嫁给消费社会的符码生产。他借用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费利克斯·伽塔里(Félix Guattari)“关于解码的涌流观点”,展示从原始世界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符码变化,在“解码”与“重新编码”的流变中,资本主义以组织化、中心化、领土化的方式对散落或者弥撒的“原始编码”即“原始世界,一个有无数口传故事的世界”,②[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王逢振、王丽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234 页。进行重新统一化编码或规范。资本主义正是利用对原始神话或原始代码的重新编码和排序,从而编织渗透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庞大符号系统,构造出看似符合“因果律的超级编码”秩序。
最后,以符号象征“归窠”的结构系统,分析资本主义符码操作是如何干扰和破坏符号象征秩序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现代符号学重新看待符号的现实语境,将当代资本主义所呈现的复杂符码图式进行符号学透视法的剖析,通过对符号内部“能指”与“所指”关系,以及符号之间横截面“聚合”与纵向“组合”不同层面的分析,结构化地剖析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符码操作产生新的符号体系,并与原有符号秩序割裂的。
巴尔特在符号关系的运动中揭示资本主义符码生产所处的符号层级。他将符号的意识关系分成了象征意识、聚合意识和组合意识,其中,象征意识代表了如地质层一样的符号深层关系,有一种垂直性地“所指”统摄“能指”的状态,承载意识和附着丰富的意蕴现象,但是,符号的意识关系中不只是象征意识,还加入了聚合意识和组合意识的作用。他进一步指出,符号在象征意识中“所指”与“能指”是“双边关系”,而在聚合意识中改变了一对一的“所指”与“能指”链条,以同质逻辑聚合了多对“所指”与“能指”,产生了至少“四边的关系”,在这种作用下排空了“所指”保留了“能指”,形成了“能指”与“能指”接连,产生了脱离“所指”的“能指”间滑动,并且,再加上组合意识在话语层面以邻近原则躲避语义意识而追逐形式,进一步加速了符号“所指层”的消解,对符号原有象征意识形成损坏。现代资本主义的符码生产正是利用加剧“聚合意识”和“组合意识”并萎缩“象征意识”,走向了符号脱离精神的操作性生产。象征意识的削减意味着以象征姿态构建的关于信仰、价值和实践体系的衰退。
鲍德里亚用符号的三级仿像说明现代社会符号象征交换关系的丧失。“一级仿像”遵从古老义务所牵连的原始象征秩序,符号与真实连接,能指依附于所指;“二级仿像”服从机器制造物所产生的工业生产系统和维护操作原则的内在秩序,符号与现实表象相脱离,成为与真实之间失去联系的符号的自身空转;“三级仿像”以模式生成秩序替代工业生产秩序,符号以自身为对象形成了符号再生产的新领域,符号仅参照能指。符号在三级别的仿像中表现出来的特征,从“复杂的、充满幻觉的”原始象征符号,变成“粗野的、昏暗的、工业的、重复的、无回声的、运作的、有效的”生产交换中的符号,再到“代码的黑匣子”“发送信号的分子”“更小的不可分单元”和“代码数据”①[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12 年,第74 页。再生产的符号。符号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象征意义、意指意义和精神气质,从symbol 的关系沦为sign 的关系。
以上分析看到,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现代符号学正是以符号象征秩序的“归窠”,说明符号象征秩序具有凝合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价值取向以及标识人类共有的文化精神的意义,由此揭示资本主义符号化生产对符号象征关系的遗弃和破坏。符号被卷入资本循环的生产中,符号从“象征”的关系转变成符号“内容”与“形式”以及“灵”与“肉”的裂解,“能指”依托于“所指”的关系转变成单向度“能指”或“形式”的操作,符号成为一种再生产,符号“所指”“灵”的地位被“能指”链的复制与剩余所侵占。
三、符号从“归窠”到“超越”的象征秩序:激活美学的革命功能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现代符号学在借助象征秩序“归窠”对资本主义符码生产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美学具有的革命意义。在这些学者看来,资本主义对符号扭曲化的操作不仅造成了符号灵与肉的分裂之痛,而且符号“能指”的现代性生产、复制、加工和包装的不断加速,形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能指”大规模剩余。为此,他们调动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内在结构以及符号的实践作用,对由资本主义符码操作造成符号“灵”与“肉”分裂的再裂解,因为只有加速资本主义符码操作的“死亡”,才能回归符号“灵”与“肉”的再度结合。符号聚集着一种解构旧秩序、孕育主体性和建构新秩序的驱动力,以“语言反抗自身法则的起义”①[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12 年,第273 页。达至对符号象征秩序的“超越”,复归美学的真正价值。
第一,以符号的对抗性冲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裹挟,加速资本主义符号逻辑的内爆。巴尔特将符号学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方法”,②[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历险》,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3 页。指明符号学关联着整个文明的象征系统和语义学系统,是对资产阶级批判的利器。他针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符号挤压和变形的分析,通过对神话修辞术和流行体系的符号学解构,以“去神话化”“祛魅化”的方式揭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遮蔽的历史事实,发挥符号学真正的动力美学,即具有裂解资本主义符号操作的革命功能。
符号的对抗性在鲍德里亚那里突出的表现是,以引动“死亡”作为标志。在他以“仿像”全景式地描摹前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符号特征时,一方面将“死亡”置于原始秩序“象征”关系的阐释,另一方面把“死亡”作为符号美学革命的动力,工业时代需将“数量等价关系”“等价法则”“价值商品规律”和“技术经济代码”的链条关系推向死亡,而后工业时代则需加速“目的性”“声望”“地位”和“社会分化”区分性对立的死亡,在符号自身死亡中重获自由与解放。无论是二级仿像还是三级仿像,都脱离了符号的“所指”和“灵”的关系,剩下的只是符号的“能指”“形式”和“空值”的残留,而符号的美学革命就在于消散能指,因为只有消除堆积和残余的“能指”才能使阻滞的符号在交换与循环中重获生机。鲍德里亚以加速携带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符号“能指”的内爆,也就是编织各种附带资本逻辑的符号形式的死亡,引向人类生产的解放和爱欲的解放。
第二,以意指实践唤醒主体意识。这集中于克里斯蒂娃的思想。她将符号的“革命”安置在“文学实践”又或称为“诗性语言”中,以“诗性”或“晦涩的”符号形式打破社会固有样态,通过符号的“驱力”,在结构化和解构化的实践过程中,对社会中停滞、消极和固化状态加以改造。她强调意指实践对建构主体的意义,提出主体的自我确认是在充满“符号态”与“象征态”辩证张力的实践过程中得以实现。她认为,存在于“子宫间”的“符号态”是主体生发精神和驱动力的能量场,包括具有发生学的意义“压缩、置换、吸收和排斥、抛弃和停滞”的驱力,而“象征态”的运动来自社会结构的支配,包括“物的差异和具体的、历史的家庭结构”①[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诗性语言的革命》,张颖、王小姣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16 页。,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感受到了来自“符号态”与“象征态”的不一致而产生的一种对抗的驱力。主体意识正是在“前俄狄浦斯”到“俄狄浦斯”再到“反俄狄浦斯”的反复过程中而不断唤醒。按照她的观点来看,主体的形成和自我意识的运动正是在切割母体中的自我、接受他者关系的自我和重新组织能指关系的自我中循环产生的,从而达至符号象征关系的“超越”方式。克里斯蒂娃的这一思想对巴尔特产生过一定影响,巴尔特在对音乐实践的分析中,以“嗓音的微粒”②[法]罗兰·巴尔特:《声音的种子》,怀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6 页。解除民族习性导向的束缚,刺激和激活听众的自我意识,强调音乐作为一种意指活动的意义。
第三,符号在肢解“能指”中重新构建理想符号的美学家园。这些符号学家对资本主义脱离“所指”产生单链条“能指”生产进行批判,将这种失去内容和意义的符号能指“祛身化”。鲍德里亚强调索绪尔革命直觉的“易位书写”,也就是诗歌的快感在于打破“人类词语的基本法则”,③[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12 年,第272 页。以符号自身的消散摆脱符号被束缚的规则、挣脱符号被冗余的价值以及解除符号被固定化的秩序,实现对普通语言学基本原则的“超越”。他将符号最终的归途引向“死亡”或者“内爆”,以消散“能指”将所有既定的法则、规定和秩序一同消散。同样,巴尔特认为符号的“显义……便总是革命”,④[法]罗兰·巴尔特:《显义与晦义》,怀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46 页。因为它不像“晦义”产生无所指的能指和造成多余的意义,“显义”不会留下符号的剩余和话语的残渣,能指在意指实践过程中消耗殆尽。
巴尔特、克里斯蒂娃将符号的革命性存储在对符号法则的反叛中,不只是像鲍德里亚以符号“内爆”肢解权力和消散“能指”,而且进一步调动意指实践中主体的角色,呼唤主体意识的觉醒,提出了符号革命的实践方式。巴尔特提出符号的理想模式在于不断激活具有主体真正想象力的符号生成机制。他以意指活动“呼唤”和“唤醒”主体的想象,使想象关系生发于对“所指”的提取和对主体内心的服从。符号的“形式”与符号承载的“敏感的观念”以宽泛的想象接连在一起,延展具有创造性的符号实践功能。克里斯蒂娃强调从“现象—文本”到“生成—文本”的过程中,强调借助主体参与而形成文本的多重意义,彰显意指活动中主体性的意义。
整体上看,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现代符号学以符号的对抗性、意指实践活动和肢解“能指”冗余,打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裹挟,逾越资本主义符码操作对灵与肉、真实与想象、内在自我”与“外在自我”的离析,以符号实践作为主体获得解放和重生的途径,从而使符号发挥凝铸精神而作用现实的革命力量,达至符号象征秩序的“超越”,通达人类符号化活动的理想栖息地。
四、结语
现代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密切的接连关系。这些深入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之中的理论家,试图把符号作为微缩镜以揭示资本主义工业化审美象征体系的遗失。他们警觉到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以疏离符号与原始象征秩序的关系,建立了一整套美学的新话语方式,以资本主义符码消费来营造大众娱乐的审美效果,打造了同一性、同质化而排斥日常生活感觉、经验和感知的商业制品的审美。为此,他们试图在符号、象征和美学之间寻求力量,复原符号与象征关系的接连,使艺术创造中的符号趋向于亚历山大·鲍姆加登(Alexander Baumgarten)对美学的追求,即处在理性与感性的一种创新性平衡姿态,也就是达至一种完满的感觉话语形式,而非脱离生活世界对人真实审美感受的压制和控制。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现代符号学对美学抱有政治诉求和理想愿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转变成符号的批判,将符号、象征与审美引向人与自然、对象世界与自我、词与物互为关照的秩序中,回归审美中的象征特质,释放出美学的政治功能和革命力量,达至美学之中理想诗性般的符号宜居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