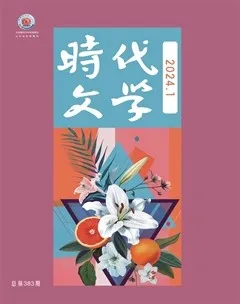黄渤海的对歌
高方
从黄海出发
若干年前,黄河多次注入黄海,浑浊的泥沙将近岸海水由蓝色染成黄色。这是“黄海”名字的由来。
我的二姨夫李大为从小生活在黄海之滨的青岛,他喜欢一个猛子扎进海水里,像一条矫健活脱的鱼,游向太阳升起的地方,眨眼便不见了踪影。
1965年的一天,身穿白T恤的李大为像一叶船帆,风儿一吹,他便远航了,从黄海驶向渤海。传说那遥远的两海交界的地方,船经过时,都会轻轻颠簸一下。
带他跨过黄渤海交界外的那道风儿是一张红榜。那张熨帖地铺在墙面上的红榜,在一个清晨映红了他的脸。
发榜那日,他和三五个同学猫着腰钻过人群的缝隙,好容易凑身到红榜跟前,身体像没停稳的船,被人群的海浪挤得左右摇摆。排列整齐的黑色字体像跳跃的音符,一旦与眼睛相遇,便能点燃眸子里的烁烁之光。
“李大为”三个字,是被身边的同学发现的,那个同学狠狠拍了一下李大为的肩膀,继而抱着他的胳膊猛烈晃动起来,他的嗓门一路攀高,不断重复着:“你考上了!你考上了!”那喊声像海浪一样一起一伏,冲击着李大为的耳膜,让他感到一陣幸福的眩晕。
那一年李大为初中刚毕业,是一个十七岁的翩翩少年,他考上的是一所半工半读中专技校,隶属于一个保密单位,毕业后可以定向进入该单位工作。那个年代,考上技校就可以领到工资,是无比荣光的事。这所技校在青岛招生500人,李大为就是其中之一。
李大为只知道这个单位与“石油”有关,那时候一首铿锵有力的《我为祖国献石油》传遍大江南北,召唤着有志青年投身这条新征程。
我的姨夫李大为是在1965年8月的一天来到胜利油田的。学生大军先是坐着绿皮火车来到辛店车站,一辆辆解放卡车早已等候在车站,并接走了他们。坐在露天的车斗里颠簸着,李大为只觉得脑壳被晃得像散了黄的鸡蛋。
头顶的天空一片墨蓝,轻缀其中的几簇星星熠熠闪亮。悬在中天的弦月潜进了辨不出形状的一抹暗云。橘黄的车灯直直探向前方,被撕开的夜色在身后又四下围合起来。
秋风乍起,车轮扬起的尘土从细小的沙粒变成粗大的砾石,李大为的脸颊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从略有知觉地擦过,到像鞭子一样抽在脸上,阵阵生疼。
荒原暗夜
初到这片荒原,李大为眼里只看见两种颜色,一种是黑色,那是石油和暗夜;一种是白色,那是盐碱地和芦苇花。
黄河从这里入渤海,像一条摆尾的巨兽,留下一片狼藉的滩涂。李大为内心先是升起阵阵恐惧,努力恢复平静后,又被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助和感伤湮没。
学校还没有建成,教室刚刚搭好框架,同学们也参与到校舍的建设中。芦苇、泥巴做成的土坯砖,这种垒房子的方式叫“干打垒”,建造的房屋墙壁厚,冬暖夏凉。几个人一组抬土到地基里,一点一点把地面填平。
一间学生宿舍住十几个人,铁质的上下铺随一个翻身的动作吱扭作响。水管里流出来的水浑浊且苦涩,难以下咽,这些都让同学们想家的思绪一点点累加。一到晚上,经常有几个同学拉伙跑到大野地,抱头一顿大哭。
荒野的夜,是最难挨的。黑夜像一张无边的织网,宿舍窗户里的灯光微弱渺小,仿佛被风一吹,它便飘摇着没了踪影。
那时油田刚开始勘探,走十里八里见不到一个人。李大为常常一个人坐在荒野上,黄昏时分,目睹又红又大的太阳孤独而又辉煌地向下落。那一刻,他感觉到了一种巨大的能量充盈天地间,且像漫天的水汽一样正在升腾。在荒野中,一个人与黄沙、旋风是一体的,与日月星辰也是一体的。
后来,为了不让想家的情绪蔓延,同学们约定:不准掉眼泪。于是晚上大家便凑在一起唱歌,唱《我为祖国献石油》,大声朗读诗人艾青写给石油人的诗,“最荒凉的地方/却有最大的能量/最深的地层/喷涌最宝贵的溶液/最沉默的战士/有最坚强的心……”
年轻人们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主意了。——空旷的荒野里,不管白昼还是黑夜,用歌声来驱散恐惧和孤独。
一个夜晚,李大为抬头仰起了脸,他看到夜空中月亮正向一片云彩缓缓地飘去,转头时他看了一下倚靠在墙边的几个同学,他们也在抱臂仰头看着天空。
他们安静地看着月亮在幽深的空中漂浮,接近云彩时,那块黑暗的边缘闪闪发亮了,月亮便一下子滑进入了云彩。
当月亮钻出云彩时,他们的脸一下子明亮起来,像是投射在幕布上的剪影,随着嘴巴一张一合地歌唱,头也微微摇动,眼睛在黑暗里闪着灼灼的光。
这歌声像一把利剑,飞向遥远的天空,劈开漆黑无边的暗夜。在孤寂空旷的荒野里,在那个月光时隐时现的夜晚,歌声给予彼此长久的温暖和陪伴。
河海相遇的璀璨
李大为每日和荒原万物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长,变得越来越强壮。那些伤感的情绪逐渐暗淡下去,他舍不得拔掉任何一株枯草,舍不得清除任何一粒雪霰,他和万物一起生长。
其实油田的待遇还是不错的。食堂一顿饭四五个菜,馒头敞开吃,在那个年代已经很好了。
冬天发的工装也很有特点。为了固定所填充的棉花,常在棉衣外面压一道道衍缝,一件棉衣压了48条缝,这样的工作服被称作“48道杠”,是石油工人身份的标志。每年回青岛休假时,技校的同学们穿着“48道杠”在栈桥一起逛逛,就是一条风景线,过往行人都要投来羡慕的目光。
最开心的事当数去基地的邮局寄钱。上技校时每月发15元工资,成为正式员工每月涨到37元。李大为总是攒够七八十块钱,便一同寄回家。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全靠在医药公司工作的父亲一人支撑。能补贴家用,这让李大为觉得远离家乡的生活也有了奔头。
技校离油田基地有五六公里远,那时候没有交通,也没有自行车,甚至没有道路,工程车、油罐车常走过的地方便是路。站在路边,一招手,路过的车便停了。司机师傅一般都是年长之人,见到路边站着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总是很热情,不待对方招手也会主动停下来,问道:“要去哪里?用不用搭车?”
基地离海更近一些,李大为听同事讲过,黄河入海时,河水与海水的交汇处,黄色和澄蓝色的水相融,一些水沉入底层,另一些水浮起,它们起初有不同的皮肤和不同的温度,保持着自己的完整和独立性,最后相遇,浩浩荡荡相携而去。
1965年冬天,李大为也遇到了他携手一生的伴侣——我的二姨王秀兰。
作为支疆青年,二姨王秀兰半年后也来到油田技校。更加巧合的是,两人还是小学同学,后都被分配到了采油一队。
那一天,阳光明媚,李大为从人群里一眼便看到了我的二姨王秀兰。她身材高挑,两条麻花辫飘荡在纤纤腰间,像玲珑翘卷的凌霄花藤蔓,一双眼睛秋波流转。二姨天生一副好嗓子,站在人群里唱《南泥湾》时整个人更是像在发光。“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啊——”她将尾音咏叹唱得极为婉转,像一只百灵鸟直冲云霄。
两人恋爱结婚后,成了油田双职工。每天2小时一次巡井,检查井压力、生产情况,回到值班室记录下来。
作为荒滩上唯一活动着的人群,油田人在生产石油之外,还要承担防汛、粮食生产等工作。那时黄河经常泛滥,汛期时油田工人便爬上堤坝去值班,看到水涨到一定水位,就赶紧去叫人,扛沙袋垒土,阻挡险情。
油田还成立了农副业处、家属工作处,专门组织职工家属改造盐碱地,种植水稻。农忙季节,职工们都会轮流到农业点帮家属们插秧。由于盐碱地比较硬,总插不好,秧苗全漂浮在水面上。后来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每次插秧时,都会事先准备好一根小木棍儿。先用木棍在田里插一个眼,然后再把秧苗插进去按紧。这个法子当时还被当成经验传播开来,临出发前同事们都会互相问一句:“带好小木棍了吗?”
后来随着盐碱地技术改良,配备了插秧设备,慢慢地职工们也不用去农业点帮忙了。再后来油田专门成立了农工商总公司,形成了工、商、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济发展的格局,极大支持了油田的开发建设。
1972年,姨夫李大为被调入油田电影队工作,每周都要到油田各小队驻地去放露天电影。那时候看电影是唯一的娱乐项目,一听说有电影队要来,同事们早早就用马扎子在广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每个石油小队都有自己的家伙什,竖杆子,把幕布扯上,电影队只管带来机器和影片。放映的片子有国内电影《地道战》《地雷战》等,还有一些样板戏和国外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等。
各石油小队为了犒劳电影队,还会在电影结束后,为他们精心准备夜班饭,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肉。
战井喷
1973年,姨夫李大为调入胜利油田工会做宣传工作,这让他有机会深入一线,记录下更多油田人的生活,他拍摄的照片也经常发表在油田内刊《胜利报》上。
他曾经把镜头对准一群孩子,拍下最温馨的一张照片。画面里两个看起来八九岁模样的小姑娘在空地上练武术,她俩穿着红色对襟上衣,黄色百褶裙,马尾用红绸子高高扎起。一个小姑娘从背后高高翘起一条腿,另一个小姑娘扶着她的胳膊和脚,帮她保持平衡。后面站着一排男孩、女孩,有舞剑的、舞棍的,纷纷操练起来。他们身后的背景是被称为“磕头虫”的抽油机井场。1978年,胜利油田采油指挥部小武术队成立,孩子们放学后一边练武,一边等父母下班。油田基本都是雙职工,井场边长大的油田二代为冷冰冰的机器增添了无限生机和活力。
1982年又一口高产油井被开发,李大为扛着相机和三脚架早早等在井口旁,他将喷涌而出的油气置于画面前端,远处的高坡上则站满了围观的人群。这种透视的角度特别壮观,拍这张照片时,井口那个最佳拍摄点围了七八个记者,相机也挤在一起。
李大为还拍过一组战井喷的照片,这组照片只有一个色调:泥浆色。抢修的人群也被喷成泥浆色,光看照片都觉得惊心动魄。
所谓井喷,就是井底压力太高,把地层的油自动喷到地面上来。高者一二十米,犹如碗粗。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天然气,哪怕一丁点火星都会酿成一片火海。每次碰到喷出这样的油,施工时工人们都格外小心,生怕冒出火星。
1983年4月29日,永69-1井在施工作业时发生强烈井喷,这是胜利油田历史上罕见的强烈井喷。半天时间,100多个大气压的油气流裹着泥沙,咆哮着从地下直蹿空中。井筒内连接在一起的长约250米的32根抽油杆像离弦的箭一样直刺天空,随后又盘旋着落在地面。重达14吨的抽油机被整个吞入地下,不见踪影。由于井下套管破裂,井口周围塌陷,形成了一个直径达十几米的大坑,坑内泥浪翻滚,气流肆虐,在五六里以外都能听到它的咆哮声,看见冲天的黄色气柱。
当听说指挥部抢喷领导小组要组织一支抢喷突击队时,所有的作业工人都抢着报名。首批抢喷突击队队员,由党员干部和有着丰富抢喷经验的技术工人组成。
现场气浪滚滚,声响很大,趴在耳边说话也很难听清楚,现场讲方案、下指令基本都是通过一块小黑板。抢喷领导小组连续实施了两套方案,压井都没有成功。大家毫不气馁,又研究制定了第三套方案。在吊车的配合下,他们奋力将大型高压闸门推向井口。装上大闸门后,大家迎着凶猛的气浪,穿上螺栓,上紧螺帽。就这样,经过多次舍生忘死的较量,凶猛的“气老虎”终于被制服了。这次抢喷历时68天,无一人伤亡。
相机定格的画面还有1986年3月的孤东会战,一万余名职工和民工投入战斗,大干一百天,没有星期天。电气大队员工足蹬脚扣子,背靠安全带,一天在杆上作业近十个小时,为节约时间,就用安全帽把饭提上来,在电线杆顶上“吃空中餐”。那是激情燃烧的年代,工人们轻伤不下火线,只要能走得动,一定要去上班。
2009年之后二姨和姨夫退休,花甲之年的老两口回到黄海之滨青岛生活,那段奋斗于渤海之滨、承载着岁月芳华的记忆暂时封存。
新景
2023年的初秋,我随青岛作协采风团来到了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市,见到了姨夫李大为人生故事里的热土。
这里已经没有一点荒滩的影子,我的眼眸被绿色充盈。被候鸟和草木围拢的抽油机,依然重复着自己“磕头虫”般的动作。
行车时,我们路过一片盐碱地作物种植基地,大片的向日葵扬起黄澄澄的脸庞。一位作家拍下一张照片发在朋友圈里,起名叫《奔跑的向日葵》,因为行车的视觉差,那些被拍得模糊的向日葵像在奔跑。后来陆续见一些作家在朋友圈里发出自己的即兴诗作,多少都有提到这“奔跑向日葵”的场景。原来我们都爱这向阳而生的花,它生长得如此热烈。
如今得益于黄河上游的治理,黄河已不再随意摆尾,它带来甘霖和丰厚的养料,广袤的黄河三角洲孕育出黄河口大米、黄河口大闸蟹等众多独一无二的黄河口农产品。其中黄河口大米还成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是一张凝聚着地域特色的城市绿色名片。
随着水稻种植业的发展,以田为画板、以稻为笔的稻田画架起了链接创意农业与休闲旅游的新桥梁。每年8月开始,广袤稻田里占地约260亩的巨幅稻田画进入最佳观赏期。稻田画题材每年不同,今年勾勒的是“乡村振兴 农业强国”“耕农田 耕心田”两幅富有寓意的主题图案,颇有一番田园诗歌的意蕴。
早在五六月,农人们便用芦苇秆定点,将黄、白、紫、绿、黑、红六种颜色的水稻秧苗插入田中,勾绘成平面图。到了八九月,各种颜色的稻子长成,便呈现出震撼人心的视觉效果。
观赏稻田画的最佳角度是登上30多米高的观景台俯瞰。我们一层层拾阶而上,迫不及待拿出手机相机,记录眼前的大美風景。空旷的田野里清香满溢,稻田阡陌交错,彩色水稻相映成趣。风吹稻浪,宛若画卷微动,目之所及一派波澜壮阔的田园风光,令人惊叹。
如今稻田画已成为网红打卡地,是旅游富民重要项目之一,全年接待游客几十万余人,成功创建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
稻香时节我们还可以狠狠过了一把大闸蟹瘾,李白曾有诗形容其味之鲜美——“蟹螯即金液”。喝着微咸的黄河水,吃着鲜美水草、小鱼虾长大的大闸蟹,颜值自是不凡——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轻轻一声脆响掰开蟹壳,只见膏满黄肥,入口更是唇齿留香。
与稻田毗邻,东营黄河口大闸蟹标准化养殖面积已达8万多亩。凌晨天不亮,养殖基地的渔民们便乘船来到黄河口养殖基地,拉出预先放置好的地笼,一个个挥舞着鳌钳、鲜活生猛的大蟹子便被捕捞上来。
早在四五月份投放蟹苗之时,外地客商便纷纷赶来,预订下这肥美大闸蟹的收购买卖。如今“黄河口大闸蟹”的金字招牌越来越亮。
秋天,是一首动人的天籁。孕育了无限“丰景”的黄河入海口,俨然成为候鸟乐园。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年几百万鸟类组成“飞行编队”,在稻田上空穿梭,声声脆鸣划破云彩,栖息湿地安家,形成“飞时遮尽云和月,落时不见湿地草”的壮观景象。东营因此成为东方白鹳全球最重要繁殖地、黑嘴鸥全球第二大繁殖地,并荣获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美誉。
凭栏远眺,黄河入海时,黄蓝泾渭分明,犹如凡·高笔下的星空色调。黄河落日,红霞漫天,天与地之间,绘就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
回到青岛后,我把手机里拍下的照片一一拿给姨夫李大为看,他戴着老花镜,连连点头,说道:“拍得不错,后生可畏!”能得到他的认可,我内心欣喜万分,嘴角都咧到了耳根。
姨夫起身,走向一个橱柜,拿出蒙灰的胶卷相机,说:“我还是喜欢胶片,那种感觉好。”我知道他说这话时,心底按捺不住一股倔强。他一边擦着相机,一边讲起了开头的那些故事,像翻动一本发黄又清晰的日历。
那天他坐在窗前,逆光之下,我看到了一张剪影。无数奔波于黄海、渤海之间的人们,他们留下了时代奋斗的诗篇,藏在时光盒子里,等待某个瞬间被开启。
窗外涛声依旧,哗哗,哗哗哗——先是一个浪头,后有更多的浪头加入这节拍,那是黄海与渤海间澎湃的对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