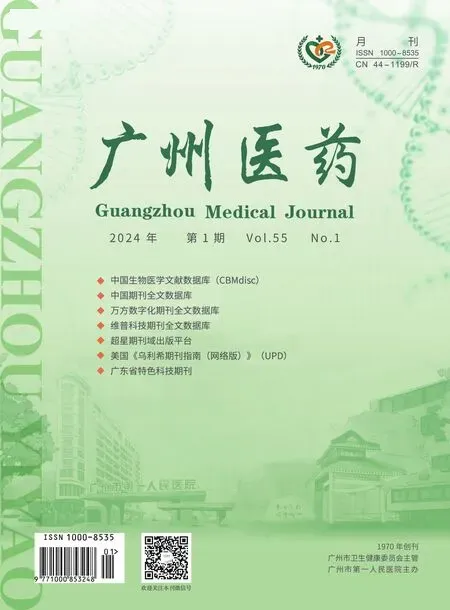结直肠癌的早期诊断策略和治疗进展
黄 庆 索彩霞 何 凤 罗青青 李旺林 曹 杰
华南理工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广州消化疾病中心(广东广州 510180)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世界上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二大原因。筛查可降低CRC的发病率和病死率。我国CRC发病率逐年上升[1]。全球范围内,CRC的发病率位居第3位,病死率位居第5位[2]。我国每年新发病例约占全球的20.5%。广州市CRC的发病率和病死率是广东省最高值[3]。目前,我国CRC的现状是:发病率高、五年生存率低、病死率高。
大多数CRC生长缓慢,由腺瘤性息肉或无蒂锯齿状病变等前体病变引起。这种缓慢的生长(约10年左右的时间)使筛查早期癌症和前体病变的时间窗口成为可能[4]。然而,在大多数发达国家,CRC筛查的依从性仍然很低。有多种CRC筛查方式可供选择,包括基于粪便的检测,如粪便免疫化学检测(fecal immunochemical test,FIT)和多靶点粪便DNA检测;基于血液的测试,如循环肿瘤DNA及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CTC)的检测;以及基于影像学的检查,如高分辨率MRI(high-resolution MRI,HR-MRI)、软式乙状结肠镜检查和结肠镜检等。根据人群风险、医疗资源以及患者和社会价值观,全球CRC筛查指南各不相同。本研究旨在总结目前国内外CRC筛查方式和指南的证据,并综述CRC治疗领域的进展。
1 基于粪便的检查
世界上大多数CRC筛查项目都依赖于粪便潜血(fecal occult blood test,FOBT)检测[5]。粪便潜血试验已被证明可以降低CRC的发病率和病死率,这些项目每年或每两年检测一次。FIT是一种粪便潜血检测形式,FIT是对检测粪便中血红蛋白的愈创木脂方法的改进,使用对人血红蛋白具有特异性的抗体,而不是非特异性的过氧化物酶反应[6]。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FIT阳性阈值为 20 μg/g(每克粪便中血红蛋白微克)。可以改变阳性检测的阈值,以更好地将结肠镜检查需求与可用供应相匹配[5]。Lee等[7]在一项荟萃分析中显示,FIT阳性阈值20 μg/g诊断合并CRC的灵敏度为0.79,特异度为0.94。
在世界范围内,在大多数进行CRC筛查的国家,建议于50岁开始筛查。笔者团队对2011—2015年广州市人群CRC进行筛查分析[3],选取30~79岁居民进行CRC筛查。对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和(或)FOBT评估高危人群,建议进行免费结肠镜检查。研究结果显示,广州居民CRC和腺瘤检出率分别为1.17%和20.60%。60岁以上人群CRC检出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明显高于年轻人群。但对于40岁以上的人群,腺瘤和晚期腺瘤的检出率高于年轻人群。因此,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进行CRC筛查,会使更多人群获益。此项筛查结果已被纳入中国早期CRC筛查流程专家共识意见和2020年中国CRC筛查与早诊指南[8-9]。
2 血液检测
早期血液检测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和糖类抗原199(carbohydrate antigen199,CA199)是临床上应用最为广泛的CRC的生物标志物,但其敏感性和特异性较低,不适合作为筛查或诊断标志物,主要用于预测术后复发。近期CRC血液生物标志物研究集中在不同类型的循环生化分子,例如血液中的肿瘤DNA、血液中RNA、血液中的蛋白质等。这些生物标志物可通过血液蛋白定量检测或免疫组化检测,血液采集或者献血的便利性意味着基于血液的生物标志物的检测可以成为CRC的适用筛查工具。
2.1 循环肿瘤DNA检测
在肿瘤发生的早期阶段,大部分散发性非遗传性癌症都存在遗传异常。大量携带这些异常的细胞从发育中的肿瘤中脱落,并且可以在生物流出物中找到,主要在粪便、血清和尿液中以游离核酸的形式存在[10]。它们可以作为检测CRC的生物标志物,或提供相关的诊疗信息。循环血液中存在有游离的DNA,这些游离的DNA包含肿瘤特异性基因组信息的改变,具有基因突变、甲基化、杂合性丧失和微卫星的不稳定性[11]。腺瘤向癌症发展的过程中涉及各种遗传和表观遗传学的改变,如“微卫星不稳定”和“染色体不稳定性”。在细胞进行有丝分裂的过程中,如端粒酶结合导致的DNA断裂和核苷酸切除修复基因的缺陷[11]。这些变化在DNA的修复、肿瘤抑制基因和凋亡基因的下调中被广泛检出。因此,对CRC的发病机制及其基本的表观遗传和遗传变化的详尽了解对于开发有效的诊断工具至关重要,这些工具可以作为诊断CRC的生物标志物。
截至目前,游离DNA已被广泛评估为CRC诊断、预后和治疗反应监测中液体活检的新型生物标志物[12]。Bettegowda等[13]通过分析206例转移性CRC患者血液中游离的DNA信息,发现临床相关的KRAS基因突变的灵敏度为87.2%,特异度为99.2%。
2.2 非编码RNA检测
非编码MicroRNA(miRNA)是非编码RNA的一个亚类,目前循环miRNA在疾病发生的CRC早期诊断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CRC的单个miRNA分子标志物可以在血浆或血清中检测得到,也被认为肿瘤诊断的标志,Kalimutho团队研究了来自648例CRC粪便样本的miRNA,并评估了使用粪便miR-144诊断CRC发病的可能性。结果表明,miR-144在CRC患者粪便样本中的表达具有高度显著性,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达到74%和87%[14]。因此,他们认为使用miRNA表达谱可为粪便中的CRC筛查提供合适的工具,但是单种miRNA作为CRC早期诊断的分子标志物精确性较差。目前相关检测是联合多种miRNA诊断CRC。例如:miRNA-21、let-7g、miRNA-31、miRNA-92a、miRNA-181b、miRNA-20等多种miRNA联合检测来判定CRC的早期检测[15]。
2.3 CTC的检测
CTC来自于原发肿瘤或转移瘤的上皮癌细胞,脱落进入循环系统,可在外周血中检测[16]。可作为检测CRC的生物标志物。CTC是指血液循环中来自原发肿瘤、转移或复发部位的细胞。CTC可单独或与成纤维细胞、白细胞、内皮细胞和血小板共同构成细胞集群簇,形成肿瘤微栓,具有较强的传播、转移能力[17]。然而,CTC的检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血液中CTC浓度很低,被检测到的可能性很小,因此该方法具备一定的局限性[18]。
3 直接可视化测试
3.1 结肠镜检查
在大多数筛查计划中,结肠镜检查通常作为初始筛查试验阳性的后续程序。2000年,美国联邦医疗保险批准每10年使用一次结肠镜检查作为筛查方式,随着CRC发病率的逐年上升,结肠镜检查量大幅增加[19]。多项病例对照和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接受结肠镜检查筛查的人的癌症病死率比未接受结肠镜检查的人低29%~68%,并且对近端和远端CRC都具有保护作用。Baxter等[20]使用SEER-Medicare数据(n=10 292)研究表明,结肠镜检查降低了远端CRC病死率(OR=0.40;95%CI:0.37~0.43)和近端CRC病死率(OR=0.58;95%CI:0.52~0.64)[21]。值得重视的是,在随机试验中比较依从性时,结肠镜检查的依从性低于FOBT及FIT。因此,在CRC筛查方案中,结肠镜检查最好作为两阶段筛查级联的第二步。
3.2 软式乙状结肠镜检查
软式乙状结肠镜检查是直接观察远端结肠的另一种选择,当检测到息肉时,可转诊进行结肠镜检查。有几项大规模试验比较了一次性或重复软式乙状结肠镜检查与不筛查,其结局可降低CRC发病率和病死率。在美国,一项大型筛查试验随机分配了154 887名55~74岁的个体,与常规治疗相比,每3~5年接受一次软式乙状结肠镜检查,发现CRC发病率和病死率分别降低了21%和26%[22]。软式乙状结肠镜检查所需的资源与结肠镜检查相似,但需要结肠镜检查来跟进FIT阳性和软式乙状结肠镜检查的息肉患者。因此,在美国,软式乙状结肠镜检查的筛查率有所下降。
4 影像学检查
影像学检查可以有效地对CRC进行分期,其准确性对治疗起到了很好的指导效果。CT可用于结肠癌TNM分期,或者MRI禁忌证的直肠癌患者。研究显示CT在结肠癌中,检测T3~T4肿瘤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7%和81%,在检测淋巴结受累方面准确率较低[23]。另一项研究也显示,CT在CRC的T分期上较准确(特异度和灵敏度超过80%),而在N分期上准确度仅为69.3%,灵敏度为74%,特异度为67.1%。CT在N分期准确率较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不同淋巴结大小的阈值的判断会导致灵敏度和特异度较低。人工智能和影像组学的运用令CT能更好地诊断淋巴结转移,一项研究显示,通过一种影像组学列线图可以较好地预测CRC的淋巴结转移情况[24]。Chen等[25]也通过直肠彩超、直肠超声弹性成像和CT结合的多参数影像组学能有效地预测直肠癌的淋巴结转移。MRI作为直肠癌的常规项目已被写入指南。HR-MRI的应用使直肠癌T2~T4分期的诊断准确率得到了明显提升,且在检查时用适量超声耦合剂充盈肠腔与使用水相比,可进一步提高图像质量(97.37%vs82.86%)[26]。淋巴结(lymph node,LN)转移是影响直肠癌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且转移性LN与反应性、炎性肿大LN的影像学表现较为相似,导致CT与MRI对转移性LN的检出准确率都不甚理想,不过MRI的检出准确率总体优于CT。Jia等[27]利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和直肠腺癌原发病灶影像组学特征的列线图模型,评估术前直肠癌非肿大淋巴结转移的价值,发现其在发现阳性淋巴结上具有一定的优势。Liu等[28]使用MRI评估淋巴结的化学位移效应、淋巴结边界、淋巴结短轴直径以及到直肠癌或直肠壁的最短距离,通过多因素的列线图来预测直肠癌淋巴结的阳性。内镜超声可以有效地判断肿瘤浸润的层次,对于直肠肿瘤的T分期具有明显优势,尤其是在T1、T2分期上;与MRI结合可以更好地诊断直肠癌的分期。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PET-CT)指南不常规推荐做,对于病情复杂或者常规检查不能明确诊断的患者可作为有效的辅助检查。PET-CT可推荐为CRC临床分期及评价治疗效果的备选方法,一般使用于术前初始分期Ⅲ期以上肿瘤患者,PET-CT有助于发现或确定其他影像方法漏诊或疑诊的远处转移病灶[29]。
5 CRC 治疗新进展
5.1 CRC手术治疗及进展
CRC的诊治已经迈入多学科、综合治疗的时代,但外科手术治疗仍然为CRC治疗的主要手段。新的外科理念出现,新的手术技术应用提高和成熟,使CRC根治手术完成度更高,也使CRC的疗效和患者的长期生存率得到不断提高。目前CRC的手术治疗从方式上来说包括:开腹手术、腹腔镜手术、机器人手术和经肛手术等手术方式。目前无论哪种手术方式,都是在“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TME)”和“完整结肠系膜切除术(complete mesocolic excision,CME)”的共识下进行的。CME、TME的理念是基于胚胎发育过程中形成的完整系膜筋膜,肿瘤细胞的脱离、转移一般不会超出系膜筋膜,手术过程中分离系膜筋膜与周围组织的间隙,完整切除“肿瘤包裹”从而达到根治的目的。
CME和TME的理念目前已得到结直肠专科医师的普遍认同,腹腔镜和机器人的高清放大作用令CME和TME完成率更高、完成质量也更好,同时这种高清放大作用也促使低位直肠癌的保肛率得到了更大的提升。在CRC手术中有两种手术方式难度比较大:腹腔镜下括约肌间直肠癌根治术(intersphincteric resection,ISR)和腹腔镜辅助经肛门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ransanal TME,TaTME),笔者中心常规开展这两项技术并对其做了相关的研究。笔者团队总结的Meta分析显示ISR手术于传统的腹会阴直肠癌联合切除术(abdominoperineal resection,APR)手术具有优势:ISR手术住院时间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与APR组相比降低;然而两组之间的肿瘤学结局相似[30]。笔者团队的回顾性研究分析也显示,ISR对于选定的超低位直肠癌患者是安全且可行的,在特定患者(小肿瘤/远离肛门边缘)中具有临床优势,肿瘤学结局与APR相似,ISR后的肛门功能评估良好[31]。现在高清3D腹腔镜和机器人手术的应用,使ISR手术具有更明显的优势,笔者中心在2020年就完成了机器人辅助ISR手术。TaTME手术对于超低位直肠癌具有明显优势,在保留神经和肛门括约肌功能等方面有优势,并且能够在狭窄的骨盆中操作时将直肠吻合到更低位或肛管。近期汪建平团队[32]的TaTME研究结果显示,TaTME与腹腔镜全直肠系膜切除术(laparoscopic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laTME)对比,无论是手术的安全性和肿瘤预后均接近。笔者团队2015年提出了简易TaTME手术,是较早开展TaTME手术的单位之一[33]。研究结果[34]显示简易TaTME手术能提高低位直肠癌的保肛率和改善患者生存质量,拓宽了保肛手术的适应证,并且易于开展。
5.2 CRC放化疗治疗及进展
CRC的化疗历史悠久,化疗方案也基本是几种常规药物(奥沙利铂、5-氟尿嘧啶、卡培他滨、伊立替康等)组合。放疗主要针对的是局部晚期的直肠癌,或者是局部复发的CRC患者。近期的临床热点研究主要集中在新辅助放化疗和晚期CRC的化疗。研究显示直肠癌新辅助放疗对于直肠癌患者总生存期无影响,但放疗增加了手术难度,同时放疗后的并发症(放射性肠炎、肛门功能差等)往往令很多结直肠专科医生试图去放疗化。笔者医院参与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的一项多中心研究也提示[35],495例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被随机分配在术前氟尿嘧啶联合放疗组、术前改良输注奥沙利铂+氟尿嘧啶+亚叶酸钙(modified infusional fluorouracil,leucovorin,and oxaliplatin,mFOLFOX6)联合放疗组和术前mFOLFOX6 组。中位随访45.2个月后,各组3年无病生存期(disease free survival,DFS)概率分别为72.9%、77.2%、73.5%(P=0.709),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1.3%、89.1%、90.7%(P=0.971)。研究显示,与氟尿嘧啶联合放疗相比,术前mFOLFOX6在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中,联合或不联合放疗均未改善3年DFS;未发现未放疗的mFOLFOX6与氟尿嘧啶联合放疗的结局差异。同时,近期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发表了大型研究结果[36],该研究纳入1 194例局部晚期直肠癌(T2淋巴结阳性、T3淋巴结阴性或T3淋巴结阳性且适合保留括约肌手术的直肠癌)患者,术前FOLFOX组585例,术前放化疗组543例。在中位随访58个月时,FOLFOX组在无病生存率方面不劣于放化疗,两组在总生存率和局部复发方面相似。他们得出结论:在符合保留括约肌手术条件的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中,术前FOLFOX在无病生存率方面不劣于术前放化疗。对于晚期CRC的化疗研究也是热点,晚期CRC的患者一般营养状态很差,三药化疗往往很难坚持,再加上奥沙利铂的药物堆积不良反应严重,低不良反应药物的化疗维持是一种选择,近期研究显示晚期患者可考虑使用三氟尿苷-替吡嘧啶联用贝伐珠单抗维持治疗[37]。
5.3 CRC靶向治疗及进展
CRC的靶向治疗主要包括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及受体为靶点、针对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为靶点的靶向治疗及多靶点激酶抑制剂类药物的应用[38]。以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及受体通路为靶点的抗肿瘤血管生成药物包括单克隆抗体(贝伐珠单抗、阿柏西普、雷莫芦单抗等)与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瑞戈非尼与呋喹替尼[39]等)两类。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为靶点的靶向药物主要有西妥昔单抗和帕尼单抗。近年来,CRC靶向治疗领域涌现出一些新的治疗靶点与治疗药物,包括在其他实体瘤中已经得到证实的HER-2(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拉帕替尼)、BRAF(靶点维莫非尼、康奈非尼)、新兴的靶点神经营养原肌凝蛋白受体激酶基因(neuro trophin receptor kinase,NTRK)及KRASG12C。拉罗替尼、恩曲替尼可通过对NTRK融合的抑制作用有效治疗NTRK融合的CRC;KRASG12C抑制剂目前得到了有效的研发,并有望在近两年获得KRASG12C突变结肠癌的批准[40]。
5.4 CRC免疫治疗及进展
免疫治疗目前在CRC治疗中仍是一种新的治疗方式,并且在过去的几年中,取得了很好疗效,尤其是在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中疗效明显。与传统治疗相比,免疫疗法可以通过激活抗肿瘤免疫来杀死癌细胞,并且专门针对癌抗原以防止正常细胞受到攻击。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1,PDCD1,PD-1)/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1 ligand,CD274,PD-L1)抑制剂作为目前免疫治疗的一个重要的免疫制剂,于2006年首次用于人体以来,现在已应用于许多肿瘤的治疗。PD-1是激活T淋巴细胞表达和介导免疫抑制的最重要受体,而PD-L1参与程序性死亡,导致T淋巴细胞凋亡或无能。CRC免疫治疗的突破源于2013年发布的一篇报道[41],研究显示1例微卫星不稳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high,MSI-H)的右半结肠癌晚期患者于2007年7月接受PD-1治疗9个月,患者获得了临床完全缓解(clinical complete response,cCR),随访复查3年未发现肿瘤复发。免疫治疗对于DNA错配修复缺陷(mismatch repair-deficient,dMMR)/MSI-H直肠癌患者的疗效非常明显,2022 ASCO年会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同步公布了一项PD-1单抗新辅助治疗局部进展期dMMR直肠癌Ⅱ期临床试验结果,研究使用了一种PD-1单抗(dostarlimab)治疗 dMMR的Ⅱ期或Ⅲ期直肠腺癌患者,12例患者单药治疗了6个月,未行手术和放化疗的情况下12例患者的肿瘤全部达到了临床完全缓解,在随访期间(范围为6~25个月)没有肿瘤进展或复发的病例,并且未出现3级或更高级别的不良事件[42-43]。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丁培荣、张晓实、潘志忠教授领衔的多中心团队回顾性分析了PD-1免疫治疗后发生cCR的dMMR/MSI-H直肠腺癌19例患者[44],其中有16例患者接受抗PD-1免疫治疗作为一线治疗,11例患者接受抗PD-1抗体单药治疗,从治疗开始到cCR的中位时间为3~8个月,在达到 cCR 后的中位随访17.1个月中,未观察到局部或远处复发,整个队列的两年局部无复发生存率、无远处转移生存率、无病生存率和总生存率都达到了100%。徐瑞华团队使用我们国产的信迪利单抗PD-1对直肠癌进行Ⅱ期临床实验,研究显示在16例dMMR/MSI-H直肠腺癌患者中,有12例出现完全缓解,其中9例患者选择了观察和等待策略,中位随访17.2个月后,所有患者均存活,且无患者疾病复发[45]。尽管PD-1的免疫治疗对dMMR/MSI-H的CRC患者疗效好,但这部分患者仅占CRC的5%~15%,而占85%~95%的错配修复功能正常CRC患者对免疫治疗效果欠佳。针对该问题,许多研究集中在联合化疗或放疗以提高疗效的策略上。许多传统的化疗药物(如奥沙利铂、5-氟尿嘧啶和吉西他滨)可以调节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作为免疫原性细胞死亡诱导剂,以重新激活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中的抗肿瘤免疫[46]。因此,化疗与免疫治疗相结合可以促进免疫反应,增强免疫治疗的效果,进一步达到改善患者临床预后的效果。同时也有许多研究显示,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在临床上可以达到1+1>2的效果。放疗可以通过诱导肿瘤抗原释放、增强肿瘤细胞免疫原性、激活免疫细胞和分泌免疫因子并促进肿瘤相关抗原呈递来有效激活抗肿瘤作用,从而达到提高免疫治疗的作用[47-48]。
6 总结与展望
CRC筛查有几种选择,每种选择都有其的表现特征和实践注意事项。在目前的实践中,主要的非侵入性选择是FOBT或FIT,因为其具有良好的灵敏度、低成本和易于使用。目前有多种基于血液的CRC筛查测试处于不同的评估阶段,而且在国内外是作为实验室开发的测试销售。结肠镜定性检查和影像学的方案等手段目前临床在积极应用中。
目前CRC仍然处于高发状态,其治疗手段包括手术方式的改进、放化疗的优化、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新进展,使治疗效果得到了明显提升。然而,早期筛查方案的优化,完善早期诊断的策略,手术及放化疗药物治疗的改进,以提高早期诊断率、降低病死率,在CRC的临床和研究领域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