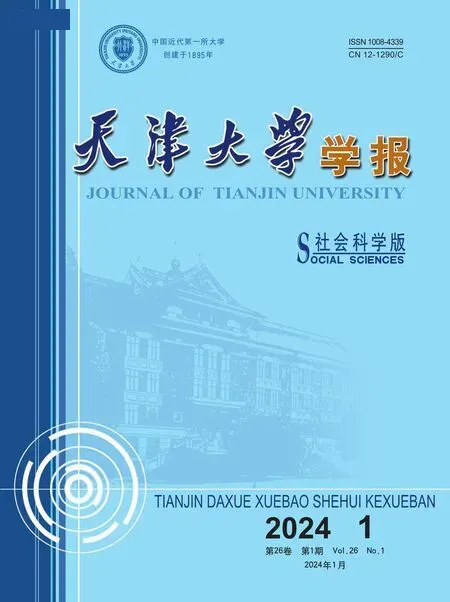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发展境况与现实转换
闫 涛, 李 樑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20 世纪后半叶,生态思想日益崛起。发展至今日,生态问题已成为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中心论题之一,生态思想亦成为普遍的思维范式和基础话语。哲学领域的生态哲学(环境哲学)、伦理学领域的生态伦理、美学领域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与文学领域的生态批评构成了当前生态思想争鸣的主要场域。自20 世纪90年代至今,生态思想成为国内学界持续探讨的热点之一,对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梳理和阐释成为生态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
一、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发展境况
生态理论的研究是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结果。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人类为实现进一步发展,就需要对自然进行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改造。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社会进步的无限性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两难抉择。因此,如何在实现人类更高程度发展的同时,又能避免对生态环境的过度污染、破坏,是生态理论研究需要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西方早期生态思想萌发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代表者是吉尔伯特·怀特(White Gilbert),他以书信体写作的生态文学作品《塞耳彭自然史》,标志着西方生态思想发展的开端,使得通行话语与研究范式为西方主导。而丰富庞大且历史悠久的中国古代思想被视为单纯的历史研究,在学界并不掌握主导权。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并无生态思想,对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现代阐释明显代替了历史研究;对自然的探讨也非古代生态思想的核心和本质特征,仅属于人生论的一部分。这种观点以西方生态话语权的强制力遮蔽了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本真面貌,割裂了自然与生态、人类与自然有机统一的关系。因此,应跳脱原有固定的基本预设和思维模式,明确万物本原并无固定形式,只有超越惯常,打破范式才能发现非常“道”,才能实现对中国生态思想的建构。
就生态思潮的发展态势和影响范围来看,面对通行的国际规则,我们似乎也很难打破现状。但可以通过对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探究,以寻回乃至掌握生态思想的话语权。
随着西方理论发展略显疲态,原有科学体系的构建逻辑无法满足社会进步的需求。在科学研究时,西方形成的是不断细分、注重抽象和逻辑、“实验性”“定量化”“公理化”“可实证性”的牛顿范式;非实证科学的“达尔文范式”“复杂性科学范式”等西方科学研究范式。而中国传统科学范式讲究和谐、自然,讲究顺物宜人、以技进道。例如,爱利亚学派的主要代表者巴门尼德认为:存在和非存在二者绝对对立、不能相互过渡,存在不能成为非存在,非存在不能成为存在。《老子·道经·第二章》中却认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万物皆以成对方式才得以具体显现,并处于不断相互转化的状态,宇宙间万物都处在变化运动之中的,事物从产生到消亡,都是有始有终、不断变化的,因变化和比较才得以存在,宇宙间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变”才是永恒的。因此,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思想研究领域,或重新阐释传统,建立起具有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中国思想,获得与国际思想界平等对话的机会,成为中国思想界认可的发展路径之一。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具有极为丰富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文化资源,就此而言,中国拥有西方难以企及的优势。而找到合适的视角和落脚点是构建中国生态思想的必要前提。生态思想主要借由对自然界一般的认识而演化、发展,其建立的基点在于人们实践所获得的对世界的系统性把握,进而通过人的理性思维运用其内在规律,使人的生产、生活活动与世界运动保持一种良性交互的张力。简言之,即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古人把自然视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基础,认为自然与人类社会相互交融、密不可分,把对自然的认知与人生修养的提高高度结合——以何种态度看待自然,便决定了或可转化为人之修养与精神境界。古人通过对自然的领悟,锤炼品性、净化情操、提升境界,达成精神的完备与修养的完成。古代中国对自然的温情态度、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崇尚、视自然为人之归属的思想,与当代生态思想有着颇多相合之处。这种历史的优势,使得生态思想极易为学界所接受。一些国外生态思想研究者难以在西方寻找到思想传统支撑,但颇为惊异地发现了古代中国却拥有着丰富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资源。他们对此的推崇与借用,坚定了国内学界对古代思想资源的信心。这不仅是对中国古代思想资源的肯定,亦展示了其现代特质。对国内学界来说,生态思想并不止西方体系,而更应当探索生态思想的中国话语。既然如此,为何不基于传统思想资源,立足于当代生态现状,重新审视古代思想资源,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当下实际的生态自然观以资益中国当代呢?
需要注意的是,对古代生态观的研究要基于客观的立场进行价值判断和本质判定。如果脱离了思想资源的历史文化语境,就会丧失其客观性,成为独立的非历史化的文本和纯粹的现代解读,使之彻底失去现实性。因为一旦历史语境被抽离,理论范式的优先性凸显出来,那么学术研究就成为纯粹的主观建构。要依照中国现实情况,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构建,从西方范式的“战胜、改造自然”转向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复归自然”。既放由事物从其本性发展,又不违背事物本身逻辑,才能达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
二、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逻辑理路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认为,万物皆分阴阳,阴阳衍生万物。人与万物皆由阴阳二气变换循环而生,因此,人与自然万物皆为同构,由阴阳二气生发,又将归于阴阳二气。人与万物相合,方可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1.天人一气
不同于被西方普遍认同的原子论,中国传统文化更认可元气论。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的初始时物质处于阴阳未判的形态、气形质混然一体未分离,这种情况下的物质形态被称之为“元气”,抑或太极。宇宙万物生成、变化乃是物质性本原的“浓聚”或“稀散”,也就是聚和散的变换循环。元气论基于有机论自然观且注重关系实在,研究的方法为整体、宏观、外拓。原子论则认为,原子方为世界本原,是一种最后的不可分割的物质微粒,原子身处虚空之中,外在因素的推动引发了原子的运动。以医学举例就是:西医认为疾病的产生是外源性的细菌、病毒,是衣原体等入侵主体的结果;中医则是通过人体内源性的阴阳盛衰来分析病理原理。中医认为,人本身内部阴阳是均衡状态,一旦阴阳失衡则会出现病理性症结,而万物中也有阴阳,例如植物、动物、矿物等,但它们的阴阳未必均衡,通过用植物、动物、矿物的阴阳之偏来纠正人体的阴阳之偏则可实现治病效果。
据《易传·系辞上传》所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阐明了宇宙从无极而到太极,以至万物化生的过程。无极化生天地万物,在无穷无尽时间与空间的场域中进行,空间的总集称为“宇”,而时间的总集则称为“宙”。混沌过后,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子会再开天,丑会再辟地,寅会再生人,新纪元又开始。形成一个往返不间断的周期性循环,这种循环是宇宙间自然规律的功能。而由太极衍生出两仪也就是阴阳两极,表示万物两两对应、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在“太极生两仪”时就开始划分阴阳了,其中用符号“—”代表阳爻,用符号“- -”代表阴爻,而“爻”就是错综复杂的意思。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一阴一阳之谓道”[1],阴阳,代表一切事物的最基本对立与统一,是事物内部两种固有属性和内在的矛盾要素。“气有阴阳”(《正蒙·神化》),“一物两体,气也”(《正蒙·参两》),就体现了一气分为阴阳,阴阳统一于气。物质世界在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下,不断地运动变化。它们是一切运动变化的根源,在原来阴和阳的基础上生出了新的阴和阳就叫四象,从卦象上分别称为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对应天象中的四象:青龙(东)、白虎(西)、朱雀(南)、玄武(北)。后又经伏羲氏推演画出八卦:乾、坤、坎、离、震、艮、巽、兑,分别指代天、地、水、火、雷、山、风、泽。八卦本质上是工具性的文字符号,由于万事万物基本构成要素具有同一性,所以古人以八卦来推演世间事物的构成以及相互关系。
世间万事万物皆存有阴阳,二者呈相互交错分布态势,往复循环,后又生成先后天之分。阴阳的盛衰消长及其升降沉浮机制有象无形,为自然万象之本,所以谓之先天;自然万物的生长化收藏俱象可触,为天地阴阳二气所化,所以谓之后天[2]。先天八卦主要阐释人与社会之间的四种关系,用自然界存在的八种事物两两相对应形象表达出来,这就是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主要从四时阴阳盛衰消长及其升降沉浮机制角度探讨天地造化宇宙万象的规律机制,所以本质上偏于形而上之道。后天八卦从字面上已经进一步抽象化,而且使八种事物彼此之间相互联系,震、巽、离、坤、兑、乾、坎、艮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内部是自我循环的,以此阐述四时之中自然界生命万物的生长化收藏之道,所以偏于形而下之道。后世先后八卦的名称也因此而来。但二者本原皆为先天太极,并无本质不同。“从先天到后天、从简单到复杂、愈变愈频、内在相互关联的宇宙生成规律,是一个气数推演模型,是‘道’的一步步展开与显现。”[3]
2.天人同构
从天地造化宇宙万象的规律机制到自然界生命万物的生长化收藏之道,表明在宇宙场域间的万事万物和现象变化中都包含着阴阳、表里两面。既互相对立斗争又相互依存转化循环的关系,是宇宙中物质存在的客观规律,万事万物的缘起生灭都要遵循于此。天地、日月、风雨、雷电、雄雌、刚柔、动静、显敛,万事万物,莫不分阴阳。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长养百骸。经络、骨肉、腹背、五脏、六腑,乃至七损八益,一身之内,莫不合阴阳之理。《天元纪大论》云:“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4]这也说明了阴阳乃是构成万物本身以及生存基本环境的始基。在《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中,基于阴阳而衍生的气化思想,同时涵盖了“气的运动变化”和“气的生化功用”两个方面。前者倾向于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后者则倾向于对生命变化的认知[5]。因此,始于元气这一基本概念,再衍生至阴阳、五行等,充分说明了在类的角度上人与自然本质上具有同一性,实际上构建了自然与生命沟通联结的桥梁。
“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存在于愚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6]在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神话图腾中都体现了远古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某些密不可分的因果联系,东汉末年徐整所著《三五历纪》描述了盘古开天辟地时:
“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后乃有三皇。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为星辰。皮肤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
这是最早的关于天人同构的神话记载,反映了人类祖先与自然本为一体,二者本身的构成要素具有同质性。在《灵枢·邪客》中便有“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的说法,就是将作为普遍认知中天地的结构和与人的身体的外在样貌结构进行类比。而《灵枢·岁露论篇》有言: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由此视角出发,会得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复杂的、对应互动关系,人体盈虚与天地相同,与万物相合。进一步推断可得出,古人关于自身身体与自然整体之间相对照的复杂关联是有一定整体把握的。但关键在于,究竟是依据宇宙万物本源及运行秩序来把握人身体构造及运动规律,还是依据人类身体构造及运动规律来构建天地万物运行秩序呢?抑或两者是同时地、双向地进行?这似乎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5]。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由于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新变化发生的同时也对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作用,这一点也体现出阴阳循环相互作用之理。《运气七篇·五常政大论》有云:“帝曰:善。一州之气,生化寿夭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高下之理,地势使然也。崇高则阴气治之,污下则阳气治之,阳胜者先天,阴胜者后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4]300-301
同处于一地域时,地势高的地方阴气居多,地势低的地方阳气居多,阴气常在的地方人寿命较长,阳气常在的地方人寿命较短。基于西方科学范式来讲的话,就是指“炎热的气候导致人体代谢加快、生命进程缩短,这一观念反映了一种更具思辨性、更高级的天人同构理论,即天和人不是在形体上的同构,而是气化上的同构。”[5]因此,中国古代对于自然的描写,大多都反映出视自然为人之归属的思想。虽然在早期的《禹贡》《水经注》等地理著作中,对荒野自然的描述亦带有恐惧色彩,将一些南方地区视为危险之地,如“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7]。文学作品《岭南江行》中:“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8],“瘴”成为中原对南方的典型认知。但在整体上古人对自然是持亲和态度的,天人合一就是其核心观点。无论处于何种时空状态下,为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人类必然要进行生产性的物质活动,必然存在对自然界的改造,这就会引发自然界原生状态的改变。但只要不超过生态系统维持及自我修复的能力,保持在一定限度内,便不会造成生态危机。古人通过长久以来对生活经验的总结,得出朴素的对于自然和生态的认知,虽存在一些局部性生态破坏行为,但没有爆发整体性的生态危机,一直处于可控范围内[9]。并且古人也会利用这种认知去保护自然,并写入律令,如《礼记·月令》记载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10]即使帝王狩猎也要遵守“采捕以时”的原则,历代统治者均不遗余力去实行山泽之禁。说明我国古人已经意识到了生态平衡之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如老子、庄子所强调的“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就已经懂得人类要与自然进行协调与适应。
3.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生态思想
正是基于天人同构这一基础上衍生出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生态观。《论衡·自然》中提及“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说明万物皆是因为阴阳二气的流转、交合而形成。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阴阳义》中提到:“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说的就是以事类相合来看,天与人是一体的,二者可以互相感应,达到天人浑然一体的境界。“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春秋繁露》)、“天地间无一物无阴阳”“离开阴阳更无道”。自然、社会,还有人体都是同构的,都是太极阴阳相互作用,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一步步演化而来的。天地与人类之间本源性、必然性的内在联系,突出了二者本身属于同一整体,也体现了天地万物对于人和事具有本源性的影响意义。传统儒家认为“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人处于自然万物之中,具有与万物的同一性,随自然万物的生灭而生灭,即“天人无间断”合而为一的完美境界。
人不是游离于自然之外的,而是类属于自然存在物的一种,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当然更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因为人本身就生活在自然之中,与自然为一体。如果妄想背离、控制自然,达到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状态,那样反而会束缚人类本身。处于自然之中当然也要遵循客观自然规律,自然之道不可违,要把自然法则看作宇宙万物和人类世界的最高法则,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效天法地”,即将天之法则转化为人之准则,并把它作为自身的行动准则。道家崇尚的“无为”并不代表不为,而是不妄为、不强为、不乱为,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季羡林对此解释道:“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蒙培元[11]认为,古代哲学是讲“生”的哲学,实质便是生态哲学。“在生态学的问题上确实是中国古已有之……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究天人之际’,其主流哲学则是‘天人合一’论。‘天人合一’的核心是‘生’的问题”,而“生”的实质不是别的,就是生态哲学。乔清举[12]亦认为,“中国哲学本质上是生态的”,曾繁仁[13]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可将之视为一种生命的生态文化。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我们说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生命的生态的文化。
所以,基于阴阳对于“生”的论述成为古代哲学思想与生态思想的内在关联。借此,古代哲学思想便形成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生态思想框架。古代生态观通过对自然现象的描述,呈现了人对自然的某种理解和其发展内在机制的深入探究,同时基于完备的阴阳八卦体系建立了以“以类和之、天人一也”为核心的生态观[14]。
三、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现实转换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华文明讲究天人共生之道,实现天人和谐共生,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既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也内嵌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逻辑链条之内。“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要以世界视角来审视未来发展之路、以人类整体命运为立足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以天人一气超越主客二分
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5]。
基于中国传统哲学视域,张世英[16]认为:“传统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思想,重点不在讲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讲‘合一’‘一体’,而不注重主客之分,不重视认识论。”实现了对于传统形而上学主客体二分的超越,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内在同一性,遵守按照自然客观规律办事的基本原则,追求可持续发展。要实现发展的前提就是要从广义的生态系统运行上遵守其内在规律,用生态、系统的观点,指导人类社会发展,使其与自然保护并行不悖,按照规律营造健康安全的近自然生态系统。在精神世界里,将生态学的观点和平等、公正观念精神化,从而形成崇高的生态精神,指导人类的社会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2.从天人共生到可持续发展
世界是普遍联系着的统一整体。21 世纪要以生态化的方式来引领世界发展方向,生态文明不单单是为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及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更美好的生活环境的向往,更是在世界各国普遍出现经济增长乏力的国际背景下,进一步推动社会经济实现良性发展、寻找新的助推经济增长“动力源”的关键环节。目前,产业资本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成为过去时,如果采用西方国家向外转嫁风险的过渡方式,则会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无疑是行不通的。因此应该调整方向,探索新的生产方式——绿色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把一味贪婪地从大自然索取的模式转向回嵌自然、回嵌环境、回嵌资源,这样才能既满足人类目前的需要,又不会对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造成危害。要从“天人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重视角出发,推进生态文明战略,运用系统思维解决生态问题。
3.最终指向: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基于阴阳二气,从天人合一的理念反映了人类与自然是共融共生、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提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理念就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要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主义和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作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内容[17]。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望本就不应局限于一国一地,理应是全人类共同的利益所在与价值追求。面对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不可逆的全球化趋势,世界日益发展成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形态”,各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利益联结的共同体。全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同一个自然环境中,断然无法只追求自身发展而不顾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也无法实现自身更好的可持续发展。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存,都有赖于生态系统的稳定[18]。在追求这一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全人类是这一过程的实践主体,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过程就是维护自身利益。把握生态问题的解决方法也不应只追求现实的“改良”,而应立足于历史长河,纵观发展趋势与规律。横向的就是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纵向的就是实现“代际公平”,而这两方面的规定性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新中国成立70 多年来,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接续奋斗和不懈努力,现在的中国既有责任也有能力去为世界提供一个可行的前进方向,提供一个符合现实情况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19]“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就是追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共同生存、相互支撑、共同繁荣。要基于中国传统哲学视域中的生态观,结合我国现实国情,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四、结 语
思想和理论不可能由纯粹的精神活动产生,而是基于对现实经验与实践的总结与升华。若探究中国古代生态思想传统,则要把思想与实际结合起来考察,避免潜在的判断。应对古代生态思想进行梳理,明确古代生态观的核心价值所在。避免出现割裂局部和全局关系、以局部代替整体,背离文本话语的强制阐释。因此,既要依据历史现实挖掘古代生态观,同时也要基于当下的具体现实性进行建构,对古代思想进行整体的梳理。除了历代典籍中关于自然的直接论述外,中国古代极为发达的山水艺术、园林艺术等也是研究的重要对象,应对其加以阐释、分析,建立起内涵丰富、层次分明、历史悠久且连续的中国生态理论,以资益中国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