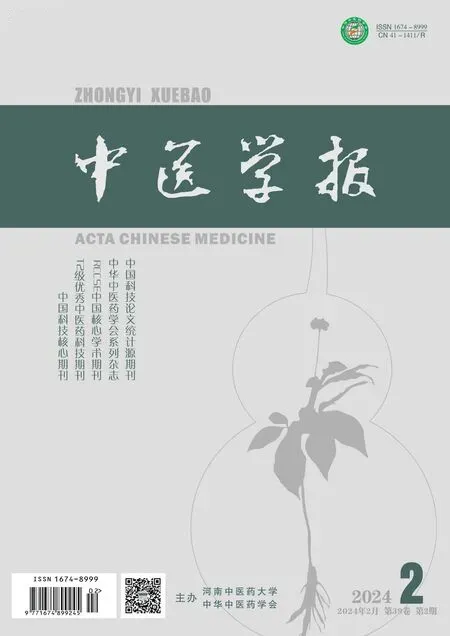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彩陶盆寓意与足少阴经功能相关理论渊源初探*
李建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北京 100039
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彩陶盆口沿处绘有8个点,这8个点正好将陶盆口沿分为八等分。在这8个点上交错绘有4个“十”字状纹和4个“米”字状纹。研究表明,这8个点表示“八方”[1],表明当时人们已有了“四正”“四维”之概念[2]。东、西、南、北四正方向标为4个“十”字状纹,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维方向标为4个“米”字状纹;4个“十”字状纹即天干“甲”字符号,4个“米”字状纹是甲骨文、金文“癸”字的祖源[3]。
彩陶盆口沿所绘的“十”字状纹“甲”在四正位置。此前笔者已论述,象征圭表测景(影)以辨方位、正四时,其寓意与“胆者中正之官”“胆主决断”“一阳为游部”“一阳为纪”等理论相关[4]。按照《黄帝内经》十天干配脏腑经络原理,天干“癸”与肾及足少阴肾经相配属,而彩陶盆口沿四维处所绘“米”字状纹“癸”的寓意与《黄帝内经》描述肾和足少阴肾经功能的相关理论是否有着渊源关系?“米”字状纹与“十”字状纹分布于彩陶盆口沿象征八方,这与少阴、少阳同主枢机理论是否相关?论述如下。
1 “癸”主水土平
1.1 “癸,冬时水土平”与“肾主冬”《诗经·鄘风》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毛诗诂训传》注曰:“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东西。”“揆之以日”是指在修建宫室之前要进行圭表测度日景以辨正方位。然日景测度是否精确,圭表所在地面的水平是其基础,故《周礼·考工记》曰:“匠人建国,水地以悬,置槷以县,眡以景。”“水地”就是通过水测定地平。
“揆”的本字是“癸”,《史记·律书》曰:“癸之为言揆也,言万物可揆度,故曰癸”。据《说文解字》“癸,冬时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从四方流入地中之形”之说及甲骨文字形,有学者指出,“癸”字的甲骨文就是以水测平的象形字[5]。还有学者认为,“癸”字的本义就是测平工具[3]。同样观点还见于元代《六书正讹》:“癸,交错二木,度地以取平也,义同准。”总之,“癸”的本义就是以水测定地平,而地平才能使用圭表测度日景以辨方、正时,故“揆”之测度日景之义为引申。
《说文解字》说的“癸,冬时水土平”是指古代房屋营造首选农闲之初冬,“水土平”就是以水测地平。而《诗经》所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宫”之“定之方中”也是指在西周、春秋时代的黄昏室、壁四星出现在正南方的初冬,是营建宫室的时节。《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指出:“肾为牝藏,其色黑,其时冬,其日壬癸。”《素问·脏气法时论》曰:“肾主冬,足少阴太阳主治,其日壬癸。”天干“癸”与肾及足少阴肾经相配属,且皆通于冬气。《素问·逆调论》曰:“肾者,水藏,主津液。”肾为水脏,具有藏精和调节人体水液代谢的作用。因此,肾与天干“癸”相配的内在逻辑当是肾主冬时、主水的生理功能可与“癸”的“冬时水土平”作用相参。
1.2 以水测平与“肾主水”“癸”能测平,其原理是水的平面可作为水平的基准,即以水平定地平,如《释名·释天》曰:“水,准也,准平物也。”《说文解字》也说:“水,准也。准,平也。天下莫平于水。” 《淮南子·说山训》说的更加言简意赅:“地平则水不流。”研究表明,人面鱼纹彩陶盆口沿处绘有的“癸”字符号与测平水土有关,人面鱼纹彩陶盆可以做为测水平之利器。这源于其内部空虚有盛水之用。如果将人面鱼纹彩陶盆埋入地下,使其口沿大体与地面相平,在陶盆内装满水就能看出地面的水平度[3]。
人面鱼纹彩陶盆的功能首先在于最大限度盛水、储水,而肾主水、主藏,其功能也如此。如《素问·水热穴论》指出了肾的盛水功能:“肾者,至阴也,至阴者,盛水也。”“少阴者,冬脉也。故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积水也。”《素问·上古天真论》曰:“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这说明肾有储存水液、精液的作用。如果肾水不平,则可能会失其“癸”一样的“测”地平的功能,盆水倾斜则会水溢胃土。“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溢于皮肤,故为浮肿。浮肿者,聚水而生病也。”因此肾有“癸”一样的“测”定地平的功能,与其盛水、藏精的功能有关。
1.3 “水静则平”与“至阴者,盛水也”“盛”有极点、顶点之义,《庄子·德充符》曰:“平者,水停之盛也。”这就是说要多装水就必须使陶盆位置水平,换言之,只有陶盆保持水平才能真正达到多装水的目的。平则静,故盆中之水静而不动是盆能多盛水和测平的前提。《庄子·刻意》曰:“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庄子·天道》曰:“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
《素问·水热穴论》的“至阴者盛水也”之“盛”也当有最大限度盛水储存之义。肾要想发挥如人面鱼纹彩陶盆一样最大限度盛水储精功能,也要保持“静”。在人体,劳则不静,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曰:“苍天之气,清静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这是说形、神不妄作劳则静,静则阳气固密,肾的封藏精气作用才可正常发挥,人体才能抵御外邪的入侵。
肾水之静,在于冬藏而不妄作劳,即“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如果形、神烦劳不静,则肾中之水液就如盆水之不静而不能测平一样,可导致水、土俱不平,即肾水涌动而易得风水病。故《素问·水热穴论》在指出“少阴者冬脉也”“至阴者盛水也”之后曰:“勇而劳甚,则肾汗出;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脏腑,外不得越于皮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为浮肿。本之于肾,名曰风水。”
在人体中,六腑与天相参,五脏与地相参,《素问·水热穴论》曰:“肾者,牝藏也。地气上者属于肾,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阴。”这里的“地气”当包括五脏藏精气功能,肾的“水平”则“地平”功能之“地”亦当如此。由于肾为“封藏之本”,受五脏六腑之精气而藏之,因此五脏要实现“藏精气而不泻”之与“地”相参的生理功能也需要肾主冬藏、主水的生理功能正常发挥。在这个意义上,“至阴者盛水也”也可以指肾藏精则五脏之精气皆充裕而隆盛。人体烦劳则肾水不静,不仅肾自身藏精功能失调致“髓海不足,脑转耳鸣”;还可致五脏之“地”的功能不平而厥气上逆,如地斜宫室倾倒之“坏都”一般:“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视,耳闭不可以听,溃溃乎若坏都,汨汨乎不可止。”
1.4 “水地以悬”与“冬应中权”圭表揆度日景不仅要求地面水平,还要求其必须与地平垂直,这样测度才准确。修建宫室也要求测量墙体及立柱的垂直度,这样宫室才牢固。我国自古就有利用重力方向总是竖直向下原理的重锤线法来检验一条直线是否竖直或一个平面是否水平的技术。与重锤线平行的线或面都是竖直的,与重锤线垂直的线或面都是水平的。如《考工记》中的“水地以悬”就是先用一根绳子悬挂一个重物以使圭表垂直的重锤线法。
重锤线法测平、测直,是圭表精确、宫室牢固的基础。在人体肾的应冬时主藏精“为固”的功能也用重锤线法来比喻。《素问·脉要精微论》指出:“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权”,古代计重的器具。冬应中权,是指冬季严寒,人体阳气需固密,人体阳气是否固密可以通过“揆度”人体脉象是否在冬季相应的如权具一样垂沉来判断。肾气发挥作用,人体气机便下垂沉降,肾的这一功能是其藏精功能的体现。《素问·六节藏象论》曰:“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精即人体浓缩之精华,其性重浊沉降,故神仙家也将之称作“真铅”,这是用以比喻肾精封藏、沉降有如重锤线之铅垂测平、测直使宫室牢固一样的“为固”人体的功能。
1.5 “精,正也”与肾“藏精”、胆“中正”具有测平功能的彩陶盆口沿所绘的象征圭表测景以辨方正时的“十”字状纹“甲”在四正位置,象征以水测平、取直的“米”字状纹“癸”在四维位置,两者相合共同标志出了地平上的八方。其寓意当与甲、癸在筑造宫室方面的相辅相成作用有关,而《黄帝内经》中与癸、甲相配属的肾与胆在人体也存在着这样的相互依存的生理关系。
《说文解字》曰:“精,择米也。”“精”的本义为挑选过的米,引申指事物中最好的部分。“精”还可与“正”同,即“精”可引申出“正”义。如广韵训“精”为“密”“细也”的同时,还训为“正也”。《黄帝内经》也有这种用法,如《黄帝内经》言胆为“中精之腑”,又言为“中正之官”。由于“精”可引申为“正”义,故也可说“精”是“正”的前提,如《黄帝内经》有言“不精则不正”,这在肾与胆的生理功能关系中也成立。肾藏精之“精”就是“精”字的“事物中最好的部分”之义,肾藏之精应“权”而“为固”,有“癸”之测平、重锤线测平、测垂直一样的生理作用。胆配天干“甲”为“中正之官”是因为其有圭表一样的作用[4],而地平及圭表垂直于地平是圭表辨方正时作用的基础、前提,故以之相参,则肾藏精之测平、测垂直一样的作用是胆为“中正之官”之圭表样作用的生理基础。这体现在肾和胆在一些生理功能的相辅相成上,如胆中精汁依赖肾的藏精功能,胆中春生之相火需要肾中精气、元气之气化;肾主骨,足少阳胆经主骨所生病;肾在志为恐,而胆主勇气、决断;少阳为枢,少阴为枢。
2 “癸”与“伎巧”
2.1 “劳乎坎”与“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尧舜时期有一工官叫“垂”,《尚书·尧典》云:“帝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垂”发明了规矩、准绳,准可测量水平,绳可测平、测直。上文重锤线法测平、测直就是绳的常见使用方法,故“垂”是以重锤线之垂直义取名。
“垂”又叫“巧倕”。《山海经·海内经》云:“义均是始为巧倕,是作下民百巧。”“巧倕”之“巧”,是指文中的“下民百巧”,《说文·手部》曰:“技,巧也”,“百巧”即古代的百工技能、技艺。“伎”与“技”通,段注:“古多叚伎为技能事”,故“下民百巧”又称百工伎巧。《鬼谷子·捭阖》曰:“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陶宏景注:“伎巧,谓百工之役。”按《考工记》记载,测平、测直技术即属古代百工之伎巧范畴,工官“垂”发明了规矩、准绳,负责管理百工,而以“垂”“巧”命名,足以说明测平、测直技术在百工伎巧中的重要地位。故有学者指出,所谓“巧倕”,“一是要使地平日晷的地面保持水平,二是要使地平日晷上树的立杆保持垂直”[6]。
《素问·灵兰秘典论》曰:“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平水土、筑房舍属于“百工之役”范畴,因此以“伎巧”来描述肾的生理功能,当与肾主冬应权、主藏精为固、主水有如“癸”“垂”一样的测平、取直功能有关。“作强”一词也与“百工之役”有关。在古代“作强”之事属于劳作范畴,劳作之事除农业生产外,就是“百工之役”。古代重农业而抑工商,聚众建筑宫室等“百工之役”主要安排在农业收获后的冬季,属官办劳役之事。《易经》后天八卦之坎卦在北方配冬季,并曰:“劳乎坎”即此意。肾之功能恰好可与官办劳役之百工技巧之事相参,又主冬时,其职能与人事之官职相参自然便是“作强之官”。《灵枢·九宫八风》将八卦之坎卦与冬季相配属,说明了《黄帝内经》时代仍承袭着无夺农时而“百工之役”在冬季这一传统。但冬主收藏,《黄帝内经》亦强调不可过劳,若百姓冬季过劳,“作强”过度而“夺于所用”则会肾虚,此时再感受“冲风”虚邪则肾病。故《灵枢·九宫八风》又指出:“风从北方来,名曰大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肾,外在于骨与肩背之膂筋,其气主为寒也。”
2.2 “二阴为雌”与“少阴者申也”敬天奉时、顺时施政是先秦时代的政治理念,举行祭祀、军事和兴土功等日常事务,顺时而动是一个重要准则。笔者以前的研究已经阐释,《素问·脉解》说的“正月太阳寅”旨在说明足太阳经功能和正月阴阳消长相参,这与正月是一年农耕的开始及祭祀农神后稷有关[7],这是敬天奉时、顺时施政观念在《黄帝内经》中的体现。正月是古人停止“君子周密”“君子居室”之收藏行为而要到室外耕田之时节,与之相反,十月则是寒冬的开始,是一年农事基本结束而营宅建室以躲避严寒的时节,故“少阴者,冬脉也”“肾主冬时”“主封藏”的生理功能当与十月初冬的敬天奉时行为相参。因此,《素问·脉解》曰:“少阴所谓腰痛者,少阴者肾也,十月万物阳气皆伤,故腰痛也。”合乎时令、医理。
然而,钱超尘先生在《黄帝内经太素新校正》引丹波元坚《素问绍识》云:“此篇以足三阴三阳配之六月,太阳为正月,厥阴为三月,阳明为五月,少阴为七月,少阳为九月,太阴为十一月。三阴三阳,每互其位,必隔一月,今本经七月误作十月殊为不伦,须从《太素》是正。”也就是说,《素问·脉解》原文当按《黄帝内经太素》所载为“少阴所谓腰痛者,少阴者申也,七月万物皆伤,故腰痛也。”郭霭春先生在《黄帝内经素问校注》一书中也持此观点[8]。
王冰对“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注释说:“在女则当其伎巧,在男则正曰作强”。以《素问·阴阳类论》“二阴为雌”之论述看,王冰对“在女则当其伎巧”的认识当指“足少阴肾经”所主之“技巧”功能可与女子之“技巧”能力相参。如果说男子作强之“伎巧”是指耕作、冬日测地平、筑宫室等事务,则女子之“伎巧”当指“针织女红技法”之巧艺及女子的心智灵巧。而与正月祭祀农神后稷男耕之事相对应。至少从汉代开始,农历七月是七夕祭祀织女以“乞巧”的月份,女子们在这一天晚上祭拜织女星乞求心灵手巧。因此,从七夕女子“乞巧”的敬天奉时内涵看,“少阴者申也”之论述与肾之“伎巧出焉”功能相吻合。
2.3 “二阴为里”与“少阴者申也”《黄帝四经·经法》曰:“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汉书·郦食其传》曰:“农夫释耒,工女下机。”女工、工女即女织,这说的都是中国古代男耕女织之分工。“正月太阳寅”寓意春季第一个月人体的阳气、津液外发于足太阳经[7],可与男耕于外之事相参;“七月少阴申”提示秋季第一个月阴气内敛于足少阴经,与女织作于内相参。这也正好与太阳、少阴之表里功能相吻合。
理论上说,六经中太阳、阳明、少阳都是表,少阴、太阴、厥阴都是里,其中太阳、少阴为表里,阳明、太阳为表里,少阳、厥阴为表里。然而《素问·阴阳类论》在指出“三阳为表”之后,仅仅提到“二阴为里”,当与《素问·脉解》描述的太阳正月、少阴申月对应的天地阴阳内外盈缩有关。这从七月的另一项风俗也可看出端倪。古代讲究耕读传家,与耕种不同,读书的士子们把七夕叫做魁星节,求取功名就要在魁星节祭拜魁星,祈愿文运亨通。“巧”的本义是技巧、技艺,而引申为灵巧、工巧、精致、美妙和擅长之义,故男子的锦绣文章、经纶天下不仅也属于技巧、技艺范畴,同时也与女子工巧一样属于“智”的范畴。按五脏与“仁义礼智信”相配属,肾主智,这当与肾藏精主脑髓的生理功能有关。因此,人体足少阴经之功能与七月申相参,不论是从敬天奉时之女子节日还是男子节日看,都与肾主“技巧”有关。
另外,笔者论述过,《黄帝内经》“正月太阳寅”之描述与足太阳经之“三阳为经”“三阳主表”功能有如“体国经野”对外开疆拓土之“武功”一样的功能有关[9]。肾主智功能可与男子锦绣文章能力相参,锦绣文章、经纶天下则为对内之“文治”。因此,少阴与七月申相参也提示足少阴肾经有如男子对内有“文治”天下一样的功能,故在这个意义上,六经中只有“三阳为表”而“二阴为里”。
2.4 七月申月与“肾者引也”七月的地支“申”,甲骨文像不同方向开裂的闪电,本义是电。“神”与“申”本为同一字,后才分化。两者都有“引”的引申义,如《说文解字》曰:“申,神也。七月,阴气成,体自申束”“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 南唐徐锴《说文系传·通释》曰:“申即引也,天主降气,以感万物,故言引出万物。”
引,指延伸、引导,《说文解字》曰:“开弓也”。段玉裁注:“凡延长之称,开导之称皆引。”无独有偶,肾也有“引”一样的作用,且肾之“引”可“和利精神。”敦煌遗书残卷《明堂五脏论》谓:“肾者,引也,为言引水谷和利精神。”《内经讲义》认为,肾的“引水谷”功能是指“肾之气化功能正常则五脏六腑之精下藏之,精足慎守则气化常行而无已”。肾的“和利精神”功能是指“肾藏先天之精,而脾化后天之精,两精相搏,神即随之产生。是知一“引”而化水谷、坚肾精、怡神志”[10]。也就是说,水谷化为精微藏之于肾,才能和利精神。若肾不“引”水谷以藏精气,则髓海不足,影响神志,如《灵枢·海论》曰:“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而《素问·生气通天论》说的“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也是由于肾劳不藏精导致的神志病。因此,足少阴肾经与申月相参当与两者都有“引”“神”一样的功用有关。
此前笔者论述过,从《灵枢·痈疽》说的:“中焦出气如露……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即津液达到“和调”的状态时才能化血入脉,再到《素问·六节藏象论》说的“五味入口……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即津液化血入脉后神气才能可得到滋养,都离不开胆为“中正之官”的生理功能发挥。而《素问·经脉别论》所说的外来的饮食物进入人体、化为精微再到“合于四时五脏阴阳”的经络脏腑之正气也是通过类似于“揆之以日”的胆或足少阳胆经“一阳为游部”“一阳为纪”作用来实现的,所以才说“揆度以为常也”[4]。
前文已述“揆之以日”,是指圭表测度日景。人体足少阳经“一阳为游部”“一阳为纪”便有圭表测度日景作用以定方位、定四时一样的作用[11]。但 “癸”是“揆”的本字亦是其前提,即地平才能测度日景以定位正时。也就是说,肾之“癸”的作用是胆及足少阳胆经“揆”的作用的前提。基于此,“肾者,引也,为言引水谷和利精神”其实是指胆及足少阳胆经使“津液和调”、使“神乃自生”的功能,只不过是肾的“癸”主水土平功能是其前提。因此不难看出,彩陶盆口沿“癸”字符号与“甲”字符号之寓意为这一认识之源头。
2.5 “正月太阳寅”“七月少阴申”与“生成之终始”正月地支“寅”也有“引”之义,《汉书·律历志》曰“引达于寅”,郭沫若指出:“甲骨文之寅字乃矢形或弓矢形,当为引之初字。”即“寅”之初义同“引”之开弓之意。《释名·释天》曰:“寅,演也,演生物也。”寅、演皆指引而使之变大变长。《五行大义》阐释得更清晰:“寅者,移也,亦云引也,物牙稍吐,引而申之,移出于地也”。寅是移动、引出的意思,即万物刚刚吐出新芽,抽芽生长冒出地面的状态。《五行大义》又引《三礼义宗》云:“寅者,引也,肆建之义也。”意思是说寅之引有上升生长、冲破阻碍的意义。
七月申之“引”“引出万物”是指万物的身体都已成就了,亦可说万物果实都已申束成形,即《说文解字》说的“阴气成,体自申束”。而《五行大义》解释得更清晰:“申者,身也,物皆身体成就也。”结合上文南唐徐锴对申的解释,便可知道万物成形是在秋气的申束、收敛之下完成的。
不难看出,寅与申都有“引”之义,但四时不同,所“引”的方向相反而作用相成。寅之“引”在春,引而生发,引而化气;申之“引”在秋,引而肃敛,引而成形。这与《素问·天元纪大论》所述“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之意相符合,《素问·脉解》将足太阳经与寅月相配、足少阴肾经与申月相配,正反映了这一点。
两者都是“引”,但对人体水谷代谢引导的方向就像寅月与申月的春秋季节一样截然相反。足太阳经“引”而升发、“引”而化气的作用是指足太阳经“正月太阳寅”的功能使人体如大地回春后“土乃脉发”一样,表现出“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的大地润泽的春生状态。也就是足太阳经正月立春后“天暑衣厚,则为汗”的布津液于腠理的功能[12],这是阴津、水液初生的升发状态。申月少阴肾“引”而肃敛,“引”而成形是指上文所述的引水谷精微收藏于肾以“和利精神”,及七月立秋后“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的肾主二阴化水谷成糟粕的作用,这是阴津、水液凝聚成形的状态。故足太阳经功能与正月寅相参、足少阴经与七月申相参,揭示了人体水谷从气化为汗、为津到凝聚成形为尿、为液、为精、为髓的从“生”到“成”的生理过程。
2.6 “七月少阴申”与“阳气者精则养神”杨雄《太玄经》曰:“寅赞柔微,拔根于元。”“柔微”指万物萌芽时的柔软微小。“元”指物的原始未生状态。这是说寅月阳气有助万物从原始未生状态萌芽于柔微状态。
人与天地相参,寅月阳气感应人体阳气,使人体发生柔微变化的部位在筋。《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黄帝内经素问校注》曰:“阳之柔,如春景和畅,故养筋。”春气圆润活泼,故曰“春应中规”,春气通于肝,在体为筋,寅月阳气可感应人体肝气,使筋圆柔灵活。而足太阳经也有如“寅月”春生一样的“正月太阳寅”的升发津液功能,由于“寅赞柔微”,故人体阳气“柔则养筋”功能虽由肝主,但也离不开足太阳经“正月太阳寅”功能之赞助。《灵枢·天年》曰:“筋为刚”,然足太阳经“正月太阳寅”功能所升发津液之滋润功能可使之柔软灵活。因此,《灵枢·经脉》说足太阳经主“筋所生病”。
《周易参同契》曰:“寅申阴阳祖兮,出入终复始”,寅为阳气生发之始,申为阴气敛肃之端故为祖,升发为出,敛肃为入,故曰出入。肾和膀胱都主气化水液,其区别即在于对水液运化之升降出入作用不同,肾阳向内引申,藏精微以养神;膀胱阳气向外引达,达津液以养筋。春气温柔引达于外,故“正月太阳寅”功能气化水液于表,用于“阳气者柔则养筋”。秋气申束、收敛于内,七月少阴“申,神也”功能收藏水谷精微于内,用于“引水谷和利精神”。因此王冰在解释《黄帝内经》“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时指出:“阳气者内化精微,养于神气;外为柔软,以固于筋。”
3 “癸”与“四维相代,阳气乃竭”
3.1 “七月阴气成”与“九月少阳戌”“七月阴气成”是指七月是万物申束成形、万物成就、果实成形之时令。少阴与七月申之天地阴阳相参在于肾或足少阴肾经在人体有使“阴气成”“成形”之生理功能。即肾能“引水谷”而藏之于肾,和合而为膏,渗于骨空,则骨强体壮,使人体有“作强”之形;入于髓海,则髓海足,髓海足则“精神和利”,“精神和利”则人体有“作强”之智,而“伎巧出焉”。故人体之“阴气成”是指一个人的成熟不仅是形体的长成,还包括心智的成熟。
“成”在先秦文献中与“癸,冬时水土平”有很大联系。如《尚书·大禹谟》云:“地平天成。”孔传曰:“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左传·文公十八年》也有“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之说。“天成”指四时成,这些典籍都将“地平”与“天成”相联系,并以“地平”为“天成”的前提。这是因为水平可以测地平,地平是立杆测景定向的前提,方位确定了便可揆度四时,故曰“地平天成”。而“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故“天成”则人与万物“阴气成”。因此,“水平”是“阴气成”的基础。
先秦时期“盛”亦同“成”,如《康熙字典》引《周礼·冬官考工记》注释曰:“盛之言成也”。《素问·水热穴论》所述“至阴者,盛水也”之“盛”也当有“成”之义,即能“盛”故能“成”。这是因为肾主藏精,有“盛水”之“癸主水土平”一样之作用。“地平天成”中的“天成”则人与万物“阴气成”,故肾的“盛水”作用是人体形体、心智成熟的基础,是少阴与七月申“阴气成”之天地阴阳相参的生理基础。
商代的青铜族徽中,有一个盆内竖木杆状“斿”的字,而且“斿”下有人扶“斿”作跪拜状。有研究认为,盆内之人竖木杆状与人面鱼纹盆有测日景作用的推测可相互印证,故这个象盆内竖“斿”、下有人扶“斿”的字,或释“盛”字[3]。这说明“盛”与“成”形同义通源于以盆盛水测景之“癸主水土平”“地平天成”功用。而青铜族徽中“盛”字中含有“斿”字则可以看出“盛”与“斿”的内在联系,即立杆测景辨正方位需要以地面的水平和圭表与地面是否垂直为前提。我们以前论述过,“斿”字即“游”字,与圭表立杆测景、辨方正时有关,《黄帝内经》“一阳为游部”“胆为中正之官”理论源于此[11]。青铜族徽中“盛”字中含有“斿”字进一步说明了肾藏精之测平、测垂直一样的作用,是胆为“中正之官”“一阳为游部”之圭表样作用的生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素问·脉解》便将“九月少阳戌”排在了“七月少阴申”之后。
3.2 “地平天成”与“四维相代,阳气乃竭”“地平”为“天成”的前提,人面鱼纹彩陶盆“癸”“甲”之分布也说明了这一点。彩陶盆口沿处绘有的八个点表示四正、四维之“八方”,与上文所引《左传》中“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之“八恺”相对应。人面鱼纹彩陶盆口沿处“甲”在四正,寓意“甲”之圭表样作用与辨正方位的关系,“利用圭表便可测得太阳回归年长度,就能够比较准确地确定分至而划分四时”[4]。即“甲”是立表测景以辨方、正时的象征,四时确立便是“天成”,故《左传》中的“莫不时序”之“天成”是由“甲”的圭表样作用完成的。
古代盖天说认为,四维是用来固定天盖的,如《淮南子·天文训》说:“帝张四维,运之以斗”。天盖斡旋形成四时是“天成”的象征,北斗斡旋着天盖转动而不倾倒离不开四维的固定作用。“癸主水土平”,地平是“甲”之“天成”作用的基础,故彩陶盆“癸”之符号在四维,其寓意与“癸”之测平作用是“甲”之“天成”作用的基础相应,即四维的固定天盖作用是以“癸”的测平作用为根本的。因此,人面鱼纹彩陶盆之“甲”在四正与“癸”在四维寓意正好符合《左传》“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之义。
《庄子·则阳》有“四时相代”之说,“代”,从人从弋。弋为戈省,意为“巡逻之戈”“游动之戈”,引申为“巡游”“游移”“迁移”“更替”,故亦有《周髀算经》所言天盖“北极枢璇周四游”以成四时之说[13]。“游”与圭表立杆测影、辨正方位有关[11],因此四时天成、“四时相代”是由“甲”的圭表样作用完成的。但四维却不能“相代”,即“癸”在四维对天盖起固定作用不能游移、更替。若“四维相代”,则“天盖”倾倒。
在人体,阳气与天相参,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阳气者,若天与日”,阳气如“天盖”一样健运不息,故曰“欲如运枢”。前文已述,肾主藏精之“癸主水土平”作用是人体阳气“为固”的基础,阳气“为固”有如四维坚固天盖作用,形体不受外邪侵袭则“四时成”“阴气成”。头与天相参,如果肾精失藏,则精气、阳气不固而可能枯竭,人体则会出现若“天盖”倾倒一样的病证,故《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四维相代,阳气乃竭。”《素问·脉要精微论》则曰:“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
3.3 “肾者牝脏也”与“少阴为枢”《素问·阴阳离合论》以门的关阖枢一体互用关系,来阐释三阴三阳之间协调统一的重要性,其中太阳、太阴为关(开),阳明、厥阴为阖,少阴、少阳为枢。杨上善注:“夫为门者具有三义:一者门关,主禁者也……二者门阖,谓是门扉,主关闭者也……三者门枢,主转动者也。”形象地说明了三阴三阳各自功能和相互关系。人体是一个由三阴三阳经脉连结成的有机整体,每条经脉各有所主,然又密不可分,就如一扇门户,将门关牢或打开都需要关(门闩)、阖(门板)和枢(转轴)三者配合才能达到目的。故《黄帝内经素问集注》云:“开(关)阖者,如户之扉。枢者,扉之转牡也。舍枢不能开(关)阖,舍开(关)阖不能转枢。是以三经者不得相失也。”
古代的门户靠门基石和连楹固定门扇,大门靠门轴转动。门轴上下出头,承接门轴的凹槽叫门臼,门轴在门臼内转动,这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门臼分上下两部分,上门臼在连楹上,下门臼在基石上。前文已述,足少阴肾经有“取平”“固定”之“基石”一样的作用,足少阳胆经有“游移”一样的作用,少阴、少阳同为枢,如果以阴阳动静及《大戴礼记》“丘陵为牡,谿谷为牝”的凹凸阴阳观念看,少阳之枢当与呈凸起状主转动的转轴(即《素问集注·卷二》说的“扉之转牡”)功能相参。《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曰:“肾为牝藏。”《素问·水热穴论》曰:“肾者牝脏也。”少阴为枢当与固定“扉之转牡”之凹陷状门臼功能相参。门臼位于基石和连楹上,而基石和连楹可保持大门水平、直立并有固定大门成形的作用,恰恰符合七月申“阴气成”“万物成形”之理,故“七月少阴申”的论述与《素问·阴阳离合论》的“少阴为枢”论述亦一致。
4 结语
追本溯源,与人体“少阴为枢”功能相参的基石与门臼的稳固作用是由“癸主水土平”之水平、垂直功用决定的,而与“少阳为枢”相参的门轴的转动开闭是由昼夜、季节等时间因素决定的,这需要有决断四时能力的“甲”之圭表样作用来完成。因此少阴、少阳同为枢而有差异的相辅相成关系,与人面鱼纹彩陶盆之“甲”在四正、“癸”在四维寓意一致,“甲”“癸”符号之寓意可为少阴、少阳为枢理论之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