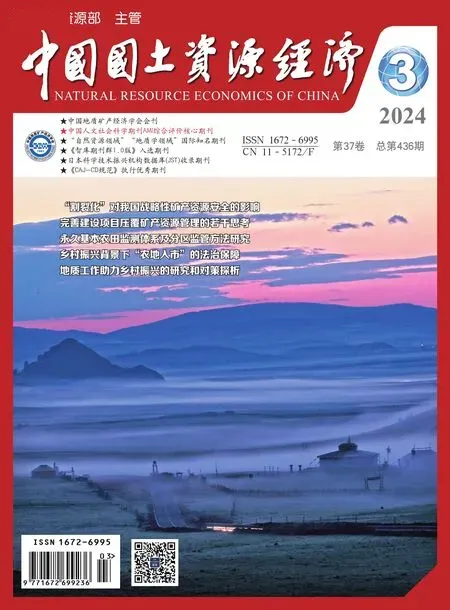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及应对
■ 王慧芝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10)
全球风险咨询公司维里斯克-梅普尔克罗夫特(Verisk Maplecroft)2023年发布的资源民族主义指数(RNI)①Verisk Maplecroft风险咨询公司编制的资源民族主义指数(RNI),主要监测的是各国特许权使用费的增长、对本地生产商品的要求及资产的征用情况。最新排名显示,与2018年相比,墨西哥从第98位跃升至第3位,阿根廷从41位升至第19位,智利从第89位上升至第70位[1],这说明拉美资源民族主义进入上升通道已是不争的事实。矿产资源是中国在拉美投资的重点领域,拉美资源民族主义抬头不可避免地对中拉资源合作产生影响。本文在系统梳理拉美资源民族主义演变的基础上,具体就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的延续与变革进行深入分析,并为如何应对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潜在风险提供思路。
1 资源民族主义的概念界定
资源民族主义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在发达国家也不罕见,是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目前学界对资源民族主义定义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共识。
戴维·R·马雷斯(David R Mares)认为,资源民族主义秉持自然资源属于国家财产的基本理念,其目的是通过自然资源的收益(租金)最大化以推动国家建设,从而使自然资源的馈赠惠及全体人民,其手段是政府设定能源的勘探、生产、运输和分配的条款[2]。张建新认为,资源民族主义是国家为日益加强其资源主权、控制其资源流向、强化其资源价值的一种政策,是矿产资源领域日益流行的一种国家主义或重商主义政策,反映了主权国家及其政府维护或控制本国矿产资源的一种强烈的思想意识[3]。马也认为,资源民族主义是基于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合法管辖,通过控制和支配资源及市场干预行为,达到为政治服务和为国家特定发展等目标服务的目的[4]。陈宇将资源民族主义视为资源占有国和生产国运用自己的主权“合法地”“合理地”调控资源生产配置,为自己赢得政治上、经济上的影响力,把资源作为国家对外战略的实力杠杆[5]。上述定义聚焦的是资源国的内部,重点关注资源国推行资源民族主义政策的动因和目标。
格里芬(J.M.Griffin)将资源民族主义定义为利用国家的强制力干预市场,以此作为提供石油的手段,从而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获得某种战略优势[6]。布雷默(I.Bremmer)和约翰斯顿(R.Johnston)认为,资源民族主义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努力将对能源矿产的政治和经济控制从外国和私人手里转移到国内和国有公司”[7]。斯蒂文斯(P.Stevens)指出,资源民族主义有两个组成部分——限制国际石油公司的运营和主张国家对自然资源开发的更大控制[8]。上述定义侧重的是国家和外资之间的关系,主要关注资源民族主义的表现及其给跨国公司经营带来的风险和机遇。
综合借鉴上述学者观点,本文认为,资源民族主义是资源国基于特定政治或经济目标而产生的收回或强化资源主权的思想意识,以及在这种思想意识指导下的一系列行为实践,资源民族主义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是一种持续、波动的风险。
2 拉美资源民族主义的历史与现状
特有的能矿资源优势为拉美资源民族主义的兴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自20世纪初萌芽至今,拉美资源民族主义共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现在正在进行第四次资源民族主义浪潮。历史上资源民族主义浪潮涉及包括传统的油气行业和农业土地,以及铜、铝土矿等矿产资源,还有水利、铁路等公共设施领域。
2.1 拉美资源民族主义的萌芽及首次高涨(20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
虽然拉美多数国家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已经取得了政治独立,但却未能改变经济上对西方列强的依附地位。在赶走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后,拉美又先后迎来了新的殖民者:大英帝国和美国殖民者。这些新殖民者凭借技术和资金优势在拉美经济领域形成了垄断地位,在攫取高额利润的同时还控制着各国经济命脉,引发了拉美国家的普遍不满。第一次世界大战激起了全球民族主义情绪,拉美国家摆脱经济依附地位、推动民族经济发展的愿望愈发强烈。玻利维亚、墨西哥相继将外资控制的石油、铁路收归国有,拉美资源民族主义正式浮出水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地区掀起新一轮国有化浪潮(表1),资源民族主义持续高涨,其核心目标是打破外资企业在资源领域的垄断地位。所开展的国有化范围包括石油、农业用地、锡矿,以及铁路、港口等公共设施领域,如玻利维亚、墨西哥、巴西先后成立国家石油公司,玻利维亚还建立了国家矿业公司。这一时期的国有化主要采用赎买、征用或没收外资企业等较为激进的方式,引发了外资企业及其母国的强烈不满。据不完全统计,1948—1958年美国在拉美策划的政变和颠覆活动达16次之多[9],导致拉美国家许多国有化进程未能延续。不过,尽管该阶段资源国与外资严重对立,但也有通过赔偿外资企业妥善解决纷争的案例。1937年,玻利维亚政府把美孚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美国虽然中止了对玻利维亚经济技术援助,但并未进行武装干涉,后经过谈判,玻利维亚政府支付赔偿金,此事得以顺利解决。事实上,自那时起拉美资源民族主义温和化迹象已经出现。1948年,委内瑞拉政府通过法令,对外国石油公司的利润实行对半分成,开创了产油国与西方石油公司产品分成和利润分成的先例,拉美资源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变得更加多样[10]。

表1 拉美主要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举措
2.2 拉美资源民族主义的第二次高潮(20世纪60—70年代)
美国的干涉虽然暂时压制了拉美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但也激起了拉美人民极大的愤怒。20世纪60年代,美国陷入内外交困,不仅深陷越南战争泥沼,还面临国内风起云涌的黑人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与此同时,1962年、1966年及1974年举行的三次联合国大会都发布了加强对自然资源管理的决议。在此背景下,拉美国家掀起了新一轮国有化浪潮,资源民族主义再度高涨(表1)。
这一阶段拉美资源民族主义的核心诉求仍是资源管理权国有化,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秘鲁、智利等国相继发生大范围的国有化运动,主要集中在石油业和采矿业领域,也涉及金融业、制造业、农牧业和服务业等部门。据统计,1960—1976年,拉美国家收归国有的外资企业达200多家,包括158家美资企业和8家英资企业[9]。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控制的石油、铜、铁、铝等重要资源,以及长期经营的铁路、电力、电话等公用事业部门,大部分已经被拉美国家收归国有。这一时期拉美资源民族主义温和化趋势愈发明显,通过间接方式强化资源主权的做法更加普遍,如智利提高对外资铜矿公司利润的征税税率,墨西哥通过收买外资企业多数股权的方式加强对硫磺、铜等矿业部门的控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席卷拉美地区,美国趁机兜售“华盛顿共识”,将市场自由化和资源私有化作为拉美各国获取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和西方援助的门槛。拉美国家迫于本国经济形势纷纷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运动,先前取得的很多国有化成果被逆转。
2.3 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及拉美资源民族主义的第三次高潮(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前十年)
私有化政策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拉美各国相继爆发反对新自由主义及全球化的群众性运动,拉美左翼趁势崛起。新上任的左翼政府主张加强国家对资源的控制,不同程度和不同范围地上调了对外资企业的税率并进行国有化,拉美资源民族主义情绪再度高涨(表1)。
这一阶段拉美资源民族主义的目标不是收回资源主权,而是要在与外资合作的基础上保持对本国资源的主导和控制,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或政治利益。拉美此轮资源民族主义虽然声势浩大,但在全球化和后冷战时代背景下,资源国政府不可能像之前一样全面实行社会经济改革,其国有化都是在以保留外资企业生产经营份额的前提下进行的,更普遍的做法是通过修订法规和调整政策来加强资源主权。这一时期国有化最集中的部门是能源和通信行业,其中委内瑞拉的国有化范围最广,包括石油、电信、钢铁、水泥、电力、大米加工、咖啡、银行、超市和酒店等行业。拉美第三轮资源民族主义浪潮使得部分国家重新掌握了本国的经济命脉,但国家干预的增强不仅使得外商投资更加谨慎,也导致了外资的撤离。如委内瑞拉激进的资源民族主义政策迫使埃克森美孚和康菲石油公司撤出该国,并将委内瑞拉政府告上国际法庭[11]。
2.4 拉美资源民族主义进入第四次上涨期(2017年至今)
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浪潮是域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拉美地区形势看,左翼回潮和新冠疫情导致的巨额财政赤字,为拉美资源民族主义抬头奠定了政治基础并创造了现实需求。从国际形势看,双碳目标所带来的能源转型需求和新能源快速发展催生出的自然资源需求(图1),使得相关国家有了控制资源的可能性。而俄乌冲突导致的全球地缘政治撕裂,人为地破坏了已有的市场供需关系,客观上刺激了资源民族主义的发酵。根据风险咨询公司维里斯克-梅普尔克罗夫特的研究报告,拉美地区是全球征用和增税风险增加最多的司法管辖区,委内瑞拉、墨西哥位列风险最高的十个国家之中[12]。

图1 全球清洁能源及化石能源投资额
该阶段拉美资源民族主义主要聚焦锂、铜等新能源矿产部门,核心诉求是借能源转型实现产业链跃升。当事国除成立国有公司外,提高国家股权占有率、增加对外企的税收和提成、单方面改变合同条款或法律框架等间接征用方式最为常见(表1)。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发展前景仍需持续观察,但考虑到能源转型的长期性、拉美悠久的资源民族主义传统及较高的新能源矿产产量和储量(图2),拉美国家强化关键矿产资源的管制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

图2 拉美特定矿产产量/储量全球占比
3 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的延续与变革
从历史演进的视角看,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具有延续性的特点,但同时也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3.1 拉美资源民族主义的周期性特征没有改变
资源民族主义的起伏变化是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就拉美地区而言,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衰与资源价格的波动有关,同时也与该地区左右翼政治力量轮替执政具有强关联性。
资源民族主义是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威尔森提出的“市场周期模型”能够清晰解释拉美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衰规律。他认为,资源民族主义与世界资源市场的繁荣萧条循环有因果关系,即在国际能源市场产品价格处于高位或者资源生产企业之间竞争激烈时,政府在谈判中占上风并可能对企业提出苛刻的要求;在经济衰退及国际能源市场上的资源产品价格处于低位的时候,企业在议价能力上变得强势,资源跨国公司得以成功地推动各国政府采取自由能源政策[13]。
拉美第二、第三轮资源民族主义浪潮均与国际油价上涨密切相关。1970—1979年,国际原油价格从每桶2.7美元涨至每桶约40美元,涨幅近14倍;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国际油价虽有波动,但基本稳定在每桶20至30美元之间,直到2008年飙升至每桶约147美元,这段时间也是拉美第三轮资源民族主义的鼎盛期。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与锂、铜等矿产价格的上涨具有明显关联,在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能源转型等一系列变局叠加影响下,拉美多国公共债务增加,资源商品供需缺口扩大,大宗商品尤其是新能源矿产价格上涨,其中电池级碳酸锂的价格从2021年初的5.15万元/吨上涨至2022年3月的51.2万元/吨,LME铜价由2020年3月的4601美元/吨上涨至2022年3月的10334美元/吨。虽然此后锂价出现下跌,铜价波动明显,但绿色转型为新能源矿产带来长期、稳定的需求,也为锂、铜等关键矿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拉美资源民族主义的上涨期一般也是左翼政治力量的上升期。当左翼政府执政时,国有化的概率显著增加,拉美资源民族主义可能进入新一轮上升期。但当右翼掌权后,左翼政府加强国家干涉的系列政策则多被弃置,拉美资源民族主义随之进入低潮。这一周期性变化呈现出“国有化—私有化—再国有化—再私有化”周而复始的独特现象。
拉美资源民族主义前三轮发展高潮的代表国家多数为左翼政治力量执政②如墨西哥的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 del Río,1934—1940年执政),巴西的瓦加斯(Getúlio Dornelles Vargas,1930—1945年、1951—1954年执政),阿根廷的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1946—1955年、1973—1974年执政)、基什内尔夫妇(Néstor Kirchner and 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2003—2015年执政),智利的阿连德(Salvador Guillermo Allende Gossens,1970—1973年执政),秘鲁的贝拉斯科(Juan Francisco Velasco Alvarado,1968—1975年执政),玻利维亚的埃斯登索罗(Víctor Ángel Paz Estenssoro,1952—1956年、1960—1964年执政)、莫拉莱斯(Evo Morales,2006—2019年执政),厄瓜多尔的科雷亚(Rafael Vicente Correa Delgado,2007—2017年执政),委内瑞拉的查韦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1999—2013年执政)。,新一轮的资源民族主义浪潮也与左翼政治力量的崛起相伴而生。自2018年起,洛佩斯·奥布拉多尔(Andrés Manu el López Obrador)、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佩德罗·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希尔马拉·卡斯蒂略(Xiomara Castro)、加布列·博里奇(Gabriel Boric)、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等左翼政治家先后赢得墨西哥、阿根廷、秘鲁、洪都拉斯、智利、巴西等国大选,标志着这些国家重回“左翼时代”,这成为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兴起的政治基础。不过,政治派别与资源民族主义涨衰的相关性并不是绝对的,如20世纪70年代的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均实行了一系列国有化举措,但这两国政府并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好;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2019—2023年执政)虽是极右翼,但他多次以保护自由市场的名义干预巴西能源和其他工业部门的相关政策,客观上损害了外国投资者的利益[14]。
3.2 拉美资源民族主义温和理性的大趋势没有改变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拉美资源民族主义已从最初的激进民粹主义走向温和理性,资源国与外资的关系也从零和博弈下的对立抗争转变为合作基础上的利益之争。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看似风头强劲,实则也未突破这一大的变化趋势。
拉美资源民族主义源于资源国对外资掌控本国资源状况的不满,为彻底打破外资垄断地位,拉美资源国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国有化实践,并于20世纪70年代基本完成了建立本国经济基础的目标,在这期间资源国和外资对立严重、斗争激烈。此后,拉美资源国逐渐意识到,如果没有外企的资金和技术,本国国有企业很难开采自己的自然资源,必须“在深深植根于历史中的民族主义与国家面临的经济现实之间尽力寻求一种平衡”[15]。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也接受了税收优惠结束的现实。拉美资源国与外资关系开始缓和,资源国的目的不再是把外资赶出去,而是同外资建立新的合作模式,使本国政府在资源的开发、经营和销售环节起控制和主导作用,同时还可分享外资公司从高价资源中获得的超额利润,增加本国收益。
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延续着温和理性的大趋势。一方面是资源国有化并不排斥外资。2017年玻利维亚前总统莫拉莱斯建立了玻利维亚锂矿公司(YLB),但他清楚玻利维亚国内技术水平有限及国际锂市场竞争激烈,表示欢迎外资进入本国锂资源开发领域[16];2020年现任总统阿尔塞上任后,外资开始参与到玻利维亚锂工业化进程中。2023年1月和6月,YLB先后与宁德时代牵头的中资企业联盟CBC、中信国安集团,以及俄罗斯铀壹集团签署协议,在锂资源开采、提炼、加工和销售方面开展合作。2022年8月,墨西哥锂业公司(LitioMx)成立,同时启动对赣锋锂业参与的锂黏土项目审查,但墨西哥政府明确表示此举不是启动法律程序,而是寻求达成协议、进行调解[17]。智利总统博里奇提出的矿产“国有化”提案已被制宪议会否决,国有锂公司前景不明,不过他设想的模式是公私合营,政府在其中拥有多数股权,并非排斥外资。另一方面拉美资源国普遍采取提高税率、重谈或停止已有合同等间接方式加大对关键资源的控制。2021年5月,智利众议院通过法案,对铜、锂征收新的特许权使用费,基本费率为3%,同时对铜征收暴利税;受智利启发,秘鲁政府也于2021年6月开始增加矿业税费,并将多余收入用于社会福利支出;2021年4月,巴西北部的帕拉州提高了铁矿石、铜、锰和镍的税率;2022年2月,墨西哥政府停止向私营公司颁发锂勘探和采矿许可证,之前的几任政府已售出了8张锂勘探许可证[18]。
3.3 拉美资源民族主义的主战场转向新能源矿产领域
历史上拉美资源民族主义主要发生在油气等矿产资源领域,也扩展到了铁路、电话、港口等公用事业部门③公用事业部门是国家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领域的国有化可以确保国家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掌控和管理,以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和公众的利益,本质上也是资源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当前拉美兴起的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重点并非针对传统的油气领域,而是聚焦于对绿色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锂、铜、锌等新能源矿产领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在能源转型背景下,墨西哥、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秘鲁等关键矿产的生产国成为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影响的主要国家。2022年4月,墨西哥参议院通过矿业法案,赋予国有企业锂矿开采的优先地位;2022年8月,墨西哥成立国营锂公司LitioMx。玻利维亚矿产资源储量丰富,2017年成立了国有锂化工公司YLB,实现国家对锂矿的完全所有。智利左翼总统博里奇上任后,国家对锂、铜等矿产资源的干预力度明显加大,除全力推进建立国有锂公司外,博里奇支持的矿业特许权使用费法案已得到众议院批准,这将使该国的铜矿经营者向政府支付更多的税款和特许权使用费。阿根廷向来以投资环境的宽松开放闻名,但其锂业监管也出现趋紧迹象。2020年,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YPF)增设锂开采部门;2022年9月,阿尔贝托总统表示“必须把锂视为一种战略资源”[19];2022年底,拉里奥哈省通过一项法律,暂停该省锂矿的勘探和特许权许可120天,并宣布锂矿是符合公共利益的“战略资源”,在锂矿开采时优先考虑国有公司[20];2023年1月,阿根廷国家经济部宣布取消对氧化锂、氢氧化锂、氯化锂和碳酸锂的出口退税政策,增加了企业间接税的负担[21]。2021年赢得秘鲁总统大选的卡斯蒂略承诺将锂、铜等矿业收归国有,还积极推动对矿产销售征收新的特许权使用费并重新谈判现有税收协议。
锂、铜、锌、白银、镍、石墨、锰和稀土等新能源矿产是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及储能电池等未来绿色技术发展的关键材料,也被视为能够填平政府巨额财政赤字的收入来源,这是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浪潮的主要驱动力。然而,目前采矿业远远落后于绿色革命所需的必要规模[2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认为,实现2050全球净零排放,全球锂、铜、钴和镍生产商的收入可能会增长4倍。据相关预测,2021—2040年全球石油生产的累计价值可能达到13万亿美元,而这些绿色资源所创造的巨大财富与同期全球石油生产的预测价值大致相同[1]。由于南美洲控制着许多此类重要资源(图2),绿色资源转型可能会改变整个南美大陆。专家预测,与“绿色经济”相关的矿产业将在未来二十年蓬勃发展[23]。从这个角度看,资源民族主义的主战场转向新能源矿产领域并非偶然现象,而可能是一个长期趋势。
3.4 拉美资源民族主义的推动者更加多元
拉美资源民族主义自萌芽阶段以来,国家始终是核心推动力,然而新一轮的资源民族主义并没有局限于国家层面,而是进一步延伸到了社区及区域层面,多元化趋向明显。
西方石油公司在拉美赚取了巨额利润,但对油气开发带来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却不愿意斥资加以解决,这引发了拉美国家,尤其是项目所在社区民众的强烈不满。在此背景下,拉美基层社区通过环境和社会责任问题成为资源民族主义越来越重要的推动者,基层社区与外资公司围绕自然资源开采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发生的冲突明显增多。拉美基层社区的资源民族主义诉求会传导到政府层面,导致相应政策的出台,拉美国家政府对外资公司在环保、社会责任方面的高标准便是例证。这一趋势客观上加大了外资公司在拉美运营的难度,实际上是保护和加强了拉美国家对本国资源的占有和主权。当前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更关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及原住民权利等问题。如墨西哥新采矿法要求公司将其收入的5%交给开发地的原住民社区;智利政府要求相关公司使用耗水更少的提锂技术,以尽量减少干旱,而干旱一直是让当地人和原住民群体愤怒的根源[1]。
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的战场还扩展到了区域层面。基于拉美国家在锂资源产能与储量方面的龙头地位,南美锂三角地区国家借助能源转型契机积极推进“锂业欧佩克”的成型。这些国家虽然打着反对西方国家产业金融资本剥削、控制锂资源大国的旗号,但其实际目的是尽快形成全球最大的锂价格垄断联盟,通过定价权迫使中下游产业向上游产业让利,同时还希望借助新能源在全球的高速发展成为全球绿色转型新的重要参与者,并不断借势扩大成员国影响力。虽然“锂佩克”的推进面临诸多现实障碍,最终能否成型尚不确定,但其折射出的拉美资源国对定价权、产业附加值、产业链升级等方面的发展诉求将长期存在,这些现象是理解新时期拉美资源民族主义的重要参考。
4 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的应对思路
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是拉美能源矿产领域的“后来者”。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能源矿产企业开始通过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拉美市场;以1992年首钢集团收购秘鲁铁矿为起点,中国对拉美能能源矿产领域投资开始加速;2000年在“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与拉美国家能源矿产部门的投资合作步入快车道。中国现在已不再是拉美能源矿产业发展的旁观者,而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对能源矿产合作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应正视拉美资源民族主义长期性、反复性的现实,聚焦于防范风险、开拓新机,与拉美国家持续深化能源矿产领域合作,在维护中国能源矿产安全的同时帮助拉美资源国实现发展的夙愿。
4.1 对拉美资源民族主义的长期性和反复性要有清醒认识,将精力集中在化解风险、开拓新机上
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的特有产物,只要民族国家还存在,民族主义就不会消失,资源民族主义亦然。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资源民族主义政策虽不可能长期持续,但由于民族国家仍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尚看不到资源民族主义消亡的可能。一个更具现实可能性的结果是资源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短期现象反复出现,这与产生资源民族主义的动力有关,除受世界经济扩张和收缩的影响外,资源约束也不可忽视。长期来看,由于资源的稀缺性,资源约束不仅始终存在,而且还会越来越严重,这就给资源民族主义留下了复活的空间。然而资源民族主义的破坏力是有限的,技术创新将不断突破资源的约束[3]。
虽然拉美资源民族主义日趋温和理性,但扩大监管范围、提高税收等隐蔽措施的破坏力并不弱。如2007年10月,厄瓜多尔突然颁布总统令,征收高额暴利税,将外国石油公司额外收入的99%收归国有,尽管此后下调了暴利税率,但中石油和中石化共同出资收购的安第斯石油公司还是蒙受了巨额损失[24]。由于拉美资源民族主义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遵循一定的周期性规律反复出现,这意味着其每次高涨都不可避免引发外资的担忧和恐惧,并会不同程度地加大外国企业在相关资源领域经营的难度。与国际恐怖主义不同,资源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因此外资企业对其态度不应是消除“威胁”,而应是正视资源民族主义长期性和反复性这一客观事实,聚焦于化解风险、危中寻机,力求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4.2 持续强化对拉美资源民族主义规律特点的认知,对相关风险早做准备
虽然拉美资源民族主义起落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有一定的规律和特点可循。在拉丁美洲的中资企业应对相关风险早做预案,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拉美资源民族主义具有周期性特征,当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大规模私人投资结束或左翼力量崛起时一般都预示着资源民族主义的上涨,出台提高税率等强化资源主权政策的概率会显著增加。尽管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并不排斥外资,但外资企业仍面临着股权稀释、政策变动等风险。如天齐锂业现持有智利矿企SQM22.16%的股份,锂国有化预期不可避免会对天齐锂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另外,拉美资源民族主义主战场已转向矿产领域,由于矿产开采极易引发破坏生态环境等社会经济问题,不可避免地迫使拉美矿产资源国在环保和社会责任方面提出高标准。以锂矿为例,目前所采取的开采模式与气候正义是相冲突的,对环境的影响不仅广受诟病,还在智利等国引发了较大的社会冲突。中国作为拉美能源矿产领域的“后来者”,再加上与拉美国家在历史、文化、语言、法律等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中资企业与拉美土著群体、工会及环保组织打交道的能力较弱,极易成为被抵制的对象。2022年1月12日,比亚迪在智利中标了8万吨金属锂产量配额合同,但仅2天后,智利法院就因环境等原因叫停了该项目。
针对上述风险,中资企业可从以下几点出发予以应对:一是密切关注拉美资源民族主义发展动向,谨慎做出新的投资决定;重点做好在建项目履约工作,通过高质量履约赢得所在国信任,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资源民族主义风险所带来的经营压力。二是针对拉美资源国在环保和社会责任方面的高标准,中资企业应投入更多时间精力,详尽研究所在国相关法律法规,与项目所在地社区密切接触,主动接受非政府组织监督检查,避免因疏忽或重视程度不足成为资源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针对对象。另外,在资源民族主义风险不可避免时,外国能源公司的强硬态度会导致其遭受巨大损失,而当所在国政府要求外资企业就资源租借条款或赔偿事宜进行谈判时,外国能源公司往往能得到比较好的结果。例如墨西哥国有锂公司的成立给赣锋锂业参与的Sonora锂业项目带来了不确定性,墨西哥政府正在对该项目重新进行审查。面对这一不确定性,赣锋锂业应坚持以沟通解决争端,避免硬碰硬导致事态升级,造成双输后果。三是中资企业应与大型跨国企业或东道国能源矿产公司结成战略联盟,共同参与拉美能源矿产资源开发。这样一方面有助于提升资源和项目的获取能力,另一方面可优势互补,显著提升抵抗资源民族主义风险的能力。
4.3 拉美不同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风险存在差异,应关注特殊性,提高应对策略的科学性及准确度
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都以对外资开放为前提,主要资源国间也未出现明显分化。但不同国家资源民族主义倾向程度不同,应对策略也应有差别。中资企业不仅要准确把握拉美资源民族主义的规律、特点,还要兼顾各国特殊性,尽量避免决策失误。
锂矿是当前拉美资源民族主义影响较大的产业,拉美锂大国虽普遍采取措施强化锂资源管控,但程度不同。其中,玻利维亚强调政府对锂资源的全面控制;墨西哥、智利经济自由主义传统深厚,且只是寻求政府在锂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并不反对外资参与;阿根廷、秘鲁虽然出现加大锂资源管控力度的苗头,但两国矿业部门都具有高开放度的传统,外资企业可享受国民待遇。目前,中国在上述五国能源矿产领域都有投资。其中,在秘鲁投资且正在运营的矿业项目主要有五矿拉斯邦巴斯铜矿项目、中铝特罗莫克铜矿项目、首钢秘铁铁矿项目、首信尾矿回收项目等,此外还有五矿江铜格兰诺铜矿、紫金白河铜矿及邦沟铁矿项目等有待开发[25];阿根廷是中资锂投资项目和投资额最多的国家,赣锋锂业、青山集团、紫金矿业、西藏珠峰等多家中国企业正在加快阿根廷盐湖提锂项目开发建设;天齐锂业、赣锋锂业也通过投资参与到智利、墨西哥的锂矿开发中;中资企业还与玻利维亚政府签署了锂勘探协议。中资企业在运营现有项目或做出新的投资决策时应对不同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风险有所区分,在防范风险与开拓新机中找到平衡点。
资源民族主义的发展与政党政治的大背景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看,资源民族主义不一定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但一定具有政治上的合理性。虽然拉美资源国在对外合作方面主要秉持务实态度,但不能排除执政党为短期政治利益牺牲长期发展利益的可能性。例如,秘鲁一向是拉美最具投资吸引力的矿业国之一,但2021年政治局外人卡斯蒂略的崛起及其资源国有化的言论引发了市场不安,多家矿企对此忧心忡忡,2022年12月,其被国会罢免总统职务并遭逮捕,但他对秘鲁矿业发展的负面影响依旧令人记忆犹新。在拉丁美洲投资的中资企业应对所在国政治经济形势、政策及立法变化进行系统跟踪和评估,对资源民族主义相关风险早做预警。
4.4 认清拉美资源民族主义理性、温和的大趋势,持续挖掘中拉资源领域合作空间,维护中拉友好合作大局
历史上,拉美资源民族主义吓跑或赶走外资的案例并不罕见,但这无法掩盖其日渐理性、温和的大趋势。即使在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中拉在能源矿产领域仍有合作的空间。
不可否认,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浪潮会带来投资风险增加、成本加大、矿产品供应不稳定等不利影响,但客观上也给中拉矿产资源开发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拉美资源国想摆脱对美欧资本、市场及技术的依赖,中国可凭借资金、技术优势对美欧形成一定程度的替代;另一方面,当前拉美资源国普遍认为,自然资源应该被用作对当地制造业的投入,而不是作为原材料出口,这意味着拥有资金、技术的外资企业仍能在拉美资源国继续运营并盈利,前提是不觊觎资源国的资源主权并积极助力延伸当地产业链条。中国应根据自身利益,对拉美资源国的发展诉求给予理解,并做出适当回应。以锂产业为例,中国应充分利用自身的产业链和技术优势,持续推进与拉美资源国在锂电池、电动汽车、储能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在保证中国能源矿产安全的同时满足拉美国家推进锂工业化进程的需求。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最大限度降低资源民族主义对中资企业在拉美地区投资的不利影响,中国政府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把参与全球矿产资源开发作为政治、经济外交活动重要任务目标加以考量。在外交活动中,尽量争取以中国政府名义与资本引进国签订投资保护协议,在双边、多边自贸协定中重视投资保护条款,以保护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并获得与东道国企业的同等待遇,协助其以经济高效的方式管控政治风险[26]。同时,可借助中拉论坛平台为中拉能源矿产资源合作提供机制保障,如继续举办中拉新能源合作论坛,推动新设中拉能源矿产合作论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