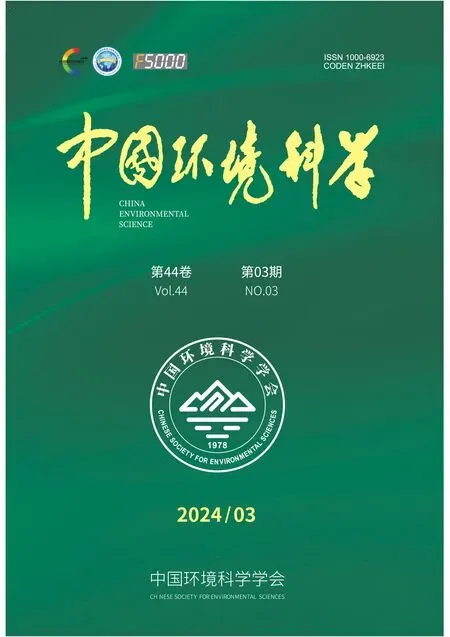生物体内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迁移转化及毒性
韩 淼,李泽楷,许 淋,李昭燕,文欣雨,侍 卿,胡小婕,秦 超,高彦征(南京农业大学土壤有机污染控制与修复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95)
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s)是一类烷基链中与碳原子相连的氢全部或部分被氟原子取代且具有末端功能基团(如:羧基、磺酸基、磺酰基、羟基和膦酸基)的人造脂肪族化合物[1].由于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与疏水疏油性,PFASs 被广泛用于农药、炊具、纺织品和食品包装等的生产中.PFASs 的大量生产和使用导致其在土壤、水体、大气和生物体等多种环境介质中被检出[2-4],如山东某工业园区土壤中PFASs 浓度高达1200ng/g,园区附近儿童血清中PFOA 含量可达845ng/mL[5].
据报道,PFASs 进入环境后,首先与环境介质发生吸附-分配作用,该过程中产生的可溶解态污染物进入生物体后经过代谢转化生成多种产物,母体化合物和代谢产物与生物组织再次发生吸附-分配,部分物质最终到达靶器官,进而与蛋白、DNA、脂质等生物大分子发生相互作用[6],诱发一系列毒性效应,如生长毒性、生殖毒性和内分泌毒性等[7-9].由此可见,PFASs 在生物体内的毒性效应与其在生物体内的迁移转化密切相关.
目前,有关生物体内PFASs 的迁移转化及毒性风险的研究较少,本文采用文献调查和文献计量学的方法,综述了PFASs 在植物、动物、人体内的迁移转化过程,总结了PFASs 的生长毒性、器官毒性、生理生化毒性、分子毒性等毒性效应及机制,旨在为评估PFASs 的健康风险,制定环境质量标准,合理控制PFASs 生产和使用提供参考.
1 PFASs 在生物体内的迁移转化
1.1 常见PFASs 及其分类
PFASs 包括以全氟辛酸(PFOA)和全氟辛基磺酸(PFOS)为代表的传统PFAS,以及以短链PFASs、全氟烷基膦酸(PFPiAs)、全氟烷聚醚羧酸(PFECA)、全氟烷基醚磺酸(PFESA)和氟调聚醇(FTOH)等为代表的新型PFASs(表1).PFASs 中含有大量碳氟键,由于碳氟键具有较高的稳定性,PFASs 能够在环境持久存在并进行长距离迁移,也越来越多地在生物体内被检出.
1.2 PFASs 在动物体内的迁移转化
PFASs 可通过吸收、摄食等生命活动进入生物体(图1),经过代谢转化为其他产物或通过迁移富集到不同组织器官.PFASs 在生物体内的迁移转化和富集能力是探讨其生态效应的基础.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表明,环境中的PFASs在生物体不同器官中的迁移转化与污染物浓度、结构、环境介质特点以及生物体内蛋白含量有关[11-12].

图1 PFASs 在动物、植物和人体内的迁移转化及影响因素Fig.1 Mi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FASs in animals, plants, human beings, and the main factors
如表2 所示,蚯蚓作为常见的土壤动物,被大量用于 PFASs 在土壤动物体内的迁移转化研究.PFASs 可以通过表皮吸收和摄食两种途径进入到蚯蚓体内,并在其体内发生降解转化和迁移等行为.例如,一些前体物质(如:8:2diPAP、NEtFOSA、N-EtFOSE 和10:2FTOH)进入蚯蚓体内会在酶的作用下发生生物降解,其在生物体内的分布与组织器官中的酶含量及酶活性相关[13-15].Zhu 等[16]研究发现6:2diPAP 在蚯蚓体内经过酯键断裂、酶催化水解等步骤生成全氟羧酸(PFCAs).组织含量分析结果表明,终产物PFCAs 在表皮中的比例(31.8%)远低于器官(95.5%)和肠道(100%),即肠道中含量较高的生物酶和微生物促进了6:2diPAP 的降解.

表2 PFASs 在蚯蚓体内浓度及富集因子Table 2 Concentrations and enrichment factors of PFASs in earthworms
PFASs 在蚯蚓体内迁移能力也受污染物浓度和理化性质影响.由于PFASs 具有疏水性,辛醇-水分配系数(Kow)被认为是衡量其迁移能力的重要参数.有研究表明,在不区分器官的前提下蚯蚓体内PFASs 浓度水平与Kow呈正相关关系.除疏水性以外, PFASs 的离子性同样会对其迁移能力产生影响.新型全氟化合物中,全氟辛烷胺铵盐(PFOAAmS)和全氟辛烷酰胺基甜菜碱(PFOAB)是典型的阳离子和两性离子型PFASs,其Kow值与高疏水性芳香族化合物相近,但由于阳离子/两性离子型PFASs 能与带负电荷的环境介质发生静电吸引,因此更难进入生物体内[17-19].蚯蚓体内PFOA 的浓度是阳离子PFASs 的浓度的6~10 倍,是两性离子型PFASs 的1.13~6 倍[19].
传统PFASs 在不同组织中的富集水平与蛋白含量密切相关.哺乳动物体内PFASs 主要存在于肝脏和血液中,而不是脂肪组织中[20],然而有学者提出,肌肉组织中蛋白质含量高,但全氟烷基羧酸(PFSAs)浓度仅为肝脏中的五分之一,基于这一现象,Ebert 等[21]提出利用膜/水分配系数(Kmem/w)来衡量PFASs 的渗透性,或可对其富集水平进行解释.
1.3 PFASs 在植物体内的迁移转化
PFASs 作为小分子有机物可被植物根系吸收,在植物体内发生降解和转化,并转移到植物的茎、叶和芽等地上部位.根系富集因子(RCF)和转运因子(TF)是衡量植物吸收和转运污染物能力的重要指标.表3 列举了PFASs 在植物体内的富集和迁移水平.

表3 PFASs 在植物体内富集及迁移水平Table 3 Enrichment and migration levels of PFASs in plants
在复杂的环境中,PFASs 与土壤组分的吸附-解吸过程以及PFASs 与植物根系的相互作用均会影响根系对PFASs 的吸收(图1).与PFASs 在其它部位的富集相比,RCF 与疏水性呈正相关,碳链越长、疏水性官能团数量越多的化合物通常更容易富集在根部.Zhang 等[26]研究了不同碳链长度的PFASs 在灯心草中的分布,结果发现PFOA 在根系的积累量是PFBA 的125.96 倍.除污染物本身性质外,环境介质也会通过改变吸附行为影响其在生物体内的富集浓度[27].例如PFASs 进入土壤后会在范德华力和疏水作用下吸附到土壤有机质表面.大量研究表明,有机质含量是影响土壤吸附PFASs 的主要参数,同时也是对植物毒性影响最大的因素[27-28].未来在风险评估过程中,应考虑不同土壤有机质含量对PFASs 毒性阈值的影响.
TF 用于衡量污染物在植物体内的迁移水平.植物根部吸收的PFASs 会依靠蒸腾作用力[32],顺着维管向上运输(图1),植物种类以及温度、湿度和辐照度等会通过影响蒸腾作用改变污染物在作物体内的迁移水平.研究发现,6:2Cl-PFESA 在绿豆、小麦和空心菜中的RCF 相差103个数量级,但TF 分别为0.18,0.03 和0.10,表明与RCF 相比,植物种类对迁移能力的影响更小,化合物自身理化性质与其相关性更大, 如链长和官能团类型[26,33].Bizkarguenaga 等[33]发现8:2diPAP 在胡萝卜体内的降解产物中,PFOA 在胡萝卜表皮和果核中含量最高,而PFBA 在叶片中含量最高,表明亲水性更强的短链化合物更容易借助蒸腾作用在植物体内迁移 .当PFASs 分子结构中存在其它官能团时,由于其亲水性差异,会产生有趣现象.例如,PFOA 和GenX 在大豆体内的转运因子分别为0.16 和1.21,说明醚键提高了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能力,但也有研究发现6:2Cl-PFESA 在植物体内的迁移能力低于PFOS,这可能是由于-Cl 是疏水基团,降低了PFASs 的亲水性,从而减弱了其迁移能力[34].总体而言,由于PFASs 的疏水疏油性,其在植物体内的富集规律仍需结合大量理化性质综合分析.
1.4 PFASs 在人体内的富集和迁移
PFASs 可通过吸入、皮肤接触以及摄入食物和饮用水等途径进入人体,通过循环系统迁移转化,并积累在生物组织中[35-36].
PFASs 进入人体后首先存在于血液中,调查发现,随着工业的发展,中国人群血液中PFASs 的浓度从1987 年的0.08µg/L 增长到2023 年的845µg/L[5].大量研究表明,PFOS 和PFOA 是血液中含量最高的两种PFASs,近几年,随着替代物的使用,6:2Cl-PFESA 在血液中的检出量也大幅上升[37].由于PFASs具有蛋白亲和力,其在血清中的含量高于血浆和全血[32].PFASs随体循环到达各个器官后同样会优先富集在富含蛋白质的器官中,如肝脏和肾脏.Pérez 等[38]对21 个死亡人体样本进行检查后发现,PFOA 主要富集在肝脏、肺和骨骼中,肾脏中含量较低,脑组织中未检出.
不同结构的PFASs 在人体内也表现出不同的迁移能力.PFOS的短链替代物PFHxS的清除半衰期为5.3a,而长链氟醚替代物6:2Cl-PFESA 在人体内完全清除需15.3a[39-40].Pérez 等[38]调查发现,尿液中PFBA 的平均浓度(545ng/L)和检测频率(100%)相对高于其它长链PFASs.由于技术手段有限以及存在伦理问题,目前PFASs 在人体中的富集和迁移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2 PFASs 对生物的毒性效应研究
研究表明PFASs 对生物具有生长毒性、器官毒性、生理生化毒性等.图2(a)中,圆圈大小与关键词出现频率呈正相关,圆圈间连线的粗细程度代表二者之间的共现关系.聚类后的关键词可分为3 大类:“毒性-环境分布”、“器官-毒性效应”和“表达-损伤机制”.由此可见,PFASs 对生物毒性效应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毒性与环境分布的关系、PFASs 对不同器官的毒性效应和基因表达与损伤机制探究等几方面.

图2 PFASs 毒性效应研究热点及热点变化趋势Fig.2 Hot spot map of toxic effect studies of PFASs and the trend of hot spot about toxic effect researches on PFASs over time
图2(b)表明,“ppar-α”、“peroxisome proliferators”和“liver”等关键词出现在2010 年左右,说明在研究早期,人们发现了PFASs 作为过氧化氢酶增殖激活受体可诱导肝毒性和肾毒性;2015 年以后,由于已知PFOS 具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特性,大量针对PFASs 及其短链替代物的研究在此阶段涌现,“plant”、“marine mammals”、“sediment”、“apoptosis”和“oxidative stress”等成为热点词,研究者们开始大量关注此类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行为、富集水平和生物毒性的相关机制;2020 年以后,由于疾病和健康等话题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serum”、“pregnancy”、“fetal-growth”和“children”等关键词逐渐成为热点,PFASs 对于器官、生殖和生命早期发育过程的影响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
迄今为止研究者们已围绕不同物种、不同靶标部位以及多种毒性机制等开展了关于PFASs 毒性效应研究.但目前仍缺乏相关文献对PFASs 的多层级毒性效应进行总结.阐明PFASs 的毒性效应及机制对预测该污染物对人群健康的风险及制定相关排放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2.1 PFASs 对生物的生长毒性
个体死亡作为表观毒性最严重的不良后果,通常用于评价短期内外源化合物的急性毒性.目前对于PFOA 和PFOS 的急性毒性研究相对成熟.有研究表明,759.6 和811.4mg/kg PFOA 可诱导赤子爱胜蚓出现半数死亡现象.此外,PFASs 对生物生长状况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生物量的变化可以作为评价PFASs生长毒性的关键指标.研究表明PFOA浓度达到100mg/kg 时,蚯蚓种群无死亡现象发生,但整体体重出现26%的下降[41].通常,PFASs 的碳链长度可影响其生物毒性.据报道,100mg/kg PFHpA、PFOA、PFNA、PFBS、PFHxS 胁迫下,蚯蚓体重下降率分别为19%、26%、29%、9%、15%,表明毒性与碳链长度呈正相关[42].除碳链长度以外,PFASs 特定官能团同样会对其生物毒性造成影响.HFPO-DA 与PFOA在结构上仅存在醚键的差异,但研究发现HFPO-DA对拟南芥和班式烟草株高和根长的抑制能力显著低于PFOA[43].
PFASs 对人体的生长毒性主要体现在对胚胎生长发育的影响.Lam 等[40]利用Meta 分析系统评价后发现,PFOA 暴露与新生儿出生体重下降有关,PFOA增加1ng/mL,出生体重减少约19g.Steenland 等[44]研究表明母体血清中PFOA 每增加1ng/mL,婴儿出生体重降低10g,虽然体重降低幅度有所差异,但这一关联反映了PFASs 对胎儿生长发育的负面影响.除PFOA 以外,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母体中 PFOS、PFNA、PFDA 和GenX 的浓度与胎儿出生体重和体型呈负相关[44].胎盘作为胚胎发育期间联结胎儿与母体的重要器官,其健康发育至关重要.研究表明除胎儿本身外,胎盘也是PFASs 的靶标器官,实验表明高浓度PFOA 和GenX 处理下胎盘重量显著上升,胚胎-胎盘重量比降低,异常胎盘重量通常标志着不良妊娠结局,说明PFASs 也可以通过干扰胎盘发育对胎儿造成生长毒性[45].
2.2 PFASs 对生物器官的毒性
当低浓度胁迫下生物体无明显表观损伤时,器官毒性是评价外源化合物对机体的毒性效应、衡量综合毒性水平的重要指标.不同于传统的亲脂性有机污染物,PFASs 易与蛋白质结合,肝脏作为蛋白质含量最高的器官,是PFASs 的主要靶点[46-47].PFASs进入人体后会影响肝酶活性、破坏肝脏组织,导致肝脏肿大、脂肪量增加甚至癌症[48].Stefano 等[49]研究表明与PFOA 和PFOS 比,短链替代物PFBA 对小鼠肝脏组织和肝酶活性的影响更小,碳链长度是影响污染物与蛋白作用进而影响毒性的重要因素.除肝脏毒性外,PFASs 的肾脏毒性、神经毒性和内分泌毒性同样备受关注.2008 年,Leonard 等[50]进行队列实验发现PFOA 生产工厂工人肾癌的发病率是普通人群的两倍.PFASs 同样可以通过改变神经元和突触生长水平导致神经毒性[51].Shaza 等[52]对多种PFASs的神经毒性规律进行探究,发现PFPeS、PFHxS、PFHpS 或PFOS 胁迫下产生了典型神经毒性表型,Zhang 等[53]研究发现HFPO-DA 对甲状腺细胞的毒性高于传统PFASs.阐明污染物结构与毒性规律的相关性是探究PFASs 表观毒性的重要研究目的,但该领域当前仍存在大量数据空白,污染物不同理化性质在毒性效应中所占比重仍需大量体内试验进一步研究.
2.3 PFASs 对生物的生理生化毒性
氧化胁迫作为近10a 常见的关键词,与肝毒性、氧化损伤、脂质过氧化和细胞凋亡等毒理现象都存在着密切联系.研究表明,PFASs 可以诱导机体出现氧化胁迫并造成机体损伤.当蚯蚓暴露于低浓度PFASs 时,其体内的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和过氧化物酶(POD)激活,参与H2O2和自由基(O2−、•OH)的解毒,以应对外界胁迫.研究发现,1mg/kg PFOS 胁迫激活SOD、CAT 和POD,随着暴露浓度和胁迫时间增加,ROS 的动态平衡被破坏[54].另有研究表明,100mg/kg PFOS 胁迫可抑制抗氧化酶活性,引起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MDA)含量显著上升[42].除此之外,PFASs 能够通过诱导异常代谢过程表现其对人体的生化毒性.PFOA 和HFPO-DA 胁迫下,脂肪酸代谢、胆汁酸代谢受到影响,催化胆固醇合成胆汁酸的关键酶CYP7A1 含量下降,肝脏损伤的标志物丙氨酸转氨酶(ALT),碱性磷酸酶(ALP)和γ-谷氨酰转移酶(GGT)水平升高,预示着潜在的肝损伤风险[55-57].
然而,现阶段针对PFASs 对抗氧化酶、解毒酶和混合功能氧化酶等生物酶以及ALT 和GGT 等肝酶的影响相关研究大部分停留于酶活性检测阶段.研究表明,有机氟代烷可以通过β-氧化等一系列反应生成氟柠檬酸抑制乌头酸酶的活性[58];氟化物也可以与Mg2+形成复合物,抑制以该离子为活性中心的酶,如Na+/K+/ATP 酶[59].但目前对于PFASs 影响酶活性的详细机制尚未被阐明,明确毒性作用机制对于预测多种替代物毒性及制定使用规范具有重要意义,是目前该领域亟待探讨的问题.
2.4 PFASs 对生物的分子毒性
PFASs 诱导的病理反应和氧化应激不仅会影响酶活性、破坏细胞器,还会攻击蛋白质和核酸等生物大分子,调控RNA 的转录过程,最终引发上述毒性效应.
蛋白质具有复杂的元素组成和三维结构,在生命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动物体内,血液是最易暴露于外源污染物的生物介质.研究表明,血清白蛋白是PFOA的优先靶蛋白,可在血浆中与PFOA形成强复合物[60].Yang 等[61]发现,PFOA 可以与牛血清蛋白中的色氨酸残基结合,在结构上降低α 螺旋的比例,高浓度PFOA 胁迫下蛋白质二级结构发生变化;Ale sio 等[46]探究了PFOS、PFOA、PFHxS 和PFBA 与血清蛋白非特异性结合强度的影响因素,发现4 种化合物与蛋白的结合强度受C-F 键数量的影响,具体表现为:PFOS(nC-F:8)>PFOA(nC-F:7)>PFHxS(nC-F:6)>PFBA(nC-F:3),这主要由于C-F 键的数量可以通过改变化合物的分子量和疏水性进而影响结合强度[47].除此之外,官能团也可以通过影响范德华力、静电作用和氢键从而影响PFASs 与蛋白的特异性结合.其中,PFHxS 和PFOS 与血清蛋白、核蛋白、膜蛋白和转运蛋白的特异性结合能均较高,表明全氟磺酸类化合物可能对配体结合域具有更强的亲和力[62-63].Jeannette等[64]探究了GenX与人血清蛋白的结合情况,对接结果表明GenX与人血清蛋白存在4 个结合位点,圆二色谱结果表明GenX 对人血清蛋白的二级结构影响较小,但仍存在破坏蛋白功能的风险.当前种种阳性结果表明,PFASs 的特殊结构对蛋白结构和功能的影响不可小觑.土壤环境中存在大量土壤蛋白,PFASs 进入土壤环境后是否与土壤蛋白相互作用从而影响土壤功能,以及进入土壤生物体内后与蛋白质的结合情况及产生毒理效应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核酸作为生命体重要的遗传信息库,在指导生命活动、维持生物体遗传性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结构而言,PFASs 进入生物体后会通过直接结合和诱导活性氧攻击两种方式损伤核酸分子,其中,直接结合的强度与PFASs 结构密切相关.目前研究表明,PFOA、PFOS、PFNA 和PFHxA 均能以沟槽结合的方式与DNA 非共价结合,使DNA 形成松散的双螺旋结构,且化合物的碳链长度与官能团种类可以影响结合强度.Qin 等[65]研究表明每增加一个碳链单位,PFASs 与DNA 的结合常数降低约1.00×104L/mol;对于官能团而言,羧基比磺酸基更容易与DNA 结合.结合亲和力的变化可能与不同链长和官能团的电负性和空间位阻有关[66].
大量外源有机物进入生物体后,机体会产生活性氧自由基以降解有机物,降低其生物毒性.自由基含有孤对电子,性质活泼,极易攻击具有高电负性的DNA 磷酸骨架或与碱基形成加合物,导致DNA 断裂或染色体畸变.研究表明,DNA 损伤程度受污染物碳链长度影响较小,但与官能团种类关系更为密切[7,67],但目前尚未有系列体内试验探究官能团对PFASs基因毒性的影响.阐明相关规律对评价及预测PFASs 等新污染物的毒性具有重要意义,是未来亟待拓展的研究方向.
3 总结与展望
PFASs 在生物体内发生吸附分配、生物化学降解、迁移富集等过程.吸附分配过程受两相物质之间作用力的影响,因此与物质结构密切相关.PFASs 在人体器官内的富集水平基本表现为肝脏>肾脏>血液的规律.总体而言,污染本身的物理化性质是决定其迁移转化能力的根本原因,相关研究通常要额外考虑生物体内不同部位的蛋白质含量等指标.未来阐明PFASs 在生物体内的迁移规律仍需要大量两相物质自身理化性质数据与试验数据支撑.
PFASs 对生物的毒性作用同样与其理化性质密切相关.但除此之外,对于毒性靶点的研究同样重要.核酸、蛋白等生物大分子具有复杂结构,目前对于PFASs 与DNA 和功能蛋白相互作用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作为细胞毒性、器官毒性和个体毒性的起点,PFASs 的特殊结构对生物大分子的损伤是对其毒性进行研究和预测的基础,是未来值得被注意的重要环节.对于更大尺度的毒性效应而言,探究毒性阈值(如:最低无效应浓度、半数效应浓度和半数致死浓度等)与其它水平毒性效应(如:器官损伤和酶活变化等)之间的相关性对于环境中低浓度污染物的毒性预测及国家相应法律法规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定量有害结局路径(qAOP)研究是通过探究不同毒性端点,定量阐明生物体损伤的层级效应的有力工具.未来可利用qAOP 和数据库探究低浓度PFASs 分子或细胞水平毒性风险,并对其个体风险进行推演和预测,为国家制定污染物排放浓度控制及总量控制相关标准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