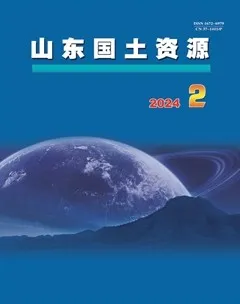粮食安全视域下的耕地概念探讨



摘要:聚焦我国耕地资源国情,从保障安全视域出发,分析粮食安全内涵变化过程中对耕地资源保障的需求,通过对国际上耕地概念的概述和从历史、常识、法律、技术等角度对耕地概念的理解,提出完善耕地概念的建议,采用定量分析法、实证分析法、逻辑分析法、历史研究法,以期为加强粮食安全耕地保障能力提供参考。现行耕地概念过于强调技术逻辑,在我国农业生产土地资源趋紧的条件下,并不利于我国的粮食安全和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尤其是园地与耕地都以生产食用农产品为主导功能。有必要适应我国农业特别是种植业发展的需要,让耕地概念回归本义与常识,将园地等支撑种植业发展的土地资源纳入耕地范围,并赋予耕地概念管理逻辑和规划属性。研究结论:统筹法理逻辑、管理逻辑、技术逻辑与常识认知,将耕地概念界定为“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形成对国家粮食安全整体利益价值追求。
关键词:土地资源;粮食安全;耕地;概念;园地
中图分类号:F30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28/j.issn.1672-6979.2024.02.011
引文格式:齐世敬.粮食安全视域下的耕地概念探讨[J].山东国土资源,2024,40(2):6574. QI Shijing. Discussion on Cultivated Land Concep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Food Security[J].Shandong Land and Resources,2024,40(2):6574.
0 引言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特别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耕地保护涉及乡村振兴、农民权益、生态保护等众多目标,但首要目标和核心价值是保障粮食安全。从人类文明进入农耕时代起,人们烧荒、垦造出耕地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农业生产。当前,立足粮食安全,耕地保护极端重要性日益凸显,从法律法规到政策制度,从中央到地方,耕地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但耕地保护涉及的关键性问题——耕地概念,政府部门、专家学者、社会公众认识不尽相同,有些概念与当前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也不相适应,有必要从国家粮食安全视域审视和探讨耕地的概念。
1 中国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始终把解决人民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首要任务。粮食安全涉及消费与生产两侧,消费侧核心影响因素是人口与人均需求(包括膳食结构),生产侧核心影响因素是耕地数量与单产水平。
1.1 粮食消费情况
1.1.1 人口情况
从历史上看,人口数量与粮食总量总是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人口数量决定了粮食的劳动生产资源和需求量,粮食总量又决定了可以维持的人口数量。康乾以来,我国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耕地数量大幅增加以及玉米等南美作物引进带来的粮食产量增加。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大陆人口为5.4亿人,至2020年,突破14亿人,增长至141178万人。其中,1990年以前,我国人口数量基本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年增长率保持在1.48%以上;此后人口增长率逐步下滑,至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年增长率降至0.53%。2020年以后,我国人口增长率下滑的总体态势并未改观。2017年我国净增人口737万人,2018年降为530万人,2019年降为467万人,2021年新增人口猛降至48万人,较2015年新增人口下降了1607万人(图1)。2022年全国人口减少85万人,首次出现了负增长,预示着我国人口进入了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区间。2021年的141260万人很可能是我国人口的峰值。
1.1.2 居民膳食结构情况
考察我国粮食消费,首先要看到40多年来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我国居民膳食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传统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模式正在向动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模式转变,特别是城市居民米、面、粗粮等主食摄入量呈持续下降的趋势,水产品、副食品、果蔬、肉类加工制品的消费量反而显著增加。动物性食物消费在2000年开始超过食物消费总量的一半以上,2017年城镇居民的人均肉类消费量超过21kg,而后呈逐年递增态势,植物性食物的消费量逐渐减少。由于动物性食物所含脂肪热量较高,蛋白质供给充足,居民营养摄入水平逐渐提升,社会消费层次有了一定提高[1]。我国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中,动物性食物消费量远少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动物性食物消费占自身食物总消费量的1/6,猪肉仍然是农村居民消费肉类产品的主要类型,占肉类消费总量的65%,农村居民对粮食的消费量从20世紀90年代的最高峰(1990年人均260kg)逐渐下降到2017年的200kg。21世纪以来,农村居民人均蛋制品、奶制品、蔬菜的消费量逐年走高,营养水平也相应有所提高,与1990年相比,2018年农村人均每日蛋白质摄入量增加了30.4g/人,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渠道增加[2]。
比营养物质变化更为直观的是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的变化,主要特点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蔬菜、水果、肉、奶的消费量明显增加(表1)。2020年我国居民消费的蔬菜、水果、肉、奶、鱼和水产较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分别增长了597%、1148%、336%、553%、767%、1164%,即使与21世纪之初(2000年)也增长了42%、85%、41%、122%、58%、211%。可以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的膳食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吃得越来越丰富。与此同时,粮食的消费在1995年之后便基本保持稳定,2010年后虽有小幅增长,但主要原因是由于饲料用途的增加。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食用消费在谷物消费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与之对应的是用于饲料的谷物消费占比持续攀升,并且2010年后这种趋势还有所扩大。谷物消费结果的变化也反映了居民食物消费中肉、蛋、奶快速增加,进而对于饲料的需求也跟着快速增加。
1.1.3 粮食消费需求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我国居民主要食品消费量中,人均年消费粮食141.2kg,这已经是2014年以来的高点;同时,近年来,人均食用油消费量基本保持在10kg以上;人均肉类和禽类保持在37kg以上;蔬菜消费量仍呈现逐年上涨趋势,达到了103.7kg;人均消费的水产品、蛋类、奶类、干鲜瓜果类也都保持了逐年上涨趋势,分别达到13.9kg、12.8kg、13.0kg、56.3kg,其中蛋类和干鲜瓜果类增长较快,较2015年分别增长了34.7%和26.5%,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这种趋势短时期内不会产生太大变化。如果以我国人口高峰14.2亿人计算,我国需要用于食用的粮食要达到2亿t左右。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6.8亿t(其中谷物6.3亿t),2015年以来一直保持在6.6億t,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83kg,高于国际公认的400kg粮食安全线,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表2)。即使按照2010年以前的谷物消费水平,有50%的谷物用于食用消费,6.3亿t谷物产量满足2亿t的食用需求也是有保障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缘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下的居民膳食消费结构升级,粮食安全的内涵从口粮安全层次上升到整个食物系统安全与营养安全的新高度[3]。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指出,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在不断升级,今后农产品保供,既要保数量,也要保多样、保质量参见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2月28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生产肉、禽、蛋、奶等动物性食品都需要消耗粮食,转化成1kg肉蛋奶平均需要大约5kg的“粮食单位”(包含粮食和牧草)。因此,居民对肉禽蛋奶需求的增加带动了对饲料用粮需求的持续增加,使得用于饲料的粮食占比不断提升。2000—2021年,我国饲料加工总量从3741万t快速增长到31697万t,增幅高达747.3%,年均增长10.7%。与此同时,主要粮食作物的饲用数量也都有较大增长,饲料粮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的14%增长到本世纪初的35%,再到2020年达到42%[45]。有研究预测,我国粮食总需求在2035年达到峰值(6.762×108 t),而饲料粮消费持续增加至2050年(3.317×108t),口粮消费稳步降低,油料与食糖消费保持增长[6]。实际上,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问题不在总量,而在结构上。我国玉米存在产需缺口,大豆和食用油缺口较大,大豆自给率不到20%,食用油自给率不到40%,优质饲料、饲草的需求也快速增加,其根源是居民膳食结构中动物性食品占比持续增长,未来饲料粮需求量很可能会占到粮食总需求量的半数。长期看,我国粮食安全实际表现为“饲料安全”,而非直接食用粮食安全。
1.2 粮食生产能力
1.2.1 耕地变迁情况
相比与森林、草原、湿地等大自然的伟力造就,耕地因人而生,是人类进入农耕文明的杰作。历史上,耕地数量总是伴随着人口数量以及因生存对改造自然的需求而变化,例如康乾时期我国人口快速增长,伴随着的是清政府大力鼓励垦荒,从乾隆五年至乾隆三十五年(1740—1770)的30年间,垦田数字已在20万hm2以上,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人口迅速增长带来的压力[7]。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民在土地改革中获得了土地产权,开荒整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全国耕地总量从1949年的1.4亿hm2直线上升到1957年的1.56亿hm2,为历史最高水平。此后,耕地总量持续下降,并在减少的结构上整体呈以下路径:基建占用>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生态退耕占用。每个时期耕地数量的波动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息息相关。1949—1977年的耕地变动与政治运动、农业和粮食生产特别相关。1978—1990年代的耕地变动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特别相关。1990年以后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大量推广特别相关[8]。进入新时代后,生态文明建设也成为耕地变动的一大因素。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结果,2019年底我国耕地数量为1.29亿hm2,10年间骤减0.08亿hm2,耕地转为林地、园地成为主因参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其中耕地净流向林地1.12亿亩,净流向园地0.63亿亩。当然不可否认也有调查原则和技术标准差异的原因,但不会影响耕地数量减少的总体趋势判断。而耕地大量转为园地,虽然表面上是农民增收的需要,但市场价格调节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膳食结构变化带来了需求侧的快速增长,进而带动了农业生产供给侧的调整。
伴随着耕地数量减少和人口增加,我国人均耕地数量也一直呈现下降趋势。1949年我国人均耕地0.26hm2,2019年减少至0.1hm2,不及建国之初的一半。应该说我国人民不缺吃主要得益于农业科技进步带来的农作物单产提升。但愈是如此,耕地保护越不能掉以轻心,毕竟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全球人均耕地数量的1/3,每一寸耕地都十分珍贵。再高的单产能力也需要乘以耕地数量这个基数。
1.2.2 粮食产量情况
建国以来,粮食亩产不断提高。1980年以前,受农田水利设施极大完善等因素的影响,亩产从建国时的68.5kg增长至182kg,30年间增长了1.6倍;改革开放以后,受杂交水稻等育种技术发展等带动,至2020年亩产增长至382kg,40年间又翻了一番。
随着亩产水平的增加,建国70年间我国粮食年产量不断提升。1949年,我国粮食产量仅为1132.8亿kg,1962年稳定在1500亿kg以上,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超过3000亿kg。此后一路攀升,到1996年首次突破5000亿kg大关,2012年迈上6000亿kg台阶,2022年粮食总产量达到6865亿kg,比新中国成立初增加了5000万kg,从而在同期人口增加一倍多的情况下,人均粮食占有量比建国之初翻了一番多参见2020—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
1.2.3 粮食生产对耕地数量的需求
以目前我国粮食亩产380kg测算,满足我国每年2亿t食用粮食,需要播种面积达到0.36亿hm2。当然饲料等需要的粮食也必须考虑,如果保持我国人均粮食占用量480kg水平(高于联合国400kg粮食安全线),需要播种面积达到1.2亿hm2(18亿亩),按照1.55耕地复种指数测算,需要耕地0.77亿hm2。2022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1.19亿hm2,如果按照1.55耕地复种指数测算,需要耕地数量也接近0.77亿hm2耕地。我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约1.4亿hm2,里面还包括了接近0.13亿hm2油料作物、0.03亿hm2棉花、0.02亿hm2糖料和超过0.21亿hm2蔬菜,如果按照1.55耕地复种指数测算,相当于使用了1.09亿hm2耕地。
目前我国粮食结构性短缺,自给率比较低的是大豆和植物油。2021年我国进口大豆9108万t,20%加工产品为豆油,80%加工产品为豆粕,作为动物饲料的主要成分。按照我国大豆单产1980kg/hm2测算,如果进口大豆量都由国内生产,需要播种面积达到4.7亿hm2,这是我国耕地资源难以支撑的。总之,伴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的升级,我国资源环境的承载力日趋紧张[9]。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既需要保护和利用好现有耕地,还需要统筹利用好园地、林地甚至具备一定条件的未利用地资源,向整个国土空间要生产力。
2 国际上对耕地概念的界定
从国外经验看,联合国粮农组织及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有些有明确的耕地分类,有的则没有明确界定耕地,而是将用于和服务农业生产的土地作为作物用地,并且大多数国家没有单独设立同级分类的园地,而是将果园、苗圃以及其他种植多年生作物的土地作为作物用地或者耕地的一部分看待。
2.1 联合国粮农组织
联合国粮农组织对土地分为4类:可耕地和长期种植作物的土地;永久性牧场和草地;森林用地;其他土地,包括城市地区、公园、未利用地和其他未另做划分的土地利用类型。可耕地和长期种植作物的土地是用于种植作物的土地,即作物用地,包括临时的(一年生作物)和永久的(多年生作物),还可能包括定期休耕或用作临时牧场的地区。多年生作物用地是种有长期生长作物而无需在每次收割后再进行种植的土地,此类作物包括可可树、咖啡树和橡胶树。此类土地包括生长开花灌木、果树、坚果树和葡萄树的土地,但不包括木材林用地。显然,联合国粮农组织对耕地的概念更倾向“农田”的概念,因为包含了大约10%用于种植永久性作物,如果树、油棕和可可的土地参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网站(https://www.fao.org)。并且相对于耕地,联合国粮农组织从保障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即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所需要的基本食品,更为重视农业用地的概念,全球农业用地约为47.4亿hm2,包括草地、牧场及农作物用地。
2.2 美国
美国是农业最发达的国家,是世界第一大粮食出口国,控制了全球超过一半的粮食市场。20世纪60年代后,美國组织进行了全国1∶20万土地利用图编制工作,将土地分为9大类:城市与建筑用地;农业用地;草地;林地;水面;湿地;荒地;苔原;永久积雪与冰。美国主要以土地功能作为分类的主要依据。农业用地主要包含3类:一是收获的作物用地,包括所有的收获了作物或干草的土地、所有果园、柑橘园、葡萄园、苗圃以及温室作物用地;二是用作牧场或放牧的作物用地,包括不需要采取额外的改良措施就可以用作作物生产的轮作草地和放牧地;三是用于种植覆盖土地表层的作物、豆类作物以及改善土壤草类作物但不用于收获和不用于牧场的作物用地。由此可见,美国农业用地不仅涵盖了我国土地分类中的耕地,还包括了园地以及相当一部分的草地。为做好土地调查和定级分类,美国还将农地划分为4大类进行差别化管理。一是基本农地,最适合生产粮食、饲草、纤维和油料作物的土地;二是特种农地,生产特定的高价值粮食、纤维和特种作物的土地;三是州重要农地,不具备基本农地条件而又重要的农地;四是地方重要农地,有很好的利用和环境效益,并被鼓励继续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10]。
2.3 法国
法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农产品第二出口大国。法国的农业有效用地4.7亿余公顷,占国土面积的85%,占整个欧洲有效农业用地的34.6%,其中耕地面积达22.7万km2,占国土面积的一半。法国对于农场土地的划分主要分为有用的农业土地、木材森林用地以及非农业土地,其中有用的农业土地又分为了农业土地、建筑占用土地和非生产性用地。农业土地包括了13种种植的土地,包括谷类、经济作物(含油种子、棉花、烟草等)、干蔬菜(豆类、小扁豆等)、马铃薯等、饲料作物(玉米、苏丹草等以及人工牧草、临时牧草(5年及以下))、休耕地、新鲜蔬菜、花卉和观赏植物、葡萄、果树、其他多年生作物、永久性牧草、家庭菜园。法国为了农业土地分类是适应以畜牧业为主、农林牧并举的农业生产结构,畜牧业在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比种植业高10多个百分点。法国同美国一样,通过农场总面积和具体土地利用面积指标,来反映农场土地占用状况和农场土地的具体利用情况。
2.4 日本
日本是岛国,耕地面积仅占世界耕地面积总数的0.4%,人口却占世界人口的2.2%左右,在自然资源奇缺的背景下,日本采用零碎地系统化耕种,走专业化集约经营农业发展之路,但也同时成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之一。日本将土地按照一定的层次等级划分了若干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别,但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最权威的是《日本统计年鉴》的划分。它将日本的土地分为农用地、森林、原野、水面、道路用地、宅地、其他用地7个大类,其中农用地又包括水田、普通旱地、果园地、牧草地4个二级类。水田是指种植水生农作物的农用地;普通旱地是指种植旱生草本作物的农用地;果园地是种植旱生木本作物的农用地;牧草地是指用于用于畜牧业的农业用地。相比较,日本对于农用地的定义是根据农业生产用途而确定,与我国不同,主要不包含林地。日本没有明确划分出耕地,而是将水田、旱地、果园地等种植业的土地作为一大类[11]。
2.5 印度
印度国土面积只有298万km2,但是可耕地面积却高达1.6亿hm2,排名世界第一。印度是世界第二农业大国,也是世界第二大米和小麦产量国,近年已成为农产品净出口国。印度的土地大体可以分为农业用地和非农用地。印度有60.4%的土地是农业用地。对于地类划分,印度主要以土地覆盖情况(自然属性)为依据,农业用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等,没有单独的园地分类。受人口因素的影响,印度高度重视农业用地保护,对用途转用实现审批制,只有转化土地性质为非农用地才可以作为工业商业用途。2005年印度设立了国家园艺委员会负责发展农业多种经营,园艺作物特别是水果、蔬菜调味料、茶、咖啡、橡胶等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呈增长态势,并允许100%外资在茶叶、花卉种植业、种子培育、动物管理、渔业、水产业、蔬菜和蘑菇培育等领域进行投资[12]。农业中的作物份额也从2011—2012财年的62.4%下降到了2019—2020财年的55.5%。
2.6 地理角度对耕地概念的认识
1949年,第16届国际地理大会发起开展全世界1∶100万土地利用图编制工作,用于世界土地利用调查的分类为9类:居民点和非农业用地;园艺用地;木本和其他多年生作物用地;栽培作物用地;改良的永久性牧场;未经改良的牧草地;林地;沼泽;非生产性用地。
199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FAO对土地覆被分类体系框架提出讨论建议:内地水域;木本沼泽;裸地;森林和林地;矮灌群落;草地;耕地及建设用地共9个一级类。1997年,UNEP和FAO正式提出土地覆被分类系统(LCCS),区分出8个土地覆被大类:耕地和管护区;天然和半天然植被覆盖土地;耕作水生植被水域;天然和半天然水生植被水域;人工构筑物;裸地;人工水域;内陆水域。目前LCCS已被批准为国际标准,包括20个分类,包括农田、稻田、农田/其他植被、阔叶常绿森林、阔叶落叶林、针叶常绿森林、针叶落叶林、灌木、草本、湿地等[13]。自然资源部制作的30m精度全球地表覆盖分类数据(GlobeLand30)采用了耕地、森林、草地、灌木地、湿地、水体、苔原、人造地表、裸地、冰川及永久积雪10种地表覆盖类型,其中耕地是指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水田、灌溉旱地、雨养旱地、菜地、牧草种植地、大棚用地、以种植农作物为主间有果树及其他经济乔木的土地,以及茶园、咖啡園等灌木类经济作物种植地。该数据也由中国政府赠送给了联合国。
3 中国对耕地概念的定义
与森林、草原等地表覆盖类型不同,耕地是伴随着人类文明进入农耕文明时代而产生的,并不是出自大自然的伟力,而是来自于人类对大自然的改造。对于耕地的概念的理解,可以从历史、常识、法律、技术等不同角度去理解,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3.1 历史角度的耕地概念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农业的出现和发展大致不超过一万年,在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驯养繁殖动物和种植谷物,表现在耕作制度上,主要有轮垦制、烧垦制,耕地由此产生。根据有关专家估算,从长时间尺度上看,全球耕地面积总体呈爆发性增长趋势,公元前一万年前,耕地面积为零;1500年就到了280万km2,然后发展到1850年的620万km2、2010年的1640万km2[14]。在中国古代,耕地更倾向于“田”的概念,而且是朝廷和民间最重要的资产,也是赋税的主要来源。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秦王政三十一年(前216年)推行“黔首自实田”,即朝廷承认土地私有。北魏在原有私有制的基础上,对于这些荒芜土地推行公有制,这便是“均田制”。唐德宗时颁布两税法,均田制宣告瓦解。明朝张居正变法推行“一条鞭法”,将各州县的田赋、徭役和其他杂税归为一条。清朝康熙五十一年实行“摊丁入亩”,将固定下来的丁税平均摊入了田赋之中。同时为保障赋税,许多朝代也组织清丈田地,甚至要求“田有军田、民田、僧道田,各项夹杂,俱照民田一起挨顺栉比鳞次丈去,但于册内各自注明,不得跳越次序,混淆丈法”[15]。根据税赋、用途等不同,“田”的分类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也比较混乱,主要包括:大粮地、征粮地、寄庄地、穀地、荒田地、额外荒田地、更名地、籽粒地、民粮地、官庄粮地、马场租地、芟草地、湖田、学田、义田、祭田、屯地、军地、杂项地、教场坡地、灶地、民佃灶地等。还有一些其他类属地亩,例如棉花地、花绒地、荣麻地等,主要用于指定的农作物生产,属于生活或军备的必须品,一般总量不是很大[16]。总之,中国古代“田”的范围要大于今天对于“耕地”的理解范围,且其分类的依据主要是性质和规划用途。
3.2 常识角度的耕地概念
《辞海》中耕地是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汉语词典》对耕地的解释是“可以耕种的田地”,更趋近于字面的理解。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地理教科书对耕地的解释是“自然土壤发育形成的,能够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并具备可供农作物生长、发育、成熟的自然环境。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耕地作为人类进入农耕文明时代而出现的产物,无论是烧荒、垦造还是其他方式,其目的都是生产粮棉油糖菜、麻桑烟果茶等培育农作物的种植,不应因种植作物不同而使耕地的地类性质发生变化。尤其是随着社会发展,农业生产的内涵有了巨大变化,耕作的对象日益广泛,耕地一词所涵盖的范围也显然扩大了[17]。对于普通种地农民而言,比较容易区分耕地和林地、草地,特别是还有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权益保障,但受知识水平、常识认知等限制,对于耕地和园地的区别,在许多时候有一定难度。《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对农业的定义是指各种农作物的种植活动,其主要利用土地应该理解为耕地,但实际上也包括大部分的园地;而林业、牧业主要利用林地、草地。
3.3 法律角度的耕地概念
《土地管理法》作为土地管理的基本法律,虽然设立了“耕地保护”专章确立了耕地保护的一系列法律制度,但并没有对“耕地”的概念作出规定。目前,界定耕地概念的法律只有《耕地占用税法》,其第二条明确“本法所称耕地是指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这个定义于《辞海》和常识理解的耕地基本一致。同时,《土地管理法》虽然没有对耕地概念作出规定,但在1998年修订时在农用地种类中删除了“园地”参见《土地管理法》第四条第三款,前款所称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1998年10月,原国家林业局在《关于如何区分林地和园地问题的复函》也明确指出依据《土地管理法》“园地”已不属于一种单独的土地类型。目前正在制定的《耕地保护法》作为专门规范耕地保护的法律,在起草过程中也将耕地概念问题作为重大问题予以研究,试图有效协调技术逻辑、空间规划、行政管理、种植状态以及公众认识等不同维度上的“耕地”,从立法上明确“耕地”的概念[18]。其征求意见稿对耕地的概念是“指利用地表耕作层种植粮、棉、油、糖、蔬菜等农作物,每年可以种植一季及一季以上的土地”。
3.4 技术角度的耕地概念
在技术标准及管理中,最普遍适用的耕地概念来自《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07),其明确耕地是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熟地,新开发、复垦、整理地,休闲地(含轮歇地、休耕地);以种植农作物(含蔬菜)为主,间有零星果树、桑树或其他树木的土地;平均每年能保证收获一季的已垦滩地和海涂。耕地中包括南方宽度<1.0m,北方宽度<2.0m固定的沟、渠、路和地坎(埂);临时种植药材、草皮、花卉、苗木等的耕地,临时种植果树、茶树和林木且耕作层未破坏的耕地,以及其他临时改变用途的耕地。虽然其总体对耕地的理解与《辞海》和常识保持一致,但其细化范围中将园地予以排除,使得耕地范畴要小于国际上多数标准和常识理解的耕地范畴。而其对园地单独分类,虽不违反《土地管理法》,但与法律修订删除“园地”的用意实不相符。2020年,自然资源部发布了《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结合自然资源改革发展需要,将耕地概念调整为“指利用地表耕作层种植农作物为主,每年种植一季及以上(含以一年一季以上的耕种方式种植多年生作物)的土地,包括熟地,新开发、复垦、整理地,休闲地(含轮歇地、休耕地);以及间有零星果树、桑树或其他树木的耕地;包括南方宽度<1.0m,北方宽度<2.0m固定的沟、渠、路和地坎(埂);包括直接利用地表耕作层种植的温室、大棚、地膜等保温、保湿设施用地”,突出了“每年种植一季及以上”,试图将耕地与园地清晰区分开。
4 完善耕地概念的建议
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来看,特别是我国膳食结构的变化以及“大食物观”的要求,即使不考虑巩固脱贫成果和农民增收因素,园地作为丰富食物来源和满足人民膳食结构变化需要的根基作用也越来越突出。从国际上来看,多数国家对于耕地等资源的管理是紧紧围绕农业生产的需要展开的,并没有将园地从耕地中单独区分出来,而是同时作为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资源加以利用。园地和耕地在土地自然适宜性上是分不出来的,园地有宜耕地基础[19]。而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訂时删除“园地”表述更使得“园地”一词在所有法律中均未有明确规定,其反映出的深意在当时虽未引起管理部门的重视,时至今日则不得不需要认真思考。如何使管理逻辑、技术逻辑更加趋近于人们的常识,减少认知成本,是“耕地”与“园地”必须处理的关系。
从使用目的和功能上看,虽然耕地和园地在种植方式和作物上有所不同,但其目的基本上都是以满足人民的食物需求为主,多数园地的利用方式不会造成耕地层破坏,种植作物转换较为便捷,从大食物观的角度考虑,园地与耕地的功能定位虽有不同,但基本一致,都以生产食用农产品为主导功能。从空间功能上来说,耕地与园地都属于农业生产空间,与设施农用地等地类为村域物质供给、基础生产提供载体[20]。虽然将园地单独归类、区别于耕地管理,使得管理更为精细化,更能够辨识用于粮食及重要农产品生产的土地资源从而加以严格保护,但也使得管理成本较高,随着耕地“进出平衡”制度的实施,考虑到园地与耕地间种植互换的频繁度和农民对于耕地、园地概念的理解程度,行政管理成本还将上涨参见《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号),该文件首次提出了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的“进出平衡”,并规定可跨行政区域统筹落实耕地“进出平衡”。。同时,在耕地备受重视的同时,园地等一些同样重要的农业生产土地资源却受到忽视,长期处于部门监管职责的缝隙之中,用途管控强度较耕地、林地、草地等差距明显,从“大食物观”和我国居民膳食结构的发展趋势的角度考虑,特别是在我国农业生产土地资源趋紧的条件下,并不利于我国的粮食安全和居民生活水平提升。
而通过“种植一季及一季以上”试图区分耕地和园地的努力在实践中也可能遇到问题,比如一些多年生草本的中药材。还有随着作物栽培技术的发展,一些作物也可能从一年生转变为多年生,像云南大学胡凤益团队就成功把一年生稻变成多年生稻,一年生花卉发展到多年生的则更多。同时,耕地的概念过于强调技术逻辑,而忽视管理逻辑,特别是规划属性,在行政管理特别是用途管制制度、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等基本制度执行时也会遇到问题,比较突出的是用途转换过严,在改进和规范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占补平衡的同时,延伸至农用地内部结构调整及设施农用地落实耕地“进出平衡”[21]。因此,在林地、草原、湿地等均强调“占补平衡”的情况下,不同地类间的空间置换缺乏操作空间和路径。而现实的复杂性决定了难以以一种绝对的一刀切方式管理耕地,耕地的多功能需要一种相适应的弹性管控方式,而以自然生产及其潜力重新定义契合“藏粮于地”的耕地概念,是实现弹性管控的基础[22]。像林地,《森林法》规定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确定的用于发展林业的土地。这体现了管理逻辑和规划属性,用途管制的基础来源于规划,为符合“规划”条件特别是“多规合一”条件下统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提供了充分基础。
现行耕地概念是小农经济的产物,需要适应我国农业特别是种植业发展的需要[23]。大道至简,有必要通过借鉴国内外以粮食种植适宜性和生产稳定性为核心的耕地内涵界定经验[24],将耕地的概念回归本义与常识。笔者认为应当将耕地界定为“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这与一般人们理解和《耕地占用税法》等所定义的耕地是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相契合,也与当前耕地多功能、土地分离。对于农作物的定义与范围则可以由农业相关国家标准予以明确。目前,《农产品分类与代码》(NY/T3177—2018)种植业产品中不仅包括粮食、油料、蔬菜等,也包括果品、烟草等,同时,在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中取消“园地”一级类,将除橡胶园外的果园、茶园等二级类直接归入耕地中,作为耕地的二级类,从而将其保护力度提升到耕地水平,明晰部门监管职责,减少行政管理成本,使耕地与保障种植业发展的功能更加适配,也与正在建立的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更加适配,更好地保障我国粮食及各类农产品的生产能力。并且,由于维持了土地利用现状二级分类,不会影响不同时期耕地数据的比对分析。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考核等也可以采取继续锁定水田、水浇地、旱地的方式保持政策延续。
5 结论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并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新时代粮食安全的基本追求不在于如何扩大生产规模,而在于如何推动粮食生产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一方面推动粮食产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另一方面有效缓解耕地等资源环境约束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威胁[25]。耕地概念是所有耕地保护制度和措施的基础,是耕地保护工作的“原点”,必须适应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统筹法理逻辑、管理逻辑、技术逻辑与常识认知,予以完善。要立足国家粮食安全整体性要求,从“大食物观”出发,破除简单以技术逻辑和客观现状界定耕地,拓展和丰富耕地概念内涵与范围,将耕地概念界定为“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使园地纳入耕地范畴,并体现耕地的管理逻辑和规划属性,从而将目前也是农业(尤其是种植业)生产重要土地资源的园地纳入现行耕地保护制度范围,形成对农业生产土地资源的整体保护,避免在多种自然资源“占补平衡”制度下园地成为农用地流失的缺口,形成对国家粮食安全整体利益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1] 马云倩,徐海泉,郭燕枝.中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及未来发展政策建议[J].中国食物与营养,2016,22(11):4650.
[2] 熊靓,王东阳.居民食物消费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20省居民食物消费调研[J].中国食物与营养,2017,23(3):4953.
[3] 马爱锄,杨改河,黑亮.粮食安全新内涵与中国粮食安全态势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111116.
[4] 黄季焜.中国农业的过去和未来[J].管理世界,2004(3):95104.
[5] 熊学振,杨春.中国粮食安全再认识:饲料粮的供需状况、自给水平与保障策略[J].世界农业,2021(8):412.
[6] 郑海霞,尤飞,罗其友,等.面向2050年我国农业资源平衡与国际进口潜力研究[J].中国工程科学,2022,24(1):2028.
[7] 白新良.乾隆初年的粮食问题[J].历史教学,2002(4):5960.
[8] 傅超,郑娟尔,吴次芳.建国以来我国耕地数量变化的历史考察与启示[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07(6):6872.
[9] 王晓君,何亚萍,蒋和平.“十四五”时期的我国粮食安全:形势、问题与对策[J].改革,2020(9):2739.
[10] 涂继美.美国耕地保护制度及其启示[J].上海土地,2021(5):3842.
[11] 龚汗青,段建南,徐洁.日本土地利用分类研究及启示[J].山东农业科学,2014(5):153156.
[12] 杨东群,李先德.印度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现状及问题[J].世界农业,2007(6):4447.
[13] 张小红,朱凌.LCCS地表覆盖分类系统简介及图例翻译[J].北京建筑大学学报,2017,33(4):4552.
[14] CAO B,YU L,LI X,et al.A 1km global cropland dataset from 10000 BCE to 2100 CE,Earth Syst.Sci.Data Discuss[EB/OL].https://doi.org/10.5194/essd2021219,in review,2021.
[15] 杨国安.清代康熙年间两湖地区土地清丈与地籍编纂[J].中国史研究,2011(4):159177.
[16] 朱义明.清代山东耕地地亩种类辨析[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9(4):5163.
[17] 夏早发,雷春.关于如何界定耕地概念的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1999(3):1415.
[18] 魏莉華.土地法治建设的主旋律:耕地保护[J].资源与人居环境,2022(6):1215.
[19] 朱改华,殷海善.耕地概念辨析[J].华北国土资源,2008(4):2526.
[20] 许庆福,许梦,张晓艳.生态化土地整治视角下的村域“三生”空间营造[J].山东国土资源,2021,37(2):6772.
[21] 张雅芹,齐俊,梁勇,等.耕地用途管制制度下的济南市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潜力研究[J].山东国土资源,2023,39(4):7782.
[22] 钱家乘,师诺,赵华甫,等.中国耕地弹性管控的理论解析与研究框架:从单一目标权衡到多目标协同[J].中国土地科学,2023,37(3):3847.
[23] 夏早发,雷春.关于如何界定耕地概念的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1999(3):1415.
[24] 孔祥斌,谢恩怡.关于耕地内涵与界定的思考[J].天津农业科学,2023(4):812.
[25] 何可,宋洪远.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粮食安全:内涵、挑战与政策取向[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3):4557.
Discussion on Cultivated Land Concep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Food Security
QI Shijing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of Shandong Province,Shandong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Focusing on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condition of our country, starting from the vision of guaranteeing safety, the necessity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during the variation of food security concept has been analyzed.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overview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cultivated land concep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common sense, technique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cultivated land concept have been put forward. Quantitative analysis, empirical analysis, logistical analysis,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have been used in this study. It will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strengthening the ability to guarantee food security and arable land security. The current concept of cultivated land overly emphasizes technological logic,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China's food securi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residents' living standard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igh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land resources. Especially, the production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the main function of gardens and cultivated land. It is necessary to adapt to the needs of China's agriculture,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anting industry, return the concept of cultivated land to its original meaning and common sense, include land resources, such as gardens that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anting industry in the scope of cultivated land, and endow the concept of cultivated land with management logic and planning attributes. By integrating legal logic, management logic, technical logic, and common sense cognition, the concept of cultivated land is defined as "land used for planting crops". It will form a pursuit of the overall interests and values of national food security.
Key words:Land resource; food security; cultivated land; concept; garden plots
收稿日期:20230905;修訂日期:20231206;编辑:陶卫卫作者简介:齐世敬(1985—),男,山东临沂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管理法律制度、测绘地理信息管理等;Email:qishiji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