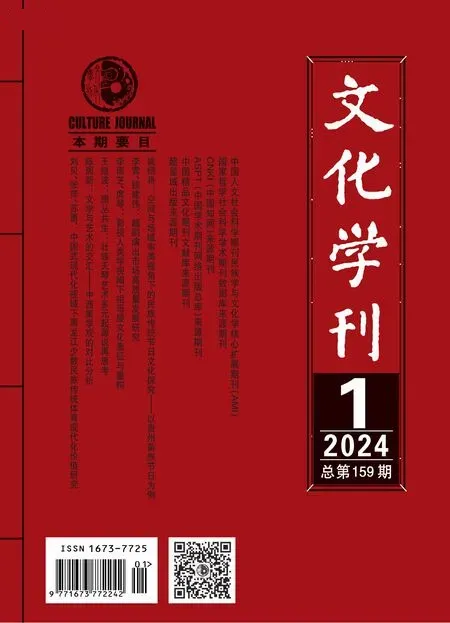晚唐作家黄滔文学观略论
张 洁
黄滔,字文江,泉州莆田人,晚唐士人,其诗文与韦庄、孙樵等人齐名。其诗文收录于《全唐诗》《四库全书》《丛书集成》,从其诗文集《蒲阳黄御史集》出发,通过分析其作品中的书信、序、赋等文章,探讨其诗歌理论和古文观点。
一、黄滔的诗歌理论——《答陈磻隐论诗书》
陈磻隐,字希畋,生卒年及籍贯不详,大致活动于唐懿宗至唐哀帝时期,与黄滔有诗文唱和。《莆阳黄御史集》有《寄陈磻隐》诗,《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有《陈蟠隐集》五卷,于今不存。《答陈磻隐论诗书》见于《莆阳黄御史集》,当是黄滔与陈希畋讨论诗歌而回复的一封书信,其以书信的形式与朋友探讨了诗歌的本质、创作和艺术等方面,表达了自己的诗学理论与文学见解。
黄滔接受并认同诗歌的教化功用:刺上化下。他认为,作为一个诗人,诗歌的创作要以“国风王泽”为本。他例举白居易的《长恨歌》所批判的社会现象,“此刺以男女不常,阴阳失伦。其意险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哉!”讥刺唐末时局混乱,战火连天,天下男子尽充军,死于战乱者十有八九,老百姓不愿意再生男孩儿,社会生育观念在战争的冲击下畸形变态。在这种时局底下,黄滔忧国忧民的本色使得他反对咸通、乾符之际的“郑卫之声”——“才调歌诗”。后蜀韦縠编有《才调集》,其自序曰:“或闲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但贵自乐所好,岂敢垂诸后昆?今纂诸家诗歌,共一千首,每一百首成卷,分之为十,目曰《才调集》[1]。”这种所谓的“韵高”“词丽”,黄滔以为这种的艺术创作与艺术追求是偏离了诗歌创作与诗歌功用的正道,以致“援雅音而听者懵,语正道而对者睡”,不知所云。
与此同时,此篇《答陈磻隐论诗书》黄滔了表达自己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方面的创见。
(一)“文”与“声”的辩证关系
其一,他认为“文不正则声不应”。著物象谓“文”,动物情谓“声”。“物物各有其状,各有其态”,描摹外在事物要真实可感,极尽状态,这样的文字才能使人动情,强调了客观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否则,“言之不当则不应”。
其二,他注意到诗歌的创作与诗歌的阅读之间真正产生互动需要情感共鸣,“文”与“声”要有互相回应。诗人“著物象”的目的是“动物情”,诗歌作品要先能使自己描写的“物象”使得自己产生“物情”。如若自己本身创作的诗歌作品打动不了自己的情感,如何可以打动阅读者呢?
其三,黄滔在《答陈磻隐论诗书》中探讨了自己的接受美学观念。黄滔认为,诗三百“感天地,动鬼神”,就是“文”所产生的“声”,而这“声”正好说明圣人删诗“合于《韶》《武》”的选诗标准。《诗经》文本接受者的心理、情绪等诸方面的反应体现出文本的意义和价值,而阅读者的一系列反应体现和丰富了《诗经》的文本潜能。黄滔还继续例举了两个艺术创作的事例,弹琴可以让鱼跃鹤舞,唱歌可以使云停尘落,“盖声之志也”。“琴之与歌尚尔,况惟诗乎!”他以为“诗”比“琴”“歌”更高尚,更应该追求“声”的回应。以此为标准来评判,他认为唐时的“李杜”“元白”四人的诗歌作品创作达到了“声文相应”的艺术高度。黄滔简明扼要以实证的方式探讨了文本的创作与文本的阅读、接受之间的关系,表明他诗歌理论的开拓性,彰显他本身的艺术理论修养。
(二)“李杜”与“元白”并提
此处“李杜”指的是李白和杜甫。“李杜”大致齐名于唐大历、贞元间[2]。与唐代不少诗人之并称多见于身后不同,元稹、白居易在世时,“元白”这一并称即已出现[3]。如《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元稹、白居易传论》曰:“(元)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4]。”《新唐书》卷一百十九《白居易传》曰:“(白)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5]。”黄滔在《答陈磻隐论诗书》应当是首先将李、杜、元、白四者并提之人。后蜀(934—966年)韦縠编选《才调集》,序有云:“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1]。”显然是晚于黄滔(840—911年)的并提。况且,黄滔并提“李杜”“元白”是注意到他们四人诗歌创作艺术的共同点——“声文相应”。时人或者后人评论、比较“李杜”“元白”两个组合的诗文创作的方方面面,黄滔却认识到他们四人作为一个群体在诗歌创作上的“著物象”“动物情”的创作追求与创作效果,在物象的描摹和情感的共鸣上与阅读接受者建立紧密联系,实现创作意图与情感回应的磁力场。
(三)客观的批判精神
黄滔在此篇回信中说:“诗本于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他肯定了诗歌的社会功用——刺上化下。但黄滔举例的却是《长恨歌》,谓:“此刺以男女不常,阴阳失伦。其意险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哉!”很明显,黄滔此时更看重的是诗歌的“刺上”功能。身处时局动乱的唐末,黄滔认为是统治阶级出问题,而不是百姓,这是非常清醒的认识,所以在诗歌创作的社会功用上,他更强调“刺上”,持有这种客观的批判精神的他可称得上是一名斗士。
其次,他提出诗歌创作要有“声文相应”的效果时,认为“自晋宋梁陈之来,诗人不可胜纪”,可“不知百卷之中,数篇之内,声文之应者几人乎”?大胆批判唐之前诗歌创作的偏颇,缺少应有的“声文相应”。这种不盲目推崇古人诗歌的精神确实可嘉。韩愈、柳宗元大力推崇古文,黄滔也是赞同者和追随者,但对于诗歌,他有着自己清醒的认知,认为本朝的李杜、元白的诗歌创作在“声文相应”的艺术效应方面比古人更好,认为此四者“信若沧溟无际,华岳干天”。予以这四人如此的评价,在后来的文学发展长河里,被证实是言不为过的。
再者,黄滔客观地评价了贾岛的诗歌。清人许印芳“跋严羽《沧浪诗话》”云:“浪仙在元和中,元、白诗体尚轻浅,(贾岛)乃独变格入僻,以矫艳俗,较诸令靡波流者,相去远矣。(韩)昌黎奇其才,赠诗云:‘天恐文章中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岂妄许可哉[6]。
黄滔也批评贾岛“搜九仞之泉,唯掬片冰;倾五音之府,只求孤竹”的奇僻,但同时看到贾岛这种艺术追求的时代意图——以矫艳俗。黄滔认同贾岛的诗歌创作艺术是因为“咸通、乾符之际”“郑卫之声鼎沸”,钦佩贾岛诗歌创作理念的时代批判性,认为贾岛是“前古之未有”的“孤峰绝岛”。或许,晚唐五代,贾岛式的“苦吟”才有“声文相应”的阅读群体。
二、黄滔的古文观点
《莆阳黄御史集》有《课虚责有赋》《与王雄书》《颖川陈先生集序》《送外甥翁袭明赴举序》《刑部郎中》二启诸篇,不同程度地反映着黄滔的古文理论,涉及古文的创作主张、创作过程、创作心理等方面,黄滔以不同的文体探讨古文创作的本质、内容和艺术等方面,表达自己的古文观点与文学见解。此处笔者只论及前人未论及或未详细论及的黄滔的文学观。
(一)探讨文艺创作的心理历程
黄滔的《课虚责有赋》,以“虚”与“有”的哲学辩证关系谈“道”如何化成“文”的过程。“含毫伫思”起源于“造化”——本于现实世界,这是为文的构思阶段。“囊括元牝,箕张混元”是素材的搜集阶段。“物居恍惚,牢笼而俟以真归。精匿杳冥,搜索而期乎实至[7]53。”对于掌握在手的素材要加以甄别、剪裁,去粗存精,为我所用。然后加之大胆的想象,“无论于远近高下,罔计于飞沉动植”。信手拈来,“扇作波澜,腾为气色”[7]53。黄滔认为有了这些还不够,说“文本于道,道不可量”,文章做得好,还要看创作者的个人身心修养和艺术修养。“取之者取之逾远,偶之者偶之不常。故其越兔影,迈乌光。向无声无臭之间;陶开品汇,于出鬼入神之际,定作圆方。乃使巧拙应机,亏全任器[7]53。”如果上述创作过程全备,那么文章就“虚”中生“有”了,正所谓“考其始而始则无睹,验其终而终则有自”[7]53。的确,为文之道,不可捉摸,也不可细究。黄滔以古代哲学的逻辑来考究文章的生成,此中又含有心理学意味。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曾经探讨过这样一个复杂隐秘的文学创作过程。从对外物的感知,到孕育、生成文学意象,再到意象的传达与接受,创作者在创作过程的审美心理活动、创作心理活动,黄滔以赋的文体形式,加之以传统的哲学视角来解读,虽不是理论的首创,但也是首次以律赋的文体来探讨、阐述这种文艺创作的心理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律赋的实用功能和范围,律赋在唐代常作为科考之文,重形式、艺术美,黄滔对律赋的使用,也是扩大律赋这一文体功能的积极尝试。
(二)“诸体兼善”之问题
《典论·论文》曰:“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8]3。”曹丕意识到文学创作者自有其擅长之技,并不能做到“诸体兼善”。黄滔《刑部郑郎中启》(一)云:“每虑或遗于片善,常忧不采于一言。比者伏蒙曲念虚芜,荣流咳唾,诲以磨铅未至,刻楮非工。冥心于雪夜花朝,空征“六义”。属意于国风王泽,罔造“二南”。将令罢课缘情,回从体物[7]201-202。”黄滔苦于诗歌造诣不深,不论他“冥心于雪夜花朝”的小事,还是“属意于国风王泽”的大事,都只能“浅近怀惭,雕镌积愧”,甚于产生“罢课缘情,回从体物”的念头,不写诗了,专心攻赋。可是不甘心就这样放弃,“前而复却,决以还疑。空眷恋于门墙,竟迟回于书幕”[7]202。为什么不愿意放弃诗歌创作呢?唐以诗赋取士,不得不为。“今则难逃皎镜,须诣平衡。冀分妍丑之姿,式定重轻之品。”黄滔一心想向刑部郎中郑讨教写诗技法,但却不知每个文学创作者都不可能做到“诸体兼善”,但必定有专工的一二项。黄滔的律赋成就相当高,在晚唐,与徐夤、王棨并称晚唐“律赋三大家”。黄滔前后历经举场二十四个年头,参加了二十场科试才进士及第,也许真的是因为自己的诗歌没办法写好的缘故罢了。如若抛开科举,专心为赋,黄滔兴许还能有更多更好的赋作,文学成就与文学地位或许也会随之而变。
(三)文体的精辟认知
黄滔《送外甥翁袭明赴举序》云:
诗言简,赋词饰,不可以叙事,故若之行也送以序。
袭明早举童子,旧儒因以小松为之目。袭明默而思,松之小者,千霄之势则尔,构厦之用则否。推是言之,龆而一飞,不若冠而十上。乃退硕乎业,果以词学擅州里誉。
……旋振于府帅州牧,遂不得留于膝下。
……矧词学擅誉,前辈梗于公道,或一倍两倍孙宏之上,今辈利于公道,无再献三献卞和之泣。若其勉诸。高堂之违,吾知不及荐闰[7]183。
黄滔以为诗语言简洁,赋词汇繁丽,都没办法用来叙事。而“序”则可叙事,适合送行之用。《莆阳黄御史集》仅存两篇序,除《送外甥翁袭明赴举序》,另有《颖川陈先生集序》一篇。《颖川陈先生集序》之“序”是文集的序言,一般是受人之托而作,《送外甥翁袭明赴举序》是黄滔外甥赴举之际而作的临别赠言。学术界目前对于赠别序的始作俑者及发展脉络尚无定论。且赠别序有别于诗序、赋序、碑序,是专用于临别送行,表达惜别之情,寄托美好祝愿。黄滔于此文开篇即论及文体特征及其功用,虽是片言只语,也能看出他对于诸类文体的认知相当精辟。于唐末,也是文体学发凡的理论先行者。
此外,《课虚责有赋》篇末有云:“然后知文苑之菁华,亦冲和之一派[7]54。”可见,黄滔主张淡泊平和的文风。黄滔将诗文理论用于实际创作,体现在其诗歌等作品中,就是静雅淡泊,如“谁人爱明月,露坐洞庭船”(《秋思》)、“无人不惆怅,终日见南山”(《辇下寓题》),等等。
陈庆元教授《福建文学发展史》一书对黄滔评价:“在唐末五代之际的闽中诗坛,黄滔不仅是一位诗歌成就比较突出的诗人,而且是唯一一位具有一定文学见解和诗歌理论的诗人。……黄滔的文论,下启宋人,在晚唐文人中,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9]。”如其所论,黄滔对于当时和后来闽地文学的创作、传播的贡献和影响是值得肯定的。而且,作为地域性文学特征明显的黄滔的文学理论开创之自觉意识和开创之功劳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