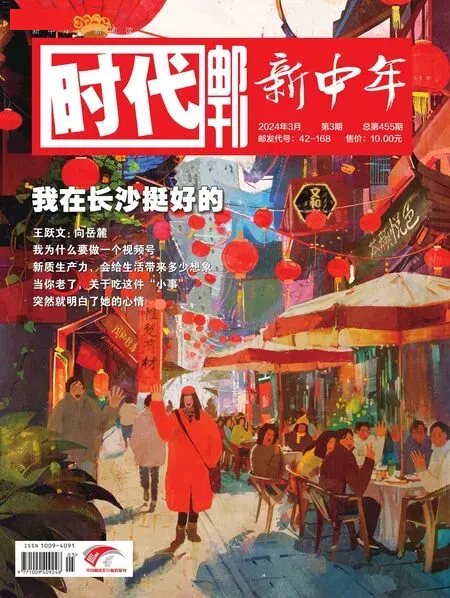重回江村
● 堵力 李超
吴江的闻名,离不开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当年在英国留学的他,写下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以一己之力将吴江的开弦弓村推上社会学研究的“国际高地”,为世界观察中国乡村打开了一扇窗。
近90年过去,江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名有志青年与土地亲情之间是如何互相成就、相得益彰的,费孝通用一生做了最好的诠释。

地灵,才会人杰;人杰,地才更灵。从春天到冬天,我们一次次走进江村,揭开这段历史背后的曲折,探访江村的建设者、记录者和返乡青年,试图让更多后来者认识到中国城乡破局的使命。
仰望城市与实业救国 费氏姐弟联手将江村推向世界
研究乡土中国对人心的抚慰作用,最有发言权的恐怕就是费孝通了。
这位学术大家25岁时遭遇了人生重大挫折——刚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毕业的他与妻子王同惠在广西大瑶山做实地调查,翻山越岭中,他误入捕捉野兽的陷阱,妻子急寻救援却在路上坠渊而亡。费孝通悔痛彻骨,姐姐费达生怕他想不开,便在1936年初夏将费孝通叫回故土吴江,来到开弦弓村养伤。
故乡的风和云、乡音与流水,为他抚平伤痕。他拄着双拐,走在田野间,渐渐从小我之痛中抽脱出来,将目光转向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开始了近两个月的田野调查。
那时的开弦弓村,传统养蚕业受到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巨大冲击,人民苦难深重。当人们对城市、对西方发达国家趋之若鹜时,新青年费孝通却在回视并锁定乡土中国,很多后人不解——他的这份自信来自哪里?
费孝通背后站着的是姐姐费达生。姐姐很小就树立了实业救国的理想,从日本留学归来便在家乡发展蚕丝工业。费孝通就是在姐姐的蚕丝试验田里,找到了中国乡村工业的最佳观察点。
1936年秋,费孝通抵英。1938年春,费孝通根据在吴江的调查,写出博士论文《江村经济》。1939年,这本书在英国出版,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著作。
费孝通“愿做山道上背盐的驮马”,一次次负重前行欲破困局。而遇到难题,他会回归故里,回到自然母体中汲取灵感,重新整装出发。
我们来这里时,开弦弓村飘着细雨,枕河而居的两层小楼旁边是一个小码头。那时,费孝通就是在这里下船开始乡村调研的。
村民姚富坤第一次见到费孝通,是在1981年,费孝通71岁,他29岁。在姚富坤的印象里,费孝通是一位慈祥的长辈。“村里人称费达生为费先生,称费孝通为小先生。”这位年逾古稀的“小先生”一进村,就拉着相熟的村民吃着定胜糕、喝着熏豆茶拉家常。
对于姐弟俩,姚富坤这样评价他们对家乡的贡献:当中华民族跌在困顿谷底之时,费达生将自己的一切都投入当地的蚕丝业,被当地人奉为“蚕花娘娘”;而费孝通则将这座小村推向学术庙堂,吸引了天南海北的人。
如今的江村,依旧是世界认识中国农村的窗口、海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农村的基地。
平视城市与青年入乡 “拉花阿姨”引出治理格局上台阶
“拉花阿姨”徐金妹是我们从震泽镇党委书记顾全口中听说的。徐金妹64岁,但她的职业生涯是从60岁开始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咖啡馆人手不够,请她帮忙冲咖啡,没想到,她用粗糙苍老的手拉出了仿佛“施了魔法”的花样,成为上海、苏州等地年轻人抢着合影的“拉花阿姨”。
“这里是集体经济,这些产业她都有份,她是这里的主人。”顾全欣赏地看着徐金妹,“她可不简单,白天在咖啡馆工作,晚上去饭店帮忙,一个月收入能有6000元。”
比起收入,更让徐金妹感到幸福的是,原本在外务工的儿女回到了村庄生活。
电瓶车驶在全长23公里的“稻米香径”乡村公路上,清风吹过,稻香扑鼻。顾全在介绍连片整治改造给村民带来的思想解放时说道:“我们这里有‘群英会三芳唱戏’。”
“三芳”指的是朱建芳、胡毓芳、谭桂芳3位村民。顾全解释,她们代表了吴江的第一二三产业。
第一产业的代表朱建芳,在齐心村工作30余年,成立了粮食生产合作社。第三产业的代表是“苏小花”咖啡店老板谭桂芳。胡毓芳是远近闻名的第二产业代表,她所创办的丝制品品牌太湖雪成功上市,行销全球。胡毓芳经常到米兰、罗马参加时装周活动,不过最让她开心的,还是在美国留学的女儿回国发展了。
胡毓芳说,公司直播团队的成员大多是90后、00后。她这两年招了好几名高校优秀毕业生。“年轻人回来了,乡村才更有生机。”
在吴江环长漾片区,震泽镇众安桥村谢家路的村民们口耳相传着“天天有笑脸,月月有鲜花,季季有水果,年年有分红”的民谣,诠释着什么叫中国式现代化。
但“美美与共”的理想境界,尚未实现。城里人每天在钢铁丛林中焦虑着,拥挤着,而农村则是大片空荡荡的小楼,只有老人守着土地。农村空心化、老龄化是这个时代亟待解决的难题。
顾全是村两委带头人,“三芳”是致富带头人,他们接下了费家姐弟的接力棒,为农村空心化破局,正在做一整套符合当地实际的乡村治理实验。
农村综合体与博物馆 “半城半乡CBD”办公也治愈心灵
费孝通极重传承,给自己唯一的女儿取名费宗惠,让“以身许国”的王同惠“永垂不朽”,也盼望后人继续“认识中国、改造中国”。
顺着费老超前的思考,吴江抓住了“江村效应”。《江村经济》世界闻名,什么是江村?可以是开弦弓村,也可以是吴江的村,也可以是江南的村,甚至是长江的村。共富的理念与振动波,以开弦弓村为圆心,向周边的村镇漾去。
“如今,经济打造着江村的物理空间,文化浸润着江村的精神田园。这才是无数外来游客追寻的精神世界。”姚富坤说,这里治愈了年轻时痛苦的费孝通,也可以成为更多城市青年的精神家园。
2019年,原媒体人吴嘉昊找到平望镇政府一起合作打造村上长漾里。她与村镇领导联络,与想来长漾里工作的年轻人联络,在各种办公楼、民宿“大干特干”。依托江村的生态、人文资源,她和团队对接了清华大学、腾讯集团,以及青年设计师等进驻“半城半乡”的长漾里。吴嘉昊希望打造一个乡村经济的综合体,“那些厌倦了城市忙碌生活的年轻人,是否想过把办公地点搬到江村?”
一直以来,学习机械工程设计专业的李鑫都有一个梦——为更多的企业、个人设计绿植方案。他认为,乡村是企业总部设点的一个好选择。因此,他来到长漾里,打造了一个植物艺术空间。
吴嘉昊与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和入驻的每家企业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要让高高在上的“设计”融入乡土,让每家企业既有自己的特点,又成为CBD的美好一景。
半城半乡半神仙,将对立的城乡关系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乡村成了城市延伸出来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人们在这里动手动脑,在一定的体力劳动中体验闲情逸致。
2023年,吴江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400亿元,工业总产值迈上5000亿元台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6.5万元。“志在富民”的梦想已经越来越近。吴江在用自己的方式延揽青春力量进入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吴江答卷正缓缓打开。
吴嘉昊还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她把吴江乡村模式推广了到广西和甘肃的农村,开始尝试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半耕半读新生活。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 中国青年返乡的使命在哪里
1999年,费老在人民大会堂操着带有浓重吴江口音的普通话对记者说:1840年鸦片战争后,东方文明弱势了,西方文明胜利了。但我们今天发现,西方文明高度发达后出现了它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时候,东方文明要起来了,我们来解开这些死结。
费老一直就是这么超前。在20世纪90年代一次回乡后,他又提出,我们应当对中华文化的全部历史有所自觉,有清醒的认识,有自知之明,有自信,且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当我们进入开弦弓村曾经接待费老的家庭时,似乎明白了他的“文化自信”从何而来。开弦弓村村民周小芳家,书房里摆满了书,桌上是笔和砚,旁边放着男主人练过的毛笔字和水墨画。在江南的乡村,无论家境如何,书要读、字要练,儿孙教育放在家庭任务的首位,所谓“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费孝通还提出了“玉魂国魄”。他晚年反复跟后辈们强调,要多思考玉及其蕴藏的精神:玉在中国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是我们这个民族独有的审美。
作为接棒者,看到这块土石中的美玉已经被前人发现、琢磨,这一代江村人应该如何继续雕琢,在文化价值发掘中进一步做出开创性的工作,让瑰宝照亮、润泽更多人?
吴江区七都镇党委书记蔡建忠拍板:在开弦弓村新改建的文化礼堂和费孝通下船的码头之间设立“驻村教授工作室”。
我们见到蔡建忠时,他正忙着筹建“江村学院”。他希望,开弦弓村能像当年的费孝通一样帮助学术新人,或者开创一个学科,或者启迪一种思想,或者开辟一种新思路。只要是创新的,“什么都可以”。
“百湖之城”苏州吴江,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在吴江,湖、淀、荡、漾,各种水系让外来人分辨不清,更因人才流动、文化交融而模糊了城乡的边界。一代又一代人像费孝通一样脚踏在这片土地上。而今,接棒者如何背靠前人的思想力量和精神牵引,坚定地走出一条属于东方文化复兴的新路径?
新的命题摆在面前。
江南人,留客不说话。来开弦弓村的时候,雨忽地大了,蔡建忠将我们引入一个大棚式食堂,叫来一份点心——粉红色的、如玉磬形状的米糕。我们说不饿,他递过来:“一定要吃,这是费老很爱吃的,每次回来都会吃。”我们捏在手里,是温热的,翻过来一看,上面有两个字——定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