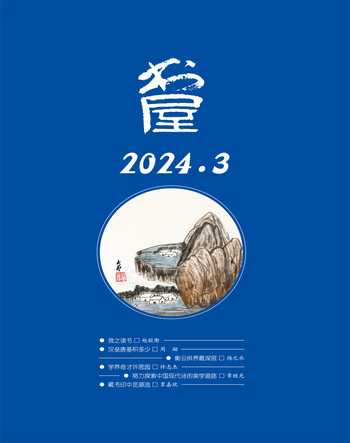衡云供养最深层
扬之水
一
1987年4月30日下午与周国平、杨丽华一同往访徐梵澄先生。
梵澄先生早年(1929年,二十岁的时候)自费留学德国,五年以后,战乱家毁,断了财源,只好归国。回到上海后,生活无着,乃卖文为生。在鲁迅、郑振铎的督促下,翻译了尼采的一些著作。抗战爆发后,又辗转于武汉、长沙、重庆、昆明,四处颠沛流离,直到1948年被国民政府派到印度教学。1949年后,在一个法国女人开办的教育中心任职,这位法国人很看重他的才华,但实际上却是将他作“高级雇工”使用的:不开工资,只包一切生活用度。他著了书,出版后,也不给分文稿费,甚至书也不给一本。在这位法国女人晚年的时候(她活到九十多岁),支撑她教育事业的四个台柱子一年之内相继去世,学院一下子就衰败了。这样,梵澄先生才争得了归国的机会(前此两番皆未获许),于1978年返回阔别三十年的家园。先生一生未婚。
曾请先生为我的《五十奥义书》和《神圣人生论》题了字,梵文、汉文各题一册:
圣则吾不能
我学不倦
而教不厌也
二
5月10日接到梵澄先生复信,其中言道:
我是唯物史观的,也略略探究印度之所谓“精神道”,勘以印度社会情况,觉得寒心,几乎纯粹是其“精神道”所害的,那将来的展望,科学地说,是灭亡。
来信说《五十奥义书》中有不解处,我相信其文字是明白的。这不是一览无余的书,遇不解处,毋妨存疑,待自己的心思更虚更静,知觉性潜滋暗长(脑中灰色质上增多了旋纹或生长了新细胞),理解力增强了,再看,又恍然明白,没有什么疑难了。古人说“静则生明”——“明”是生长着的。及至没有什么疑难之后,便可离弃这书,处在高境而下看这些道理,那时提起放下,皆无不可。这于《奥义书》如此,于《人生论》亦然。
书,无论是什么宝典,也究竟是外物。
通常介绍某种学术,必大事张扬一番,我从来不知此作。这属于“内学”,最宜默默无闻,让人自求自证。否则变怪百出,贻误不浅。
三
10月13日下午与周国平一起往访梵澄先生。
先生今日情绪极佳。首先谈到我写给他的信,认为还有一定的古文修养,但文尚有“滞障”,而文字达到极致的时候,是连气势也不当有的。我想,这“滞障”大约就是斧凿痕,是可见的修饰,而到炉火纯青时,应是一切“有意”皆化為“无意”,浑融无间,淡而致于“味”。
又打开柜子,找出十几年前发表在新加坡的几组文章《希腊古典重温》《澄庐文议》《谈书》,并告诉我说,昔年他在印度阿罗频多学院时,由于那位主持人(法国老太太)的故去而使他的生活难以为继,因而卖文为生,虽所得无多,但不失为小补。如我对这些旧作感兴趣的话,可以拿去发表,但要请人抄过之后,再拿去给他看一下。
又翻出《鲁迅研究》,让我们看发表在上面的《星花旧影》,是谈他和鲁迅的交往,并录有若干首他写给鲁迅的诗。当年墨迹的复印件也让我们看了。文字纯静而有味,诗有魏晋之风,书似见唐人写经之气韵。
先是,沏上酽酽的红茶一杯,继而又拿出月饼,一人一枚,分放三小碟,一剖四牙儿。先生和周君都吃了,我没吃。走时却将之装入塑料袋,硬要我带走,说:切开了,不好放,我一个人如何吃得完?
四
11月2日,如约往梵澄先生家取稿。今日又逢他兴致很高,聊了一个多小时,并出示他几十年来所作旧体诗,请我为之联系出版。惶急不及细读,蓦见一首《王湘绮齐河夜雪》,遂拈出,当场录下,诗云:此夜齐河雪,遥程指上京。寒冰子期笛,落月亚夫营。战伐湘军业,文章鲁史晟。抽簪思二傅,投耒怅阿衡。危国刑多滥,中期柄暗争。所归同白首,何处濯尘缨。初旆还初服,传经事偶耕。金尊浮绿蚁,弦柱语新莺。兰蕙陶春渚,桑榆系晚晴。知几无悔吝,吾道与云平。诗后补注曰:湘绮楼有《思归引》自言其事,苍凉感喟之意皆为其格调所掩,未尽写出,概可于他篇见之。兹则直抒其意,语有当时人所未敢言者,于此又见古人之弥不可及也。——“所归”二句皆用古语而稍变,《引》中亦尝说及石崇事,此又白居易咏甘露之变者也。
因与道及王湘绮撰写《湘军志》一事。先生说,他当年亦尝与鲁迅先生论及此。周问,徐答:《湘军志》用的是《史记》笔法,但太史公虽叙事亲切,每似己之身历其境,却始终保持冷静,湘绮则徒有其一,而无其二。鲁迅先生深然此言。但后来先生得知,鲁迅是赞同司马氏之冷静的。
由此又把话题转向谈史,谈黄石老人与张子房,谈鸿门宴,谈杨贵妃。先生颇有与众不同之见。遂曰:何不撰几则“读史札记”?
五
11月7日上午如约访梵澄先生。——前番交下一册手稿《天竺字原》,嘱我抄录其序,以收入“杂著”。临别问及下次晤面时间,乃答:“星期六。”已而又笑曰:“我,黄石公也。”盖因当日曾论及黄石公与留侯桥下之约。然既如此言,我岂非成了张良?不敢也。
先生将目录审定一回,以为尚嫌单薄,便又寻出一册在印度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出版的《行云使者》,嘱我誊录其序及跋,亦一并收入书中,并应我之请,言当为全书作一序。又将此编初步定名为“异学杂著”。
谈及散原诗,言至今记得一好句:“落手江山打桨前。”“初读之时,以为‘落手江山,寻常句也,未尽得其妙,而于心中徘徊久不去。约有半年时光,忽而悟得,此乃江中击水,见江山倒影而得句。细玩其意,得无妙哉!”
将日前检得朱记“国史馆长”一则示与先生,先生正之曰:“王闿运晚年非‘寒素也。仅示一例。当年湘中有一朱姓秀才,弃文从商,经营茶叶买卖,后成巨富,茶行遍布。其向湘绮求文,先是,奉呈银子三千两,王弗受。遂易之以水礼(绸缎、果品之属),乃应。可知王名重当时,囊中曾不少物也。”
继而又述一则王之轶事:“时有一和尚犯事,坐罪站笼。寺中诸和尚欲救不能,乃贿于王,以求为之说情。一日,王拜会县令,说笑一回,起身告辞。主人送客,王见笼中和尚,佯称曰:‘这和尚站得好!那日同他对弈,竟一子不相让。言讫而去。和尚由是得免。——能与王对弈者,岂非友乎,县令固不愚也。”
忆及著述之甘苦,乃云:五十年代迻译《五十奥义书》,时在南印度,白昼伏案,骄阳满室,寓居之墙又为红色,热更倍之,每抬臂,则见玻璃板上一片汗渍,直是头昏昏然也。然逢至太阳落山,暑热渐退,冲凉之后,精神稍爽,回看一日苦斗之结果,又不禁欣欣然也。
人入暮年,可有孤独感?答曰:余可为之事,固多也。手绘丹青,操刀刻石,向之所好;有早已拟定的工作计划;看书,读报,皆为日课;晚来则手持一卷断代诗别裁集,诵之,批之,殊为乐事,孤独与余,未之有也。
六
11月24日上午往梵澄先生处取《散原精舍诗集》。借书本是为请他写书评的,但今日却言不愿为之,原因是恐牵涉诸多人事,乃欲令我代笔,而不署先生之名。恐无力荷此任。
又示我一副对子:人寿丹砂井,春深绛帐纱。云此联乃廖季平所为,但先生不满于下联,因欲改写,然后书于壁,并让我也试为之对。我何尝有此急智,再三言之:不能。先生曰:不急,不急,待对出,信告可也。
辞别而归。未及进家,脑子里蓦然跳出一句:神通梵铃中。情知未称得对,也只得以此交卷了。
七
11月26日,雨化为雪,天寒甚。
为梵澄先生送去《周天集》稿,请他为之序。雪犹未止,路滑难行,骑车至团结湖,已觉双腿发颤。
先生稍肯日前之对。示我一纸当日所书梵文墨迹,云:此曰梵寐文。以此易下联之后三字,当为佳对也。
谈及八指头陀,犹记其若干好句,如“袖底白生知海色,眉端青压是天痕”。此登高之作也。又曰:陈石遗尝有诗:山鬼夜听诗,昏灯生绿影。八指头陀乃云:后句不妥,当易为“宽窗微有影”。
又示我学诗之途:先由汉魏六朝学起,而初唐,而盛、中、晚唐。追摹杜工部、玉谿生可矣。我说,学诗乃青年人事,如今已过此界,何以为之。先生曰:不然。知高适否,四十岁以后方学诗,岂非卓然大家。
又说:我向不以灵感为然,学识方为第一,所谓厚积薄发是也。即如八指头陀,大字不识一个,不过以“洞庭波涌一僧来”一句成名,后之为诗,则多为一班名士所助。
八
12月17日上午访梵澄先生。先生正在临《泰山金刚经》,因让我当场临写几字,顺势告以执笔之法、运笔之道。说目前我已到了中级阶段,欲再向上跃,则须反求于古,即所谓取法乎上,从汉魏学起,求朴,求拙,勿钝,勿利。又提起我的那首小诗,指出其中病句,并曰学诗与学书的道理是一样的,先从《古诗十九首》入手,熟读《文选》诸诗,而唐,而宋,元、明可越过,清初王渔阳诗不可不读。
又取出他的诗作,选出若干首读给我听。有《前落花诗》(五古一首)和《后落花诗》(七律十五首),写得极好,开篇两句“落花轻拍肩,独行悄已觉”,已觉得很有韵味。
九
1988年12月5日,往朝内,接到浙江社寄给梵澄先生的书,遂携往徐府。
徐先生笑哈哈地说:“我正在‘大做文章哪。”原来他正在给贺麟的诗写序言。细问之下,方知贺是他五十多年前在海德贝格的老同学。同学之二则是冯至。冯、贺二人系同月同日生,贺长冯五年。因此层关系,每岁二人寿诞之日,徐皆邀冯、贺往某处小酌,酒饭之间,忆旧而已。今年却未循此例。询其原委,答曰:一来物价昂贵,质次价高,无甚兴味;二来贺麟年事已高,听力减退之外,言语也欠伶俐,故而免仍旧例。
送我一册今年第二期的《新文学史料》,内载冯至一篇《海德贝格记事》,所记徐诗荃者,即梵澄先生也。字里行间,非仅情深意笃,亦可见至诚之钦慕。
又送我一方自镌印章:水月一色。印钮为一拄杖寿星。
闲谈之际,说起陈康,原来也是徐的德国同学。他告诉我,陈是扬州人,平日总是气色平和,雍容有节,与之相处很好。四二年徐在重庆中央图书馆时,陈还去看过他,如今却是多年没有来往了。听说他的夫人是外国人,目前家于台湾。
交还我《散原精舍文集》,忽又忆起什么,乃开卷,翻至卷七《南湖寿母图记》,为诵以下文字:“今岁十二月为太夫人六十生日,清道人乃作《南湖寿母图》志其遭,余故亦尝履是区而不能忘者,以谓今日之变极矣。政沸于上,民掊于下,崩坼扰攘,累数岁不解。耳目之所遘,心意之所触,吞声太息,求偷为一日之乐而不可必得。当是时,如仁先兄弟者,尚能娱亲于萧远寂寞之滨,优游回翔,寤寐交适,冲然与造物者俱,不复知有世变然者,不可不谓非幸也。盖天之于人,虽若悬运会以纳一世,而其沕穆大顺之气潜与通流,莫可阏遏,必曲拓余地,导善者机藏其用,以滋息人道而延太和淳德于一心,呼吸之感,福祥之應,环引无极,亦终自伸于万类,不为所挠困而获其赐。揽斯图而推之,其犹可憬然于天人相与之故也欤。”诵罢赞不绝口:“真好文字,文字好哇!”
十
1989年4月3日,往梵澄先生家送稿。他见到我非常高兴,说:“我很想你。”大概人到老年会特别感到孤独。他说他有一位女朋友,是七十年代在印度结识的,美国人,研究精神哲学。有一年夏天,这位女子跑到梵澄先生那里去谈天,并带去一个水果蛋糕,出于礼貌,梵澄先生表示很好吃,说了几句好话,她竟然十分当真起来,写信让她的母亲从美国航空寄来一个。这一年圣诞,又寄来一个,此后年年不断。后来她来北京,相见时,先生告诉她:“水果蛋糕我已经吃够了。”
他的两个老同学,一个贺麟,一个冯至,贺已垂垂老矣,讲话都不容易听得清了。冯近日心境不好,来往也不多了。因此他反复说:希望你能常来看看我。
当他点起烟斗的时候,又说道:“我现在对自己的文字已经不在乎了,送到出版社,就随它去了。”
十一
1990年10月23日,访梵澄先生。先生自湘西归来后,即入院,滞五十五日,上周方回寓所。今日看来,气色仍不错,精神也健旺。
得其两帧照片,一摄于印度,一摄于此间。
说起吴伟业与钱谦益,他说,我很同情梅村,也能理解他,只将他作一大诗人看便了,倒不必去论仕清之类。
提到下周是他的寿诞之日,则曰:向不过生日,不过是离死更近罢了,有什么值得庆贺。有多少人打听,至今秘而不宣,连最好的朋友也没有告诉。说到这里,想起什么,乃道:“你比最好的朋友还要好了?”
十二
10月29日,访梵澄先生。先生素服王湘绮,今由《王闿运手批唐诗》又道及湘绮楼的许多轶事。他说,这部手批不是王的字迹,当由其学生所抄。王的手批本,他早年是读过的,且记得很熟,今日此本中不少调侃语被节去。
十三
1991年4月13日,访梵澄先生,他正忙着阅《苏鲁支语录》的校样。谈起此著的翻译经过,因说鲁迅先生办事极是爽快,而且非常负责,译稿是鲁迅推荐给郑振铎的,郑当时手中已有一部全部译好的稿子,却放过不用,接受了徐译,而那时,他才刚刚动笔,是译好一卷交出一卷。“这是鲁迅先生的面子吧。”先生说。当时他手边拮据,于是提出预支稿费,鲁迅因此在给郑的信中婉转提及(大概是写了一句“他可是有条件呀”)。后郑还对徐说:“你原本可直接对我说啊!”
十四
1992年1月17日,说起昨天恰好去看望贺麟。“他看去气色很好,也有精神,但只是在床上躺着。”先生写了一本谈王阳明哲学的书,他认为只能请贺先生为他看一看,提意见,但显然已不能,不免慨叹。“当初与鲁迅先生一起探讨学问,后来再没有这样的人了。”“那么,可说是举世无知音了?”先生点头叹息而已。
十五
1993年5月5日,说起章士钊,先生说,他与章有世谊呢——他的伯父与章交情很深,先生的堂兄法政大学毕业后,挂牌做律师,后因连举丧事,家贫无以为计,遂投书章士钊,章即为之疏通,做了省里的推事官。先生在重庆时,他的好朋友(蒋复璁)几番拉他去拜见章。但先生想到“三一八”惨案,想到鲁迅先生的痛骂,坚持不往。
十六
6月30日,说起陈寅恪的诗,我说,总觉得一派悲慨愤懑之气,发为满纸牢骚。先生说,精神之形成,吸纳于外,以寅恪之祖、之父的生平遭际,以寅恪所生活的时代,不免悲苦、愤慨集于一身,而痛恨政治,世代虽变,但人性难变,所痛所恨之世态人情依然。……其诗作却大逊于乃父,缘其入手低——未取法于魏晋,却入手于唐,又有观京剧等作,亦觉格低,幸而其学术能立,否则,仅凭诗,未足以立也。先生说,他与寅恪原是相熟的,并特别得其称赏。后来先生听说他作了《柳如是传》,很摇头,以后也没有再来往。
十七
1994年2月23日,谈到王荆公,先生说,司马光说他贤而愎,真是一点不错。苏东坡有一个上皇帝的万言书,他也就照样来一个,一点不少,此所谓拗也。他的诗的确作得好,有一首诗,还是和别人的,写得真好。“已无船舫犹闻笛,远有楼台只见灯”,试想想,这是怎样的情景?又有“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风吹水雪崩腾”,这一个水字就有多么妙!他人只想到“海”字,想到“浪”字,而这一个“水”字,便是只有荆公想得出。
十八
7月22日,近有乡人送他一盒君山银针,木制锦盒为外椟,内又两只小木盒,标价二百八十五元。先生说,在湘卖十块钱一杯。
十九
1995年2月21日,先生说他正在读马一浮的《蠲戏斋诗》。蠲,去除;戏,佛经所谓戏语。马一浮曾与汤寿潜的女儿订婚,但她不幸早亡,马于是终身不娶。汤很看重这位“望门女婿”,知他生计并不宽裕,便时常送钱来,但马坚拒不受,即使悄悄放在桌子上或抽屉里,马发现后也立即追还。抗战后,马不得已跑来跑去,最后到重庆,办了一个复性学院。开学时,有二十来个学生,学期中,剩下一半,学期末,一个也不剩了。
先生说,马一浮的诗,写得好的,真好,追摹唐宋,是诗之正。但更有大量古怪的,大段大段生搬三玄(老、庄、易),佛经上的,也照样剥捉来,是生了“禅病”。并拿了一册,一一指点我看。
二十
1999年1月24日,晚间接到姜丽蓉电话,说是从梵澄先生的通讯录中查到电话号码,因以“徐先生病危”相告。遂赶往协和医院。先生已处于抢救状态,失去意识,只有吐气之功而无呼气之力。从云南来的侄女在一旁守候。医生说“只是时间问题”。一会儿宗教所的人来了,两人便开始讨论身后安排,遂退出。
我印象中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先生身体还好的时候,那一天我从院里出来,当门一辆黑色的卧车,先生恰才侧身落座,一眼看到我,连忙要下来,我于是赶上前请他坐好。匆忙中来不及多说什么,先生叮嘱道“你还是要常来看我呵”,算是作别。后来屡屡忆及这一幕,我想,要说永诀,这一次竟是了。
二十一
丽疋大妹:
秋气已凉,柳叶未落,蝉声犹曳,明渊静波,时杖策公园,会意时景。然亦深念大妹,久息音闻。不知近况何如矣。想《通鉴》一出,意致颇复飞扬。愚意尚有汉代、三国极佳题材,未入史评也。但汉文彩已高,读之惊魂动魄,倘再加评述,难于逾越马、班,或者有《续通鉴》之作乎?
近来贱躯无恙,暖气已来二日矣。暖气未到,曾微患喷嚏,缓缓遂已痊愈。但近来工作效率稍减。而咖啡粉告罄,附近遍处购求未得。倘大驾下次枉过,仍乞依旧往某店购之。或海南产,或云南产,皆远胜速溶之西品。尚欲得麻杆小字笔二支,则前番已面托者。——单车缓驶,绕道不远,则所搅不多,而益我已厚矣。
第十期雜志已到,知拙文尚无错字。“此又君之功也”,感谢无既。
端此奉候,并解未勤致信之面责。想释然矣。即颂编祺
澄上
十一月八日,一九九五年
二十二
丽疋大妹:
此次示下校样,颇感苍凉,不留心此学逾一甲子矣。对此竟如隔世,应当重新从头再学。手边亦无一本可参考之书,于《辞源》所载及批评之说,皆只能唯唯而已。但近年出土之宝藏法物实多,端赖专家善研究之。忆当年考古新学入华,有一学者名李济,所造似不深,而李氏又因离开大陆,亦不得志于台湾,闻大陆之发现,弥叹其欠缺“田野工作”,不及见也。赍志而没。窃叹于今振兴考古学,人才与经费俱缺,其事难能。而古物之出土,遭损毁者亦巨,可复慨哉!兹录微见数点,供大妹参考。此亦不可耽执之学,养成癖好,极难解除,如马蠲叟所讥曰“骨董市谈”,则亦无甚意义矣。必国富民康,然后可有人才蔚起,奠定斯学,发扬光辉。所冀为期不远。——顺便书数字。澄白。
二十三
丽疋大妹惠览:
岁星周转,又入新春,侧闻一年之间,研究之结果丰多,深可庆喜。芳菲腾上,辉耀声香,及此韶光,遂增述作,尤可为新年贺者也。拙稿印刷,未知安迪进行何如矣。友人就已订本观之,谓天地头尚当延长,则可分两本而长,似较大方,免簿书之气。此议可采。商务馆昨寄到鄙人之逸文一篇,将来待大妹发落。目前欲稍结集前作,亦未能匆匆作结论,故尚不能悠然闲放,而假期又颇虚度矣。有暇驾临鄙寓一叙,多事尚有待于玉塵一挥,时深盼望。冬寒稍减,调摄为劳。聊驰寸笺,敬颂福安
澄上
一九九八年一月三十日